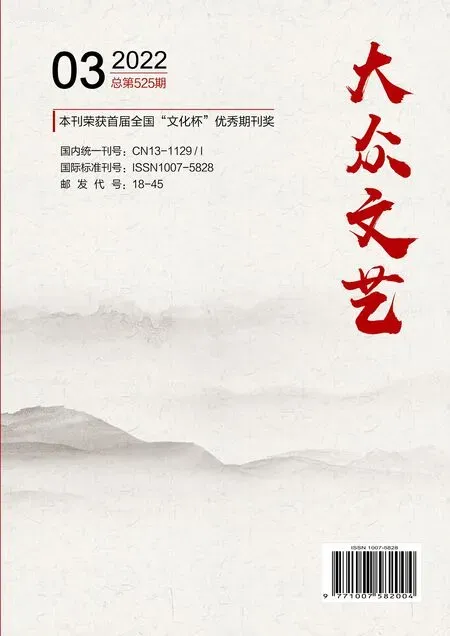从《歌德谈话录》看歌德晚年的文学思想
德国作家爱克曼(J.P.Eckermann)所辑录的《歌德谈话录》记载了歌德晚年的日常生活。在这部书中,两人谈话的内容涉及文艺、美学、政治、宗教、自然科学等多种领域。诚如中文版译者朱光潜在译后记中写道“《谈话录》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文艺方面,它记录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
而歌德的文艺思想如韦勒克所讲“很少见于条理分明的阐述文字,难以把他真正的文艺批评跟关于造型艺术以及一般艺术与自然的思辨分割开来”歌德的文艺观点分散于各类信件以及谈话的只言片语中,其文学观点也多从具体作家或作品出发进而讨论普遍性问题。因此,其文学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现象。
一、文学创作要从现实生活出发
歌德早年受到赫尔德影响,曾经阅读莎士比亚的大量著作。此后,他完全被莎翁的天才创作所折服,在1771年法兰克福莎士比亚纪念大会歌德发表演讲说“莎士比亚,我的朋友,假如你还活在我们中间,我一定只跟你在一起,假如你是奥瑞斯特斯,我是多么乐意当你的配角皮拉德斯。”之后,歌德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回到了在认识上远比过去较深化的古典主义”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也从对其天才的称颂转向对其质朴风格的赞扬。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歌德称赞他能够通过巧妙的途径将外部冲突与内在冲突、古与今有效地结合起来。他说“他更应归属于朴素类作家,因为他的价值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他是难得多愁善感的。”
因此,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像莎翁一样,以现实为根据、将内心感受与外界联系起来。所以,歌德在晚年指出当时德国文学界青年的弊端便在于不擅长到客观世界中去发现材料,不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寻创作的源泉。在歌德看来,文学创作要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具体印象,再用艺术的方式将这些现象和关照融会贯通。他认为“现实生活提供诗的机缘,提供诗的材料……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
在这里,歌德明确指出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出平凡事物的不平凡侧面是诗人的本领所在。而之后的创作,所谓用艺术方式进行加工,则基于诗人个人的才能和独创性。
(二)注重才能和独创性
歌德一生推崇才能并始终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离不开诗人独特的创造才能。他多次表示出对莎翁才能的崇拜。“我们必须承认,并不是轻而易就能找到一个人,他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洞察世界,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就能找到一个人,他能像莎士比亚那样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见解,并且让读者跟他一起在更高的程度上领悟世界。”
同样由于才能出色受到歌德推崇的还有诗人拜伦。在和爱克曼的对话中,歌德毫不吝啬对拜伦的赞美“依我看,在我所说的创造才能方面,世间还没有人比拜伦更卓越。他解开戏剧纠纷(Knoten)的方式总是出人意外,比人们所能想到的更高明”
而当我们将歌德对于诗人才能的提倡与德国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时候,不难发现歌德企图唤醒沉睡的一类人并以此来改变当时德国文学界的状况。在他看来,德国社会将青年人变得异常驯良,这样会把一切才能、独创性、野蛮劲都驱散掉,而这将是德国文学界的大敌。“使简单的题材通过高超的处理变为有意义的作品,需要才智和高超的才能,而这恰恰是现代的诗人们所欠缺的”因此,他呼吁有才能和独创性的人才出现为德国民族文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诗人要掌握描述特殊事物
众所周知,歌德和席勒开启了德国的古典时代,共同促进了德国古典文学的繁荣。但在文学创作究竟是一般还是特殊的选择上,二人始终存在分歧。席勒认为文学创作是从一般走向特殊,而歌德则提倡文学创作应该由特殊到一般。因为“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歌德晚年在编辑他和席勒的通信集时,曾写下一段极重要的感想:“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到时候才意识到。”
由此看来,由一般到特殊的寓意诗只代表诗人书写的一种特殊事物本身,不具有更广的代表性及象征性;而由特殊到一般的象征诗“则用意象来暗示某个丰富的观念,而这个丰富的观念却又超越于意象,其意蕴不是意象本身能够穷尽的”。歌德由创作中的一般与特殊进一步引出寓意诗与象征诗的区别,为后来作家进一步明晰诗的创作体裁提供了借鉴。
(四)对题材的选择与处理
说到题材,它在文学创作中起着基石的作用,无题材便无诗歌,而且题材涉及的内容很广,似乎只要诗人会利用,没有题材是不可以入诗的。但歌德指出,在创作时,对于题材的选择要有一定的尺度。
首先,一种纯粹诗性的题材比政治性题材要好。在有同等题材可选的情况下,要力求避免政治性题材。尽管歌德在魏玛公国担任要职,与政治密不可分,甚至他也极度推崇法国诗人贝朗瑞的政治诗,但歌德认为政治不是诗人的恰当题材,因为“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
其次,宗教最好作为一种题材出现但不能在文学思想中占据太多的位置。著名波兰诗人奥迪涅茨曾经在访问歌德后激动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在这儿,‘自然’这个名词已经反复提到至少有两百次,而‘上帝’这个词却也没有提到……”这种情况或许能表明歌德对基督教和文学之间微妙关系的态度。正如朱光潜所说“基督教在歌德手里成为一种材料和方便法门,正如希腊文艺借助于希腊神话一样,这种神话是家喻户晓的、一般听众容易接受的。”
关于题材的处理方面,歌德指出作家首先应该写小题材,因为小题材善于把握且作者熟悉。任何大部头的诗都是从小题材开始写的。“如果你目前写一些小题目,抓住日常生活提供给你的材料,趁热打铁,你总会写出一点好作品来,这样,你每天都能感到乐趣。”
其次,诗人在选择题材时可以省度自己的年纪。歌德曾经以自我创作举例试图对此说明:“在我够年轻的时候,还可以把我的感性气质渗透到理想性的题材里去,使它有生气。现在我老了,理想性题材对我已不合适……”换句话说,诗人身上所透露出的感性理性气质在不同年龄段是不同的。以感性理性巧妙融合为基础,诗人在选择题材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思考自己所拥有的气质。
二、结语
一部《歌德谈话录》,毫不夸张地说,也是一部歌德晚年思想史。歌德认为“谈话录”这种记载“含有任何一本书所不能包括的只可能从各本书中精选出来的最好的东西”。荣幸的是,我们读到的《歌德谈话录》确实如此。而由于歌德本人既从事文学创作又总结理论经验,所以他拥有一般文学家无法企及的理论深度也不似纯文艺理论家容易流于空洞。因此,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我们得见歌德文学思想的光芒。而我们也要感谢爱克曼,正是他清晰的提问与如实的记载,我们才有机会贴近这位“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的灵魂。
[1][6][8][9][12][14][15][16][德]爱克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49.6.56.9.240.239.5.166.
[2][美]雷纳·韦勒克;杨岂深、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5.
[3][德]歌德;安书祉译.《莎士比亚纪念日》载于《歌德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
[4][1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18.406
[5][7][德]歌德;安书祉译.《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载于《歌德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38.235
[11]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2.
[13][丹]勃兰兑斯;成时译.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