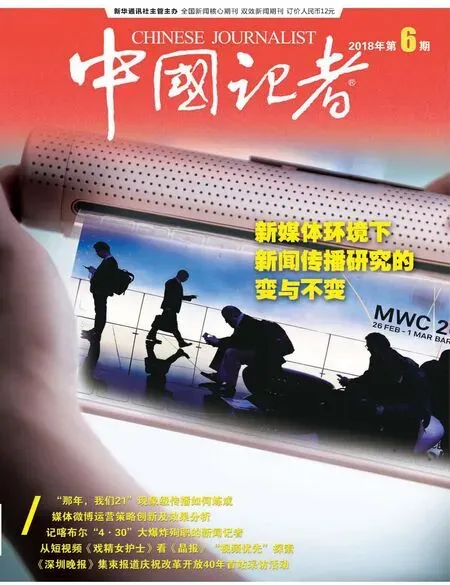让知识成为社会的知识:新时期新闻学术传播新渠道及方式创新
□ 文/吴 飞
内容提要学术文章的传播对象已经转移到新媒体平台上,虽然目前因为各种评价体系尚未能与时俱进,所以大多数学者的论文发表仍然首选传统杂志,但本文认为,未来的评价体系必然会有调整。从知识生产的目的与传播问题的角度,进一步提出,知识的价值不能仅仅止于少数人探索真理,更应该让它们成为社会的知识、公众的知识。

吴 飞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传播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2017年浙江大学发布了《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引发广泛讨论。浙江大学在这一文件中规定在相关媒体发布文章传播率达到微信10万+水平,可以被定为在一级学术期刊刊发。
我注意到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支持,有反对。不过反对的声音更高一些。
反对的声音主要关切点是:其一,学术水准应该由专业社群来判断,不应该交给普通公众,因为转发文章的人,未必有学术判断力,因为市场法则往往倾向于标题党、碎片化的观点,大多数的10万+的文章,都语不惊人死不休,往往以极化而非理性的表达来达到吸引眼球目的;其二,在惯常情况下,很多有创新的学术观点,往往是阳春白雪,知音者寡。历史上的许多大家的思想观念,都在他身后很长时间才能为大众(甚至是学术同仁)所接受。因此,以社交媒体转发10万+这种即时性效果来判断文章优劣是不科学的。
赞同者则认为一些人先将10万+庸俗化,进而把学者写10万+的行为庸俗化,这样的理解在逻辑上不成立,他们间的关系不能被简单等同。赞同的理由是“10万+代表着实在影响力,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学者而言,面向公众传播的作品获得10万+,是对能力的肯定和价值的体现。作为依靠公共财政扶持的学术事业,反哺公众是应尽的义务。学术成果不该仅以枯燥晦涩的方式呈现在核心期刊上,更应该以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公众传播。”[1]
2017年12月6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张东刚在回应“网络文化成果能不能算科研成果”时表示,任何成果,不管在哪发表,只要有正能量,对人有正面的促进、引领作用,都是好成果。评价应以内容为标准,不应以载体为标准。[2]张东刚表示,前不久,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已经把有关网络成果纳入学校的评价体系,在科学研究、成果认定、职称评定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一篇文章在纸质媒体上发布,阅读量是有限的,而一篇在网上传播的好文章,阅读量是无限的。
这一问题的论争涉及面相对复杂,既包括学术场域的权力问题(比如说,谁有资格来制定学术场的游戏规则),也包括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问题,甚至还包括知识的类型与知识的目的问题。本文主要从知识生产的目的与传播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知识生产为了谁?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麦可·布洛维的观点[3]。麦可·布洛维把社会学分为四类,即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他认为,四种社会学的提法回答了任何社会学家都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两个“元问题”,即“社会学是为了谁”和“社会学是为了什么”?[4]他的这一分析,对我们回答新闻传播知识生产为了谁的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
大体上说,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很类似,既提供专业的学术知识,为学术共同体服务,但也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知识。这与哲学或者理论物理学的知识生产不同。哲学虽然被称为智慧的知识,但更多是对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元知识”进行反思与追问,所以一些大哲学家虽然仍然有广泛的社会听众,但一般公众真正能够用哲学术语来思考并用哲学知识来指导社会实践的并不多。无论是柏拉图、还是海德格尔,他们的知识生产更多地是在学术场域内的传播。而理论物理学更是如此。相反,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不同,一方面它们提供纯粹的专业知识,这类知识同样追求一些“元问题”与“元话语”,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提供公共知识与政策服务。
知识的服务对象不同,那么与之相应的传播渠道自然也应该不一样。这个问题即使在书报时代也一样,如潘恩的《论常识》就是通过小册子向社会大众发行的,而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则主要在大学课堂讲授。
在相对传统的知识分子圈里,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传播知识似乎并不被鼓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听众对象水平参差不齐,作者不得不采用一种大众语言而非学术语言来表达其思考与观点。如果知识是为同行撰写的,是在同行内部进行专业讨论,学术杂志就成为他们发表的主要渠道。因为在这些专业性的刊物上,可以进行专业性的(充满专业术语与行话)的讨论,而且经过长期发展,也形成了一套规范而严格的编辑出版制度,如此大体上可以保障学术发表的质量。相反,如果知识是为公众写的,那么学术表达就必须转换成公众语言,如此学术味自然会降低,讨论的深入程度也同样会打折扣。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出现了,即知识生产到底为了谁?是同仁圈里的自娱自乐,还是希望知识能够为更多人接受?社会上的普通公众是不是真的没有能力来鉴赏学术著作?米尔斯指出,在杰斐逊所领导的美国早期民主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在受过教育的人民中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听众。现在学院和团体却阻止了知识分子对公众说话。米尔斯提到潘恩可以用小册子的形式直接向读者传播观点,而今天写小册子几乎无人问津[5]。与此同时,大部分杂志因为出版规范及依赖广告和发行量,而不能冒险发表“离经叛道”的观点。米尔斯因此指出:“在知识分子与其潜在的公众之间,存在着被他人拥有并操纵的技术的、经济以及社会的结构”[6]。
二、知识传播渠道创新如何可能
美国华盛顿大学语言学教授内奥米·巴伦(NaomiS.Baron)在《读屏时代:数字世界里我们的阅读意义》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写了什么、读了什么、谁在生产、谁在消费、人们希望从读写体验中收获到什么……这些问题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在数字时代,要重新讨论这些问题,也就不足为奇。她分析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习惯于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有时阅读量会很小,比如一封邮件,一个网页;有时候阅读的文本可能会很长,比如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甚至是古登堡项目中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的书籍。奥米·巴伦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除了学术阅读和长篇内容纸质版还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外,其他方面,电子阅读在受访者(美、德、日三个国家的学生)中所占比已紧追纸质版,尤其在休闲阅读上已有领先(如小说、资讯等)。显然,屏幕文字的吸引力在显著增强。个中原因,除了成本小、便利性外,还有一个是社交化。[7]
如果读者已经不看杂志,他们的阅读注意力已经更多地用在各种移动屏上,那么仍然坚持只在纸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观点显然要重新检视。从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术发表的情况看,大多数论文仍然发表在各种不同的学术刊物上。但这些刊物已经注意到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大多数刊物都办有自己的公众号。事实上,新媒体传播渠道给学术文章的再传播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徐贲教授在《数码时代的大学知识》一文中指出:“大学自身的价值观、社会和政治环境、大学与统治权力的关系都对大学的知识及其权威有直接影响。数码文化……让我们从知识的认知特征上重新认识大学及其印刷文化基础,而数码文化的特征正需要在与印刷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无论从哪一个组成部分看,传统的书刊作为主要的学术思想传播的时代与今天的数据传播时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徐贲认为,“在开放的数码世界里,没有人阅读的文字是死文字,没有价值,也不值得生产”[8]。
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David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TooBigtoKnow)一书里发现,“大学里兴起了一场讨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将它们发表在业内闻名,但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一位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从而深刻影响了本学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哪怕他并没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9]
这一问题与前文所指的浙江大学的文件规定引发的争论有相近的一面,即如何评价知识的价值问题。戴维·温伯格指出,新时代的知识是“网状”的,依靠“链接”与“元信息”,知识变得没有边界,当信息大到toobigtoknow时,我们获得了无限接近事实的客观信息。针对新时代,我们需要具备能力自行定义主观的知识边界(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汇入通过网络融入知识网络。
以笔者自己主办的公众号“重建巴别塔”为例,这一公众号的定位是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是以,公号的文章保护了学术文章发表时几乎全部元素(从内容摘要到注释,全部保留),但为提高通过屏幕看文章的舒适性,我们会在文章中添加了少量的图表、或者作者方面的信息。这些辅助性符号一方面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另一方面还增加了与文章相关的补充信息。有时,我们还加上一系列相关文章的链接,如此,原本孤立文本得以形成知识链条,如果读者有深入阅读的兴趣,便可以更方便地寻找和阅读。
三、知识应该成为社会的知识
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Wolf)在其著作中曾担心说,数码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年轻的阅读者会面对网络中铺天盖地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占用他们有限的注意广度。这样的年轻阅读者在阅读书本时,在需要非常深入地理解所阅读的内容时,会完全专注吗?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在无意中创造了只有“连续的部分注意力”的年轻人,他们集中注意力和深入到书本表层意义之下的能力的发展方式,再也不会与我们老一辈相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苏格拉底曾担心,貌似会永久存在的书本会让年轻人在开始阅读前就以为自己知道书本内容的精髓了[10]。
我认为她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必过于紧张。因为伴随着互联网而成长一代,他们对网络的适应能力和数字阅读的能力,都较他们的上一代完全不同。何况数字阅读技术也有快速发展,许多新的形态和更便于接收的数字传播模式被创造出来。连我这样的60后,也相当适应数字阅读形态了。比如我几乎每天都会在微信阅读或者各种不同的读书APP上阅读理论著作,有时在跑步运动时,还会通过语音方式来“听”书,总体感觉,这样的形态越来越丰富,效果也越来越好了。
2008年出现的学人网(academia.edu)是一个知名学者的网络社交媒体。据报道,截至2015年4月,该网站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2100万。因为这样一个学术平台,很多学者走出了个人研究的小天地,在这里分享自己的学术论文,查看自己的学术影响,跟踪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在该网站的首页标示着这样一句醒目的话:提高您论文引用率达73%。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最近的研究发现:近五年中,凡是将论文上传至academia.edu者,其引用率都提高了73%。[11]笔者创办的重建巴别塔公众号,虽然只是纯粹的新闻传播学术文章发表平台,也已经有数万订阅用户,这样的用户量远远超过了一般纸质杂志的发行量。 (作者是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10万+文章也可算论文?对浙大试验不妨多些包容http://money.163.com/17/0917/16/CUI35JP7002580S6.html
[2] 网络文化成果算不算科研成果?教育部:以内容为标准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12-06/8394106.shtml
[3] 吴飞.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2(5)
[4] [美]麦可·布洛维.公共社会学[J].社会,2007(1).[美]麦可·布洛维.奥巴马时代的公共社会学[J].Justine Zheng Ren译,21世纪国际评论,2010(3)(原文见Innovation -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22, No. 2,June 2009)
[5]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M].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0.
[6] C. Wright Mills, “the social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Irving Louis Horowitz,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96.
[7] [美]奥米·巴伦.读屏时代:数字世界里我们的阅读意义[M].庞洋、周凯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8] 徐贲:数码时代的大学知识,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919/15681552_0.shtml
[9] [美]温伯格·戴维.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10] [美]玛丽安娜·沃尔夫·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M].王惟芬、杨仕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1] 郭英剑.技术改变学术:“数字化学术”的诞生[N].中国科学报,2015-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