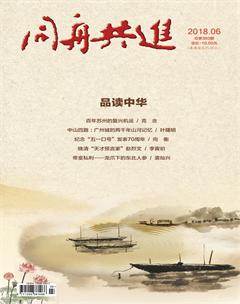晚清“天才预言家”赵烈文
李寅初
他是湘軍之父、中兴名臣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僚,提前近半个世纪预测大清崩溃全过程,被誉为“天才预言家”。
他完美地实现了归隐山林的梦想,在江南水乡,盖了一座依山傍水的园林,藏书万卷,娶了五个妻妾,其中两妾还是亲姐妹,光艳照人。
他学识渊博,诗词上佳,擅长易经、卜卦,通晓医药、金石、佛学、盐政,但后人最重视的却是他“售价300元”,洋洋200万余字的日记。
这个人,叫赵烈文。
“不出五十年”大清灭亡
咸丰十一年(1861),7月盛夏,正在东流大营紧张地主持围剿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迎来了一个年轻人。6年前,两人曾见过面。彼时,曾国藩听闻这个年轻人才华横溢,于是遣人以“两百金”礼聘之,果然“一见称赏,礼为上宾”。但可惜的是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年轻人就因母亲病重而辞归。6年后,这个年轻人的学问和见识都大有长进,两人再见,分外亲热,立即畅谈了一番时政要务。
这个年轻人就是赵烈文。此后数年,他逐渐成为曾国藩最主要的幕僚之一,为其谋划政务,提供建议,凡运筹决策以及军书章奏,多出裁定”。曾国藩十分赏识他,两人亦师亦友,亲如家人,成为无所不谈的忘年之交,甚至于一天之中密谈三四次。有时候曾国藩来找他,看到有客,或者在吃饭,曾还会在客厅里耐心等待。以曾国藩当时的身份,等待一个幕僚,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
同治六年(1867)6月20日晚上,两人进行了一次石破天惊的谈话(以下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北京)气象甚恶,明火执仗(白天抢劫)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采未开,若非抽心一烂(中央政府垮台),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赵烈文)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中央政府垮台),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殆不出五十年矣”,大清就要灭亡!这个预言的分量不言而喻。曾国藩闻罢,“蹙额良久”,然后颇为小心翼翼地询问道:“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明确地否定了这个可能,认为大清“恐遂陆沉”,不会像东晋、南宋那样有偏安江南的机会。
曾国藩不死心,又提出了“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的观点,试图推翻赵烈文的预言。但赵烈文再次明确地打破了曾的幻想:“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他认为清朝打天下时杀人太多,得天下太容易,好运已经用完,君主再有德行也靠不住了。经过赵烈文一一剖析之后,曾国藩显然被说服了,情不自禁地吐露心声: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从赵烈文的日记看,平定洪杨后,曾、赵曾屡次一起讨论大清将来的命运,从这些谈话中看,每次听闻各种负面消息时,曾国藩经常是“扼腕良久”,频叹“奈何”。他似已心知清朝灭亡不可避免,但在儒家思想的激励下,他又仿佛心生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德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同治六年的曾国藩还没有见过慈禧、同治、恭亲王等人。一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1月,他去北京住了1个多月,4次受到慈禧召见,才第一次有机会直接观察最高执政群体。这年的5月28日,在保定直隶总督官邸,两人又进行了一次长谈。曾国藩“蹙额”逐一点评了当政要人,在他心目中,这些人皆非中兴大清之辈:
两宫(慈禧、慈安)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 )、文祥、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馀更碌碌,甚可忧耳。
历史几乎分毫不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44年后的1911年,枪声响彻武昌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在一夜间走向土崩瓦解。此后的10多年,袁世凯称帝,孙中山二次革命,北洋军阀蜂拥而起,中国迎来了一个“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
这一切,早在44年前就被赵烈文预见了。那一年,他才刚刚35岁,平灭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声望正达顶峰,几乎无人知道一个眼光犀利、观察敏锐的年轻人提前看到了大清的结局,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兴名臣已心灰意冷到了“日夜望死”的地步。
赵烈文为何做出这样的预言,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走寻常路的书生
道光十二年(1832),赵烈文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世家。他的家族明清两朝先后出了9位进士,其父曾官至湖北按察使,可惜在赵烈文10岁时即病逝。赵烈文小时候很聪慧,4岁即进私塾读书,但科举之路却不太顺,3次赴考皆落榜。赵烈文于是断了仕途之心,专心在家向亲友讲求经世之学。放弃科举的举动颇为特立独行,此时他才22岁。
赵烈文预言的基础来源于深厚的学识和广博的见闻。他读书讲究经世致用,非常关心洋务、河工、盐政等大政时事。曾国藩多次称赞他“博览群书”,“洞达时务”。咸丰八年(1858)五月初五,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批待购书目,涉及艾儒略《万国全图说》、汤若望《坤舆全图说》、南怀仁《坤舆图略》、陈伦炯《海国见闻录》,等等。
他熟读史书,对历史上的成败兴亡故事烂熟于心,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名著,他至少通读了5遍。27岁时,他立志要通读二十四史,在日记里写道“少时读书多不肯竟,学正史中终卷者,两汉、三国、通鉴而已。馀虽多泛览,而掩卷茫然,深自痛恨,今发愿句读《二十四史》一过,自非有故不得间止,后废业者无颜展此卷矣”。果然,从第二天起,他从《史记》开始,一部一部地读下去。无论是在朝不保夕的逃难路上,还是在军务繁忙的幕僚生涯里,甚至病榻抱恙之时,他都坚持读史,述写心得,最后顺利实现了通读二十四史的志向。
赵烈文独具慧眼的洞察能力,还可以从咸丰十年(1860)的两则日记上看出。这年8月,他分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变迁,“斯艺萌于宋,盛于明,极于本朝(清)。成弘正嘉(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之文,似苞甲未拆,精义覃覃而外不可见;庆历天崇(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如花始舒,光采微露;国初至于乾嘉(乾隆、嘉庆),如花方盛,绚烂盈目,而精实已输;至道光以来,则断红零落而已”。赵烈文认为,历经数百年变迁,八股的“变化升降”之道已经穷尽。他进而做出大胆预测:“后来取士之方,恐将易辙矣。”历史果如他所料,1905年,经张之洞、袁世凯奏请,清廷诏准自1906年始停止科举,兴办学堂。至此,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彻底废除。
咸丰十年12月,他在读到时人赖襄所著的《日本外史》,粗略了解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后,颇感慨日本近年来的变化:迩来泰西与之通商,炮火之精,舟楫之利,以蕞尔小国,夷然处之而不惊。嗟乎!安在地广人众始为强哉。”此时,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才刚刚开始改革。大部分清廷要人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国,不足为患”,直到30年多后,黄海上的隆隆舰炮声轰碎了他们的迷梦。
这些所见所闻让赵烈文忧时伤世,对大清帝国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思索,最终得出了“不出五十年矣”就要灭亡的判断。咸丰、同治年间,大清内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乱,权力中枢屡有大变,外有英法列强越海而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硝烟未尽。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抚逐渐取得了军事实权,势力渐重,种下了此后军阀割据,“人自为政”的种子。从这点来说,曾国藩既可算是大清的中兴名臣,也可算是它的掘墓人。
这一点,赵烈文也看到了。在预言大清灭亡后的第三天,他就不无担忧地向曾国藩分析过练就湘军的弊端:今师一胜(平定太平天国)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其实,类似这样的洞察,在赵烈文的日记里俯拾皆是,比如他看到了中国根本之患不在长毛,而在西夷“其志不在小,国家之患无有甚于是者”;也看到了淮军腐败不可恃,“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
赵烈文喜做山水之游,自谓“天下行省十八历其十一”,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颇令人称奇的是,他不仅精通医药,而且长期研究易经,擅长卜卦。每遇大事难以决断之时,他都会寻求易经帮助。庚申年间,当李秀成率太平军席卷江南之时,他连续多日观察天象,卜卦后认为天下将要大乱,家乡不保,于是果断说服家人逃到上海崇明岛。在上海,他依靠医术谋生,时常出入租界,直接感受到了欧风美雨。
4年后,当赵烈文回到故乡常州,发现赵氏宗祠屋宇虽然还在,但墙壁倒塌,神牌、神橱不知所踪,曾居住过的旧宅也是茅草深深,街道不可辨识。洪杨之乱前,赵氏两房家族男丁有140多人,大乱之后仅存“十七人而已”,幸存比例刚过1/10。而整个中国则在这场历时14年的大乱中,人口锐减四成,损失大约1.6亿人。
退隐:“虽万户侯不易也”
赵烈文仕途不显,最高只在河北磁州、易州两地做了“知州”——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市长。在短暂的宦海生涯中,他算得上是尽职尽责。坐堂理讼、下乡查案、兴修水利、考试文童,事事亲力亲为,官声颇佳。有一次,一个叫“薛登科”的陌生乡民送他一双靴子,次日又宴请他,捧酒跪拜,“状如欲涕”。赵烈文心中纳闷,询问一番后才知道,薛有一件案子在衙门里拖延了很久,痛苦不已,但去年赵上任后“一日而决”,所以特地来感谢他。
赵烈文并非没有做官的才能,曾国藩认为他“天分绝顶”,“再能勉力,便为全才”。曾国荃、李鸿章等人也十分器重他,多次上奏保举,为他谋差。但赵烈文考虑到家室负累,“爱钱无以对知己,不爱钱无以了一身”,并且自身性格散诞,不愿打着老师曾国藩的旗号升官发财。他的生平志向只不过是“求一技之安,得以安隐读书而已”。于是,光绪元年(1875),在做了7年“市长”后,赵烈文找了一个借口,主动辞官退隐。辞官之际,他感到“如释重负,身心泰然”,此后终身未再出仕。
退隐生活自在逍遥,除了偶尔外出访友、寄情山水外,赵烈文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在一座花式园林里读书著述、把玩金石碑帖。这座花式园林是他在同治四年(1865)买了四亩地后开始修建的,断断续续修了22年。赵烈文称之为“能静居”“静圃”,当地人则俗称“赵园”,他为这座宅子付出了不少心血,多次从上海、苏州等地买来奇花异草,亲手种植。至光绪十二年(1886)全园完工之日,已有“楼堂榭亭为屋一百二十间,走廊内外通共八十余间”,此外还有石山两堆,大小桥六架,“果树、花卉以千记”。他还特别建了一座藏书楼,命名为“天放楼”。十几年不停地买书藏书,最终达数万卷,成为江南有名的藏书之所,时人章钰曾有“天放楼金石图书之富,标映南中”之说。
如今,历经时事动荡,战火烽烟,这座大园林仍幸运地保存完好,它和隔壁的曾园合在一起称为曾赵园,是江南地区著名园林之一。曾园也是一个大有来头的园子,其主人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
赵烈文辞官后接连娶了两个妾,加上此前的一妻二妾,一生娶了5个妻妾。最后迎娶的两个妾是亲姐妹,一个叫大俞,一个叫小俞。据赵烈文自己说,这两个妾都非常漂亮,一个“清逾秋月”,一个“丽胜春葩”。一介书生,衣食无忧,坐拥书城,妻贤妾艳,赵烈文十分满意这样的生活,在日记里感叹“吾老是乡,虽万户侯不易也。”
卖了300块的“日记”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年代里,财富烟消云散的过程更快。虽然赵烈文被后人誉为“天才预言家”,但他大概没有料到自己花了22年心血建成的江南名园会那么快地易入他手。
光绪二十年(1894)赵烈文去世后,家境迅速衰落,藏书也被陆续变卖。民国初年,赵园被另一个常州巨富盛宣怀购得,盛又将其舍予常州天宁寺为其下院,此时上距赵烈文去世还不到20年。其实,早在光绪六年(1880),赵园规模初具之时,赵烈文就希望居住者要“念创业之不易,修身慎行以答天休,庶几永之,以保守之,岂不美哉”。光绪十二年(1886),赵园建设将毕之际,他似乎也有了一些不祥的感觉,觉得“家况日落”,20年建造已“力为之疲,神为之瘁”。据说,1931年赵烈文女婿邓邦述曾策杖重游故地,于园中兀坐移时,看到物是人非,书去楼空,不觉感慨万端,凄然而归。
赵烈文一生著述颇丰,但除了留下了《能静居日记》和《落花春雨巢日记》两部日记外,其它诗词文稿都失落了。《落花春雨巢日记》记录他的早年经历,目前仍未刊行。能静居日记》则有洋洋200万字之多,起自咸丰八年(1858),止于光绪十五年(1889),首尾30余年,完整无缺。内容包罗万象,精彩纷呈,对晚清政治、经济大政,尤其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李秀成等人都有最直接真切的观察。学界公认其价值不在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的《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之下。
不过,这部日记命途多舛。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首次选刊了日记中躲避洪杨之乱的内容。上世纪40年代,学者陈乃乾根据所见的日记稿本,在其整理编辑的赵烈文年谱中大量引述了日记原文,但这些面世的内容都未得日记全貌。抗战爆发后,赵烈文的孙女困局孤岛上海,因生活所迫,以300元的价格出售日记稿本(一说是由其子赵宽以500元售出),后流入汪伪政权内政部长陈群之手。陈群将其带至南京,藏于他的私人藏书楼——泽存书库中。日军投降后,陈群自杀,家产抄没,日记稿本于1949年随大批中央图书馆的善本图书运往台湾。1964年,台湾首次将其影印出版,全貌问世,引起学术界轰动。2013年,历经3年标点整理后,大陆也推出了简体横排版,大众才得以一睹日记风采。
回望赵烈文的一生,他曾吹沫于欧风美雨的时代最前沿,交往着军国变局中最关键的人物,“负王佐之略,擅倚马之才”。但因个人才性、志趣的原因,辞官归隐,走向金石古籍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像赵烈文这样的文人很多,但大都湮没在了时间长河里。相比于他们,赵烈文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他“无意”中留下的200多万字日记中,读到他的惊人预言,看到他颇为风流倜傥的生活。我也一直好奇,他去世后,那两个妾的去向。算起来她们当时一个不到30岁,一个才20岁出头,在动荡岁月里,不知普通女子的命运又如何。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