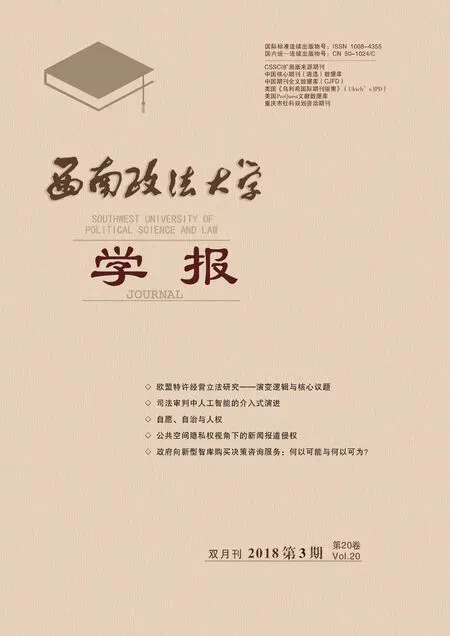司法审判中人工智能的介入式演进
(辽宁大学 法学院,沈阳 110036 )
一、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之实践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于1956年的达特矛斯会议,随着其价值与潜力逐步彰显,各国纷纷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拟抢占战略制高点*例如,日本内阁于2016年1月22日审议通过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于2016年10月12日发布的《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准备(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我国国务院于2017年7月8日印发并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目前尚缺一个明确且统一的界定,笔者较为认可的定义是:人工智能是指能够执行任务(这种任务如果由人去执行,则需要其具备智慧)的机器(包括硬件和软件)[1]。现阶段,人工智能已经逐渐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司法领域,建设智慧法院便是新时代下的因应之策。关于人工智能对于司法审判之介入,中外皆然,仅有程度不同,并无实质差别。
(一)域外实践
IBM公司于2016年研发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律师——ROSS,该平台基于IBM沃森(Watson)智能电脑,现就职于纽约 Baker & Hostetler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处理公司破产案件[2]。它可以与人类直接进行对话,对案件的关键要素进行分析,在判例法中寻找答案,并辅之法律检测、法律备忘录等功能*更多信息可访问:https://rossintelligence.com/ross/#.。在此之后,法院也转向应用人工智能系统,比如由伦敦大学学院、谢菲尔德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团队所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已成功预测数百例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案件审判结果,准确率约为8成[3]。
(二)我国的实践
2016年杭州云栖大会上,无讼推出“法小淘”,标志着我国第一款人工智能法律机器人的诞生*可参见:蒋勇的演讲视频,http://v.qq.com/iframe/player.html?vid=i0337sqvetr&tiny=0&auto=0.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1日。。“法小淘”基于司法大数据,辅之语音识别技术,通过提取客户咨询的关键字来分析案由,然后根据客户提供的诉讼法院,从30万名律师信息中找到合适的律师,并提供了律师所在的律所、同类案数量、同法院案件数量、标的额区间等信息[4]。它还可以通过广泛采集、挖掘算法、综合处理、科学分析,对法院内外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探寻新形势下审判执行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司法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司法预测预判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让数据为司法业务服务[5]。
人工智能在法院内部的应用,最成功的案例当属上海“206工程”,即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这一系统旨在将专家经验、模型算法和海量数据相结合,把统一适用的证据标准嵌入数据化程序中[6]。在刑事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206工程”逐步向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扩展,覆盖了民事、商事、海商、金融、知产、行政全领域,其中既有案件量较大的案由,如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信用卡纠纷,也有体现上海特色的案由,如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等[7]。
由上观之,国际上对于人工智能与司法活动之融合逐渐紧密,这些成果,散布于律师、法官等各个法律职业。其实,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司法审判的模式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世界官僚制的可预测属性之描述相吻合,“这是法制型统治的必然结果,在受法律制度支配的行政体制下,如果制度是公开的,那么裁决就必然可预知”[8]。诚然,司法审判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中间涉及的众多因素或许注定使这一形式沦为象牙之塔,但笔者能否认为,成文法国家创设法律的原始目标不就是这样吗?
二、人工智能与传统法官的互补性关系
审判工作之系统性限制了人工智能的适用范围,但不足以完全否定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中的适用性。问题的核心在于,人工智能与传统法官能否结合起来,构建一种互补性关系。
(一)传统法官的阙漏
法官可以作为人工智能进行裁判之结果是否合法与合理的评判者,但法官的判决结果又有谁来进行认定呢?或许,最理想的人选不外乎是当事人和上级法官之结合。对于前者,尽管他们大多不具备法学背景,但怀着“朴素的法感觉”所作出的评价,或许比我们这些所谓的具备专业素养的“外人”要可靠得多。对于后者,鉴于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故而无法武断地认定上一级法官对于案件的评价更符合正义,但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二审制度在满足当事人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权益的同时,更体现出法院内部对一审结果的审查、监督与救济。由此观之,用案件二审结果作为评价一审判决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指标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为了避免主观臆想,我们可以从全国性官方数据中寻找一些答案。需要额外说明的是,此处的一审案件上诉率是指二审收案量与一审判决量的比值,二审发改率是指二审中发回重审与依法改判的案件数与二审结案量的比值。本节数据均来自于《中国法律年鉴》(2013年-2016年)。
观察图一,不难发现,近几年我国法院审理各类一审案件的上诉率维持在22%左右。显而易见,将当事人进行上诉直接等价于其质疑法官审判的结果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影响上诉的原因有很多,如上诉机会成本的高低、对二审能否胜诉的预判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初审法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诚然,司法审判中,追求上诉率为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但该数据至少可以表明,我们的法官本身(诸如审判的公正与透明、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程度)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图二中,二审发改率在14.5%左右徘徊。司法实践中,若二审法官对案件法律适用(尤其适用新出台的法律)与一审法官存在差异,可能会出现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之情形,但发改率的高低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审法官的办案质量。原因在于就现有法院人事制度设计而言,上级法官的职位绝大多数都是由下级法院逐级遴选而产生的,故而我们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上级法官对于案件的评判比下级法官更加精准。此外,鉴于全国众多法院都将发改率作为法官考评的重要指标,上下级法院与法官之间的“沟通”必然随之变得愈发频繁。所以,笔者可以合理地推断,实际应该被“发改”的案件数量会比现有数据更高。
诚然,通过上述数据作为认定当事人对案件满意程度以及初审法官素质的论证不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这中间涉及到太多的政治因素、考评体系、个人偏好等,是我们难以知晓的,甚至数据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知晓,关于《中国法律年鉴》中的情况统计表,有些单位是“件”,有些单位是“人次”,鉴于同一个案件中可能会存在多个当事人,例如共同被告,因此将不同的计量单位统一计算后所得的数据难免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然而,种种偏差并不影响大致的趋势,也不影响笔者的论证,在此处追求绝对的精确没有实质意义,现实中也是做不到的。综上所述,将如上两组数据作为认定法官素养之依据或许是较好的一种方法,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将人工智能与传统法官相结合能够为司法审判带来难以估量的正向影响。
(二)人工智能的补正
司法审判的很多流程是可以进行拆解并分立的,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最简单与直接的方式,便是将各个步骤“智能化”。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介入可以有效提升司法审判的“质”。最直观的优势在于可以避免外界干扰,最大程度地保证司法独立。这一举措对于预防冤假错案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刑事错案来讲,证据问题是主要原因[9]。通过大数据对频发的同类案件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证据标准指引,对其进行校验与对比,并将出现瑕疵的证据进行拦截,可以有效排除非法证据,降低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如若各级法院引入此类系统,实现数据互通共享,便能统一制定法律裁判的尺度,提供定罪与量刑建议,避免司法活动太过任意*“同案不同判”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在马路上,某人向他人借用手机打电话,同时向远处行走,然后趁其不备,迅速逃逸的行为。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而法官的判决却不尽统一,有的定盗窃罪,有的定诈骗罪,有的定抢夺罪。。
“教科研+”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随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尝试研究教师发展的核心素养,他们大多都提到了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是其专业发展的核心素养之一.新时代的教师必须掌握一定的教科研能力,才能够应对新时代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最新要求,没有教师的发展核心素养,就不会有学生的发展核心素养.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介入可以有效提升司法审判的“效”。借助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缩短法官对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同类案件等信息的检索时间,从而提高审判效率。借助语音识别与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将相关信息迅速进行电子化处理,有效缓解司法系统人力资源的紧张状态。对于特定案件来讲,人工智能系统对起诉书、要素表、庭审笔录等各类前置数据进行智能判断分析后,按照文书样式要求,可以一键式生成判决书等各类裁判文书,极大节省了法官的时间与精力[10]。
此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的现实直接导致了各地法官间的素质差别极大,在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尤其如此*不同地区法官间的素质差距极大,司法考试(2018年正式更名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A、B、C证之划分也间接证明了国家对这一现实的默许与无奈。。中国初审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将这些民间的不规则的行动尽量用移植过来的那些法律概念和概念系统包装起来,使它们能在这个合法的概念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家园[11]。现阶段,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的种种进步,对于素质高的法官来说或许只是简单地提升效率,但就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来看,似乎在弥合不同地区及不同级别的法官间参差不齐的素质上更具现实意义。
(三)人工智能的补正不能完全冲淡传统法官的地位
人工智能的诸多优势已逐步彰显,尤其在算法、数据、算力这“三驾马车”的齐力推动下,其对司法审判的准确预测程度会越来越高。鉴于我国传统的文化结构以“人情”为纽带,在此社会环境下,这种排除人际关系、枉法裁判、行贿受贿的“法官”似乎具有别样的魅力。然而,据此得出完全由人工智能进行司法审判之结论,未免太快了。从逻辑学的角度讲,法律的适用是一个三段论推理的过程。在其中,一个完全的法条构成大前提,将某具体的案件事实视为一个“事例”,而将之归属法条构成要件之下的过程,则是小前提。结论则意指:对此案件事实应赋予该法条所规定的法效果[12]。尽管近年来关于司法三段论的批评甚嚣尘上,然而,逻辑合理性始终都是我们法律推理所必须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13]。由该视角出发,笔者认为,现阶段,至少在如下方面,人工智能就传统法官而言具有先天的劣势:
其一,从法律条文本身来讲,文字表达具有笼统性,法律规范也是抽象的,尤其法律原则缺少明确的假定条件,行为模式也模糊不定,人工智能对立法原意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作为规范人们行为总和的法律制度,必然要以人性作为其存在的土壤[14]。这一点在亲属法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关于离婚诉讼之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尽管同时规定了感情确已破裂的几种情形,但这种列举未免过于僵化,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与人类主体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不同,AI的本质属性是自然性和机械性[15]。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人性,对于诸如“感情确已破裂”之理解难免出现偏差。
其二,从案件事实的认定来讲,定性是判决的前提,为最大程度还原事实的真相,必然要求司法人员亲历,这既是心证形成的过程,也是实现程序正义之要求[16]。人工智能系统若全面介入司法程序,暂且不论准确性高低,至少面临合规等困境。庭审中,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追加发问,处理诸如当事人突发心脏病、以听不清法官发问等方式干扰诉讼进行等突发情况,这需要多年审判经验与生活经验的积淀,法官的灵活性是人工智能难以具备的。此外,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核方面具有明显的弱势,譬如原始证据丢失,替代性证明材料是否具有同等证明力的问题。由此观之,受现有技术的桎梏,人工智能显然难以由“幕后”走向“台前”。
其三,从裁判文书的生成来讲,某类案件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当庭质证、法律适用乃至最后的判决等构成要件具有相似的结构化特点,将相关信息录入人工智能系统便可以实现裁判文书的自动生成。但纵观现有实践,即便此种预判精确度很高,却缺乏对判决结果的逻辑论证,由于当事人难以知晓该系统内部的“心证过程”,势必会降低裁判文书的权威性与被接受程度。若判决缺乏说理性,很可能仅仅依靠话语权的强制力加以解决,沦为“单纯的暴力”[17]。就刑事案件来讲,这种方式可能具有较大优势,但鉴于民事案件考虑的因素过于庞杂,此领域的运用仍须努力。此外,由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文书可能会降低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与人民朴素的正义观相悖。
(四)批判人工智能的前提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反思
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还有很多潜在的问题。例如,对于同一案件,如若上下级法院之间都依靠于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判断,必然对现有审级制度造成严重的冲击。尽管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的探讨才刚刚起步,但也有很多类似的观点*参见:张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J].法学评论,2001(05):18-19.。对此,至少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现阶段,笔者差不多是完全赞同的。然而,在将人工智能定位于法官办案辅助工具的论证中,存在一个默认的前提,即传统法官不存在此类缺陷、存在此类缺陷的可能性较小,抑或即便这种风险转化为现实,法官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也远远弱于人工智能。若不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法官进行司法审判的劣势与人工智能相当,甚至更大,那这样的论点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更没有论证的必要了。
如果说对于人工智能进行司法审判的很多质疑都可以随着算法的改进、技术的进步而消解,甚至可以在庭审中考虑将测谎仪与之结合,但有一点批判确是致命的,即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工智能也难以具备与人类一样的情感。诚然,很多案件需要法官在情与法之间权衡,故而需要其具有一颗仁爱之心和情理之心[18]。可是,较之“铁面无私”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让具备人类感情的法官进行司法审判真的就那么完美无缺吗?我们试想这样一种情形:庭审过程中,某罪犯声泪俱下,另一罪犯一脸冷漠,这是否会影响法官的判断?当然,你可以反驳说,我们的法官都具备专业素养,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并不会受此影响。那么笔者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某一男法官怀孕三个月的妻子因被他人轮奸而羞愤致死,一尸两命,那么他在审理强奸案的时候,会不会倾向于判处更为严重的刑罚?若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至少可以证明在司法审判中具备人类感情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着实有待商榷;若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样惨烈的遭遇都不会影响他的判断,都可以漠而视之,那和冷冰冰的司法审判机器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可能的路径:构建新型审判模式——差别审判与事后监督相结合
随着人工智能的优势逐渐彰显,为其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战略之一,许多学者都在试图将人工智能纳入司法审判的体系之中。历史告诉我们,工业革命往往是生产力跃升的关键性因素,故而在信息时代下,智能化是发展司法生产力的重中之重[19]。种种实践表明,现阶段人工智能预测精准的案件大多集中于众法官意见相对一致并且清楚如何审判的情形,质言之,该案件的公正审判之过程一定能被算法化。然而,再优秀的法学家也无法穷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案件情形,故而将普遍适用的有限算法强行应用于纷繁复杂的无限案件中是有失公允的。
现今,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运用主要集中于规范化量刑*诸如德国的JURIS资料库、美国的量刑准则系统、荷兰的北极星求刑系统、日本的检索咨询软件等,但最为著名的当属澳大利亚量刑研究系统,其精密与详尽程度,堪称世界之最。。随着技术臻于完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事实简单的案件,人工智能坐上主审法官的位置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或许这个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不能因此忽略前瞻性立法的价值。当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转化为某种法定的要求,如何协调人工智能与传统法官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此情形下,将两者有机结合,加之程序设计以保障司法审判之质效的努力似乎更为稳妥与可行。这种制度架构,一方面明确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司法审判;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公,又规定了事后经由当事人申请或法官审核等方式进行种种限制,这显然在努力兼顾防范人工智能进行司法审判的风险与规制人工智能合理介入的因应之策。
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伊始,受现有技术水平与发展阶段的桎梏,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与从技术和法律的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应否介入司法审判相比,以程序规范进行救济似乎存在更为显著的优势,原因在于它并不需要对人工智能进行司法审判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清晰且明确的掌握,也不需要其审判的结果能够与法官审判的结果存在多大程度的吻合,甚至不需要法官完全了解人工智能的论证逻辑与思维方式,就人工智能发展的现阶段来讲,这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一)差别审判
司法资源是社会公众都可能需要但又不能同时享有和使用的准公共产品[20]。判决并非公正的充分条件,每次诉讼程序之运行必然消耗一定量的司法资源。鉴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对于“已有先例”的简单案件主要由人工智能进行审判,对于涉及复杂价值判断的重大疑难案件由人工智能辅助,以此种差别化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分流是未来几年内完全可以考虑的。诚然,复杂程度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主体进行审判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不仅对行为人至关重要,对于可能会承担判决结果错误风险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任何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的尝试都必须循序渐进,以事先进行的各种试验为基础,而这种制度创新绝对不能颠覆司法之正义价值。
探讨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之主要意图在于提升判决质量的同时提升效率,这个过程中要尽力避免传统法官审判模式与人工智能审判模式发生硬性冲突,从而加大两者衔接的成本。为了实现两者的无缝对接,一方面要以审慎的态度确定以传统法官为主、人工智能为辅进行审理的案件类型以及人工智能的适用范畴,避免因为算法的歧视与误判导致重大疑难案件有失公允;另一方面又要对以人工智能为主进行审判的案件之核心因素进行更加细腻与精准的处理,以节约出更多的司法资源分配到复杂案件中。在司法实践中,即便人工智能所作出的关键性判断被完全采信,但形式上的判断权依旧掌握在法官的手中[21]。因此,笔者此处的“主”与“辅”指的乃是实质上的判断权,而非是形式上的判断权。鉴于我国关于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的实践才刚刚起步,缺乏对其使用及适用范畴的规范性表述,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法中的速裁程序等,以期准确理解和把握案件的不同情形,形成可以相互衔接的差别审判制度。
(二)事后监督
AI系统组件之间的内部工作和相互作用可能比以前的技术更加不透明[1]。此处似乎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司法的透明性与算法的隐蔽性相互抵牾。对于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要求不通晓计算机技术的法官对系统的运行在事中进行控制、在事后进行解释是很困难的。在法官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要求其对人工智能的“错误决定”负责未免失之于苛。两相比较,更为现实可行的方式是:以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更新和细化程序规范为标准对人工智能审理的案件进行事后监督。
对于该制度的设想,构成性要素有很多,包含但不限于:事后监督的对象、提起监督的主体及方式、事后监督的主体、实施监督的具体形式以及其他一般性程序问题,这些都是设计事后监督程序时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上述内容不尽相同,但作为事后监督的各个环节,其本质是要求法院为人工智能所做出的判决进行合理化解释(也很可能是一种修正),由此将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损害降到最低。在司法审判领域,较之传统法官而言,人工智能还只是一个“婴幼儿”,笔者构想的此种事后监督的模式之初衷在于实现传统法官、人工智能与涉诉当事人三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质言之,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在促进法院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司法审判更加小心谨慎的同时,增加当事人对于判决结果的认可、接受与服从程度。
(三)价值定位
就人工智能发展的现阶段来讲,尚难以模拟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2]。由此观之,将其界定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似乎无可非议。然而,笔者对此处“辅助”一词的理解存在些许疑问,是从该系统发展的现阶段来讲,只能起到辅佐之作用,还是鉴于最后的决定权一定会经过法官之手,所以只能是一种辅助性工具?若是前者,此类系统还处于“婴儿期”,必然可以随着日后的优化与升级加以弥补;若是后者,假使一个法官在办理某个案件的过程中,大多依赖于人工智能所作出的判断。质言之,如果可以量化的话,人工智能对于形成的最后结果之影响程度超过50%,此时若称之为“辅助”,未免有失偏颇。随着时代的发展,毋庸置疑的是,人工智能对于司法审判的介入程度会越来越高,正是因此,这种前瞻性的探讨才更具价值。从长远来看,即便笔者对于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法官这一观点持保留意见,但究其原因,并不在于技术上不能,而在于当事人难以接受。质言之,法律调整是对现实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若完全弃法官而不顾,不是人工智能在改善司法审判,而是在支配司法审判,有失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此外,需要特殊说明的是,本节对于人工智能与法官这两种审判模式的所有讨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未曾明言的假设,即上述两种方式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诚然,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人工智能更适合于“已有先例”的简单案件,法官在涉及复杂价值判断的重大疑难案件中所做出的结论似乎更具合理性,也或许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本文的重点并非将两者完全孤立,从而论证何种情况下适用何种审判模式,而是假定两者尽管分立却可以进行良性互动。质言之,笔者并不主张某领域下一者代替另一者,而是坚持人工智能与法官相互补充,在不同案件中的主作用与辅作用相互置换,共同构成一种全新的司法审判模式。鉴于此,探究两者间的“黄金分割点”在何处设立以及随着技术与时代的发展该“点”如何变化进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才更具现实意义。
四、结语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畴内,很多关于人工智能无法完全取代法官的批判都过于片面,因为这些人大多不具备计算机领域的专业知识,仅仅以一个法律人的视角进行论证,难免有失偏颇。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审判方兴未艾,注定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此类研究中,一个更为前沿甚至吊诡的问题在于:法律能否被代码化*虽然这有些异想天开,却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域外有一个组织——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对人工智能与法律的交叉领域研究了很多年,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更多信息可访问:http://www.iaail.org/.?法律能够存在并外显的一个基础性要件在于以语言文字作为载体,若完全可以由代码进行表示,人工智能彻底取代传统法官似乎也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知识图谱是支撑智能搜索和深度问答等智能应用的基础,能够为许多相关学科领域开启新的发展机会[23]。它的诞生可以说是法律摆脱文字载体的重要一步,但无法否认的是,距离法律完全代码化必然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JS
参考文献:
[1]Scherer M U.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isks,Challenges,Competencies,and Strategies[J].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2015(29):362.
[2]环球网.IBM研发出世界第一位人工智能律师——Ross[EB/OL].(2016-05-16)[2018-03-01].http://tech.huanqiu.com/original/2016-05/8935344.html.
[3]环科.人工智能成功预测人权案[J].科学大观园,2016(24):53.
[4]武杰.AI,这次“狼”真的来了[N].法治周末,2017-11-07.
[5]孟焕良.大数据作笔,为律师和法官“画像”[N].人民法院报,2016-10-23(008).
[6]严剑漪.揭秘“206工程”:法院未来的人工智能图景[J].上海人大月刊,2017(8):40-41.
[7]严剑漪.上海智能辅助办案覆盖民商行政全领域[N].人民法院报,2017-12-03(001).
[8]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M].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27.
[9]何家弘,何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8(2):3-19.
[10]夏雯.南京鼓楼法院:人工智能助推案件繁简分流[J].中国审判,2017(24):24-25.
[11]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11.
[12]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50.
[13]孙海波.告别司法三段论?——对法律推理中形式逻辑的批判与拯救[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9(4):133-144.
[14]李伟.亲属法价值取向中的人性根基[J].法学杂志,2017,38(09):63-72.
[15]张劲松.人是机器的尺度——论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1):49-54.
[16]朱孝清.司法的亲历性[J].中外法学,2015,27(4):919-937.
[17]孙万怀.公开固然重要,说理更显公正——“公开三大平台”中刑事裁判文书公开之局限[J].现代法学,2014,36(02):42-53.
[18]潘庸鲁.人工智能介入司法领域的价值与定位[J].探索与争鸣,2017(10):101-106.
[19]刘楠.新时代司法生产力与智能司法的精准导航[N].人民法院报,2017-12-18(002).
[20]李鑫.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司法资源分配问题研究[J].学术论坛,2015,38(2):134-137.
[21]刘振宇.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建设[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8-16(005).
[22]龚怡宏.人工智能是否终将超越人类智能——基于机器学习与人脑认知基本原理的探讨[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7):12-21.
[23]刘峤,李杨,段宏,刘瑶,秦志光.知识图谱构建技术综述[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6,53(3):58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