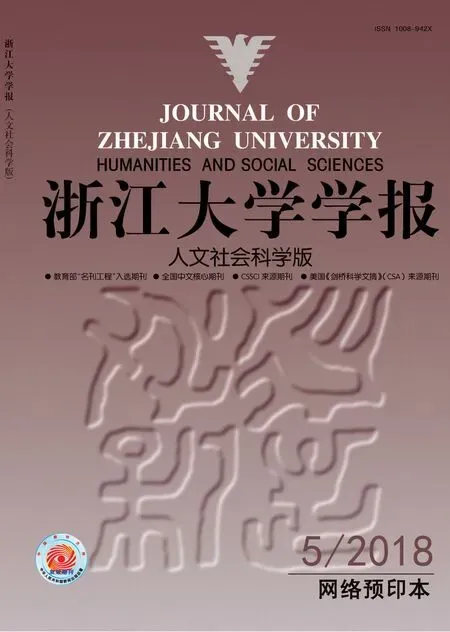主持人语: 强化问题导向,开创中国法学新局面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法学研究者提出的必然要求。一个法学研究者如果不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就不可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就不可能发出时代的声音。只有强化问题导向,才能实现法学创新,才能开创中国法学新局面。如何强化问题导向,是每一位法学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国法学研究的问题导向显然不够,不少法学研究者并未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许多研究成果对法治实践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贡献。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就是强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要解决实际问题,就要走进实践,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就要脚踏中国大地,就要接中国“地气”。法学研究者走进实践,可以开展调研,可以开展实验性研究,可以与实践机关协同创新。以实验性研究为例,法学实验就是强化中国法学研究问题导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十多年来,国内法学界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实验性研究尝试,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笔者也相继主持开展了若干实验性研究,包括“法治指数”“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以及“智慧法务”,许多学术思考便是来自这些实验。一系列经验表明,实验性研究将成为一些学者强化问题导向的方法选择。
开展实验性研究首先要求法学研究者主动走进实践。事实上,无论是“法治指数”还是“司法透明指数”,无论是“电子政府发展指数”还是“智慧法务”,设计的实验目标都来自于实践。例如,司法透明指数或阳光司法指数是笔者在2011年参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阳光司法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概念,是针对浙江省当时正在开展的“阳光司法”实践所提出来的。司法透明指数的提出得益于2006年余杭法治指数实验,余杭法治指数实验开展的背景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主持实施的“法治浙江”战略。笔者与斯坦福学者合作开展的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实验的背景是杭州市委市政府推动的“智慧城市”建设,2017年启动智慧法务实验的背景是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司法”等实践。我们启动“智慧法务行动计划”以后,又瞄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将智慧法务实验与“一带一路”课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如果不走进实践,就很可能无法发现这些实验性研究问题,法学实验的具体开展也就无从谈起。
通过实验性研究可以总结提炼学术概念,提出学术命题。一个学者最重要的能力莫过于学术判断力,学术判断力是区别学者学术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些学术判断、概念提炼以及理论构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实验性研究,如果没有法治指数、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等实验,也就不会有“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这个学术命题。“实践主义法治观”的提出虽然也受惠于实践哲学、现实主义法学、功利主义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法律社会学等理论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由于实验性研究的开展。如果不开展实验性研究,笔者不一定会提出“大数据法治”这个学术命题,也不会提出用“大数据法治”重构法治理论系统。现在,我们尝试用大数据方法来测评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并且投入巨大成本开展智慧法务实验,试图用智慧法务实验的相关成果支持“大数据法治”的理论逻辑,进而支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系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逻辑一定要建立在法治中国的实践上,主要的学术材料一定是来自中国的法治实验场域。
通过实验性研究可以构筑学术理想。每个法学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学术理想,都有构筑自己学术理想的独特方式。法学研究者提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命题,就可以长期沉醉其中,编织自己的理论系统,经营自己的学术王国。实验性研究是构筑学术理想的方式之一。在开展实验性研究之前,法学研究者的学术理想也许不够清晰,目标也许模糊;一旦通过实验性研究提出学术命题,法学研究者就可以用学术命题来构筑学术理想,就可以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命题,它能让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很快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实践哲学、中国法律传统、西方法律思想、知行合一精神、实证主义方法、大数据法治以及部门法等可以得到合理的谱系化安排。由此,法学研究者进入构筑学术理想的资源配置最优化状态,并产生学术研究的热情、激情和动力。这种热情、激情和动力正是法学研究者形成自己学术风格、实现学术理想的智慧源泉。
实验性研究要正视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不是每个法学研究者都具备开展实验性研究的条件,法学研究需要实验场域,需要团队力量,需要经费保障,有时还需要实践机构的支持。例如,“智慧法务”实验需要的条件就很苛刻。“大数据法治”的研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一个人的“小作坊”式研究无法完成这样的宏大建构。“大数据法治”研究需要融合法学、计算机、数据分析等不同学科,是典型的新兴交叉领域,传统研究方法根本无法适应,大多数法学研究者望而生畏。我们尝试引入社会资本来支持智慧法务实验,“1818智慧法务平台”就是在引入“天使投资”后推出的实验平台。在此基础上,我们引进技术团队,开发智慧法务软件,归集智慧法务大数据,建立法治联盟,提供线上线下法律服务。通过这样打破常规的实验性研究,我们观察“大数据法治”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动态变化,探寻大数据支持法治系统工程的原理和规律。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验性研究,实验性研究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学术团队的一个特色。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反对“法治教条主义”,主张“法治实践主义”。强化问题导向就是“法治实践主义”的一种表达。在强化问题导向问题上,我们不能停留于文字和口号,需要的是实际行动。一大批活跃在法治实践舞台上的法学研究者将成为开创中国法学新局面的主体力量。
在中国法学的问题导向不断强化的历程中,《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传播中国法治之声的主阵地。本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及其理论”主题栏目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丁相顺教授的《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该文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论文基于比较法视角,对司法职业化改革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深入探讨。康兰平博士和笔者合作的《司法透明指数评估的大数据方法研究》则试图通过对司法透明指数进行理论证成和实践回应,进一步探究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的思维变革和方法论格局演变,提出在之后的研究中,一方面既需要回应民众的司法诉求,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应当厘清司法公开的社会机理,提高司法实施成效和决策水平。与此同时,也需要保持谨慎而谦抑的态度,洞悉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能”与“不能”。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预印本的其它文章
- 近代浙江土地调查述论
- 大学—校友关系的关系性研究
- 发挥社群网络效应 构建新型参与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