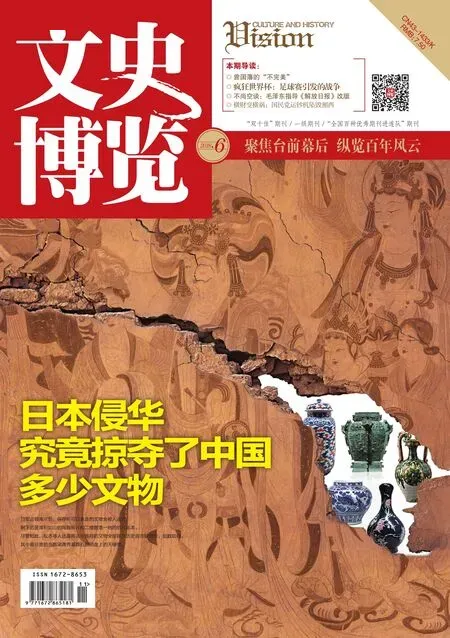“工人老大哥,吃饭用钵钵”
李鹏程

“工人老大哥,吃饭用钵钵”,这是孩提时传唱的歌谣。歌谣中包含有两个信息,一是工人们盛饭用的器皿是钵子,二是那个时代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乃至农村都建有食堂。食堂大多采用甑子蒸饭,蒸饭的器皿就是钵子,或是大锅煮饭,分饭时也用钵子来盛。
所谓钵子,其实均是些“瓦货”,初期的钵子为黝黑色,非常粗糙,后期的钵子有些改进,感观呈深黄色,再后来也有陶瓷的钵子,质地相对细腻了不少。钵子的容积有大有小,机关学校的钵子容量,一般为二两、三两,鲜有四两的,而工矿企业一般为三两、四两,甚至半斤,鲜有二两的,这与职业定额供应的粮食有关。
“四天八餐”的农村钵子饭
自1958年开始,中国农村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全国人民一个劲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阔步迈进,旋后就是以队为单位办起了公共食堂,其口号是“吃饭不花钱,努力搞生产”。生产队集体行动,社员们下工后统一就餐。队办食堂一般设在人口集中的自然村落,在堂屋里垒大灶,大灶上放置大铁锅,铁锅上叠甑子,甑子里放钵子。取下几块门板当案几,灶里烧大柴,利用铁锅蒸汽煮饭。
做饭的过程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竹甑、木甑蒸,甑子分若干层,用升子量米,依次倒入钵子里;一种是先煮大锅饭,饭熟后根据定量的多少用秤称好放入钵子里。分群体配额(16两一斤),老人每天大约8两米,妇女儿童12两米,壮劳力接近16两米。吃饭要登记,普遍实行两餐制,一般早饭定在9点左右,晚饭定在下午3点左右,社员自嘲为“四天八餐”。大家一边进行着集体劳作,一边享受着食堂的钵子饭,热热闹闹过了近一年。
可是好景不长,因上年度政府号召搞建设,青壮年社员大多被抽去炼钢铁、修水利了,没有精力及时收回粮食,翌年又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口粮显然就青黄不接了,全国开始进入“过苦日子”的时代,钵子饭随之严重缩水。区区二三两米饭何以抵挡住强体力劳动的折磨,何以填饱辘辘饥肠呢?于是有人便发明了“双蒸饭”,即初次饭熟时,米粒不够膨胀,于是在熟饭里再加些水,第二次蒸发饭粒膨胀,体积增大,成了满满一钵子。然而,吃下不久,肚子仍然空空如也,不得不上山找些野菜、挖些能吃的树根来充饥。
“三两米,用甑蒸,肚子饿了刨树根,小孩吃了黄哼哼,妇女吃了不怀孕,农民吃了鼓干劲,干部吃了拉猪粪”,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时社员对队干部的意见不少,因为他们掌握粮食,且大多将亲属安排在食堂工作,虽然没条件吃香喝辣,但“天旱三年,饿不到伙头军”,填饱肚子还是没问题。其他社员就没有这般福气了,请假外出要停饭,偷懒违命要扣饭,忍饥挨饿过日子,乃至发生饿死人的事件。
因食堂钵子饭实在无法填饱肚子,于是挖的挖野菜,刨的刨树皮。我祖父为了求生存,也发明了用盐水汤来充饥的土方法,几碗盐水汤下肚,暂时缓解了饥饿。孰不知这是一种慢性伤害,不多久就遍体浮肿,直到腿肚子肿得有小水桶那么粗,医生看了无奈,只能用银针放水,不久祖父就离世了。
中央鉴于全国的实际情况,在1961年上半年宣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农村的钵子饭就此消失。
单位钵子饭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国家对干部、工人的口粮实行定量供给。机关干部和教师、医务人员一般每月27斤,乡镇干部每月32斤,工矿企业分工种定额粮食,一般在32斤以上,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煤矿工人等,定额在45斤左右。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单位,大多建有食堂,由司务人员统一到粮站购买大米回来,再由炊事员整成钵子饭。县直机关一般实行三餐制,乡镇机关采取二餐制。虽然没有农村那么轰轰烈烈,但持续时间长,并经历过“过苦日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
在“过苦日子”的时代,机关干部的粮食指标缩减至24斤,那时,我跟随父母生活在县城,一起渡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母亲回忆说,因为大家吃不饱,干部也褪却斯文,变成了“饿老虫”。一次外婆来县城看我这个大外孙,特意带来几个鸡蛋,父亲刻意放在角落边,期为牙牙学语的我补充一点营养,不料被几个“狗鼻子”叔叔发现了,继而一抢而光,如果不是饿得不行了,他们绝对不会在孩子口里夺食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经常到父亲供职的县委、县革委食堂蹭饭吃。那时的食堂,采用锅炉蒸汽煮饭,闻着饭香,不由得垂涎欲滴。6人一桌,凭票就餐,一色的钵子饭,用的是公筷,舀汤用调羹。生活条件开始改善,桌子上有了两菜一汤,每餐都还有点肉末。桌子旁边虽然置有条凳,一些干部还是习惯站着吃,或靠近大门蹲着吃。吃完晚饭后,居住在县委大院的叔叔们,一般围着食堂对面的那蓬大竹林,看林中的莺歌燕舞。当时感觉食堂饭菜美滋滋的,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机关食堂消失殆尽了。
我上中学时,学校有寄宿生,他们自带大米和钵子,有些同学吃不饱,便悄悄通融炊事员,在钵子上放个红薯什么的,后来被更多的同学所知晓,每到上甑时分,便有鱼贯的队伍去加餐。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工厂,吃的就是典型的食堂钵子饭。几口大灶上,一排的方型木甑子,叠着有近一个人高,甑子宽有1.2米,每层0.2米,灶口烧着煤。一班小青工,自备筷子,捧着钵子饭,就着一菜一汤,吃得风卷残云,有时心血来潮,煽动伙伴敞开肚皮吃他三四钵,害得炊事员莫奈何。每到星期六打牙祭,一小钵蒸肉肉香四溢,需要多出一角五分钱。
改革开放后翌年我上大学了,每月34斤米,在司务处兑换成饭票,其实还是吃的食堂钵子饭,只是盛饭的钵子换成了自带的洋瓷碗,筷子变成了金属叉子或调羹而已,从窗口排队领饭菜。这时的菜肴渐渐丰富起来,一排排地摆在案几上,有时还眼花缭乱,不知如何取舍,有段时间为了攒些生活费,还与同学合购五分钱的汤。校园生活几年了,就是弄不明白“辣椒炒肉”和“肉炒辣椒”的真正区别。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材料的改进,工矿企业、学校食堂大多采用电力蒸饭,甑子已被铝合金饭盆所取代。铝合金饭盆分成多个小格子,蒸饭盛饭便不再使用钵子了。就餐人员不是自带的精致碗筷,就是食堂提供的瓷碗,或金属托盘,钵子饭就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取消了口粮计划供给,县直机关的食堂随之基本解散了,纵使那些没有解散的食堂,也进行了改革,一般实行个人承包,每餐配有多个菜,有荤有素,讲究营养搭配,菜肴花样翻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钵子饭了。
进入新时期,不知是对过去生活的怀念,还是对自身营养的需要,大街小巷的酒家饭铺又复现了钵子饭。虽然是钵子,但钵子质地考究,饭香菜美,与当年食堂时期的钵子饭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到了2012年,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大多数机关单位又恢复了内部食堂,采取铝合金盆子蒸饭。年长的人却发觉,虽然还是食堂,但没有当年钵子饭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