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绘画,重回技术:王华祥访谈
孟尧 王华祥

王华祥飞地艺术坊讲座现场
孟尧: 1993年《将错就错》出版的时候,你的素描教学改革已经在中央美院做了多久了?
王华祥:1988年毕业以后,我先是在一些进修班还有大专班教素描。那个时候我采取的是局部作画的方式,跟美院传统的方式不太一样。当时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素描。后来我在版画系上课,也教这种局部作画的方法,画出来的形是有一点变形的。最初院里的很多老师开始不太接受这种方法,但是紧接着我得到了靳尚谊先生的支持,我的教学方法也得以在全院推广开来。有许多后来很有名的艺术家都上过我的课,像忻东旺、翁奋、蒲凌。1993年《将错就错》出版的时候,我自己的个人实践已经从一种学习的状态变成一种明确的观念。我对现代艺术有了一个更进一步、更理性的思考。我认为可能走向独立个体、独立思考的一步,必须离开模仿、离开所谓的全因素的方法和标准。所以“将错就错”理念下的局部观察和局部推进的方法,也在那时候变得更加理直气壮。
孟尧: 1998年,你在美院外开了名为“将错就错素描营”的绘画学习班,当时的教学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华祥:其实当时办学的出发点既不是考前班,也不是向美院输送人才。相反,起因是在美院听过我的课的一些本科生、进修生,觉得课太少,没听够,希望能够跟我个人学习,于是为了满足这些学生跟我学画的需求,我成立了 “将错就错素描营”,这也是“飞地艺术坊”的前身。
我在“将错就错素描营”的教学,实际上沿用了在艺术学院曾经影响过忻东旺他们的那一套方法。这种方法不设方向、不设标准,顺应画者的天性与过程中的偶然性,作画的人会体会到一种随心所欲的将错就错的状态。所以接触过“将错就错”的人,可能对他们以后的艺术道路都会形成一种自信。
孟尧:后来正式创办“飞地”的时候,主要的学员好像是高考的学生?
王华祥:在2002年以后,也就是飞地办学两年多的时候,大学开始扩招。一开始我还挺高兴,因为学生开始多起来。但是到了2004年,飞地的学生最多的时候已经到了四五百人,那时候我对教学其实极其厌恶了,以至于2005年我觉得我必须终止这样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在招生的广告词上明确地表态:我招的是不要学院的人、学院不要的人。但实际上后来来飞地的人都是要去学院的,都是奔着考试来的。所以,那个时候飞地的发展完全走到了我办学的反面。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对教学的极度失望,离开了飞地,把学校交给过去我培养的一些学生打理,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应该说当时的飞地是越教越不像话,飞地的高考班因为只重视应试,艺术水准越来越差。2011年,我将原有的高考班并入飞地大基础部,教学上由基础部统一安排管理,不再分研修班和高考班,对飞地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孟尧:从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线来观察,我觉得你个人艺术的变化和飞地艺术坊的发展以及“反向教学系统”的不断完善,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说,飞地艺术坊也可以说是你思想和技术的试验田或者试练场。
王华祥:我是本着反学院的态度和立场去办学的,但是当我发现整个教育变成了一个市场,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学院的反抗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因此我决定重新拿起画笔,要用画笔去重新影响美术界,2006年我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整容——王华祥的美术史肖像”就是我这种想法下产生的成果。
“将错就错”近距离的创作的时期,应当说是我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平行的阶段,但是到后来我就发现我走向了“反艺术”,因为我其实对所谓的当代艺术是特别不喜欢的。我经常会在一些讲演场合或者是做发言的时候,以“我不是艺术家”甚至 “艺术是绘画的敌人”为题。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决定调整我自己的艺术实践的方向和飞地艺术坊的办学方向:要重返绘画,要重回技术。要带着观念的艺术和带着形式的艺术、带着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的成果和思想,去融入到我们对于新的绘画的探索当中去。
当时有风险投资公司来找我们,希望包装飞地上市,很多地方也来找我们希望合作办学,我都拒绝了。因为我非常清楚,他们眼盯着的是考生市场巨大的利益,那个事情对艺术没有任何益处。对于飞地的未来,我非常明确,我们不再去迎合市场的需求。我在飞地做的 “向后的实验”,让我对传统有了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因此有了一种更加彻底的尊重,因为我看到了绘画里边永恒的一面。飞地艺术坊教授的技术,我们的这种精细、极致的写实,曾经影响了好些年的艺术培训。很多人以我们为假想敌,要以我们为超越的对象,所以后来出现了那些画照片画得秋毫毕现的风气。但是我们已经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越走我们越发现传统历史当中的那些伟大的巨匠真的是永垂不朽。不仅如此,我们还复原了那些高不可攀的技术和当初的一些绘画的秘密,这个过程其实社会上并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宣传、去写书总结。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绘画在未来能获得一种在当代的地位,获得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话语的权力和高度,以及划时代的影响力,这些可能是我的目标。
孟尧:你曾经说飞地艺术坊是反学院体制的产物,那么在今天,你觉得飞地艺术坊所反对的那个学院体制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华祥:今天的学院其实有相当多的做改革的艺术家、教师。以中央美术学院来说,像版画系、雕塑系、实验艺术系,包括设计学院,应该说做得都相当的当代、前卫了。在很多层面,学院基本上可以说和当代艺术平行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在写实的、具象绘画的领域,以油画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方向衰落到无以言表的程度,非常糟糕。
当年我反对写实,反对那种再现的艺术,因为那个时候它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它阻碍了艺术发展的丰富性,这种单一性是对于人的多元的自由的诉求的压迫和控制。但是今天跟那个时候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了。今天有许多人对于写实抱有一种偏见,这个偏见是对自己生理的一种伤害、否定,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因此我对写实会充满一种相反的态度,我们提倡在多种选择当中应该有一种关于写实的自由。但是这既不是拿写实去否定其他的艺术,也不是拿写实去控制其他的追求。

飞地艺术坊旧址
虽然我在教学上提出了反传统、反模仿的口号,但是我的教学一直是在叛逆和尊重两种对立的态度中交织进行的。叛逆的一面大家都知道了,而尊重的这一面可能社会上的人并不知道。飞地的训练,也要求学员对对象有一种 “半尊重、半探秘”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客观事物当中所存在的那种极具个性化的东西,要有一种发现和呈现的能力;对画面上随机与偶然出现的东西,要有一种发现和利用的能力。
我在飞地的教学,不是要去开一个什么历史的倒车,我们只是去把那些看起来已经消失的东西让它呈现出来,并且去做一种创造性的继承。我们希望对未来的绘画的复兴,起到一种引领的和基础性的作用。什么叫“引领”呢?就是我们认为被忽略了的身体、手艺,实际上是被忽略的人的生命的价值,它需要由绘画体现出来。
孟尧:最近看了飞地艺术坊微信号上发布的你点评学员作业的系列文章《飞地课堂》,在这些你在课堂上即兴点评整理的图文里,明显能感觉到你的教学运用的是一套精确的“量化”评价系统。它确实和传统的经验教学模式有很大差异。我觉得“反向教学系统”不仅针对性地在解决具体的绘画语言和表达问题,它更是一套逻辑清晰的视觉思维方法,是一种具有基础性和广泛参考意义的启发式教学模式。在一定层面上,了解“反向教学系统”,对学艺术史、非艺术实践类专业的学生,也会有积极的帮助。
王华祥:我有相当的部分是抛弃了那种经验教学的模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试图把造型当中的那些最具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来,比如说“五步法”,素描当中的五大要素,我对它进行分门别类的训练,并且制订一定的带有形容词性质的评价标准,这个实践再加上一个感性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暂且也可以叫做经验部分,也可以叫做一种无言的部分(就是无法言传的部分),这就是尊重人的视觉、感觉、感受、体验。在这个教学探索的过程当中,理性的这个部分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像其他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样,带有一些偏差和过分的理性,它会对感觉造成伤害。但是近四年来,我一直在做平衡感性和理性的实验。从实际的教学效果看,无论是思想僵化还是脑中充满成见之人,只要经过这个教学的系统的训练,都能够使他的生命重新得到一种开垦,好像是板结的土地重新被松土,重新充满活力、充满生机。这在飞地的教学中,应该说屡试不爽。所以,“反向教学系统”不仅是一种充满人性的和鲜活生命体验的技术,它其实还是一种技术哲学。它不仅仅可以服务于一个要成为写实画家的人,它也可以帮助那些学习艺术评论、艺术批评、艺术史专业的人,获得一种理解和阅读真正的绘画的眼光,这种眼光是有穿透时间和风格的能力的。
孟尧:“素描”和“写实”可以说是飞地艺术坊的核心关键词,你也强调,你倡导的写实是一种回归自然的努力,是一种治病的良药。你这里说的“病”,仅仅指向绘画吗?
王华祥:如果说我们在早期“将错就错”那个时候,还是指向一种对于单一绘画、单一风格和标准的敌对和叛逆,到了今天,飞地的教学正在通过一种写实方式,通过一种对对象的观察,通过一种方法化的、工具化的观看和思考,让我们学会找到一种认识和接触事物的方法论。学员在飞地所得到的东西远远不只是一个绘画的技术。他们在这里其实获得了一种最全面的素质性的训练。来飞地学习过的人,他们虽然从事的工作、年龄,以后的人生目标都不相同,但这些人都能够从跟自然、跟对象的交流当中,能够体会到那种我所说的自由和快乐,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飞地的这套训练方法不会导致他们变成邪教式的对于其他艺术的敌视或者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漠视,不会出现那种极端的、偏激的、非此即彼的状况,这是很多教育所带来的副作用。但是在这种教育当中教出来的人是包容的,眼光是整体的。他可以画画,他也可以不画画,这套方法对生命是报以极大的关怀。这种能力其实来自于他们得到了一个能够比较深刻地观察事物的整体的一种方法,所以一般的事情可能困扰不了飞地的学生、来过飞地的人。这个心理的强大是难以描述的。我刚才的这些总结其实都在说明也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其实指的不只是绘画。
孟尧:就今天飞地的状况而言,你达成了哪些诉求,又还有哪些不满?
王华祥:从诉求来说,我们已经做到了素描方面绝对的高度,我说的“高度”,一方面是技术上,一方面是精神上。素描已经成为飞地人的一种观看世界的方法、一种工具,也会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表达我们内心的一种特别有效、有力量的手段。比如说通过飞地的训练,我们可以把写实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从它的起因到它的衰落都看清楚。我们永远不认同这种所谓写实衰落的“事实”,因此我们做一种相反方向的努力。我们也已经获得这样的认识,这个认识可能跟全世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才有勇气去跟美术史家和批评家对抗、对战。而且,我们不仅有态度和认识,我们还有能力去破译那些历史上伟大的绘画的密码,就像科学家对于人体的基因进行解读一样。其实我对于绘画的解读,已经到了基因阶段。我不在飞地教学,飞地仍旧能够正常运转,而且学员都画得很好,这就是证明。
素描,我认为它不仅是飞地人的一种母语,也是画家的母语。正如靳尚谊先生所说,这一套方法、这个母语其实几百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也是这么看的。并且我们已经掌握了这种母语,因此我们就可以去借鉴不同的语言,丰富我们的词汇量,从而使这个语言的表达更加能够去适应环境和时代的需求。
可能有人会问,即便我们能够做到跟过去的人一样好,甚至超过他们,那又如何呢?有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的访谈可能无法说清楚,但是我至少可以说一个结果: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目的是为了面对今天的艺术,回答今天的艺术存在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艺术存在着很多虚无主义的问题,或者说以艺术的名义干着非艺术的勾当。这样的一些东西如何来拨乱反正,绘画其实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对于传统绘画的研究,从方法到观念,从画面到人的身体,它所折射、所承载的这个人性都是最有力量的武器。
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其实是我更期待的事情。所有前面的这些准备和铺垫、这些研究,几十年来的这种探索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这些语言用于表达。那么在怎样表达这个层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是每一个飞地人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画家要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当下的艺术,比如说行为艺术家、观念艺术家,他们的表达还比较能够跟当下的生活有关系。而写实画家的表现不是很好,除了技巧之外,大部分人的思想极其贫乏、空洞,情感也极其虚假,表面上在描述、描绘生活,实际上他们跟生活没有任何关联。因而,飞地人和我提倡的新的绘画是要向观念艺术家学习,向当代艺术家学习。但是当代艺术最大的一个问题——它的价值观有问题。作为一种新的舶来的艺术,它后面的价值观多半是剽窃、挪用西方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思想又是一种舶来的假象,并非真正扎根于中国、从中国的土壤里产生的思想,价值标准也是别人的价值标准。就好像是我们的很多技术不是我们的原创,很多的东西都是抄别人的,当别人一旦改变他们的标准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非常被动,我们只能跟随他们另外的主张或者是我们再去适应他们新的规则,这一点上来说跟中国今天的发展极其不匹配。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写实画家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所有的中国艺术家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真正的当代艺术还没有出现。现在我们都是模仿秀,在做模仿的练习,但是我想就写实绘画来说,我已经完成由他人的语言向自己的母语的转换。我们会超过西方、超过全世界的人,这就是我能够证明它是母语的原因。

飞地艺术坊展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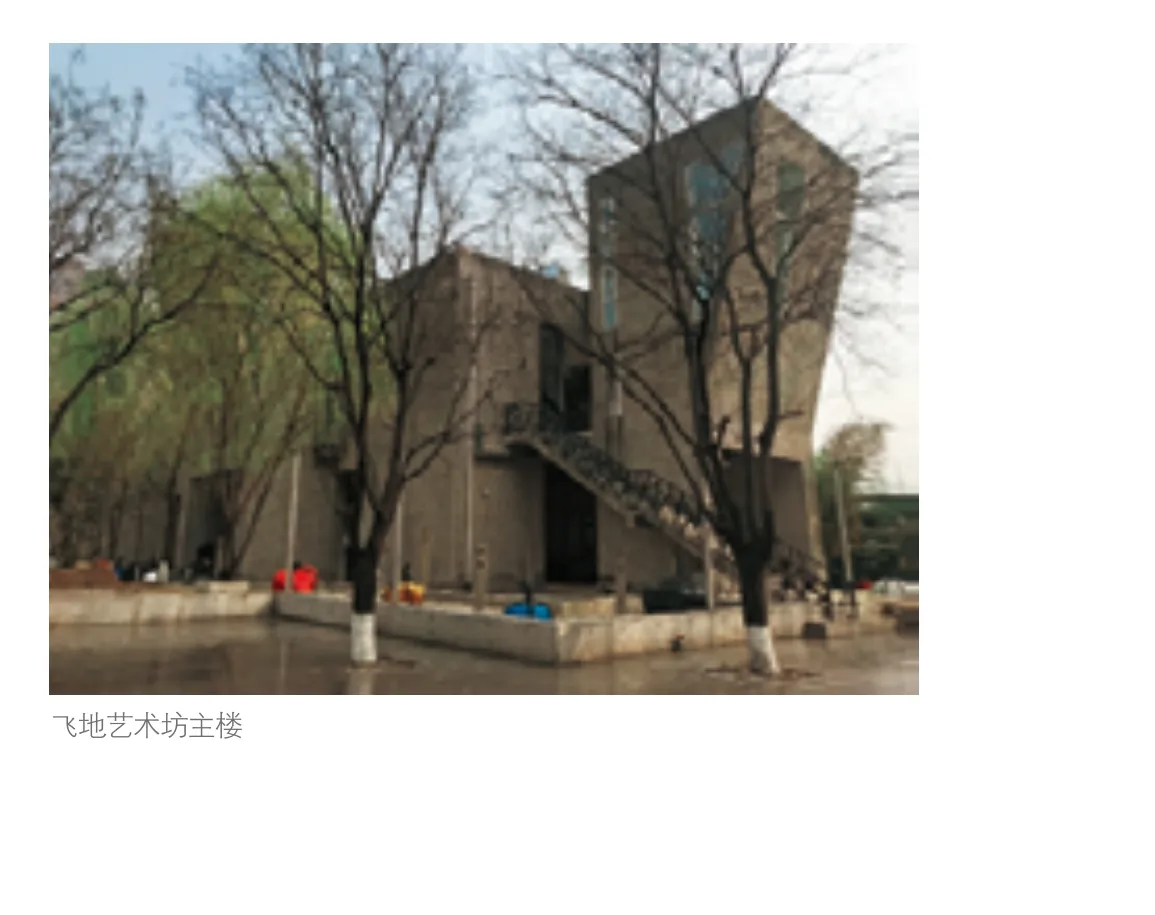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