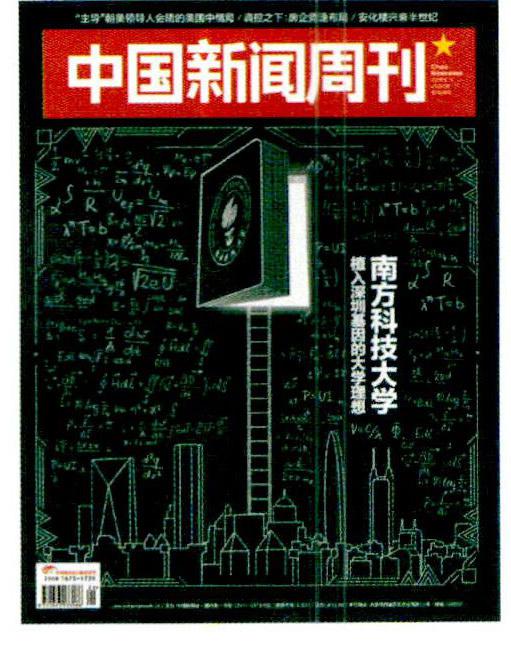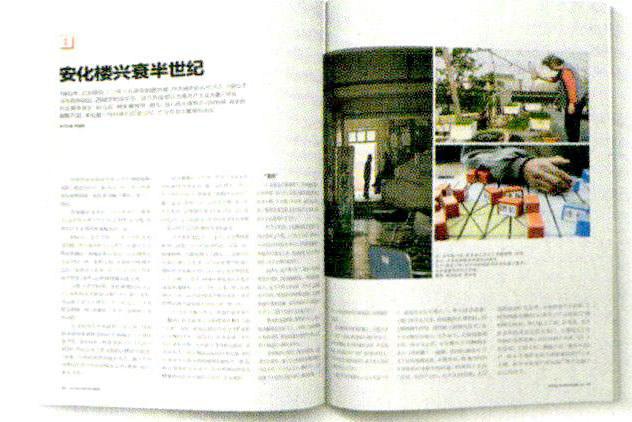尴尬的楼和失意的人
毛翊君
封面反馈
@vixin:从第一届学生开学算起,南科大“出生”7年多了,作为家有考生的家长,我一直关注着她的发展与变化。承载着“创新”的基因,完善各项体制,相信这所大学会越來越好。
读者来信
《夏伯渝:戴着假肢登顶珠峰》
26岁登山的初衷夹杂着虚荣,但是截肢以后登顶珠峰就已经成了夏老生活的强劲动力,促使他热爱生活,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去和病魔作斗争,并且成了最终的获胜者,磨练了他的心志和人格。(改变)
记者手记
很多次从广渠门内地铁D口经过,从来没察觉这栋立面像政府办公楼的建筑会是居民楼,还有着一段跟城市公社试点有关的历史背景。
这栋楼名为安化楼,类似的建筑还有两栋,分别在北京城三个区,同时建起。在东城的北官厅大楼已经拆除,连地图上也没有了痕迹。西城的福绥境大楼,经过拆迁动员,居住者寥寥无几,成了“鬼楼”。这里仍满满当当地住着人,楼里昏暗,像是上世纪的光景,跟普通破旧的筒子楼别无二致。
楼的故事被记录过好多遍,讲述了关于大跃进时期的起因,设计者的初心,以及楼内居民五六十年来的变化。我找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希望获取更多资料,但办公楼里年轻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最后,是退休办的老同志热心接待了我。
见到工程师金诚,是在他西城的家里。老人九十二岁,对于他而言,记忆犹新的是老院长曾指出这个公社大楼的设计问题——不设厨房,就成了单身宿舍。但在当时的政策之下,理性的声音被高涨的热情淹没。
当我告诉他,建筑界有人将这几栋楼跟法国的马赛公寓媲美,老人的坦诚让我有些意外。他说出了那段光辉历史下的诸多问题和局限,尤其防火和抗震,是没有标准的。
很多居民都误以为楼的建筑用料是建设人民大会堂之后所剩的,结实、充满荣光,像是残存的一点荣耀。金诚摇头否认,谈到当时所遇上的困难时期,连普通建材都十分紧缺。
住在楼里的人早已没有荣耀感,他们有钱的邻居,在房价飞涨之前,早已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买了其他房子。说起当年住进公社大楼,他们诸多悔意,由住这栋楼的悔意又延伸出人生的起落和失意。
近十年搬进去的住户都在等着拆迁换房,来来往往的出租者相互戒备。最老的居住者,曾和老邻居亲密无间,又经过特殊年代的猜疑,经过生死,最后跟楼一起老去。土地没法被高价利用,巨大的成本无处承担,拆迁遥遥无期。有人说起过改造和保护,但也没有了下文。大楼终于还是成了尴尬的存在。
详见表刊2018年6月11日出版总第8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