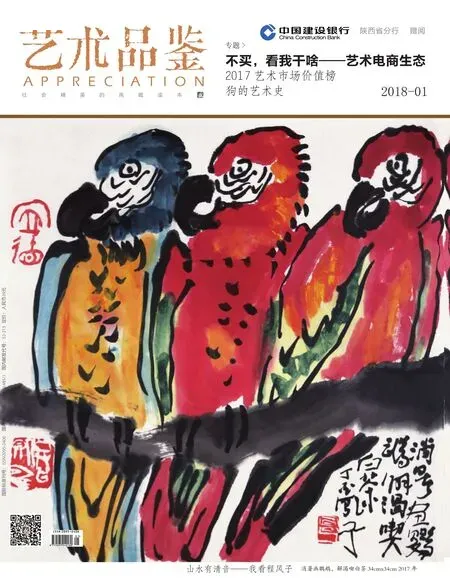当代美术与传统国画能否“融会贯通”?
随着当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人认为传统国画已渐渐“西化”。作为国粹和民族文化瑰宝,中国画将以怎么样的条件和基础传承下去并有所创新?国画是否需要为适应当代美术教育而改革?当代美术与传统国画能否“融会贯通”?这是当下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正方顾绍骅:当今美术教育下的中国画很像个“畸形儿”
据可靠的历史记载和文物史料来看,从展子虔的《游春图》到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画从诞生到中华民国之初,完全走着一条自成体系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用中国人的办法,画中国人的想法”的独立画种。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冲击,中国画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是把中国画的大门紧闭起来,贴上封条?还是融入世界艺术发展的滚滚大潮流,与西方油画和其它当代艺术比肩于世界艺术之林?后者成为了有识之士们的普遍共识。是,近百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无论我们多么虔诚和谦逊,无论我们有过何种积极的善举,中国画还是在自家园子里打转转。
前两年,网上在年轻人群中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画和油画的问卷调查,结果才20%喜欢中国画,80%喜欢油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国画必须通过申遗来得到保护,那么我们就要正视自身的局限,“老眼光”、“老一套”肯定无法实现中国画的国际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民族艺术慢慢地在裹足不前中灭绝。
这需要在观念上再解放,再认识。之前的“二高一陈”、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石鲁、李可染、吴冠中、周韶华、刘国松等老一辈艺术家虽然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差距很大,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走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认识陷阱,从根本上打破思想文化民族、地域和技术介质的局限,始终用世界的、发展的和最具人类智慧的思想对待

顾绍骅 台北故宫书画院客座教授与名誉院长 中国诗书画出版社副社长

郭怡孮 中国美术协会员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

王旭 青年艺术家
中国画艺术创作,确立中国画是人类艺术中的主体意识和主流思想,确实使中国画同油画一样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通”。
欧洲文艺复兴,催生了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同样我相信,中国艺术思想如果能够再解放,势必影响我们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要实现强国梦,缺乏“大文化观”、“大艺术观”,老是画地为牢,夜郎自大,创作出具有世界影响和国际高度的艺术品永远只能是一个梦。
任何艺术形态既有其民族性和地域性,又是人类艺术的一部分,还必须接受人类文明大环境的检验,如果经不起这个大潮的涤荡,就只能说明自身存在局限和不足。
反方王旭:中国画不需要为了当代美术而改革
改革难免会成为一种运动。事实上,中国画一直强调师心、尽性、师道。心乃性,性乃道,道乃心,都是一回事。“道”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能,通达的,自然的,求变的。中国画要说改革,必须要革心,心是理之源,心不明,道就不存。近现代中国山水画,在形式上袭“四王”、在内涵上规矩于以董其昌为首凄迷琐碎的文人画,这些事实是存在的。这些因素都是人心不明,不钻研学问而造成的。真正有学问的人,不会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也不会食古人的残羹,奴役于前人规矩,束缚于前人典籍宗派。你看黄宾虹,他是最不主张革新的人,但他的画和理论,是近现代大师名家里面最经得起推敲的:能汲取唐人王维的秀密、而不塞实;能师法北宋董巨、范宽的厚黑、而不滞闷;能资取元人千笔万笔无笔不简的理念,而不繁琐;能借鉴明代稳重沉著的章法,而不袭,这些都是道彰的表现。对黄宾虹的绘画,影响最深的就是北宋山水,浑厚华滋,这是黄宾虹先生的风格所在。
其实艺术就是在东方,为什么中国人的崇洋媚外的秉性还不改呢,祖国强大了,我们应该自信,更应该在文化上自信,毕竟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有底气返璞归真。你看,美院毕业出来的,能学到真东西的有几个,甚至没人会写毛笔字,也很少有人能懂中国画和中国画理论,他们大多是盲背课本,短见识,少见闻,缺工夫。现在社会上,美院是生产艺术家的主要加工厂,很多学生学历很高,硕士、博士什么的,连中国画史、中国画论的一般常识都不具备,连近现代的一些书画大家名家的名字都说不出几个,就可想而知他们的缺失程度了。中国传统书画界也罢,西画界也罢,睁眼不识晋唐、宋元、明清,除了齐白石画虾,他们或许只知道徐悲鸿画马。
正方顾绍骅:改良中国画不应是改变中国画
改良中国画的呼声最早由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发出,以后的岭南画派诸贤和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身体力行地在改良中国画的历史进程中做了一系列的具体工作。
尤其是1947年以来,在徐悲鸿提出“新国画”号召之后,中国画的主流进行了开天辟地的大改造、大换血,从而彻底告别了“四王”模式,引进了西方艺术经典,使中国画的面貌焕然一新。反思这一期间的得失,不免有喜有忧。
在中国画改良的实践历史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以郎世宁为先,是他第一次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但他当时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大清宫墙之内。
再后是徐悲鸿引入欧洲古典现实主义全部教学和创作经验,把素描确立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必备基础,刘海粟和林风眠的西方现代主义,“二高一陈”的经日本改造再转手国内的西方光影和透视学,再到蔡若虹、江丰、王朝闻对文人画和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清除之后,引入了苏联巡回画派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模式,以及50年代至60年代初傳抱石、赵望云、关山月、黎雄才、李可染、宋文治、亚明、张仃、罗铭等山水写生运动,再后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星星美术、云南重彩和“85思潮”之后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直接输入,等等。这一次次的推波助澜对现当代中国画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在正确、理性接受这些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画在改良的过程中也悄悄地改变了。让人们开始怀疑,我们笔下的东西还是中国画吗?
如今,当你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在浏览中国画史后,不禁会惊呼,原来那个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画种到了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之后几近断流、失传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十年”以后,失去“道统”的中国新文化主导下的中国画作品,很像混血的“畸形儿”,怎么看都不像自己亲生的老爸老妈,越看越不顺眼。
针对这一现象,我赞同刘斯奋先生的“矫枉过正”说,就像体弱的孩子吃补品过多过量,造成了次生伤害,倒不如不吃的好。在一些西方批评家的眼里,经过欧洲古典写实主义风格改造后的中国画,不过是一件尚未完成的创作草图。
基因突变是遗传学的问题,如果改良到了基因突变并体现在中国画上,那绝对是一场“文化灾难”。中国画的改良或改造,其实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我们在改良中国画时对母体的生命器官的撤换所剩无几了,那种宣纸上画速写素描、油画水彩的做法越来越让人匪夷所思。
完全抛弃儒、释、道三教圆融的“道统”文化,就等于抽离了中国画的魂;抛弃“写形”传统,完整移植西方素描、解剖、透视等造型手段,等于抽离了中国画的骨;抛弃笔墨和线条,用笔触、体面关系入画,就等于抽离了中国画的髓;抛弃“既白当黑,墨分五彩”之说,完全引入西方的结构、色彩学原理就等于抽离了中国画的血。
改良尺度的拿捏是需要保持清醒头脑的,对此,学术界的担忧似乎越来越强烈,“否定素描教学”、“质疑对景写生”等的呼声日趋高涨。我认为最要紧的倒不在于此,而是中国画家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中国画艺术本体的问题,突出什么才是中国画必须一以贯之坚持的灵魂和坚决不可改变的遗传基因。
反方郭怡孮:新美术流派更迭交错 难以长久
对于中国画教学,首先要认清中国画成因,中国画和西方绘画在成因上有很大不同。其中,传统哲学在中国画中起到了较大作用,哲学为画家树立起思想标尺,反映到绘画中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形态。在这样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表现写实性的需要,开始文学入画,更多的绘画作品中表现出了文学的叙事性,这在之前的绘画中是没有的;而后的诗词入画更是为绘画增添了灵魂,诗歌具有节律性,讲求起承转合,具有跳跃性和诗眼。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画并不是完全写实,而是把诗性提升到中国画很重要的部分,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书法入画,更多则是加入了线条的元素,与西方也有较大区别。西方的线条基本上是完成本质塑造形象的作用,每一笔都有自身的功能。但中国画除此之外,线条又是表达画家精神世界与感受心态的手段之一。另外,中国画讲究序列性,虚实浓淡中有着连贯的气韵。这是文人画很重要的标准。到后期,随着审美的变化,中国人喜欢斑驳厚重的韵味,金石开始入画,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代画家。
在近百年来,西方的造型融入到中国画中,造型观念、构成观念成为极具艺术感的一部分。中国画一旦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理念,使得现代感加强,而其观念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既写意又写实、既表现又再现、既宏观又微观,是与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切合而不极端的艺术,并不会排斥其他艺术形态。另外,中国画的写意观念有利于画家发挥自身的想象力,从不同的角度吸收有利观念,不会受制约影响。由此看来,我认为中国画的发展可以长久不衰。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当代绘画的发展规律目前还很难看出,固然丰富、刺激,适合现代人的思考方式,但究竟会如何发展下去,发展到何种程度还不可预测。而目前的程度还有待改进,缺少创造型画家,由于中国画的成因非常复杂,当代画家思考过少,简单的模仿则会显得没有生气。学院式教学是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促进了整个中国画的发展进程,并在此过程中有重点的借鉴了西方绘画教育体系。而在目前,西方绘画的教学大都是理念或观念性的艺术,在教学上也只能授予观念的创新,而不可能教技法的继承。西方美术更注重个人精神的表现,写实相对弱化,对中国画教育产生了一定冲击。当下新流派层出不穷,而实际上,新美术流派特征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传统,否定之前某些理论的新型形态,但就目前发展来看,还没有完全形成如同西方那样人们公认的传统绘画系统。由此,新美术流派更迭交错,难以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