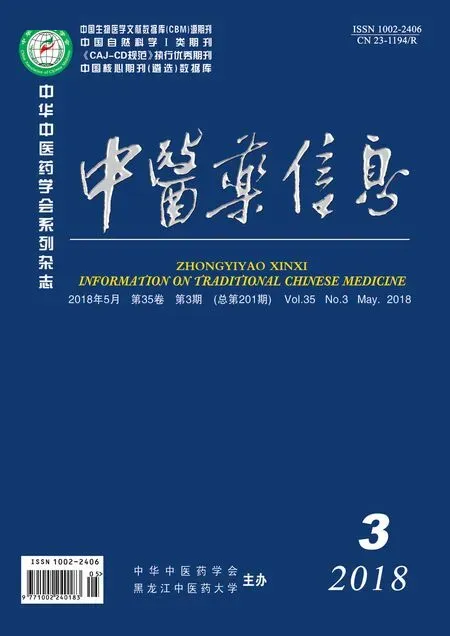针灸综合疗法治疗急性周围性面瘫
王邦博,杨晓倩
(海南省中医院,海南 海口 570203)
周围性面瘫是临床上一类常见的周围神经病变,主要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面神经非特异性炎症,导致所支配的肌肉出现异常活动[1]。疾病常以单侧起病为主,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口角歪斜、说话漏风、流涎等,症状常进行性加重,在发病后几小时至几天内达到高峰,急性期主要予以肾上腺皮质激素冲击、维生素B族营养神经等治疗[2]。而中医学认为周围性面瘫是由于脉络空虚、风寒侵袭所致,因此以中药及针灸等疏通脉络为主要治疗方法[3]。为了进一步探讨针灸综合疗法对急性周围性面瘫患者的治疗效果,我们选取了2015年1月—2016年5月在我院确诊为周围性面瘫急性期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予以常规西医治疗和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针灸综合疗法,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5年1月—2016年5月在我院就诊的周围性面瘫急性期患者共171例,其中男93例,女78例;年龄32~74(43.83±9.37)岁;病程(2.36±1.21)天。根据随机数原则,将入组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89例,观察组82例,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病程等,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1.2 纳入标准
1)符合中国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发布的《中国特发性面神经麻痹诊治指南》中的周围性面瘫的诊断标准[4];2)发病时间2~4天;3)既往无相关病史;4)了解本次研究目的,并自愿加入本次研究,入组时已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1)由于脑卒中、脑部肿瘤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相关症状;2)发病时间大于4天者;3)合并有其他组织、器官重大疾病或恶性肿瘤者;4)患者或家属不愿参与本次研究者。
1.4 方法
1.4.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治疗方法。1)醋酸地塞米松片,批号:B14202002505,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41021038,生产企业: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服药方法:初始剂量0.75~3.00 mg,2~4次/日,维持剂量0.75 mg/d。2)维生素B1片,批号:B13202001686,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44023349,生产企业: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服药方法:1片/次,3次/日。3)三维B片,批号:A14202002931,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35021332,生产企业:福州闽海药业有限公司。服药方法:1~2片/次,3次/日。4)利巴韦林片,批号:A14202304845,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10960157,生产企业: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服药方法:0.3 g/次,3~4次/日。
1.4.2 观察组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针灸综合疗法,具体内容如下:
中医辨证:急性周围性面瘫患者发病后7~10天内面神经处于水肿的炎症状态,患者往往出现面部肿胀且大多伴随耳朵前后疼痛症状,其病机为经气输布不利,经脉阻塞,故在治疗时需要疏通经脉气血,又因病变部位在头面部,为阳明经与少阳经分布部位,故应疏通阳明经与少阳经的经脉,以实现恢复气血输布的作用。
针刺方法:针灸选穴宜多循经脉走形远端穴位,少局部取穴,依据此选穴原则选取以下穴位进行针灸治疗:1)足三里:位置在小腿外侧,犊鼻下3寸,犊鼻与解溪连线上,刺法:直刺1~2寸;2)太冲:位置在足背侧,第一、二跖骨结合部之前凹陷处,刺法:直刺0.5~0.8寸;3)外关:位置在前臂背后区,腕背侧远端横纹上2寸,尺骨与桡骨间隙中点,刺法:直刺0.5~1寸;4)合谷:位置在第1、2掌骨间,当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刺法:直刺0.5~0.8寸;5)下关:位置在颧骨下缘中央与下颌切迹之间的凹陷中,刺法:平刺0.5~1寸;6)四白:位置在瞳孔直下,当眶下孔凹陷处,刺法:直刺或斜刺0.3~0.5寸;7)风池:位置在枕骨下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刺法:朝向鼻尖直刺0.8~1.2寸;8)百会:位置在后发际正中上7寸,当两耳尖直上,头顶正中,刺法:平刺0.5~0.8寸。风池穴采用点刺法,其余穴位进针时手法要轻柔,使用泻法,泻其经脉瘀阻,留针20~30 min,每日1次,10日为1个疗程,疗程之间间隔3日让患者休息。
艾灸方法:使用温和灸法。选穴:阳白(前额部,当瞳孔直上,眉上1寸)、牵正(耳垂前0.5~1寸)、地仓(口角外侧,上直瞳孔)、太阳、翳风(耳垂后乳突与下颌骨之间凹陷处)、风池、足三里。将艾绒制作为花生大小的圆锥状艾柱,艾柱下放置2~3 mm厚姜片,根据患者承受情况每穴灸13~15柱,1~2次/日。艾灸过程中注意及时更换艾柱并清除燃烧灰烬,避免灰烬落入患者眼睛与口鼻中造成患者不适,如患者自觉温度过高则加厚姜片厚度,避免艾柱烫伤患者。
1.5 观察指标
采用Sunnybrook面神经评定系统量表[5]和面部残障指数调查问卷(Facial Disability Index,FDI)[6]对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进行评分和分级,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相关评分和分级。同时,采用House-Brackmann面神经功能评级分级标准(H-B分级)[7]对患者完成3个疗程后(即治疗36天后)的疗效进行评价。
1.6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面部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H-B分级I级;显效:面部症状和体征大部分消失,H-B分级II级;好转:面部症状和体征部分消失或有所改善,H-B分级III级;无效:面部症状和体征没有明显改善,或甚至进一步加重,H-B分级IV级或以上。
总有效率(%)=(痊愈+显效)/总例数×100%
1.7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的形式表示,组间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比较,组内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的形式表示,组间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分析。P≤0.05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unnybrook分级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Sunnybrook面神经评定系统量表得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得分均提高(t=38.506,21.034;P<0.001),且治疗后观察组优于对照组(t=16.033;P<0.001),详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unnybrook面神经评定系统量表得分比较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FDI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FDI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FDI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FDI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FDI评分比较
2.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90.24%高于对照组68.54%,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4。

表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周围性面瘫(Facial palsy),又称为Bell面瘫或面神经炎,是指面神经管内面神经的非特异性炎症引起的周围性面肌瘫痪。该病的病因主要是由于受寒、病毒感染(如带状疱疹、单纯疱疹等病毒)或者自主神经功能不稳等,导致局部神经营养血管痉挛,进而致使面神经缺血水肿等,造成面神经压迫[8]。周围性面瘫一般为急性起病,症状逐渐加重,在数小时或1~3天内症状达到顶峰,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为一侧面部表情肌瘫痪,口角歪斜、流涎、讲话漏风等,同时可能伴有味觉丧失、听觉过敏、乳突部疼痛等[9]。临床上,对于急性期周围性面瘫的治疗原则以减轻面神经炎症水肿、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与防治并发症为主,故常规以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维生素B族为主要治疗手段。该病的患者在接受常规治疗后,有70%左右患者可以完全痊愈,但仍有部分患者恢复不佳[10]。
中医学认为,周围性面瘫是由于劳作过度,机体正气不足,风寒或风热等邪气入侵而致使经气阻滞、气血不和、瘀滞经脉,导致面部经络失于濡养,肌肉纵缓不收而发病,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对于急性期周围性面瘫的治疗主要以针灸和中药治疗为主。针灸能够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调和气血、活血化瘀,进而治疗周围性面瘫[11-12]。有报道指出,与常规西医治疗相比,针灸治疗能够明显提高周围性面瘫患者的治愈率[13]。除了针灸,有时还选用艾灸等手段,对周围性面瘫患者进行治疗。艾灸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激发人体的防御功能,扶正祛邪,改善面神经周围的血液循环、减轻炎症。黄春华等的研究指出艾灸也能有效提高周围性面瘫的康复率[14]。
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面瘫量化指标(包括FDI评分和Sunnybrook分级)都明显降低;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与近期的一些报道相一致。这说明在西医常规的治疗上,采用针灸联合艾灸的综合治疗能够加快急性期周围性面瘫患者的恢复,提高治愈率。
近年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医注重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在缓解症状以及消除实际病因上起到重要作用。而中医理论更注重以人为整体的治疗方式,同时采用辨证分型,将患者自身的不同体质考虑到诊疗中[15]。可见,中西医结合能够给予患者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提高患者康复速度与效果,这一观点在周围性面瘫的治疗中已经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予以急性期周围性面瘫患者针灸综合治疗,能够有效加快患者的康复,提高疾病的治愈率,应该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1] 邵旭,于炎冰,张黎.面-副神经吻合术治疗周围性面瘫[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14,30(4):348-351.
[2] 赵杨,冯国栋,高志强.贝尔面瘫诊断及非手术治疗进展[J].中华耳科学杂志,2014,12(3):346-350.
[3] 孙玲.浅谈周围性面瘫标本兼顾的治疗体会[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2):450-452.
[4]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肌肉病学组,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肌电图与临床神经电生理学组.中国特发性面神经麻痹诊治指南[J].中华神经科杂志,2016,49(2):84-86.
[5] 张晓杰,姜曌,夏峰,等.中文版Sunnybrook面神经评分系统的验证[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6,42(2):85-90.
[6] 高雅贤,刘学霞,刘利平,等.针灸综合疗法治疗周围性面瘫的时效性研究[J].现代养生,2015(10):214-215.
[7] 孙岩,徐耑,郝亚南,等.简易面神经功能评价量表在特发性神经麻痹评估中的信度和效度[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5,21(2):224-227.
[8] 聂智樱,毛弈韬,彭安全,等.面神经减压治疗周围性面瘫的临床分析[J].中华耳科学杂志,2014,12(3):415-418.
[9] 吴海燕,姜鸿,冯国栋,等.经乳突面神经减压术治疗贝尔氏面瘫[J].中华耳科学杂志,2014,12(3):380-385.
[10] 陈茂华,朱迪海.尼莫地平对面肌痉挛患者微血管减压术后周围性面瘫及听力的影响[J].中国药房,2016,27(5):681-683.
[11] 何勇,潘浩,徐涵斌,等.宋南昌教授治疗周围性面瘫经验[J].中国针灸,2015,35(6):597-599.
[12] 刘志丹,梁薇,杨艳.周围性面瘫临床研究文献中医证、治特点数据分析[J].中医药信息,2014,31(2):33-36.
[13] 贾先红,任玉乐.穴位透刺配合电针用于治疗周围性面瘫及预后测评的研究[J].实用医学杂志,2014,30(10):1655-1657.
[14] 黄春华.护理干预配合艾灸对周围性面瘫康复的研究[J].吉林医学,2014,35(23):5261-5262.
[15] 李建欣.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性面瘫的临床观察[J].中医临床研究,2015,7(31):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