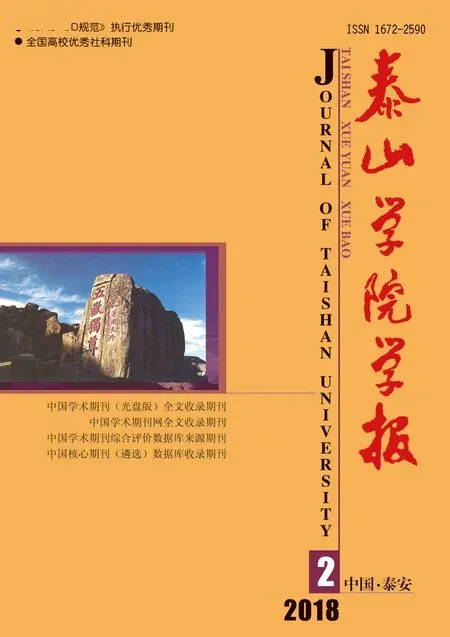国内外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综述
石芳芳,崔海洋
(东北财经大学 萨利国际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据世界旅游理事会(World Travel &Tourism Council)的数据显示,2016年旅游业总收入对全球GDP的贡献达7.61万亿美元,占总量的10.2%;同时,提供了2.92亿个工作岗位,占全球总量的9.6%(WTTC,2017)。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也给旅游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Kashima等,2015)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目的地居民是旅游地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直接影响着旅游地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Stylidis等,2014)。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旅游及相关领域的主要核心学术期刊(包括《旅游学刊》、《旅游管理》、《旅游科学》、《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等)在1980-2017年发表的关于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文献,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理论构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梳理、影响感知/态度的因素和研究方法总结。
一、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理论构建
(一)愤怒指数理论
1975年,Doxey(1975)创建了愤怒指数理论,该理论表示随着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旅游者对居民生活影响的增强,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会经历一系列变化:从最初的欢迎,转变为冷漠,再到愤怒(对犯罪、物价上升等消极影响表示愤怒),最后到敌视 (公开地或隐蔽地对游客进行冒犯)。主客之间的关系由融洽阶段、冷漠阶段转至恼怒阶段、对抗阶段(王莉、陆林,2005)。此理论为后续的居民感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区分了居民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态度的变化,但却把目的地居民看作同质性的整体,忽略了个体态度差异(Nunkoo、Ramkissoon,2012)。
(二)社会交换理论
Homans于1958年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此理论认为,人类存在的社会关系是基于交换行为而产生的,实现利益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是交换的最大目的。依据该理论,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当人们意识到成本大于收益时,人们就很可能终止或放弃此次社会交换。Ap(1992)指出社会交换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当居民意识到他们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他们所承担的损失时,便会对旅游业在该地的发展抱支持的态度,反之,则持反对态度。这一理论逐渐成为解释居民态度的主要理论。李有根、赵西萍、邹慧萍(1997)、王咏、陆林(2014)等学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中国旅游业进行了研究。
(三)社会表征理论
另一个广泛应用于解释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理论是Moscovici(1976)提出的社会表征理论,社会表征是人们对周围的事物、事件和目标作出反应的一系列看法与观点,它是针对某一社会现象或目标事物的常识性知识体系,包括价值观、信仰、态度等。Pearce(1996)将其应用于旅游学,认为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源于社区共享的知识体系,即社会表征,社会表征通过影响居民感知,进而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国内一些学者,如应天煜(2004),张朝枝、游旺(2009)等探索了这一理论在旅游中的应用。
(四)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Buttler(1980)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也被应用于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此理论认为旅游地演变一般经历探索、参与、成长、巩固、停滞、衰亡或复苏6个阶段的周期。居民的旅游感知与旅游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有关。在前四个阶段,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机会和收益感知较为强烈,而在目的地的停滞和消亡阶段,随着一系列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出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逐渐转为消极、不支持。Ryan(1998)和Akis(1996)等学者的研究结果验证了此理论。
(五)社会阈值理论
社会阀值理论(Lawson,1998)认为,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承载力存在一个阀值,当旅游发展给当地带来的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跨越此阈值时,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将由积极转向消极,对旅游业的态度也将由支持转为反对。Allen(1990)等人的研究支持了社会阈值理论。
(六)旅游经济依存度理论
Smith、Krannich(1998)根据地区经济对旅游的依存度,将旅游地分为饱和依存型、意识依存型、饥渴依存型。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受当地经济对旅游业依存度的影响。饥渴依存型社区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正面感知最为强烈,而旅游经济依存度较高的意识依存型和饱和依存型社区的居民则对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的感知更为强烈。
以上理论中,愤怒指数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社会阈值理论和旅游经济依存度理论区分了居民在目的地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差异,但忽略了目的地社区居民因其自身的因素或对旅游业介入程度的不同,其感知和态度在旅游发展的同一阶段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相对而言,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则能够为目的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个体差异提供更好的解释。
二、居民感知与态度内容
(一)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负向感知与态度
随着旅游业发展的不断深入,其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凸显。总的来讲,居民对旅游发展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积极影响持肯定态度,尤其是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如就业机会的增多(Boley等,2014),居民收入的增加等(卢松等,2009;史春云等,2007;衣传华、黄常州,2013;Almeida等,2015; Fredline、 Faukner,2000; Lankford、Howard,1994; Lawson等,1998; Mason、 Cheyne,2000; Ritchie、 Inkari,2006; Vargas-Sanchez等, 2011)。Gon等(2016)在意大利两个滨海城市的研究发现,当地居民普遍认为发展休闲游艇旅游既改善了目的地,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旅游者,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催化剂。Liu、Var(1986)在关于夏威夷居民态度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经济效益表示强烈支持,但还未意识到旅游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环境影响。Almeida等人(2015)发现居民在考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时,经常会把旅游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放在经济影响之后。卢松等人(2009)对遗产地西递居民旅游感知的历时性研究表明,随着旅游的不断发展,居民对旅游的经济效益始终保持高度的关注。
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也研究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感知(Besculides等,2002; Brougham、Butler,1981; Brunt、Courtney,1999; Fredline、Faulkner,2000; Usher、Kerstetter,2014)。旅游地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增加了当地休闲娱乐场所(Besculides等,2002; Fredline、Faulkner,2000; Mccool、Martin,1994);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陈方英,2008; Lankford、Howard,1994; Williams、Lawson,2001);提高了旅游地居民文化素质(卢松等,2009;衣传华、黄常州,2013);完善了城镇社区结构(Brunt、Courtney,1999)与环境质量(Rezaei,2017);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衣传华、黄常州,2013; Fredline、Faulkner,2000; Usher、Kerstetter,2014);促进了当地文化活动的复苏与开展(Mccool、Martin,1994);提升了民族文化自豪感(Rezaei,2017)。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Fredline、Faulkner,2000; Milman、Pizam,1988);增强了国际知名度(陈方英,2008;孟华、范方堃,2010)等。
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居民逐渐开始觉察到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等负面问题。主要包括交通的堵塞(Eshliki、Kaboudi,2012; Liu、Var,1986;Perez、Nadal,2005; Williams、Lawson,2001);社会治安下降,如偷盗、赌博、酗酒等不良行为的增加(王雪,2013;Gaunette等,2015;Richie、Inkari,2006);自然环境的污染与噪音的增加(衣传华、黄常州,2013; Williams、Lawson,2001);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竞争(Perez、Nadal,2005; Teye、Sirakaya,2002);传统文化、宗教遭到侵蚀或商品化(Milman、Pizam ,1988; Richie、Inkari,2006);居民好客程度下降(王雪,2013);物价水平升高(孟华、范方堃,2010; Kim等,2015)。衣传华、黄常州(2013)发现主题景区的旅游开展造成了常州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急速上涨,附近房价的暴涨,以及旅游收益分配不均(王雪 2013)等。Johnson(1994)等人对一个处于经济转型的滑雪目的地居民进行了历时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发展初期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期望值和支持度很高,但5年后当地居民的支持率急速下降,由94%跌至28%。
(二)基于态度差异的居民分类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学者便开始对旅游地居民进行分类研究,Davis等人(1988)按照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将美国弗罗里达州居民分为五种类型:热爱者(Lovers 20%)、憎恨者(Haters 16 %)、谨慎的支持者(Cautious Romantics 21%)、中立者(In-betweeners 18 %)和理性爱好者(love 'em for a reason 26%)。与此类似,Madrigal(1995)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热爱者(Lovers 13%)、憎恨者(Haters 31%)和现实主义者(Realists56%)。Ryan、 Montgomery(1994)将居民分为:热爱者(Enthusiast 22.2%)、中立者(Middle of the Road 54.3%)与愤怒者(Somewhat Irritated 24.2%)。Gon等人(2016)把居民分为:支持者(supporters 51%)、谨慎者(cautious 29%)和怀疑论者(sceptics 20%)。
Pérez、Nadal(2005)以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居民为调查对象,将其分为:发展支持者(Development Supporters 11%)、慎重发展者(Prudent Developers 26%)、矛盾和谨慎者(Ambivalent and Cautious 24%)、保护主义者(Protectionists 20%)、替代发展者(Alternative Developers 18%)。Brida、Osti(2010)的研究将居民分为:环境支持者(Environmental Supporters 40%)、发展支持者(Development Supports 27%)、保护主义者(Protectionist 14%)、矛盾者(Ambivalent 18%)。Sinclair-Maragh等人(2015)以居民对不同因素的关注度为依据,将居民分为:“关注公共服务和环境的群体”、“关注社区的群体”、“关注社区公共服务的群体”和“漠不关心的群体”。
部分国内学者的分类研究与国外研究结果类似,比如,Chen、Tian(2015)对奥运会举办地北京和青岛的居民根据其对奥运的影响态度进行了分类,包括热爱者(Enthusiasts)、现实主义者(Realists)、容忍者(Tolerators)和憎恨者(Haters)。苏勤(2004)、陆林(1996)、史春云(2007)、张兴华(2010)、衣传华(2013)对古镇或古城的居民分类大致相同,都可分为积极的支持者、矛盾的支持者、理性的支持者、冷漠的支持者、愤怒的支持者。另有一部分国内研究发现居民中对旅游发展的支持者或中立者居多,而反对者较少。如宣国富等人(2002)对海口与三亚居民的分类研究结果显示,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差异并不明显,仍以热爱者、现实主义者、矛盾的支持者为主。章锦河(2003)对西递被调查居民的分类研究结果与宣国富等人的分类结果相似。
以上分类研究对不同类别的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描述,但是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类别的居民会持有某种特定的态度(Sharpley,2014)。
(三)居民对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影响的感知与态度
以往的关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研究大多将旅游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没有区别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然而,同一旅游目的地可能有影响各异的多种旅游产品,目的地居民对不同类型的旅游态度可能有很大差异。因此,近几年来很多学者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将旅游产品具体化,这样调查出来的居民感知与态度更加有指向性,更为明确。Chiappa 、 Abbate(2016)对西西里岛一个停靠港社区居民对邮轮旅游发展态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总体上居民对当地邮轮旅游的发展持积极态度。Gon等人(2016)分析了沿海地区居民对休闲游艇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感知与态度。Wang、Luo(2017)调查了地震后北川县居民对黑色旅游发展的看法。Rezaei(2017)关注了亚兹德居民对本地历史遗迹修复后旅游影响的感知。Xu等人(2015)从个人利益和社区影响两方面考察居民对葡萄酒旅游的看法。Oshimi、 Harada 、Fukuhara(2016)研究了居民对国际体育赛事影响的感知。Chen、Tian(2015)对比分析了奥运会举办地北京和青岛的居民对奥运会的影响感知。曹莎(2017)以2015年世界休闲体育大会为例,调查了目的地居民对大型节事的态度。周学军与李勇汉(2017)则针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扶贫旅游研究了当地居民对其影响的感知与态度。
三、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
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可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类(Murphy,1985)。外在因素指旅游地特征,如旅游者类型与数量、旅游业的季节性、旅游地旅游发展所处的阶段或旅游地经济发展水平;内在因素包括居住地离旅游区的距离、居住时间的长短、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程度、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知情状况、参与旅游决策的程度、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社区归属感、人口学特征等。
(一)外在因素
一些研究发现目的地旅游发展状况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感知(黄玉理,2006;黄玉理等,2008;史春云等,2007;Amuquandoh,2010)。Liu、Var(1986)在关于夏威夷居民态度的研究中发现,越是在经济衰退的地区,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越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往往会忽视旅游所消耗的社会和环境成本。Gursoy等人(2004)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当地经济衰退,当地居民可能会更重视旅游业的积极影响并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黄玉理等(2008)指出,在旅游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居民旅游感知倾向于积极,但当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规模,居民的态度便由积极逐渐转为消极。与此类似,史春云等(2007)认为随着旅游地逐渐走向成熟阶段,盲目的、狂热的支持者相对减少,出现更多的理性的支持者,他们对旅游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比较关注,认识也更加的冷静与客观。黄玉理等(2008)将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目的地平遥与丽江就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处于起步阶段的平遥古城的居民对积极影响的感知比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丽江古城的居民更为强烈,而对旅游的消极影响的感知较弱。除此之外,旅游者的类型(Almeida等,2015;Butler,1974)以及游客的数量(Doxey,1974)也影响居民的感知。
(二)内在因素
1.居住时间
许多研究表明在当地居住时间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不同(Ryan、 Montgomery,1994;Weaver、 Lawton,2001;Lankford、 Howard,1994)。比如,Mccool、 Martin(1994)的研究表明居民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越长,对旅游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感知越强。与此类似,Davis(198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群体分类中,“憎恨者”群体中40%是在当地居住时间较长的居民,而“热爱者”中这类居民仅占16%。与此相反,张兴华(2010)的研究发现在本地居住和工作时间较短的年轻人对旅游发展持更消极的态度,大多数为“愤怒的支持者”,而“理性的支持者”大多是在本地居住时间较长的中年人。然而,Liu、 Var(1986)有关夏威夷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显示,居住时间长短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2.经济依赖程度
居民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程度也是影响其感知和态度的主要因素(Milman、Pizam,1988;Murphy,1985;Pizam,1985;Ryan、Montgomery,1994;Zamani-Farahani、Musa,2008;Davis、Allen,1988;Brougham、Butler,1981;Brida、Osti,2010;张兴华,2010;史春云,2007;黄玉理,2008;),对旅游业有高度依赖性的居民对旅游的发展通常持更积极的态度,早期Pizam(1978)的研究便证实了这一点。章锦河(2003)有关西递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也表明,从事旅游业的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高于没有从事旅游业的居民。陆林(1996)在分析职业类型对居民感知影响中显示农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程度相对消极,工人、商贸服务业、职工、管理人员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相对积极,个体经营者对其感知更为强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类似的结论。
3.文化与空间距离
许多研究显示,距离也是影响居民感知的另一重要因素(Jurowski、 Gursoy,2004;Pérez,2005;Raymond、 Brown,2007)。Keogh(1990)发现,在景区发展的初期,那些居住地离景区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益处有更为积极的感知,他们能够优先享用为发展旅游而改善的基础公共设施,所以持有更为乐观的态度(李卫华,2006)。Belisle、 Hoy(1980)的研究也表明,随着居民距核心区距离的增加,他们对旅游业发展表现出越来越消极的态度(Ritchie、 Inkari,2006;Korca,1998;孟华、范方堃,2010)。然而Pizam(1978)的研究表明,居住地离景区近的居民对于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持更消极的态度(Gursoy,2004)。原因可能是随着游客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地居民对于消遣娱乐设施的使用程度,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交通的拥堵,犯罪率的上升,垃圾噪音的增多,生活成本的提高;而居住地远离景区的居民则希望当地旅游能够进一步发展,并分享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效益。
4.决策参与度与社区归属感
Cooke(1982)的研究发现居民参与旅游决策或对旅游业发展的控制程度会明显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Horn、Simmons,2002;Jackson、 Inbakaran,2006;Lankford,1994;Weaver、Lawton,2001),居民对旅游发展决策参与的越多,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会更加积极。š的调查显示知情和参与程度较高的居民对旅游业的正面感知比其他人更强。同时,一些研究者发现社区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产生作用(Sheldon、Abenoja,2001;Mccool、Martin,1994;Ap,1992)。Gursoy、Rutherford(2004)的研究表明,社区归属感强的居民往往比归属感弱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有着更积极的感知与评价。
5.人口学因素
人口学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与职业等。一些研究表明性别对旅游感知存在一定影响(李卫华,2006;章锦河,2003)。Mason、Cheyne(2000)的研究表明女性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影响较男性更为敏感——对于建立酒吧或咖啡馆给当地带来的消极影响,如酒驾的增多、交通拥堵、产生更多的噪音等,女性比男性的反对程度更高;而对于积极影响,如提供了一个可以外出吃饭和消遣的地方、创造了工作岗位、提升了景区形象等,女性所持有的支持态度也要比男性更强烈。Harrill、Potts(2003)的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关注经济影响,更倾向于支持当地旅游业的大力发展(Jackson、 Inbakaran,2006)。
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旅游感知存在一定差异(Almeida等,2015;Haralambopoulos、Pizam,1996;Pérez、Nadal,2005)。研究发现收入水平高的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更为强烈,而收入水平低的居民更关注旅游带来的消极影响。
年龄也是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感知的因素(Tomljenovic、Faulkner,2000;Teye等,2002;Ritchie、Brent,1988;Kim、Petrick,2005;Almeida等,2015;Allen等,1988;张兴华,2010;史春云等,2007;李卫华,2006)。Tomljenovic、Faulkner(2000)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研究显示,年长比年轻的居民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态度更积极。史春云(2007)对九寨沟的研究也表明,老年人对旅游的消极影响感知较弱。
教育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也有所差别(黄玉理等,2008;李卫华,2006;史春云等,2007;张兴华,2010;章锦河,2003;Allen等,1988;Almeida等,2015;Andriotis、Vaughan,2003;Davis等,1988;Korca,1998;Teye等,2002)。对旅游发展持赞成态度的居民一般都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同时也能够对旅游发展有较为全面的认识。Andriotis、Vaughan(2003)研究发现“社会环境关心者”(Socially、 Environmentally Concerned)大多为学历较高的人群。章锦河(2003)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越高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越强。陆林(1996)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不同的居民在旅游对经济、环境影响的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于旅游的文化影响感知存在显著差别,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持更加肯定的态度。
宗教也是影响居民感知的重要因素。Zamani-Farahani、 Musa(2012)分析了宗教信仰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宗教信仰程度越高,对旅游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越积极;宗教习俗的践行在居民对于文化活动和生活质量上的感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上述因素外,个人对旅游业的理解、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影响着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李卫华等,2006;Ap、 Crompton,1992;Brougham、Butle,1981;Husbands,1989;Joppe,1996;Lawson等,1998;Ryan、Montgomery,1994;Williams、Lawson,2001)
四、研究方法
目前,绝大多数有关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文献主要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Oshimi等,2016;Gon、Osti,2016;Gaunette等,2015;Deery等,2012;衣传华,2013;孟华、范方堃,2010;陈方英,2008;曹莎,2017),定量分析通常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因此各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分析数据的方法和变量的选取上。国外常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Carneiro等,2017)、聚类分析(Gaunette等,2015;Gon、Osti,2016;Rasoolimanesh等,2015)、面板数据(Oshimi等,2016)等。Sharpley(2014)表示日趋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实际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同时也可能是学者对无力构建理论的一种掩饰或弥补。Deery(2012)等人指出虽然这些定量研究会增进我们对旅游发展的影响以及居民对其态度的认识和了解,但这些调查结果仍只是描述性的,不能解释为什么居民会有这样的感知和态度。
此外,目前有关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大多数研究都为截面研究,而历时研究却相对较少,而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因此,截面研究的结论有一定局限性。
为此一些学者开展了历时研究,如Lee、Back(2003)比较了居民对韩国博彩旅游业不同时期影响的感知。Perdue(1999)等人选取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博彩旅游社区,就当地居民对博彩旅游影响的感知进行了对比分析。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Carmichael,2000;Kwan,2004),这些研究表明,居民初期大都能感知到博彩旅游的积极影响,但随着博彩旅游业的发展,居民对其消极影响的感知也越来越强烈。
还有一些学者在大型节事活动举办前、中、后分别调查了当地居民对该节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态度(辜应康,2015;Chen、Tian,2015;Kim、Petrick,2005;Lee、Taylor,2005)。辜应康(2015)等人以上海世博会为研究对象,分别在上海世博会举办前后对居民进行影响感知的追踪调查。研究发现,居民对世博会举办前积极影响的总体感知高于对消极影响的感知,但在世博会举办后居民对消极影响的感知更加强烈。卢松等人(2009)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为研究对象,于2002年11月和2006年12月分别对西递居民有关旅游影响的感知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进,居民从个体层面对旅游业的依赖日益加强,同时,更加重视和认识到旅游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1980-2017年之间国内外关于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研究,发现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目的地选取过于集中与单一。国外大部分的研究局限于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也包含部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目的地,而其他地区,如加勒比海、非洲和中东等地区,并未得到关注。同时,研究焦点多为居民对休闲类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Nunkoo、Ramkissoon,2012),而对其他类型旅游的影响关注较少。国内有关居民感知的案例研究地主要集中于皖、浙的古镇和古村落,如周庄、西递、乌镇等,而对其他类型旅游地的居民研究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未来的研究不仅能够拓宽地理范围,同时也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如宗教旅游、医疗旅游、商务旅游、教育旅游等展开研究,以便更加全面、细致地理解不同地区的居民对不同类型旅游的感知与态度。
第二,目前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在数据收集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定量分析虽然能够方便地展示感知与态度的内容,却不能深入解释其背后的成因。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中,截面研究占主导,而随着旅游发展的推进,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也会随之改变。因此,建议未来的研究能够将定量与定性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积极探索跨区域、跨文化、跨类型、跨时间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