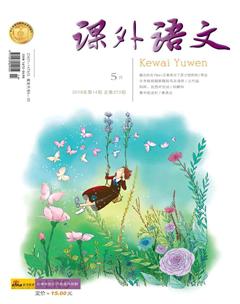留一点空间
韩陆倾贤

到了高二之后,名句背诵绝对成了一件苦差事。几大张几大张的纸发下来,面对成百上千的名言警句,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字不落地背出来,它们的意思、内涵反显得不那么重要,更无须去谈对这些真理的思考与探索了。
中国古人实在是太过聪明了一些。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几千年前的诸子百家几乎是为后人撑起了一整片天。但是翻开儒家经典,几乎都是些结论性的句子,那些先哲已为你想好了所有,只等你将这些结论记住。一片天是很广大,却总是别人创下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思维空间,似乎总是少了那么一点。
假如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西方的先哲更为注重的是一种思辨的过程。他们的传道授業往往是以论辩的形式产生,正过来,反过去,举例、因果、归谬,长篇大论,啰啰嗦嗦,在字里行间他似乎什么都没明确告诉你,似乎又什么都说完了。这还不能提供多么广大的空间,毕竟言语总有苍白无力的时候。相较之下,寓言则更为生动逼真【本句表达欠妥帖——要知道,“寓言”也是用言语表达的】,诸子百家中也有那么几位可爱可亲的,例如庄子。庄子的寓言是最为神采飞扬的,他为你描述一只大鸟,告诉你“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让你判断惠施的大葫芦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比起结论式的、毫无回转余地的名言警句,初读庄子,我们可能只是井底之蛙,天空只有方方的一块;我们需要自己逐步爬上去,然后发现一整片广阔无垠的天地,可是,那是我们自己的。
可翻开那些名句背诵的纸,《论语》能占上好几面,《庄子》却少之又少。
中国的绘画亦如此,画什么都要讲究个“留白”,总要留一点空间给予观画人自由地放逐思维。张爱玲曾在《画论》中提到,一幅画上的题画诗,无论写得多好,总感觉掐掉了那一块好不容易留下来的空间,你看到苍松翠竹可能感叹自然之美,可我看到了,却总想起小时候漫山遍野疯跑玩乐的酣畅。
似乎是背那些名句背得怕了,总想看些奇怪吊诡的故事;也似乎是被天天一打开电视机就能听到的语言暴力给弄怕了,里里外外的人一直在讲话,一直在告诉你这告诉你那,我什么都没想,可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我知道的是跟你跟他都一样的,不知对错的,似乎在达成共识之后,就没有再去辨别对错的必要了。我们的思维拥挤在一起,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啊。
我总希望能多留一点空间去思辨、去判断,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总是背道而驰。你说微博拓宽了空间吧,可真的是这样吗?而不是一大堆更快、更多的结论式的句子纷乱袭来,挤走唯一仅剩的一点点独立思维的空间吗?
我也总希望高考名句的纸上,能突然出现一段庄子的寓言,不要求逐字逐句地背诵,只是单纯地,留一点空间给我们……
【简评】
本文作者见识过人,知识面宽广,对“留一点独立思维的空间”这一论题领悟深刻,体验深切;行文中左右逢源,从校园生活中的名句背诵到西方先哲对思辨的重视,由中国绘画里的留白到微博的“背道而驰”“挤走唯一仅剩的一点点独立思维的空间”,无不深具穿透力,更有“庄子的寓言”贯通前后文,其思路、文字均如行云流水。而首尾照应、扣题点题又是那么自然、恰切,不见斧凿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