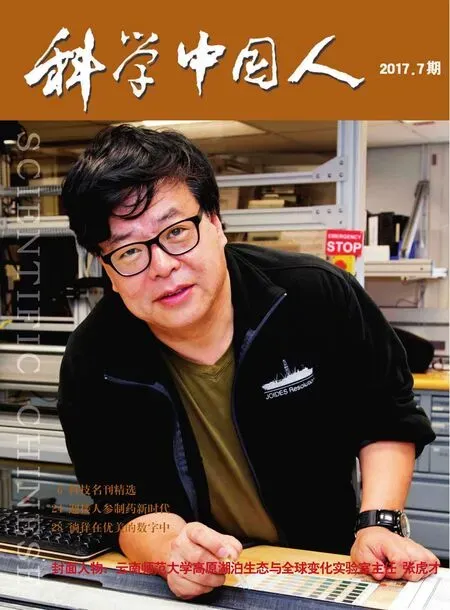剑指尖峰终无悔 人潜于世助国昌
——记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
本刊记者 吴 彪 郑莉颖

侯云德院士与科研及产业团队合影
他不喜宣传,在聚光灯前露面的次数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传染病防控领域有所了解的人大都知道他的名字;他不善言辞,普通话说得也不大标准,当别人称赞起其丰功伟绩,他定会连连摆手,强调自己只是有幸做了队伍的领头人;他不会偷懒,即便耄耋之年仍坚持搜集、翻译国内外病毒研究的最新动态,发挥余热,当好一线研究人员的坚实后盾;他甘做人梯,桃李天下,不论是步履艰难的岁月还是荣光环绕的今天,但凡接触到有想法、有能力的青年人,总想着竭尽所能地往前推一把、拉一下。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他走了很长远的路,亲历了最危险的疫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样也在我国疾病防控研究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2018年1月8日,当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响彻侯云德的名字时,人们肃然起敬,更为这位躬耕医学的科研工作者感到一份欣慰。一生勤勇为家国,他的大半人生都沉浸在分子病毒学、传染病防控及基因工程药物的研制中,“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
行路留痕 初露锋芒
少时家道中落,磨难雕了他的筋骨,塑了他的脊梁。
1929年7月13日,侯云德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武进区),那时候卢沟桥事变尚未发生。祖父主持着钱庄的营生,父亲是公司职员,当时殷实的家境使他的童年度过得相对欢愉。随着1937年后战线全面拉开,侯家举家北迁,逃难之中家财散尽,侯父与祖父双双失业,这也让年仅10岁少年的好日子结束了。初尝苦难,侯云德摆过摊、捕过鱼、养过鸡,在本该“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纪,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学业。
生活的历练并不会磨掉一个人的锋芒,之于侯云德,即便岁月蒙尘仍可以看出贫苦中的磨砺赋予他的勤恳。小学毕业,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步入初中,因表现优异直接跳读初二,1945年考入当时全国有名的省立常州中学。时至高考,因受大哥侯钰德的医生朋友影响,侯云德立志学医,顺利考取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誓要把医学难题琢磨透彻。7年的学习让他扎实了基础,对医学病毒有了了解,有了兴趣,更产生了疑问。
1955年毕业分配至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室,侯云德还未来得及站稳脚跟,便于次年通过统考成为我国第一批留苏预备生。后经过两年的俄语培训,29岁的他奔赴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在那段时间,他接触到很多先前从未了解到的知识,脑中的疑团也解开不少。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汲取更多的知识养分,他常常在图书馆或者实验室一待就是一整天,深夜被管理人员赶回宿舍的次数已经很难数得清了。
“当时学细菌的人比较多,而病毒学是新兴专业,是国际上的前沿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专门的病毒所,只是在微生物系里设有病毒室。另外,相对于细菌而言,病毒更难控制。”侯云德想要在这片新鲜的土壤里开垦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他终日埋头啃书、做试验,成为每天最晚离开研究所的人。渐渐地,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别人口中,一旦研究所里的同事遇到疑难,总会有人热心地推荐这位中国留学生。同时,因为所看书籍浩繁,侯云德在实验中产生了诸多新的想法,当他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后,不知不觉在3年半的时间里竟陆续发表了17篇论文。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也不禁好奇起来,亲自跑去研究所确认:侯云德是谁?他的论文发表的怎么会这样多?
夜以继日地大量阅读带给侯云德的影响是长久性的。当研究所发生一件从未有过的怪异事件时,专家们束手无策,侯云德反倒成为了揪出“真凶”的关键人物。“动物房里的小白鼠一下子全都死光了,没有人知道原因。”据侯云德回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研究所的人都乱了阵脚,究竟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作祟?成千上百种细菌、病毒中,又该是哪一种导致的呢?在进行了初步了解后,侯云德的脑海中有些东西一闪而过,似乎有苗头又似乎什么也抓不住。这种感觉让他很是焦躁,同样也更激起他想要一探究竟的决心。查阅大量文献,抽丝剥茧,侯云德将目光锁定在乙型副流感病毒——仙台病毒上。该病毒最早在日本仙台一实验室分离得来,具有溶血性,普遍存在于小鼠和猪体内。幸不辱命,而后侯云德成功用小鼠细胞分离出该病毒,并首次发现了仙台病毒在血清学上存在的两个型别。

专家简介:
侯云德,著名医学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技术总师。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3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
1929年7月出生。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60余年来,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他在干扰素研究、仙台病毒细胞融合机理及痘苗病毒基因组结构与功能研究方面获重大突破,主持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了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干扰素α1b,以及其他细胞因子系列产品。身为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他领导设计了我国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总体科技规划,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10年来历次的重大疫情,为国内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构筑做出了卓越贡献。先后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奖三等奖1项、原卫生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0项、何梁何利基金医学奖、中国医学科学奖、第四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首届树兰医学奖等奖项。2018年3月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
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的浅尝辄止,恐怕实在不符合侯云德惯有的倔劲儿。他和仙台病毒较起真来,通过一步步地深入挖掘,在国际上首次阐明了其致单层细胞融合现象及机理,并证明了它对人体的致病性。在确立仙台病毒溶血活性与细胞融合活性均由同一病毒特性引起之际,侯云德还率先建立起一种病毒溶血抑制试验,用于全面研究具有溶血活性的病毒抗原关系。而此时距离1958年日本学者冈田发现仙台病毒具有触发动物细胞融合效应仅仅3年,在信息传播并不畅通,甚至可以说完全闭塞的年代,这一重大发现完全可以与之并称为同期创举。
而后,侯云德梳理研究资料于1961年写成了一篇全俄文、独创性的关于副流感病毒的学位论文。也正是鉴于他对仙台病毒的突破性发现和系列研究斩获,苏联医学科学院组织了一次无记名专家组投票,与会专家们一致认可了侯云德相关研究及其论文在领域内的卓越贡献,使苏联高等教育部第一次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忽略以往正副学位申请必须间隔6年的惯例,直接授予他博士学位。在举行学位授予仪式的晚宴上,侯云德的导师戈尔布诺娃教授显得比他还要激动,热泪盈眶地向人们说道:“侯云德是我从事科研工作30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病毒所的荣誉。”

三元基因首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持之以恒 家国为先
1962年,侯云德学成归国便和病毒杠上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在和呼吸道病毒打交道,并在国内首次分离出Ⅰ、Ⅱ、Ⅳ型副流感病毒。结合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地区呼吸道病毒的主要流行趋势,他研究发现Ⅰ型副流感病毒存在广泛的变异性。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侯云德希望能再往深处走一步。他常常说科研工作者要懂一点儿哲学思想,“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造世界”,学习病毒学的目的要发现病毒,认识病毒,更要预防病毒和控制病毒。为了能够减缓病毒性疾病蔓延速度,在治疗方法上有所突破,使患者尽快摆脱病痛的折磨,他翻阅古籍围绕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材进行研究,迅速锁定并以科学的方法证明出黄芪同干扰素联合使用具有治疗感冒的奇效。在确定了以干扰素为研究突破口的前提下,以侯云德为首的研究小组快速投入到抗病毒药物的研制中去。
1976年,他们的研究团队收获了第一份硕果。在发现人脐血白细胞具有较强的干扰素诱生能力之后,侯云德先是培育了高产新城疫病毒株NDV-F系,紧接着又制订出人白细胞干扰素的分离、提取和纯化流程,最终将可用于临床的干扰素制剂成功研制出来。而后受到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的启发,侯云德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可能要做一件大事,一件能够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要为国内干扰素研究闯出一条路,解开由于长期依赖进口、经费短缺而使中国科研工作者束手束脚的桎梏。按耐住内心的激动,侯云德不声不响地重复着试验,迈过一道坎、解决一个难题,离目标就又近了两步。他经过反复试验,好不容易以病毒诱导的形式从上万毫升的人血白细胞中提取出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mRNA),但后续的测定又遇到了麻烦。从文献中了解,想要成功测定这种信使核糖核酸必须使用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但当时国内并没有非洲爪蟾蜍,引进经费也严重不足。侯云德只好和同事们埋头寻找可替代的生物细胞。经过几番周折,北京饲养场内的非洲鲫鱼被认为能够提供最符合试验条件的卵母细胞。随后他们采用显微注射将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顺利注入鲫鱼卵母细胞,建立起鲫鱼卵母细胞内的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翻译系统,为研究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此项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干扰素大会的高度评价,并顺利入选1981年出版的国际权威书籍《酶学方法》。
从干扰素的制剂提取到其翻译系统的建立,侯云德花了5年时间。当他运用基因技术看着干扰素基因被成功导入到细菌中,呈现“次方式”的繁衍,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国内病毒研究学界都沸腾了。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由于缺少外汇储备,加之进口干扰素价格十分昂贵,几乎所有的病毒研究从业相关人员都在“节衣缩食”。有了成熟的技术依托,有了完善的细菌“工厂”,干扰素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不再是梦,可以说侯云德一度解救了当时科学研究经费紧缺造成的水深火热局面。
在国内,人们称侯云德是干扰素之父,这是一项接连一项亮眼成绩相互叠加、累积形成的认知结果。在基因工程干扰素领域,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是早期最具价值贡献的开拓者之一。若真要仔细列举过来,独创Ⅰ类国家级新药自然是首当其冲。
1982年,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最适合中国人抗病毒反应能力的人α1b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基因工程多肽类药品——重组人干扰素α1b。该独创性药品获国家Ⅰ类新药证书,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时代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国内基因工程原创药品为零的尴尬。更值得一提的是,重组人干扰素α1b比之先前在国际上市的重组人干扰素α2a、重组人干扰素α2b等,疗效确切。其副作用更小,能有效治疗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慢性宫颈炎和疱疹性角膜炎等多种国内常见疾病。为表彰这一划时代的特殊贡献,199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被颁发给侯云德及其项目团队。
这个奖项拿得不容易。据那时的研究组成员回忆,有关人体α1b基因的克隆很复杂,首先要拿到单纯的基因就需要一定的工具辅助。但受制于当时的科研条件,工具要自己制造,所需制剂要自行研发,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精准的铺垫。如今科技发达,几分钟、几小时就能得到的结果,放在那会儿可能耗费的是好几个人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好在所有的辛苦没有白费,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我国相关的干扰素基因工程研究遍地开花。侯云德所率领的科研团队也有了诸多不俗斩获:1983年采用TGATG序列成功使融合基因表达非融合的αl型干扰素蛋白;1984年在研究重组干扰素基因的表达时,发现了原核增强子样序列;1987年组建成温控型原核高效表达载体pBV220系列并广泛应用于我国基因工程药物的研发和生产;发现并克隆表达了中国人αlb型干扰素基因的两个新等位基因,证明其为部分中国人的优势基因;采用定位突变技术把αlb型干扰素86
位的Cys替换成Asp,增加了其稳定性和抗病毒、抗肿瘤及免疫调节活性;研制成功一种具有靶向肿瘤细胞的脑啡肽干扰素,提高了干扰素的镇痛作用和抑制肿瘤细胞的分裂能力……
“他是一个优秀的设计者,也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如是说道,“不能否认,他对于我国医学病毒学的研究和病毒病的预防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对病毒全基因序列的研究,还是进行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的研发,在那10多年里,侯云德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针对当时已知的最大动物病毒——痘苗病毒,他构建了我国痘苗病毒天坛株的基因文库,完成了该病毒全基因组的测序和分析,首次在国际上更正了有关痘苗病毒基因组的HindⅢ P片段的部分错误结论,被国内外学者普遍证实。同时他还带领团队构建了系列新型大肠杆菌高效表达载体,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了大肠杆菌增强子样序列,为我国基因工程药物研发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在面向基因工程药品的研发事业中,1个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干扰素α1b)和6个国家II类新药又相继问世,侯云德携团队为我国医药发展领域再创辉煌。

全家福
人隐于世 果遍于坊
虽不爱抛头露面,不愿大肆宣传研究成果,但有段时间侯云德却跑得格外勤快:实验室和地下室,科研单位和政府机构,总是少不了他忙前忙后的影子。
时值1986年,国家积极推动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为保障政治独立和民生安全作出重要批示,提出了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侯云德作为该计划生物领域的首席科学家肩担重任,既要对整体医药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布局进行顶层指导设计,又要兼顾研究开发和产业化进程的推进步伐。准确地来讲,那时他除去科学家的外衣更像是一个企业家、实干家,一门心思地为药品后续发展谋出路、寻门路。
1992年,在侯云德领导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楼的地下室,一个名为三元基因的公司悄然成立了,侯云德亲自担任公司首任董事长。时任三元基因总经理程永庆回忆说:“那时候侯老师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抽屉,专门存放着各式各样的研究论文和获奖证书。他曾殷切地希望将这一页页纸变成实实在在的药品,变成能够让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品。”面对当时100%依赖国外进口药物的境况,国内缺医少药,广大农民看不起病、用不起药的事实,侯云德痛心疾首。
果然,三元基因不负众望,设计和建立起我国第一个通过GMP认证的基因工程干扰素生产线,首次实现了基因工程药物依照国际化标准的大规模生产。程永庆说:“建成中国第一条通过国家GMP认证的生产线,实属不易,全部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都是我们克服重重阻力从国外引进的,有美国的、瑞典的、德国的、日本的、法国的……而这条生产线建成投产,让许多海外同行都不禁为之惊叹,不敢相信中国竟还有这样的企业。”
外界的反响如何,侯云德一概不理会,他知道即便是第一条生产线建成了,后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能够尽快完善药品生产系统,达到成熟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他将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给国内数十家企业,从一个点勾画出一条线,从一条线向着更广阔的面发展。短时间内,他的高效举措使数以万计的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成果转化作出了表率。
然而事实上,侯云德所做的远远要比我们看到的多。除了完成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他活跃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创新领域,在驱动国内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10倍增长的同时,积极推动近20种基因工程药品上市,切实保障了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整体水平的稳步提升。截至1996年,侯云德已连任3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专家,彼时的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同过去相比增加了100倍。据不完全统计,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组人干扰素α1b(商品名:运德素®)已累计使用了数千万剂,成功治疗了数百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儿童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患者。
而近20年,侯云德更是凭借发现干扰素对控制SARS冠状病毒传播有显著效果,为我国抗击“非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病树还春 学以致“勇”

2006年8月禽流感国际会议
谈及SARS,人们仍会心有余悸。那是一场毫无准备的硬仗,来势迅猛,掀起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恐慌,也造成了遗留至今的举国之痛。依据SARS的病毒特性判断,它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消灭”或自动消失的。时刻警惕、时刻防范,如何将病毒传播扼杀于摇篮,迅速应对突发疫情?抗击SARS所付出的沉痛代价,留给中国疾控工作者的是深刻的教训与无尽的思索。
2008年,侯云德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专职技术总师,那时起,“绝不重蹈覆辙”便成为萦绕在他心头的信念。然而,他到任的工作还未全面开展,2009年的甲流疫情就开始席卷全球。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拉响6级警报,我国也快速成立了由原卫生部牵头,侯云德担任专家组组长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专家委员会。眼看着疫情来势汹汹,侯云德回忆说:“那会儿我们火速召集国内10家顶尖疫苗生产企业来开会,一天天倒排,看看最快什么时候能拿出疫苗。”
经过紧锣密鼓的赶制,依据文献和过往经验,专家组完成了一系列严格的科研测试之后,在第87天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甲流疫苗,阻止了大规模疫情的暴发,反应速度之快,打破世界纪录。中国疫情应对的反应速度让世界震惊,8项世界第一的科技成果为严控甲流蔓延做出了重要贡献:除去疫苗研制的反应最快,“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思路在重大传染病防控新机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上率先完成灵敏性和特异性均最优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诊断试剂,为尽早发现、最快隔离控制疫情创造了条件;引入中医药治疗手段,严格遵照科学医学方法获突破,明显缩短了流感的治疗病程……
身为全局的掌控者,侯云德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一不留心走错一步将会使十几亿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他需要准确把握疫情走向,提出最佳的应对方案,需要考虑我国国情,作出最迅速、有效的判断。彼时,在卫生部会议室内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围绕甲流疫苗接种究竟是一针还是两针,在场专家们的争论陷入胶着。不同于世界卫生组织通用的两针免疫策略,侯云德所提出的一针接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先例。不过时间容不得过多犹豫,一方面结合疫苗临床试验结果以及多年的病毒研究、免疫记忆规律等,一方面顾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药品生产效率的滞后性,侯云德当机立断,通过“打一针”策略成功干预了甲型H1N1病毒的扩散,大幅度降低我国人群的患病率和病死率,节约社会成本2000多亿元,有效保障了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期间的重大研究成果不但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更直接斩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侯云德与程永庆
纵然国际传染病传播风云莫测,近年来国内的总体局势却一直相对稳定,并未有大规模疫情的暴发。这正是得益于侯云德始终秉承的能力建设理念,奉行着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他提出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成功阻隔了涵盖中东呼吸综合症、西非埃博拉等多次重大疫情,增强了国内传染病综合防控平台建设能力,对构筑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具有显著作用。
为他人暖 非自安息
对科研一丝不苟,对生活极尽简洁。在侯云德学生、同事的眼中,他的日常形象和严苛是搭不上边的。他是一个赶时髦的老头儿,能够玩转在线社交软件,60岁的时候还跃跃欲试要同学生们去蹦迪庆功。他对自己节俭到抠门,但会不遗余力地奔走为青年人提供相对舒适的科研和生活环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武桂珍回忆说,“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在武桂珍看来,任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期间,他理应享受副部级待遇,可却对物质上的享受从不上心。起初,他出门的座驾是一辆年份久远的红旗牌汽车,随着老机器、老部件面临着“寿终正寝”,汽车到了非换不可的地步。相关人员问他想换什么样的,侯云德只吐出了5个字:“带轱辘就行。”
他确实不会心疼自己,但凡和他接触的人都对此深有体会,同时人们也对他以身作则、甘为人梯的无私精神留有深刻印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原所长李德新说:“在年轻人的培养体系上,侯院士下了很大的工夫。从1995年,我们这一批人海外求学归来,他就非常支持我们大展拳脚。期间,鼓励并帮助大家申请原‘863’课题,在持续的研究任务中予以指导。他带动了一代青年人的发展,也全面推动了我国病毒研究的发展。”
作为侯云德的嫡系弟子,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对恩师感触最深的还是“润物细无声”的品格教育。“老师不论多忙,只要一有时间准会到实验室和我们聊天,聊最热的技术趋势、最新的科研动态,用这种方式传递出实时有用的信息知识……闪光灯前,他总把机会和荣誉推给年轻人。”
“侯老师常说,病毒可以致病,也能够治病。”现任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程永庆说道:“在学习和工作的交流中,他一般不会训导什么,可在言谈举止中,他会让学生自己领悟该做些什么。”
侯云德身体力行地影响了一代人,截至2017年,他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200余名,其中不乏我国病毒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优秀领头人。他对学生从不发脾气但对自身的要求极其严苛。为了能够保证行文风格和质量,他曾在最繁忙的研究阶段挤时间,亲自操刀完成了一本105万字的病毒学书文撰写。历时一个多月,他每日都会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终于将详尽描述病毒基础研究的宏篇著作《分子病毒学》顺利结稿。时至今日,89岁的他依旧不停歇,每日梳理全球最新的科研成果资料,编制生物信息数据库,为我国传染病控制、新药和新型疫苗的研发提供最及时、最前沿的科技信息。
“……吐尽腹中丝,愿作春蚕卒;只为他人暖,非为自安息。”这是侯云德写给自己的一首诗,名为《决心》。和病毒斗争了大半生,他用毕生所学筑牢防病防毒的高墙,用创新和传承谱写了中国生物基因工程、传染病防控进程的华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