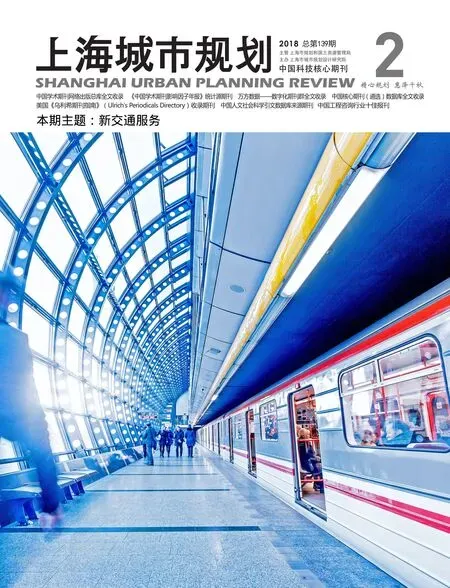共享移动性创新、规制变革及其社会障碍
冯苏苇 FENG Suwei
平台经济①平台经济(platforms economics)一词较早出现在EVANSD. Platforms economics:essays on multi-sided businesses.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2011)一文中。类似的表述还包括sharing economy , collaborative economy, multi-sided platform, two-sided internet markets等。快速崛起为共享移动性发展带来了契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对出行行业规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平台经济作为共享移动性的技术载体和交易场所,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它在出行领域各个市场的渗透和生长;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所导致的新旧业态之间利益冲突日趋激烈,亟需出行行业规制及时更新,引导和调节两者公平竞争、融合发展。规制更新决定了平台经济和共享移动性今后的走向,因此结合我国城市机动化背景,探讨其更新方向及所存在的社会障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
1 共享移动性及其影响
近年来,经济、环境和社会力量快速提升了共享移动性对车辆、自行车或其他出行方式的共享使用。在我国城镇化和机动化特定背景下,平台经济在出行领域的快速崛起为共享移动性提供了技术基础,共享移动性在交通需求管理中所承担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成为广为关注的议题。主要的共享方式②有文献认为公共交通也是共享移动性的一种方式。,如网约车(Rridesouring)、共享单车(互联网无桩租赁自行车)、汽车分时租赁以及汽车合乘等,正在改变人们的交通选择,并对出行市场和城市交通产生变革性影响。经验数据和实证研究表明,共享移动性对出行行为、环境、土地利用以及社会关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这些复杂的作用机制仍需更多的观察和研究来证实。

图1 共享移动性的分类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usan Shaheen的定义[2],共享移动性(Shared mobility)是一种创新的交通策略,出行者通过对车辆、自行车和其他方式的共享使用,按需获得各种交通方式的接入。它包括各种形式的汽车共享、合乘以及应需(On demand)出行服务,也包括可替代的公交服务,比如辅助公交、定制公交、私人微公交服务(Microtransit)等。根据撮合主体的差异,共享移动性以社会关系、企业组织、点对点(平台经济)等3种方式进行出行活动的组织和安排(图1),并呈现各方式之间相互叠加的趋势。基于社会关系(家或亲缘关系、工作关系等)的合乘行为是共享移动性最早的自组织形式。1970年代开始,美国、加拿大等国采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利用内部信息技术,对员工通勤合乘进行撮合和激励,以改变“单人单驾”出行方式,降低个体机动化外部成本。2010年后,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推广运用,平台经济为大规模点对点出行交易提供了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共享移动性服务开始大规模进入市场,2012年非盈利的汽车共享(Ridesharing)约占加拿大和美国交通方式分担的8%—11%[3]。依靠社会关系、企业组织和平台经济等媒介的撮合,共享移动性既包括同一运载工具内部空间的非竞争性共享(你有我有),如小汽车合乘、顺风车和各种辅助公交等,也包括对运载工具的竞争性共享(你有我无),如网约车、汽车和自行车分时租赁等。
共享移动性对出行产业链以及交通参与方产生了一系列综合影响,包括:
(1)移动终端叫车服务(App-based ride-hailing service)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转移了部分出租车和公交客流,Uber等交通网络公司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 TNC) “创造性破坏过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备受争议[4],其服务可靠性与透明性、员工保障、社会公平、与传统产业公平竞争等问题广受关注[5]。
(2)伴随着自行车回归城市的世界性潮流,无桩租赁自行车(共享单车)快速兴起和拓展市场。在我国城市自行车路权有待保障、骑行行为不规范以及公共空间管理滞后的背景下,共享单车带来的“快速自行车化”过程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诸多挑战[6]。
(3)共享汽车(分时租赁)兴起于1990年代的欧洲和2000年代的美国,初期由于缺少大规模风险投资而发展缓慢,之后运营商选择与其他共享移动性服务(如E-delivery网络约租车和网约车司机)进行合作。2014年,全球约有500万共享汽车用户以及超过10万辆共享汽车[7]。它的推广有助于降低机动车拥有量、鼓励多模式移动性以及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源[8]。
(4)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对出行模式、支付方式与移动性方案提供整合性服务,并成为一种新趋势——原来提供单一服务和移动性的公司,现在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多模式服务。MaaS意味着从传统的个人拥有出行工具到将出行作为一种服务来进行消费,而多边平台粘合了出行者、交通运营者、数据供应商和MaaS供应商,是将交通运输转化为一种整合性服务的最佳场景。
(5)汽车制造商将新的移动性作为盈利策略的一部分,从共享移动性中进行风险投资并获得收益,打造可持续的交通系统。
(6) 城市成为共享移动性的扩散主场,中央和城市地方政府加快政策供给和规制更新,协调新旧业态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保障公众出行服务的高效、安全、价格可承受,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做出前瞻性引导。如果说平台充当了共享移动性“创新性扩散”的技术推手,那么出行市场的政府规制,或者说在新旧业态交织过程中政府主导的规则更新将很大程度上改变共享移动性的发展方向,下节介绍平台经济和出行市场规制。
2 平台经济与出行市场规制
2.1 平台经济崛起与冲击
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型双边平台企业在资本推动下快速崛起,催生了个人之间以点对点方式交易的商业模式。这种新型的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平台提供了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居间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有利于闲置资源接入与再利用,促进就业和释放经济活力,被称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在企业监管、税收及不正当竞争方面也存在诸多争议,其垄断性行为、超常盈利能力以及对传统线下实体经济的冲击,成为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平台交易标的包括居民生活性消费品、金融资产以及劳务等,出行领域代表性业务包括网约车、共享单车、汽车分时租赁等,从我国市场情况看B2C、C2C方式均有,目前以B2C方式为主。平台经济以可接受的交易成本为供需双方创建一个匹配[9],交易成本降低表现在交易者之间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联络成本和合约签订成本,实际上是用一种交易成本更低的租赁合约形式取代原有的买卖合约形式[10]。由于交易成本下降,消费者满足需求呈现出由“以买为主”向“以租为主”的转变[11]。比如,传统出租车服务具有高的搜寻成本和低的有效供给,司机为避免空驶而聚集在需求量高的地段,最终降低了有效需求,而网约车提供线上的交易撮合降低了搜寻成本,动态定价为司机进入和退出市场时机提供指导性信息,创造了一个真正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有效市场[12]。
数字信息技术使线上信息成本大幅下降,推动了共享型或协作型经济平台的兴起,驱动因素包括全球经济背景、技术创新与突破、参与者经济社会需求和环保态度等[10],即:(1)全球金融危机后产生的大量失业和消费替代,以及各国产业转型带来的再就业压力;(2)互联网发展、数字技术克服了点对点交易关于信任、声誉等一系列制约共享行为的障碍;(3)参与者个人经济因素,如省钱、便利及高质量服务,对社群认同和增强社会联系的渴望以及对环保的重视等。
平台的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相互叠加,使其具有向少数大公司集中的强烈趋势③美国科技五强(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和中国互联网双雄(腾讯、阿里)的市值加在一起,逾3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GDP。来源:王力为,全球领袖纵论何以监管平台巨头,财新网,中国改革,2018年第2期,2018年3月1日,http://cnreform.caixin.com/2018-03-05/101217232.html。,引发监管者对平台垄断、过度攫取消费者利益的担忧。而它对传统行业的补充和侵蚀、以及对原有规制的突破和违背是平台经济引发争议最突出之处。现行监管框架主要为传统市场所设计,在保卫传统行业商业模式(及就业)与可能产生更广泛利益的创新模式之间,管制者面临如何取舍的价值判断[13]。此外,平台在各类用户和不同市场侧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方面占据优势,加剧了平台及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单向镜”现象④“单向镜”是经济学家Pasquale在2015年提出的一个比喻,平台对个人生活的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用户并不了解自身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如何影响展示给他们的信息。,即平台个人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与用户有限认知能力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用户担心丧失个人自主、不透明、问责不足以及数据可能被用于损害个人利益。研究发现,Uber通过“加成定价”算法来制定价格,透明度不足[14],平台服务在可靠性、员工保障、社会公平以及与传统行业公平竞争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争议[15]。
2.2 传统出行市场规制及其放松
出行市场规制是政府及相关管理机构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如缓解交通拥挤、维持运行安全、降低尾气排放、保障路权公平等,通过一定的法令、规则和标准,对各种组织和个人的交通供给和需求决策进行引导和干预的过程。本质上,它是政府部门在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之外,在交通管理领域行使其公共管制(Public regulation)职能的过程。传统出行市场规制包括交通活动参与者(个人和企业)及运载工具应遵循的准入、价格、服务质量、安全保障等相关的法令、规则和标准。
在特定种类的出行市场中,规制根据市场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管理风险来制定具体规则。比如出租车服务具有流动经营、随机服务、点垄断、交易成本高、时空约束、非自由交易、选择受限等经济学特征,使得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存在特殊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准入(司机、车辆和企业)、数量、价格、服务质量、安全等方面采用相应的管制措施。
一般而言,规制的变更来源于公共价值观变化、特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以及管理者对行业管理的认识与经验等因素。在特定情形下,政策制定者也会根据市场变化主动调整监管方向,以确保行业的公平竞争。确立之后的规制粘合了多种利益相关群体,他们的利益随规制变更而发生变化,成为受益或受损的各方,同时会有新的利益相关方进入政策视域,他们对规制变更的态度和诉求各不相同。从规制主体来看,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关系推动了规制的不断演进。从变更的动因来看,规制的加强或放松与公共价值观变化、市场变化催生的社会问题、公共决策过程及其体制环境相关,一般会滞后于市场变化。此外,规制的变更过程要接受一般经济学原理的检验,只有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群体的诉求和损益,并使规制变更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才是社会净收益最大的政策选项。
平台经济进入出行领域改变了消费者偏好、产业布局、业态结构和竞争态势。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网信办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在共享移动性所涉及的网约车、自行车和汽车租赁等领域,规制也相应进行了更新和调整、加强或放松。以出租车和网约车为例。长期以来,出租车行业由于严格的数量和价格管制,车辆和服务供给跟不上城市出行需求增长,特许经营加份子钱的管理模式实现了政府、企业、司机之间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但也造成司企负担不均衡、冲突加大,出租车服务质量下降而饱受诟病。自2010年易到用车在北京地区上线测试以来,国内多个平台的涌现使网络预约租车服务覆盖到全国数百个城市。平台经济释放了供给端红利,部分缓解了打车难问题,但新旧业态处于不对称管制状态,利益冲突和矛盾日趋激化。2016年7月,由国务院、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新增制度供给方式指导行业发展。之后全国有200多个城市陆续发布了网约车管理办法。在政策执行中,平台公司更为看重线上扩展、获取规模和流量,而出租车等个体机动化运输服务则强调线下经营活动的便捷、安全及价格可承受,两者在经营目标上存在一定差异,网约平台在获取地方经营执照、督促司机合法合规经营等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新旧业态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放松管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探索。
3 规制变革的社会障碍
平台经济有效促进了共享移动性的推广,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其监管力度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商业模式是否能够存续,也决定了共享移动性今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本节从潜在社会风险与成本、平台治理有效性、新旧业态融合发展等角度,讨论规制变革的可能方向及存在的障碍。
第一,线上与线下经营模式之间存在目标冲突,平台与供需双方权利不对等,即使规制明确了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如果政策执行不力或不到位,运营过程潜在的社会风险与成本仍可能发生外溢。传统运输服务的实质是企业组织运力、完成人或物的线下空间移动,需求与供给双方需要直接发生关联,企业是运输活动的第一责任人。而平台的目标是运用营销策略产生间接网络效应⑤间接网络效应是指平台通过营销手段使市场一侧的用户增加,另一侧用户也相应增长的现象。而直接网络效应,是指由于平台提供了社会互动机会,消费者被平台上的其他消费者所吸引,他们从各自的体验中获益。,尽可能多地粘合供需双方,作为流量入口获取大规模数据,以实现范围经济效果。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分别与平台建立代理关系,再形成服务关系,这种以平台为中心的委托代理关系,与传统的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直接关联的机制存在实质性差异[16]。
比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不仅是信息撮合责任,而且是承运人责任,一旦发生服务或事故纠纷,平台首先要承担全部责任。而实际竞争中,为了进入新市场、争夺入口和流量,一些平台不惜采用低价、补贴等方式粘合非法客运,甚至允许异地司机和车辆跨境经营,并为司机报销行政罚款。这种“平台+黑车”的运营方式在遭遇纠纷、事故、犯罪等问题之后,只能依靠个人协商、社会调解或法律途径加以解决,管理部门为维护市场秩序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执法成本。
第二,巨型平台企业在多个共享移动性领域形成了对原来市场的互补或替代,服务稳定性来自平台自监管治理模式是否有效,也决定了新业态对传统服务的渗透程度。传统的共享发生在家人、亲戚和朋友间,是人际关系网络上的强连接,具有互利互惠的价值导向。平台并未过多依赖政府监管,而是依靠人们自我监督和彼此信任的“弱连接”机制,让陌生人通过互联网参与商业化交易[17],采用对所有参与者都开放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相同的目的,并不明确指定参与者的行动[10],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交易过程也是人际关系重构过程,满足参与者对社群的认同和增强社会联系的渴望,但却很难通过平台获得可持续的社会联系。此外,平台上出现的伪造评价还会造成偏差,导致网络信任下降,不利于交易完成[18]。可见,平台对交易关系保持开放性以获得更多的用户接入,这种“弱连接”机制和自监管模式还有待市场的检验,是否需要引入内外部监管机制取决于参与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低的时候需要设立监管体系,反之则不需要[19]。
第三,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使新旧业态尚处于不对称监管状态,规制如何引导两者公平竞争、融合发展是值得积极探索的方向。多种共享移动性服务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格局与消费模式,对传统产业和原有的规制体系产生了冲击,比如,各地网约车管理办法均对准入条件(平台、司机和车辆)做出了规定,但网约平台运用低价、折扣和积分等营销手段粘合了大量非法营运的司机和车辆,使一些城市原有的出租车数量管制几乎不再发挥作用,导致个体机动化服务局部供给过量,引发司机超时工作的隐患。传统出租车行业仍然处于数量、价格等强管制状态,不利于参与市场竞争、稳定营收。平台进入退出壁垒较低的经济特征决定了市场上总会有多个竞争者存在,是一个可竞争市场,用户需要不断对信息中介进行选择,而传统出行产业由于规制约束无法参与充分竞争而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市场难以提供稳定可靠的出行服务。因此,对公交、出租车以及汽车、自行车等租赁业应进一步放松管制,鼓励企业参与竞争,推动建立线上线下合作机制以及利益协调机制,将有助于共享移动性的扩散和发展。
4 结语
在西方机动化发达的国家,共享移动性在推动小汽车合乘增长、有效利用资源、引导环境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1]。对我国高密度城市而言,公交为主导的供给方式以及公交优先的政策背景使共享移动性具有天然的生长环境和发展优势。共享移动性已经改变传统出行市场格局,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出行者、服务供给和运营方、中央和地方管理部门进入其视域范畴,新旧业态的更迭也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多元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规制作为引导产业良性发展、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必然发挥更大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共享移动性与机动化的互动关系具有两个方向,共享移动性既可以将出行者从公交方式抽离出来,加剧私人机动化趋势,也可以合乘、顺风车等“共享”车辆空间方式减少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重大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供给。在改善移动性和安全性、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下,规制更新需要进一步评估扩大共享移动性的潜在收益和风险,考虑每种共享服务特征及规制能力,权衡安全要求的效能和成本,以及服务扩张可能对特殊群体(如不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残疾人、老年人等)产生的潜在社会不公平,鼓励新旧业态的公平竞争、融合发展。
(致谢:感谢上海交通大学黄少卿、《中国交通报》杨红岩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方嘉雯等给予的指导。)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TRB Report.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mobility:examining the rise of technology-enabled transportation services[R].2015.
[2]SHAHEEN S, CHAN N, BANSAL A,et al. Shared mobility: definition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early understanding[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2015.
[3]CHAN N, SHAHEE N S.Ridesharing in North Americ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Transport Reviews, 2012, 32(1): 93-112.
[4]ROGERS B.The social costs of Uber[R].2015.
[5]FLORES O,RAYLE L.How cities use regulation for innovation: the case of Uber, Lyft and Sidecar in San Francisco[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rocedia,2017(25):3756-3768.
[6]冯苏苇. 快速自行车化的公共经济学辨析[J].交通与港航,2017,4(3):13-16.FENG Suwei.Analysis on rapid diffusion of bicycle sharing based on public economics[J].Communication and Shipping, 2017, 4(3):13-16.
[7]SHAHEEN S, COHEN A.Innovation mobility carsharing outlook: carsharing market overview,analysis and trends[R].2016
[8]NAMAZU M, MACKENZIE D, ZERRIFFI H,et al.Is carshaing for everyone? understanding the diffusion of carsharing services[J]. Transport Policy,2018(63):189-199.
[9]DERVOJEDA K, VERZIJL K, NAGTEGAAL F, et al.The sharing economy, accessibility based business models for peer-to-peer markets[R]. 2013.
[10]刘奕,夏杰长.共享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动态[J].经济学动态,2016( 4):116-125.LIU Yi, XIA Jiecha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and policy study on the sharing economy[J].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6(4): 116-125.
[11]卢现祥.共享经济:交易成本最小化、制度变革与制度供给[J]. 社会科学战线,2016(9):51-61.LU Xianxiang. Sharing economy: minimized transaction cost, reform and supply of institution[J].Social Science Front, 2016(9): 51-61.
[12]ROGERS B.The social costs of Uber[R]. 2015.
[13]伯廷·马腾斯. 线上平台经济政策面面观(上、下)[J].比较,2018(89):112-170.MARTEN B. Overview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its policy[J]. Comparative Studies, 2018(89): 112-170.
[14]COHEN M, SUNDARARAJAN A.Self-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peer-to-peer sharing economy[J].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Dialogue,2015(82):116-133.
[15]FLORES O, RAYLE L.How cities use regulation for innovation: the case of Uber, Lyft and Sidecar in San Francisco[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rocedia,2017(25): 3756-3768.
[16]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J].中国法学,2015(4):286-302.TANG Qingli. The regualtion path on the‘ special car’type of sharing economy[J]. China Legal Science, 2015(4): 286-302.
[17]李飞翔,谭舒. 共享经济现象背后的四维伦理反思及启示[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1):21-27.LI Feixiang, TAN Shu.Four-dimensional ethical reflections and enlightenment behind of the sharing economic phenomenon[J].Science & Technology Progess and Policy, 2018, 35(1): 21-27.
[18]FRADKIN A, GREWAL E, HOLTZ D,et al.Reporting bias and reciprocity in online reviews: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 on Airbnb[R]. 2014.
[19]HART B, HOFMANN E, KIRCHLER E. Do we need rules for‘ what’s mine is yours’? governance i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 (8): 2756-2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