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识字教学理论梳理及思考
卢素侠 谭士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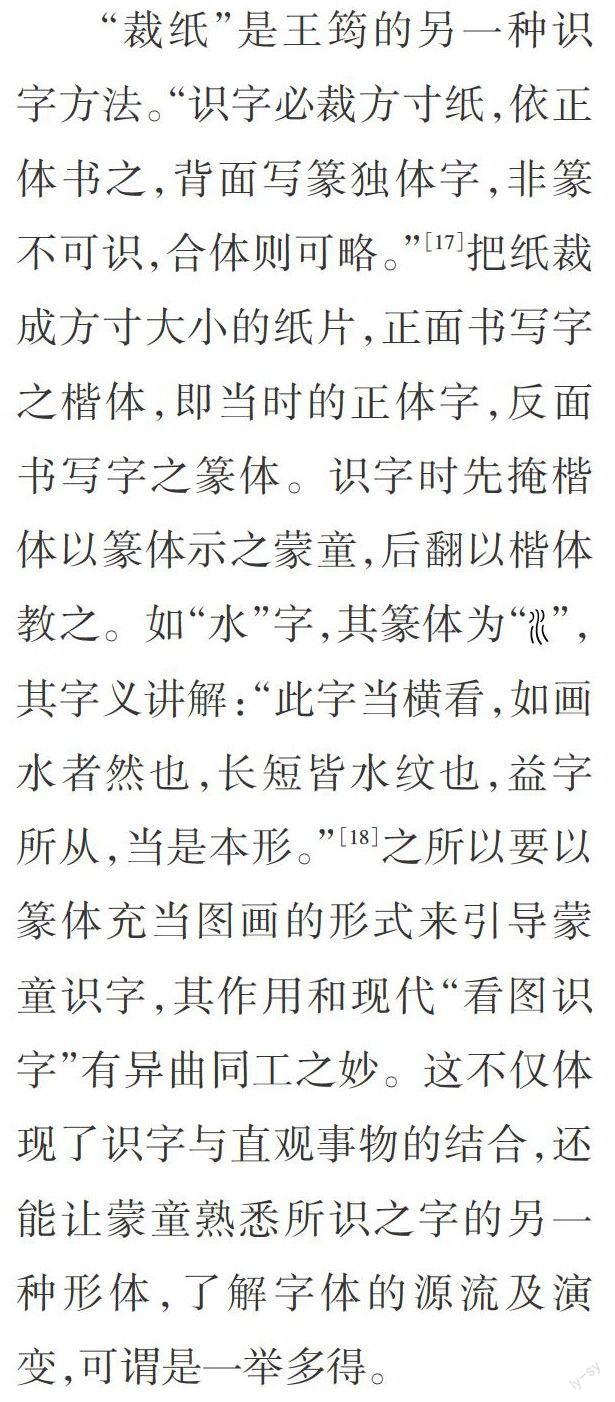
识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在我国,最早的识字教程出现在西周“六艺”教育中的“书”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出现了王筠的汉字学理论体系及识字教学理论成果。作为文字学家,王筠的汉字学著作有《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句读》《说文韵谱校》《说文属》等;其识字教学理论集中体现在《文字蒙求》和《教童子法》中。
一、以阅读《说文解字》为目标的识字数量与质量
识字的终极目的是阅读。那么,儿童到底需要认识多少个汉字才能实现基本无障碍阅读呢?这是汉字学及识字教学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儿童阅读的文本存在差异,所以不同时期对儿童识字数量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关于识字量,王筠在《文字蒙求》自序中说:“总四者而约计之,亦不过二千字而尽,当小儿四五岁时,识此二千字非难事也。”《文字蒙求》四卷共收录汉字2050个字,第一卷是象形字,收录汉字264个;第二卷是指事字,收录汉字129个;第三卷是会意字,收录汉字1254个;第四卷是形声字,收录汉字389个;外加“补缺”字,收录汉字14个。
王筠为什么为蒙童确定2050个汉字来学习呢?这2050个汉字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当时必不可少的识字工具书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共收单字9353个,相对于一般的蒙童来说,识字数量巨大,学习起来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王筠应老友陈山嵋之邀,为其孙编撰一本启蒙识字工具书。为了让蒙童在最短时间内认识一些阅读必需的汉字,王筠就在许慎《说文解字》内选择了当时使用频率较高、组合能力较强的2050个书面语单字,编纂成《文字蒙求》。《文字蒙求》的字量约占《说文解字》字量的21.92%,所占比例看似不多,但它对《说文解字》的阅读却产生着“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影响。认识掌握了这些高频率出现的2050个字以后,蒙童就能较为轻松地进一步学习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其他汉字,从而能较快实现基本无障碍阅读。
高频字在读物中出现的频率高,构词能力强,儿童掌握了这些汉字,进入阅读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王筠为蒙童选择所识汉字,不仅在数量上有所考量,而且在此基础上特别选择其中的高频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在此之前的识字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从传播儒家思想出发,编选文章和确定要学的汉字,而非从儿童阅读这一需求出发确定所学汉字。这一识字理念对现今识字教材编撰的价值也不可小觑。长期以来,我国语文课程标准都十分注重对识字数量的规定,而对识字质量缺少要求与指导,致使小学识字教材中非高频字出现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阅读效果。如1992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识字量的规定是2500个,事实上其中只有1700个左右是高频字。如此看来,今后的识字教材实在应从王筠识字教学理念中获得启示。
二、“先纯体字后合体字”的识字顺序
从结构上,汉字分独体字和合体字两种。纯体字也就是独体字,以笔画为直接单位,简单几笔组成一个完整汉字。合体字则由偏旁部首和独体字按一定结构规律组合而成。“从整个汉字辨认的过程来看,儿童识字首先辨认的是字形的大致轮廓,其多为独体字。然后才是组成部分,其字多为合体字。”
纯体字多为象形字、指事字。《教童子法》开篇就提出“先取象形指事纯体字教之”。“视而可识则近乎象形,察而见义多是指事。”象形是借形为象,而成字体,指事是以符代形,为象形之简化。合体字多为会意字和形声字。“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難讲者。”显然,王筠《文字蒙求》的识字编撰顺序是先纯体字后合体字。具体体现为卷一象形,先集中识字264个,让儿童对汉字有初步的了解,简单识记。卷二指事字较少,仅120多个,此时儿童在象形字的基础上,识记此一百多个字,自是不困难。到第三卷的会意字,虽然猛然增到1200多个,但有前面两种字作基础,蒙童也基本可顺利掌握。
《文字蒙求》先纯体字后合体字的识字理念,对蒙童心理特征的把握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教育家的看法。王筠开始观照儿童感知汉字字形能力的发展规律,将识字内容进行了循序渐进的编排,符合由易到难、由简到繁、从具体到抽象的学习规律。
三、“好字养德”的识字教育思想
识字教学一个重要内容是指导写字。学生能否正确规范地书写所学汉字,是检验识字效果的一个重要标准。清代蒙学教育对于书写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他们认为一个人的书写,要从小抓起。清人张行简在《塾中琐言》云:“馆徒学书,与其判之于成幅之后,空劳改窜,曷若督之于把笔之际,立予纠绳。”至于儿童开始学习写字的时间,也不是越早越好。王筠认为:“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
值得关注的是,清人在强调蒙童掌握一定书写技巧的同时,十分注重写字的“正心”。如胡渊的《蒙养诗教》中云:“拈毫运用惟虚掌,先字操持必正心。心正自然令笔正,此言珍重胜南金。”万斛泉的《童蒙须知韵语》中云:“双钩与悬腕,搦管求坚劲。柳公有遗言,心正则笔正。”至于临帖什么字体,王筠认为:“学则学《玄秘塔》《臧公碑》……不可学赵,他字有媚骨,所以受元聘。犹之近人作七言转韵古诗,对偶工整,平仄谐和,不以为病,一韵到底者乃忌之,所藉口者王右丞也。然此人亦有媚骨,进身则以《郁轮袍》,国破即降安禄山。虽唐人不讲节义,然李、杜、高、韦,何家不可学?必学降人?”不难看出,王筠十分关注蒙童识字写字过程中“德”的教育,重视“好字”对蒙童潜移默化的人格影响。受此论影响,清代蒙学读物中广受欢迎的是欧体字。李光明庄是晚清有名的私家刻坊,在所刻《三字经注解备要》的书前著录中印有类似书目推荐的字样,其中“欧体三字经六十文,欧体百家姓二十六文,欧体千字文四十二文,欧体治家格言三十文”。
王筠这一“好字养德”的识字教育思想对当前识字教学也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当今时代是硬笔代替毛笔、键盘代替手写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朴素书写在工作生活中日益弱化。受此潮流冲击,学校的识字教学也呈现出重认识轻书写的倾向,教师对学生写字姿势的指导严重缺失,导致学生握笔姿势大多不够正确,坐姿也不够端正。在写字指导过程中,一味追求应试需要的默写字形的准确性,缺少对学生进行品德与人格的教育。“字如其人”“写方方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等识字教育思想的的确确应该得以真正落实与强化。
四、“得有乐趣”的识字教学原则
蒙童年纪小,无意注意和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而汉字是一种抽象的语言符号,想要让蒙童在识字过程中保持较长时间的注意力,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激发儿童的识字兴趣。
王筠在《教童子法》中强调:“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具体到识字教学,他认为只教辨字形读字音,却不讲构字几何,也不阐释字义,识字无异于嚼蜡,年纪小小的蒙童实在难以下咽。因此他提出教蒙童识字必须重视释义。他还认为蒙童的思维自成一界,字义讲解不可依循常规,需要“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对字义的讲解要适合儿童的理解能力,不能过于烦琐复杂:要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对字义的讲解不可一味地按照书面语解释,人为增大难度。例如“月”,《说文解字》:“阙也。大阴之精。象形。凡月之属皆从月。”《文字蒙求》说解:“月圆时少,阙时多,且让日,故作上下弦时形也。中一笔本是地影,辞藻家所谓顾兔桂树也。”王筠对“月”的这一解释可谓趣味横生:月圆时少,阙时多,所以是弯弯形,“月”中两笔那是嫦娥的玉兔和月宫的桂树。说解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不仅能使学生对训释更容易记忆,且在识字中增强了许多的趣味。
王筠在强调兴趣识字的同时,还明确提出蒙童的注意力时间有限,识字教学时要让儿童的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交替转换,切不可一直让孩童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王筠“得有乐趣”的识字教学理论对当前的识字教学也颇有借鉴意义。当前的识字教学,许多老师不注意引导学生探究字理,一味强调机械重复,抑或对字义牵强解读,实在是误人子弟。
五、教“日常之物”的识字教学内容
文字是代表事物的符号,认识文字的终极目的是通过阅读认识生活,通过写作表达生活。因此,识字教学必须结合字义的教学,让学生将汉字与实际生活中的事物联系起来。
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提出:“讲又不必尽说正义”,“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文字蒙求》卷一开篇即说道:“字因事造,而事由物起。牛羊,物也,牟芈则事也;艸木,物也,出乇贩卤皆事也。归根到底,字还是有物而生,象形更是这样。”他运用生活中常见的实物教以具体感知,主张识字与生活实物形象的配合,让儿童可观可感可触可碰。他认为,汉字最初就是根据日常具体事物而造。因此,《文字蒙求》在选字方面注意选择那些反映日常生活之物的汉字,对其释义也取之日常,或是加入常识性的解答。例如“雨”:“一象天,则地气上腾也,冂则天气下降也,阴阳合而后雨,点则雨形。”“火”:“火之行。上锐下阔,其点则火星蹦出者也。”“斤”:“斫木之器。盖即今之锛也。”而对“鼠”的说解更是簡洁直观:“此字当横看,大首伏身曳尾。”
对于那些意义抽象的汉字,王筠则以具体实例比较的方法来告知。“如识‘上‘下二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上”“下”二字均无具体实物,怎样让童子快速理解记忆其字形字义?王筠以生活中具体事物的摆放来告知学生。
王筠教“日常之物”的识字教学理念,对后来识字教学教材的编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的识字课本为儿童选择汉字都充分吸收了这一思想。
六、“打包”与“裁纸”的识字教学方法
儿童在识字过程中,遗忘现象是很突出的。因此,巩固所识汉字对识字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筠针对遗忘这一学习现象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打包识字。“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打包识字”类似现代的高频复现,它强调识字的累积和复习,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规律。其第一遍是初识生字,总体有个印象,第二遍回读复看生字。在读书过程中见到生字,摘抄生字五十个作一包,亦效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彻底掌握所识汉字。
打包识字的教学方法,不仅遵循了儿童非一次性领会的学习心理,而且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初识生字字形,识记生字字音,接着对孩童阐释字义,“解至三遍”,教至孩童都已了解,最后令其自解。其过程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反复再现,以此加深记忆,巩固夯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浆,不至滑过。”
反观当前识字教学,很难见到有对生字除课本印刷楷体之外其他字体的讲解,学生对所习之字通常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也是我们在识字教学中所要反思的。此外,王筠在识字教学中注重多种识字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也值得我们借鉴。
作为清代识字教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筠的识字教学理论内涵丰富,形成了独特的识字教学理论体系。新时期识字教学改革日新月异,识字教学理论日益发展,但对以王筠为代表的传统识字教学理论进行深入开掘与有效梳理,并在教学中吸收借鉴,仍然是促进识字教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