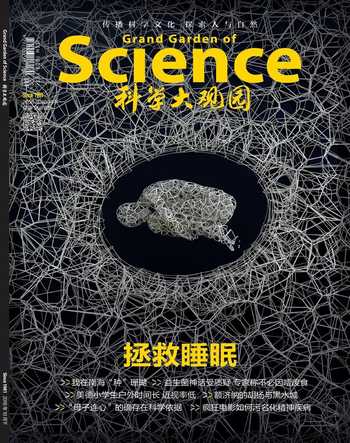人们缘何对金发趋之若鹜
在美国打开电视或是社交軟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清一色的金发——事实上,自然产生的并不常见,全世界只有2%的人生来是一头金发。
打开美国电视或者刷一下Instagram,不难发现,无论是政治家、新闻评论员、名流,还是社交媒体红人,几乎清一色都是金发。碧昂丝、爱莉安娜·格兰德、金·卡戴珊和贾斯汀·比伯的黑发当中也或多或少地有一些金色点缀。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首名女性希拉里·克林顿把头发染成了金色。仅就特朗普政府团队而言,总统自己、女儿伊万卡·特朗普、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国土安全部长、教育部长、小企业管理局局长都是一头金发——唯有其公关总监霍普·希克斯的深色头发显得独树一帜。
金发在美国这么火,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2016年总统大选来临之际,著有《公民:一部美式抒情诗》的诗人克劳蒂亚·兰金和摄影师、电影制片人约翰·卢卡斯率先对金发缘何如此流行进行了探究——特别是刻意染的金发。一名黑人教授曾向在耶鲁大学教授诗学的兰金发问,希望知道她对黑人学生把自己头发漂白这类现象的看法。兰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当我开始考察这一现象时,金发的风靡程度让我觉得十分有意思。”兰金告诉我,并提到了希拉里和特朗普这两个例子,“从亚裔男性到白人女性,放眼望去几乎所有人都在染发。”借助一部iPhone和录音笔,兰金和卢卡斯花了两年时间,拍摄和访问了100余名曾染过金发的人,他们来自各种各样的地方和群体——伦敦、纽约、共和党全国大会、非裔朋克、餐厅和博物馆。
这些照片和访谈在布鲁克林的先锋艺术中心新近举办的“贴上邮票”展览上展出,它属于种族想象学会为研究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之一。尽管艺术家们不会要求受访人表明其种族或族群背景,但“贴上邮票”的访谈对象的确具有丰富多元的背景。展览包括一系列的照片,其中有些经过了缩小处理,以适应邮票的篇幅,配有来自实地访谈的录音,橱窗上还相应地列出了金发染料的成分表。邮票上的影像内容是各种人工染成的金发特写,常常与染发者乌黑的发根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自然产生的金发并不常见:据估计全世界人口中只有2%是生来就有一头金发的——在美国白人当中也只有5%左右。金发是基因突变的产物,在北欧人身上较为常见,但有少量的澳洲原住民、北非人和亚洲人也会如此。
即便如此,各大陆的人们多年以来仍以柠檬汁、双氧水和指甲花染料来为自己染发。黄金时代的著名演员珍·哈露在1930年代曾被誉为拥有一头“白金般秀发”的新星,她甚至同时动用了漂白剂、双氧水、氨水和力士的肥皂渣来实现发色的渐变。1956年,伊卡璐又首次推出了家用染发套装,号称可以“提亮、染色、修护与洗发一步到位”,染金发就此进入了美国的大众生活。
就某人为何选择金发而言,可以提出一大堆理由。对“贴上邮票”里的受访者们来说,它是一种掩盖头发花白,让自己更年轻,获得更好的待遇,变得更好看,或者让人更能做自己的途径:
金发构成了一种颇为复杂的自我表达形式。
它可以标示年轻、美丽、特权与从众性。
话说回来,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兰金没有提醒的话,受访者基本不会注意到白人和金发之间的紧密关联。“我认为,身为美国人而言,一定程度上讲,白人和人民这两个词对我们来说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兰金说,“这样一来,当人们想起金发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人民的发色,亦即那些有价值的人群。但他们未能理解这种价值是跟白人联系在一起的。”
以此观之,金发就构成了一种颇为复杂的自我表达形式。它可以标示年轻、美丽、特权与从众性。但也能代表叛逆、独立以及获得关注和尊重的欲望。这一选择既有彰显个性的成分,又与社会教给人们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交织。
兰金和卢卡斯专门为此提出了一个术语:共谋性自由。
“就算你自由地选择了染金发,它仍与白人所推崇的价值……密不可分,”兰金说道,“这么一来,如果你不是白人的话,到头来就不由自主地沉迷其中了,受困于自我施加的压迫,而不论你认为自己是否有自由这么做。”
不过,说起非白人群体对染金发的推崇,疯狂“漂白”倒未必是对种族的拒斥:它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所有权宣示,并不真正指向任何越轨行为,而是企图拥有一些没法被拥有的东西。
“我认为,染金发起初可能是一种同化的形式。金发令人更容易被社会接纳,”一名男子在展览的访谈中对兰金说,“我觉得现在的有色人种群体不再这么考虑问题了,他们染金发只是单纯因为自己想染而已。”或者再考虑一下演员葛雷塔·李的情况,在《纽约时报》近期某篇有关亚裔女性染金发潮流的文章中,她接受了时尚作家安德莉亚·程的访谈,并表示染金发就是一种单纯的宣示:“我在这里。请关注我。看见我。”
兰金和卢卡斯表示,他们在展览中使用邮票,是希望借它来表明金发乃是某种形式的通货、一种达到某一新终点的途径——得到接纳、承认、好评和自我感。“试想,当你想把某个东西寄到某处的时候,是不是会贴上一张邮票?你想要抵达某个全新的去处。你自己又怎么看呢?你觉得自己想要去到什么地方?”卢卡斯指出,归根结底,“没贴邮票的信封是哪里都去不了的。”
兰金和卢卡斯的展览,当然不是要公开反对人们染金发或者主张人们必须因循守旧。但“贴上邮票”,的确也邀请观众展开追问:为什么金发几乎无处不在、人人趋之若鹜?它能为眼下热门的有关种族、归属和特权的广泛讨论,提供些什么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