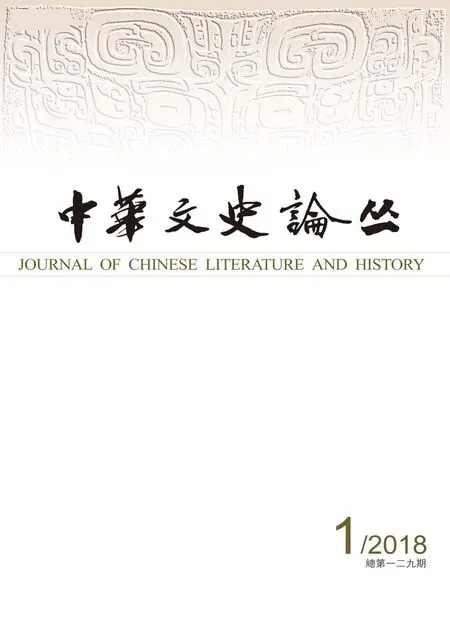“三皇”與三皇時代考論
趙逵夫
一 簡單的歷史回顧
(一) 問題的提
1936年,顧頡剛、楊向奎兩位先生在《燕京學報》專號之八發表了《三皇考》一文。這其實是一部近二十萬字的專著。論文認爲“皇”字在戰國以前只當形容詞和副詞用,訓“美”、訓“大”,慣於用來形容天神,偶然也用爲動詞,到戰國之末纔人化;認爲“三皇五帝”爲戰國秦漢間人所僞造,對蒙文通等“悍然斷三皇五帝爲古無其人”、“悍然斷凡稱‘三皇五帝’的都是晚出之書、誕妄之説”的觀點,大爲稱贊。此前的1929年,《史學雜誌》曾發表蒙文通、繆鳳林先生的兩封信,總題爲《三皇五帝説探源》。蒙先生以爲“戰國之初惟説‘三王’,及於中葉乃言‘五帝’,及於秦世乃言‘三皇’”;繆先生以爲“三皇之説蓋起於道家理想之世的具體化”。*《三皇考》、《三皇五帝説探源》,並見《古史辨》第七册中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頁20—282,314—337。蒙、繆兩文實上承劉恕、崔述、康有爲、崔適諸家,*劉恕説見其《通鑑外紀》卷一,言“《周禮》經周末秦漢增損,僞妄尤多”,“秦以前諸儒或言五帝,猶不及三皇”,四部叢刊縮印本,48册,頁17下,19上。崔述説見其《補上古考信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以爲“皇乃尊大之稱”(頁1),言“世又傳倉頡始作書契,然則書契之起於羲農以後,必也;羲農以前未有書契,所謂‘三皇十紀’帝王之名號,後人何由知之?”(頁4)康有爲之説見其《新學僞經考》,其中《史記經説足證僞經考》中説:“劉歆欲臆造三皇,變亂五帝之説以與今文家爲難”,《康有爲全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12。崔適之説見其《春秋復始》,亦以爲“三皇”之説係劉歆所僞造。下啓顧頡剛、楊向奎二位之宏論。
顧頡剛、楊向奎兩先生的論文發表三年之後,吕思勉先生有《三皇五帝考》,*與顧、楊之《三皇考》並收於《古史辨》第七册中編。該文對相關之古帝傳説有所條理,是在總結、凝練以上論著基礎上寫成,運用文獻方面注意時代之先後,考慮到其相互關係等方面,顯得紮實可信。然而論“三皇之異説有六”,第一條所列舉爲緯書《河圖》、《三五曆》,第二條所舉爲《史記·秦始皇本紀》,第三條所舉爲《尚書大傳》,第四條所舉爲《白虎通》,第五條所舉《春秋緯》之《運斗樞》、《元命苞》,第六條所舉爲皇甫謐《帝王世紀》,給人的印象仍然是“三皇”之説産生於漢代以後。而且除第二條、第六條外全爲緯書,緯書形成於西漢之末至東漢大盛。第二條是漢代的書,第六條則爲晉代著作。文中説:“然皇、帝二名,雖出先秦之世,究爲後起之説。”“戰國之世,列國皆稱王,關涉較多,强弱漸判,乃謀立一更尊於王之號。於是借天神之名而稱之曰帝。”“然論古史者,猶不以是爲已足也。乃不從尊卑著想,而從先後立義,據始王天下之義,造一皇字,而三皇之名立焉。”*吕思勉《三皇五帝考》,《古史辨》七中編,頁343,344。仍以爲“三皇”之説爲秦漢以後人所造。
以上這些説法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大。近二十多年中有著名史學家還説:“人間歷史上的‘五帝説’已盛行後,直至戰國末季,還没出現人間歷史上的‘三皇説’。可是天神的三皇説在戰國末季卻出現了。而到戰國結束時期寫出的《吕氏春秋》一書中,開始出現人間歷史上的‘三皇’一詞,但没有具體的人名。可知這顯然是受神秘的‘三、五,三、五’,這套數字的概念影響下,率意地順口説成的,所以舉不出人名。也有不可免的因素是,人們好古,喜歡層累地向上追加古史,在已習慣於五帝説之後,又要向上追溯,以致三皇説終於不免産生出來了。”*劉起釪《幾次組合紛紜錯雜的“三皇五帝”》。該文又云:“很顯然,最初的(轉下頁)所以,對這個問題不能不認真加以探討。*(接上頁)三皇是指天神,與五帝初爲五方帝之稱天神並無二致。”見《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06,107。又,20世紀九十年代很有影響的學者李衡眉在《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所刊《三皇五帝傳説及其在中國史前史中的定位》一文説:“早在本世紀初,已故顧頡剛先生即已指出,三皇五帝之説,實非華夏族上古神話中所固有,其産生當在戰國秦漢之際。此時期正當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化劇變的大時代。這一看法,頗有見地。”頁179—190。
(二) 紛亂中科學思想指導下的思考
1947年徐炳昶、蘇秉琦二位先生合寫《試論傳統材料的整理與傳説時代的研究》一文,刊《史學集刊》第五期。論文對傳説時代研究文獻的類型、傳説材料的整理、傳説時代研究的基本方法與原則、傳説中的史實、傳説時代的歷史等問題都有系統而精闢的論述。如關於傳説材料的整理,根據傳説的本質或來源分爲“原生的”、“再生的”兩類;又根據其價值分爲三等: 第一等是直接引用的,保存於古代社會間的古代傳説或遺迹的材料;第二等是根據舊説或兼采異説而有所損益,或係綜合整理的著述;第三等是改竄舊説,另成系統,或者材料晚,與舊説抵觸者,或來源不明,或根據再生傳説記述等。同時,又按材料的内容與寫定的先後,分爲三期: 第一期包括商周到戰國前期的作品,第二期包括戰國後期到西漢末的作品,第三期爲東漢以後的作品。徐旭生(炳昶)與蘇秉琦合寫的這篇論文雖然刊於七十年以前,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過去的百年中關於上古史的很多論著對有關材料不作科學的分析,不考慮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及産生的遲早,只着眼於相互間的抵觸與差異;不考慮先秦文獻流傳中的複雜性,而從中提取個别的詞語、材料來確定整個文獻産生的時代;不考慮先秦文獻存留至今日的是極少數,一些反映遠古歷史的文獻,春秋戰國時人尚能看到而今天已不可能看到,以默證爲據否定一些傳説;不考慮一些遠古時口傳材料同遺迹、實物、圖騰符號、原始文字、岩畫、地畫及陶器、銅器上圖案的相輔流傳,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事件要素的實際;不考慮當時還有些禮儀制度和古老的習俗尚可作爲推斷遠古歷史的參考等等,而以所論遥遠渺茫完全加以否定。總之,只在尋找各説的牴牾之處,只在發現矛盾,不是從中發現反映歷史真實的線索與材料,不是探究相關材料之間的關係並排除後人所附加的東西,而是不分先後一鍋煮,淡化、淹没了一些較早的文獻。
儒家經典中只有《周禮》、《易傳》和《荀子》中提到“三皇”及燧人、伏羲、神農,其他都没有涉及。這是因爲《周禮》中所包含一些較早的文獻,並非孔子所編定,而其成書又在孔子之後。荀況的思想已同正統儒家思孟學派的思想有了一定距離。儒家强調禮制,與道家抨擊禮制、追求小國寡民、保持人之常性的思想對立,故一般不提三皇與三皇之世,而是借堯舜以説盛世。道家以三皇之世“教化而不誅”,無法權、禮制的約束,人民飽食暖衣而不知其他,認爲是人民所嚮往的理想社會,常借三皇之世的“無爲之治”來反對三王(夏、商、周)五霸以來將人民推入長期的戰爭災難,反對專制者爲維護自己的統治所標榜的種種説教,故多言及“三皇”。法家、兵家雖也重禮制法規,但不似儒家只借禹、湯、文、武論禮制、言大義,所以在論及遠古社會時也會提到三皇、三皇氏、三皇之世。過去有的學者斷言“凡稱‘三皇五帝’的都是晚出之書”,*見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三皇考·童序》(第三册)中轉述劉恕語。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2。是違背事實的,也没有完全弄清儒、道、法、兵各家社會政治理論上的差異。
王玉哲先生在其《中華遠古史》第一章末尾説的一段話很有道理:“我們對這些古籍流傳下來的遠古傳説,哪怕是帶有神話性質的傳説,也不能棄之不理。我們既不能盲目地信爲實録,也不能全部斥之爲荒誕不經。有巢、燧人、伏羲、神農、黄帝等傳説均出現於戰國……不過這些古代傳説大都多少有些口耳相傳的依據,不會完全是無根的向壁虚造。”*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8。我認爲我們對傳説中的“三皇五帝”應該抱這樣的態度,進行認真的研究。對王玉哲先生的説法要作一點補充的是: 提到三皇及其時代的《周書》、《國語》、《左傳》、《太公伏符陰謀》、《周禮》、《六韜》、《管子》、《易·繫辭》、《世本》等有的成書於春秋時代,而加進了一些較遲的材料;有的雖成書於戰國,但其中包含有較早的材料。至少這幾種書中關於燧人、伏羲、神農傳説的記載應是春秋以前所傳。這在古文獻更深、更隱蔽的文化因素中可以得到印證。
新時期出土的大量文獻證明,以往被定爲僞書的一些典籍並不僞;對漢字産生歷史的新的認識,史前考古取得的成就以及國外口傳史理論的引入,都使我們覺得關於“三皇”的問題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近十來年中有幾篇談“三皇五帝”或“三皇”的論文問世,有的在文獻的鈎稽與運用上尚有缺憾,有的在理論與方法上不是很清晰,我因就此舊文加以增訂發表,願向學界朋友請益商討。
二 如何看待春秋戰國時代關於“三皇”的傳説
(一) 先秦文獻關於三皇的記載及三皇的歷史順序
《周禮·春官·宗伯》中説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彭林整理《周禮注疏》卷三一,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027。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索隱改補皆非》條云:“《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十七史商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90。關於《周禮》一書,過去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劉歆僞托。在疑古思潮影響之下,大部分人不相信它的文獻價值。張亞初、劉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據近五百件青銅器銘文中的近九百條官制材料,與《周禮》一一對比,認爲“《周禮》在主要内容上,與西周銘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頗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則《周禮》一書雖爲春秋戰國時人所編訂,但保留一些西周文獻是可以肯定的。目前發現的西周金文中無“外史”,但有“内史”、“中史”。則本有外史可以肯定,只是出土文獻中尚未見到而已。夏商西周共一千三百年,各方面事情無數,出土的文字資料纔有多少?所以,《周禮》關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的説法,不能輕易否定。春秋以前人不僅相信有五帝,也相信五帝以前有三皇。
《太平御覽》卷七六引《六韜》云:“至於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舉“三皇”之後兩位。《六韜》之書實爲姜子牙的《太公言》、《太公謀》、《太公兵》删削而成,其中加入了一些春秋戰國間有關軍事的文字,但也包含有流傳很久的材料。《太平御覽》卷七六又引《太公伏符陰謀》曰:
武王曰:“三皇之治,母禮義而民利之,何也?”太公曰:“三皇之時,近之則利,去之則病,所謂上聖神德而治,其次教而化之。近聖賞罰之。”*《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356上。
則傳世太公之書中有關於“三皇”的内容可以無疑。且兩處所載,意思相合。惟書名或作此,或作彼,不同編抄之本同時流傳,亦古書流傳中常見的現象。
《管子·輕重戊》云:
虙戲作,造六法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黄帝(燧人)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見黎翔鳳《管子校注·輕重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507。“燧人”原作“黄帝”。郭沫若《管子集校》引陳立、張佩綸、聞一多之説俱以爲“燧人”之誤。下文始言“黄帝之王,童山竭澤”,則此處當爲“燧人”無疑。今據以改正。法,原作“峜”。洪頤煊云:“‘峜’當作‘佱’。‘佱’,古文‘法’字。”郭沫若《管子集校》引莊述祖説同(莊氏又以爲“佱”可通“政”)。又引聞一多之説,引《説文》等補證爲“法”字之説。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99—402。
提到伏羲(亦作虙羲)、神農、燧人,並對他們的功業有概括的論述。《管子·揆度》云: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二三,頁1371。
據這段文字,《管子》中實以燧人爲“三皇”之首。則《輕重》篇先説伏羲,是從論輕重的角度,以事爲序,非以時爲序。
《易·繫辭下》也是只提到“三皇”中的後兩位,先説“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然後説“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最後説“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周易正義》卷八,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50下,351下,352上。
《莊子·繕性》: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黄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又《盜跖》:
神農之世……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551,995。
這也是以燧人、伏羲、神農爲序,神農下連黄帝。*《莊子·至樂》述孔子就顔回之齊答子貢語:“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頁620。雖因所論事不及伏羲,而此二者次序則順。又《莊子·盜跖》在有巢氏與神農之間有“知生之民”,言其“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頁995。“積薪而煬之”乃言會點火取暖,應指燧人氏而言。《韓非子·五蠹》論上古之世,“使王天下”,*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085。也以燧人氏爲首。
《尚書序》孔穎達疏云: 倉頡,“慎到云: 在庖犧之前”。*黄懷信整理《尚書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孔穎達列數説而慎到之説在最末,説明並不贊成慎到之説。孔氏所見慎到之書是否有竄簡之類,也難説。但無論怎樣,《慎子》一書言及庖犧是没有問題的。又,明代以來流行的萬曆間人慎懋賞編《慎子》,其《内篇》有云:“昔宓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曰: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慎子内外篇》,四部叢刊縮印本,94册,頁3上。雖然慎懋賞在《自敍》中自言“爲輯其可知者”,然而多雜取他書之文以充篇幅,即如上引後一段,與《易·繫辭下》的一段文字大同小異,故本文不以爲據。
《荀子·正論》云:“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37。這是由後向前推而言之(“太皞”指伏羲)。總的來説,先秦典籍中雖然個别文獻中由於引述角度上的原因順序有所變化,但可以看出當時普遍的看法“三皇”是以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爲序的。
《禮記正義》卷一孔穎達疏引《易緯·通卦驗》“遂皇始出,握機矩”之語,注:“遂皇,謂遂人,在伏羲前。”*吕友仁整理《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據《隋書·經籍志一》,鄭玄注《易緯》。*《隋書》卷三二,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940。鄭玄是東漢時經學大師,博學多識,故於三皇的順序承秦漢以前舊説。
漢初伏生的門徒張生、歐陽生據伏生説所著《尚書大傳》卷五云:
遂火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托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托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疏,故托農皇於地。*《尚書大傳》,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頁45;又見四部叢刊縮印本,11册,頁59下。《史記·秦始皇本紀》“人皇”作“泰皇”,“泰”,蓋由“太”而來,“太”又由“人”而誤成。
這裏“三皇”的次序,同先秦所傳一致,只是根據漢代天命論中的“天、地、人”之説將三皇分别托之於“天、地、人”,爲唐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中“天皇、地皇、人皇”説提供了依據。另外,所謂“火,太陽也”之説,與上古所傳“鑽燧生火”之説並不相合,同樣是加進了漢人的觀念,由東漢時以“祝融”代替“三皇”中燧人氏而來。故其説與《風俗通》引《含文嘉》、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等緯書之説同。*參《風俗通義·三皇》引《春秋運斗樞》説:“伏羲、女娲、神農,是三皇也。”吴樹平《風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0。《孝經援神契》宋均注:“以伏羲、神農、遂人爲三皇。”《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993。譙周《古史考》受此影響,所説與之相同。《白虎通》卷上《號》云:“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49。與上古所傳一致,惟順序上將燧人置於最後,可能是當時文獻中關於伏羲、神農的記述較多,而關於燧人的記述較少,印象較爲模糊的原因。下面接着説:“或曰: 伏羲、神農、祝融也。”這明顯是受了《尚書大傳》的誤導。
其他異説也見於漢代緯書及魏晉以後之書。緯書《尚書中候敕省圖》、《春秋元命苞》、《春秋運斗樞》皆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無燧人而有女媧,東漢高誘注《吕氏春秋·用衆》、唐司馬貞補《三皇本紀》等從之,然而與古代所傳女媧與伏羲氏的關係相矛盾。因爲古文獻中言女媧與伏羲俱爲風姓,而且有的書中説女媧是承伏羲而王,“承庖犧(伏羲)制度”,是屬於伏羲氏的。*《帝王世紀》云:“女媧氏代立,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女媧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楊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3。《春秋命曆序》以“遂皇、伏羲、女媧”爲三皇,*《緯書集成》,頁880。這裏增加了女媧而去掉了神農。可見即使緯書中也是自相矛盾的。一個是去燧人而增女媧,伏羲、神農之順序未變;一個是去神農而增女媧,燧人、伏羲的順序未變。將女媧加進三皇之中,很可能與吕后稱制之時一些方士、文人爲迎合輿論需要而造作有關,後被造緯書之方士所采用。緯書中很多内容來自秦漢間方士之説,所以也不是没有這個可能。司馬貞補《三皇本紀》重拾此説,則應與迎合武則天稱帝時的宣傳需要有關。
燧人氏、神農氏在先秦很多文獻中都提到,前者反映了中國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磨製石器過程中發明了人工取火的事實,後者反映了中國母系氏族社會晚期很長的一段時間爲原始農業時期。在這兩個漫長的歷史階段中,必然會出現較傑出的氏族、聚落首領。漢唐時有的書中去掉燧人氏或神農氏,是毫無依據的,是缺乏歷史見識的行爲。
《禮稽命徵》又以伏羲、神農、黄帝爲三皇,魏晉以後僞《孔傳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馮翼注《世本》及王嘉的《拾遺記》承其説,這與魏晉以後朝代更迭中道教流行、方士神化黄帝、不斷擡高黄帝的地位有關。*漢代緯書中也有同先秦時期較早文獻所載大體一致者,如《禮含文嘉》以“虙戲、燧人、神農謂之三皇”,《緯書集成》,頁494。至於劉恕《通鑑外紀·引》以包犧、神農、黄帝爲三皇,*《通鑑外紀·引》以包犧、神農、黄帝爲三皇,《顧頡剛古史論文集·三皇考·童序》中稱引劉恕的話,以伏羲、神農、共工爲三皇(頁9)。特此説明。毫無根據,可以不論。
一些論著或工具書不論時代先後、不加分析地羅列出五六種或七八種説法,而不是探究其産生的先後、主次與相互關係,往往遺漏一些時代較早的記述,徒爲亂人耳目,並無意義,這裏不再一一羅列。
(二) 關於三皇歷史的承傳
《莊子·天運》“孔子西遊於衞”一節載春秋時魯太師師金之語: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可見在先秦時代對三皇、五帝時期社會生活的規則,所謂“禮義法度”等的大概情況、大體的區别,人們還是知道一些的。以爲三皇之間、五帝之間、五帝與三皇之間,禮儀、法度、習俗並不完全相同。*《莊子集釋·天運》,頁514。下文“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節載子貢之語云:“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頁526)此與上文之論“三皇五帝”無關,當作“五帝三王”,乃承上而誤。又有因“三王”在前而誤改“王”爲“皇”者,皆不可從。
《文子·道原》云: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王利器《文子疏義》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
戰國之時人們認爲三皇時代的領導管理行爲完全是順應自然、依賴自然,與人們的生存活動合爲一體。當時肯定有許多較具體的傳説存在。《文子》的《精誠》、《九守》、《道德》、《自然》等篇還提到“三皇五帝”。《吕氏春秋》的《貴公》、《用衆》、《禁塞》、《孝行》也都提到“三皇五帝”。
以上所列各書中均未言“三皇”具體所指,聯繫前面所引《六韜》、《管子》、《易·繫辭》、《莊子》、《文子》、《慎子》、《荀子》等書及下文所引《世本》、《尸子》、《韓非子》文字可知,這是因爲“三皇”具體所指爲當時人所共知,不必每次提及都得一一列舉。
可能很多人會説: 數千年前的社會現象,靠口耳相傳,可靠嗎?首先,我們認爲,根據傳播學的規律,歷史事件流傳時間越久,越概括而凝練,一些枝葉會不斷失去,一些次要事件的情節、過程會集中到主要事件上去,一些次要人物的事迹、事件會集中到主要人物身上去,慢慢地只有主幹而没有情節和過程。對於這些自古相傳的極其概括的事件,具有代表性、標志性的人物,我們不能輕易否定。
其次,在文字産生以前,人們的羣體記憶力要比我們想象的强得多。因爲當時生活内容簡單,歷史單純,人們會設法把自己氏族、部落的重大歷史事件傳下去。比如上古文獻中常看到的韻語,就可以使傳説不易走樣(先秦兵書中多韻語,就是爲了便於記憶);聯繫相關地點、遺迹編成故事,代代相傳(如關於燧人氏察五木以發明鑽燧取火的事等等),在有關遺址立石,刻上圖騰標志,在陶器、玉器、石器上刻畫上有關圖畫等。在近幾十年發現的陶器、玉器、銅器上還發現了一些勾畫字符及圖像,今人雖不能解,但上古之人是知道它們所包含的意思的。
《説文·古部》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頁50下。“識”即記的意思。人類從很早起就根據生理特徵來進行社會的分工。盲人的記憶力特强,因而瞽史、矇瞍均前後相承以講誦歷史。另外,上古時保存文獻者往往是代代相承,也有利於保存和解説,因爲還有些世代相傳的遺迹、遺物和刻在木、石、陶器上的圖案、符號、文字記録,也由這些人看管和解説。這些東西起着提示要點、保持記憶的作用。《世本·作篇》云:“沮誦、倉頡作書。”*宋衷注《世本八種·張澍稡集補注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9—11。“沮誦”,即詛誦,爲執掌和講誦歷史與文獻者。“沮”爲“詛”之通假。“詛”之“咒詛”、“盟誓”二義,均包含有反覆念誦之義。《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吕友仁整理《禮記正義》卷三九,頁1180。這反映着遠古口傳與書傳相輔而行的事實。《莊子·大宗師》寫南伯子蔡問女偊,何以知“道”。女偊曰:
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莊子集釋》卷三上,頁256。
反映了遠古時代有專職口傳史事的人員。所述人名“副墨”即是“與書寫文字相輔而行”的意思;“洛誦”、“於謳”、“瞻明”(上古盲人多以“明”爲名)之稱,也同職守有關。這些人專門向氏族、聚落成員及後來之王侯貴族講誦古史、古事、古言、古禮。由此可見,上古時代是有一套傳承歷史的體系的。
再次,中國初期的文字符號在距今六千多年前已經産生。這個時間相當於神農時代。以前學者們認爲中國文字從殷商時代開始。唐蘭先生1933年爲商承祚《殷契佚存》作的序中,提出安特生《甘肅考古記》所載辛店期陶器上的彩繪符號是一種較古的文字,與商周文字屬於同一系統。他於1934年問世的《古文字學導論》中重申此看法,推斷“假定中國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備,至遲也在五—六千年以前”。*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頁79—80。近幾十年在全國很多地方出土的大量刻畫符號和原始文字,證實了唐先生的論斷。臺灣學者李孝定先生自1969年以來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由已發現的陶文研究漢字的起源;大陸學者郭沫若、于省吾先生也於1973年、1974年先後發表論文,認爲中國文字從仰韶發現的刻畫符號算起,已有六千多年的歷史。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論著更多。當時的原始文字有可能多寫在木板、樹皮、竹片之類較易書寫的東西上,這些東西不可能保存至今日,我們只能在陶器上看到一些標識一類的簡單文字或符號(郭沫若以爲屬花押、族徽、物勒工名之類)。即使是刻畫符號和標識類原始文字,也可以記下一些很關鍵的内容(如族名、地名、大事、特定事物的數量等)。它在相當長的時間中保持着口傳史料要素上的準確性。
第四,直至春秋時代,尚存有比《尚書》更早的遠古文獻。《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説左子倚相:“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皆古書名。”*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340。《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云:
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説,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黄懷信整理《尚書正義》卷一,頁2,458。
從炎黄時代到春秋末年共兩千五百多年,到今天也就留下了《尚書》、《周易》、《詩經》、《春秋》、《左氏春秋》、《國語》、《逸周書》等不到十部書。僅西周滅亡、春秋列國數百年的戰火和秦始皇的焚書、項羽的燒咸陽宫,上古文獻的損失已可想而知。那麽,上古文獻當中留下來的一些歷史文化信息,我們應極其珍視,不能輕易否定。
近幾十年,考古工作者、歷史學家研究的結果,證明中國史前期,即在炎黄以前確實存在磨製石器及發明人工取火、經濟上以初期耕耜和漁獵爲主的段落,以原始農業和畜牧爲主的階段及初步發展的農業爲主的階段這樣的三個歷史段落。如果依傳統的説法認爲“三皇”是指五帝之前的三個帝王,自然是有問題的;但如果説戰國之末纔出現籠統的“三皇”之稱,尚未編造出“三皇”具體所指,不但不符合文獻所反映的事實,也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中國史前階段所經歷的社會狀況缺乏足够的認識。
(三) 對有關文獻的認識與評價
過去關於先秦典籍的認定大體采取“有罪推論”的辦法,只要有一點問題或疑點,便判定全書爲“僞書”。實際上先秦典籍的成書與流傳情況與秦漢以後大不相同。比如前面提到的《管子·輕重戊》,在上一世紀中,學者們或認爲“漢文景間所作”,*王國維《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觀堂集林(附别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156—1158。或言“並漢武、昭時理財家作”,*羅根澤《管子探源》,《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489—499。甚至主張王莽時所作,*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總之,爲漢代所成,幾成定論。但五十多年來,學者們對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論斷。容肇祖先生在五十年代有《駁馬非百〈關於管子輕重篇的著作年代問題〉》,肯定《輕重篇》的著作年代“大致是戰國”,“疑出自齊人依托管子的著作”,*《歷史研究》1958年第1期。論證至爲嚴謹。今人胡家聰《管子新探》第二十章對《輕重篇》的作時作了進一步的深入探討,*胡家聰《管子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對主張作於漢代各説提出的理由一一加以辯駁,並以大量事實證明作於戰國時代。新近出版的池萬興的《管子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對《管子》一書及各家之説進行認真研究後指出:
《管子》一書既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間之作,它包含了春秋時代齊國的史官以及管仲的門人弟子、後代,直到戰國田齊時代稷下學宫崇尚管仲功業的可以稱之爲“管仲學派”的稷下學士的論著。也就是説,《管子》一書的斷限應該是春秋管仲時代到戰國末年。*見池萬興《〈管子〉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管子〉的作者與時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63。
李學勤先生有《〈管子〉“乘馬”釋義》一文,對治《管子》者一直未能弄清楚的“乘馬”一詞之義加以考釋,認爲其本義是軍賦單位,這同古代兵農合一、行政編制與軍事編制合爲一體的制度有關。李先生説:“《乘馬》篇首列於《經言》,説明其形成較早。值得注意的是篇中已出現‘輕重’的字樣。”文章又引《史記·管晏列傳》中説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等文字,論證“《輕重》的不少基本思想是與包括《乘馬》在内的《經言》一脈相承,輕重家乃管子這一學派的繼續和發展。”*李學勤《〈管子〉乘馬釋義》,《管子學刊》1989年第1期,頁31;又《李學勤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頁119。那麽,《管子·輕重》與春秋時管仲非無關係,其中言及伏羲、神農、燧人,言齊桓公與管仲曾討論燧人以來之事,未必没有根據。同理,《莊子》、《列子》中説老子、孔子、子貢及宋太宰曾言及“三皇”或“三皇五帝”,即使有關孔子、子貢的是虚構的寓言,老子、宋太宰及莊子與其門人、弟子曾多次言及三皇應是有所依據的。
關於《周禮》,上文已説過。《六韜》一書的性質,前面也已提及。此書自宋代以來不少人懷疑是僞書,清姚際恒言:“其辭俚鄙,僞托何疑!”《四庫總目提要》亦言其“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836上。然而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了一些失去篇名的殘簡,其内容與今本《六韜》基本一致;次年河北定縣西漢墓又出土一批被稱爲《太公》的竹簡,其篇目有編序,有的内容同今本《六韜》一致,有的則超出今本。三國時人謝承著《後漢書》卷三言徐淑“善論太公《六韜》”,范曄《後漢書·何進傳》言“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74;《後漢書》卷六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246。今本《六韜》全書也是以文王、武王同太公對話的形式寫成,則今本《六韜》乃東漢時由《太公》改編而成。《漢書·藝文志》兵家類無《六韜》,而道家類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漢書》卷三〇,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29。我以爲《六韜》一書,其《武韜》之五篇當由《太公言》删削而來,《文韜》十二篇當由《太公謀》删削而來,其餘《龍韜》、《虎韜》、《豹韜》、《犬韜》計三十三篇,由《太公兵》删并而來。其中也有後世附益之文字,但主要材料應有很早的來源。此有《羣書治要》、《文選》注引《武韜》、《太公金匱》文字可知其大概。則其成書應不遲於《孫臏兵法》。*陳青榮《〈六韜〉作者及其成書年代》一文認爲《六韜》成書於春秋時代。見其《姜太公新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或主成書於戰國,見劉宏章《〈六韜〉初探》,《中國哲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頁48—56;徐勇主編《先秦兵書通解》,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列子》一書,自清代姚際恒以來,不僅將其中文字有矛盾或與史事不合者皆定爲後人所附益,甚至連劉向《敍録》也定爲僞作。民國以來,衆口一詞,斥爲“僞書”。但近年來嚴靈峰、鄭良樹、陳廣忠、馬達等先生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證其原書散佚殘缺後,後人整理中摻進了一些後代的文字,但原書並不僞。*見嚴靈峰《列子辨誣及其中心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鄭良樹《〈列子〉真僞考述評》、《〈列子〉成書時代研究管窺》等論文五篇,見其《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陳廣忠《爲張湛辨誣──〈列子〉非僞書考之一》、《〈列子〉三辨──〈列子〉非僞書考之二》、《從古詞語看〈列子〉非僞──〈列子〉非僞書考之三》,刊《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馬達《列子真僞考辨》,北京出版社,2001年。
又《文子》一書,在河北定縣西漢墓出土了竹簡本,即使流傳中多有竄亂增益,也只是和西漢前期的《淮南子》有些牽扯不清,絶非宋人黄震所説爲《通玄真經注》的注者唐代默希子(徐靈府)所僞造*見《黄氏日抄》卷五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708册,頁410下。。
由這些來看,過去一些學者斷定“言‘三皇五帝’之書皆晚出”,並不能成立。有的學者因《莊子·天運》篇提到“三皇五帝”,便認爲《天運》篇之寫成比《吕氏春秋》還遲,這都是先入之見。商先公先王世系見於漢代人所著《史記》,個别人物《山海經》等書提到,但文字錯誤,根本無人注意,經王國維研究,與甲骨文反映的基本相合。對先秦古書不作具體分析而簡單地分爲“真”、“僞”兩類,是對先秦古書流傳情況不了解的表現。李學勤先生有《對古書的反思》一文,*見《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對先秦古書的複雜情況有細緻的分析和精闢的論述,此處不多説。
總之,先秦典籍中關於燧人、伏羲、神農及“三皇”的傳説是有早期傳説與文獻的根據的。
三 由“皇”字本義看“三皇”的身份與服飾特徵
(一) 過去對“三皇”的誤解
人們對“三皇”的傳説完全抱着懷疑的態度,有種種原因,而舊的史學家將“三皇”只作爲具體的人,並且在服飾、形象、權力、勢力範圍等方面理解得同後代帝王一樣,與現代歷史學、考古學所揭示的史前階段的實際大不相合,是原因之一;學術界對早期文獻缺乏正確的分析與判定,很多問題没有弄清楚,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緯書《春秋運斗樞》在列舉“三皇”之後有這麽幾句話:“皇者,合元履中,開陰布綱,指天畫地,神化潛通。”這完全將三皇説成像天帝一樣法力無邊的神靈;《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道爛然顯明。”*上引兩條緯書文字,並見《太平御覽》卷七六《敍皇王上》,頁355上。這也同樣帶有神化的味道。這種解説形成於讖緯盛行的漢代。歷史發展到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這自然也就成了學者們否定三皇存在的最簡單的原因。
作爲氏族、聚落的首領,“三皇五帝”的“皇”同“帝”,並不是緯書中寫的神通廣大的神聖,其形象也非東漢武梁祠石刻上的身穿長服、着冕垂旒的樣子。武梁祠上的那種形象不可能出現在五六千年之前。但這並不等於“三皇”不會出現在那個漫長的歷史時期。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本是指遠古時期的氏族,但傳説中則變爲指具體的人。從傳播學的理論上説,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是一個規律。自然傳播中,人們會把一些事迹、事件集中在與之有關聯的、影響最大的人物或者事件上去。因爲每一次的傳播,接受者總是根據自己的知識積累來理解並在傳播活動中無意識地進行加工補充。結果在集體記憶中必然地忽略一些細節,淡忘一些次要的人和事,而將有關情節集中到具有標志性的人物和事件上去。
從歷史發展的實際來説,有氏族、聚落,就會有氏族、聚落的首領。在一個氏族或聚落的發展史上,也總會有一位最傑出的領袖。所以,以前人是拿“燧人”、“伏羲”、“神農”指這三個先後登上遠古歷史舞臺的氏族或中心聚落的最傑出的首領,也是合於長時間中羣體傳播的規律的。
他們既然是首領,雖然不會如周秦以後帝王那樣身着黻繡、頭戴冕旒,但也不會如今天一些普及讀物上畫的或某些紀念地、展廳所塑,披着長髮,肩上和腰裏纏着樹葉(明刊本《三才圖會》上的神農像即是滿身樹葉,手裏拿着一棵草在吃)。理解上的簡單化,也同樣違背了歷史的事實。當時雖然没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特權,但是,第一,他們作爲氏族或聚落的首領統領大家,總有一定的權威;第二,他們對外是氏族、聚落的代表,要顯示氏族或聚落的威望;第三,他們也是行使神職的人物,在氏族或聚落内部有一定的宗教地位和圖騰象徵性。那麽,他們至少在聚會、儀式等行使職權的場合,總會有某種標志性的服飾。
(二) “皇”字本義考
《説文·王部》説:“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是。”*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頁9下—10上。近人汪榮寶認爲《説文》的解釋是據秦代以後變更古文立説的,並未揭示出“皇”字的本義。其《釋皇》一文云:
汪氏關於“皇”字上部的解説,至爲精闢。《説文》解“皇”字的構成與本義全錯。汪氏論述引及鄭玄注《王制》中“皇,冕屬,畫羽飾焉”二句七字,更具啓發性。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先生在對長安縣張家坡銅器銘文彙釋時説:
查《周禮·春官·樂師》有皇舞,鄭司農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又《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我意畫羽飾之冕亦是後起之事,古人當即插羽於頭上而謂之“皇”。原始民族之酋長頭飾亦多如此。故於此可得“皇”字之初義,即是有羽飾的王冠。*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羣銘文彙釋》,《考古學報》1962年第1期,頁1—32。
不僅引述了幾條重要文獻,還列舉民俗現象爲據,更顯得堅實可信。


文章引了《説文·皃部》:

李學勤先生發現,現存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玉璧上有冠狀符號,他説:“可能是一種有羽毛的冠。”並説:“原始的‘皇’字或許是一種用羽毛裝飾的冠。大汶口陶器符號‘丁’像這一類冠。”*李學勤《論新出土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文物》1987年第12期,頁80。這裏將“皇”字追溯到了距今約六千三百年到四千四百年的大汶口文化時代。
汪榮寶、郭沫若和陸宗達、王寧、李學勤先生關於“皇”字的解釋都極準確精到,可謂各有貢獻。
《詩經·周頌·有瞽》:“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孔穎達疏:“設其横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朱傑人整理《毛詩注疏》卷一九之三,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956。錦雞等的尾羽都較長,裝飾起來遠近可見。
所謂“冕屬”,非一般人平時所穿戴。《王制》言有虞氏在祭祀儀式上纔戴這種名叫“皇”的冕冠。蔡邕《獨斷》卷下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獨斷》,四部叢刊三編本,32册,頁1013。也説“皇”同“收”、“冔”、“弁”,都是冠弁之名。
根據民俗學的原理,儀式上,尤其祭祀儀式上的服飾大都是前代服飾的遺留。而“皇”作爲一種冕冠,在有虞氏即舜的時代已是很古的冠弁式樣了。

又《禮記·王制》中“有虞氏皇而祭”,這個“皇”,《經典釋文》卷一一作“”,曰:“音‘皇’,本又作‘皇’。”*《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175上。可見“皇”、“”本是一字,是隸定時分化爲兩種寫法: 以“”爲有虞氏以前一種冠冕之名,以“皇”爲遠古時的人王即“三皇”的“皇”字之稱。那麽,可以肯定“皇”最早的寫法其上部並不從“自”,而是像羽毛之形。*之隸定爲皇,或者同上部“羽”左邊“习”上的短横與提畫殘缺有關,或者因後人已不知其本義而取其異體。
至於“皇”字的“美”義,見《廣雅·釋詁一》:“皇,美也。”“華”義,見《爾雅·釋言》:“華,皇也。”*《爾雅·廣雅·方言·釋名》清疏四種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9年,頁360下,134上。都是由羽冠一義引申而來,據陳獨秀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所編《小學識字教本》的解釋,“美”的原始義爲人戴羽之形,“美、義均非從羊”,否定了《説文》的解釋,而認爲“美爵”的“美”字“像人戴毛羽美飾之形”。*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107。至於“皇”字的“大”義、“君”義,則由聚落首領一義發展演變而來。
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不可能有高貴華麗的紡織品來爲聚落的首領作冠服,取之於自然,用最長、最美麗、最珍貴的羽毛來裝飾其冠,應該説是一種創造,在人類服飾史、美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遠古時期,氏族、部落的首領未必與後代的帝王一樣,有專門的宫殿,成天有很多人圍着他轉,因此,也不會時時戴着那種具有特殊標志性的“皇冠”。但是,在軍事會議、祭祀或其他儀式上,一定是戴着這種冠,同時也穿着相應地顯示身份的服裝(如虎豹之皮的外套等),而最關鍵、最突出地顯示其身份的是戴着這種皇冠。主要以冠飾顯示地位、級别、身份,這不但在中國從上古至近代是如此,全世界很多民族都是如此。
四 遠古皇冠之俗在後代的遺留
炎帝作爲神農氏最後一位首領,自然是戴皇冠(羽冠)的。黄帝、顓頊等是否也戴皇冠,難以肯定。舜、禹以後的首領、君王除在祭祀儀式上之外,肯定是不再戴羽冠了。但作爲人們記憶中留下極深刻印象、與很多傳説相聯繫的一種冠戴習俗,仍存留於其他很多方面。
(一) 中原與周邊少數民族文化中皇冠的遺存
首先在具有模擬性表演場合的演員的佩戴上保留了下來。上古的舞蹈中,有一種“皇舞”。《周禮·春官·樂師》:“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玄注:“故書‘皇’作‘’。鄭司農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鄭衆謂:“‘’讀爲‘皇’。書亦或爲‘皇’。”*彭林整理《周禮注疏》卷二六,頁863。
其次,在後代周邊一些少數民族君王、顯貴、巫師之類特殊人物冠飾上的遺存。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銅人像冠式中,有一種“三聳羽飾的武冠”(見圖二)。*宋鎮豪《中國風俗通史·夏商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383。三星堆遺址相當於中原殷商時期。蜀人是氐、羌南徙後同當地土人交融形成的,它的文化帶有遠古北方民族的一些特徵。寧夏賀蘭山岩畫的“人面像”上,“有的插羽

圖一 西漢滇族執干戚舞者,雲南晉寧銅鼓紋飾(《文物》1974年第1期)

圖二 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藏品(又見宋鎮豪《中國風俗通史·夏商卷》,頁381)
毛”,“有的頭上有角狀和羽毛裝飾”。*見李祥石《寧夏賀蘭山岩畫》,載周菁葆主編《絲綢之路岩畫藝術》,頁12。這與後來景頗族祭司的冠飾相近。關於中國少數民族中以羽飾冠的風俗,王政《戰國前考古文化譜系與類型的藝術美學研究》一書的第十章《中國岩畫人物“羽飾”與巫術“美飾”人類學》部分有很多事例,*王政《戰國前考古文化譜系與類型的藝術美學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可以參看。
《周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周禮注疏》卷一六,頁496下。這自然不是一般羽毛,而是又長又美的珍貴羽毛。《尚書·禹貢》“徐州”下言及“羽山”,又説到“羽畎夏翟”。*黄懷信整理《尚書正義》卷六,頁204,205。畎,山谷。夏,大。“翟”之本義爲長尾的野雞。後亦用以指野雞的羽毛。雄野雞有五彩羽毛。《詩經·邶風·簡兮》:“右手秉翟”,毛傳:“翟,翟羽也。”*朱傑人整理《毛詩注疏》卷二之三,頁222。則羽山是因爲自遠古出長大的五彩錦雞毛而得名。鯀被殛於“羽山之郊”,*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472。時當虞舜之時,此山已因雉羽而出名。由此也可以看出,羽爲冠服之裝飾遠在堯舜之前。根據當時的經濟發展情況,一般人只是以獸皮、樹皮、樹葉遮其身,以“畫羽”爲飾,只能是氏族、聚落的首領。
再次,古代知天文者等特殊身份者戴此冠。這好像是繼承了遠古氏族、聚落首領所兼宗教職責“上知天文”的一方面,且只限於鷸羽。《説文·鳥部》:“鷸,知天將雨鳥也。”*《説文解字》,頁81上。顔師古《匡謬正俗》以爲因此古之知天時者戴此冠。1984年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奏讞書》簡一七七記春秋時魯國一佐丁“冠鷸冠”,柳下季以其“有小人心,盜君子節”,*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72。收以爲奴。可見即使由(五彩羽飾的冠)演變爲鷸弁,也非一般人所能戴。《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4240。子臧以罪出奔,又不知天文而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誘殺於陳蔡之間。
第四,春秋戰國之時,勇者也戴有羽之冠。《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子路年輕時“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史記》卷六七,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650。所謂“冠雄雞”,即指以帶有尾部羽毛的雄雞皮罩在冠上,羽毛後揚。

圖三 戰國鶡尾冠騎士(洛陽金村出土金銀彈狩獵青銅器局部,周汛、高春明《中國古代服飾大觀》,重慶出版社,1995年,頁299)
當時中原地區武士流行戴鶡冠,也是繼承了遠古皇冠體現的勇武、威風的一面,但也只限於鶡羽。同時也不是滿頭插或插一圈,而是插兩支。《續漢書·輿服志下》云:“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鶡者,勇雉也,其鬥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670。戰國鶡尾冠騎士的圖像,在青銅器中尚可以看到(見圖三)。
第六,有的隱士也戴鶡冠。*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22。隱士、道士的服飾多保持古時的式樣,以顯示不同流俗,與古人同心。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羽冠爲古代流風。
以上這些遺俗從不同的方面承襲了三皇羽冠的一些特殊含義: 舞蹈者取其儀式性並表示爲古代禮俗,氏族首領取其爲權力象徵一義,知天文者取其得先聖神力一義,貴族取其表示身份高貴一義;武士取其威武一義;隱士則取其行不同俗、道接往古一義。
三皇不像後代的帝王有很大的勢力範圍,但都是特定歷史階段中最强氏族或聚落的首領,冠服習俗也影響及其他氏族或聚落,加之三皇延續的時間總共約五千年上下,所以其羽飾冕冠的遺風存留在以後的很多習俗之中,至當今的戲曲服飾中尚可以看到。如武將或少數民族首領常在冠後插着兩支孔雀尾翎或錦雞尾翎等。我們看宋人作《明妃出塞圖》表現漢代北族官員,頭上就插兩支野雞毛(見圖四)。元代后妃及命婦行禮時所戴的顧姑冠,頂上也插有翎羽(見圖五)。滿洲清朝官吏的帽子上還有花翎,學者們都以爲這是北狄韃子服飾,非華夏傳統,其實,這是我們老祖宗最古老服飾風俗的遺留。有意思的是,在殷墟婦好墓出土一個圓雕玉人(編號371),頭髮編成一長,繞頭纏在頭上,經左耳後,將梢纏至右耳後側。同墓出土另一圓雕裸體玉人(編號376),髮的梢塞入右耳後根下。還有一圓雕玉人,腦後垂一短(編號371)。看來梳子的風俗在商代以前是比較盛行的,原生活在中國東北長白山一帶滿族垂子,也是古風的遺留。清代官員帽上插花翎,情形與此類似。中原地區的人民遭遇戰亂之後的遷徙,無非一向南、一向北。所以少數民族的服飾往往反映着較原始的習俗。

圖四 宋人明妃出塞圖中北族官員形象(局部)

圖五 戴顧姑冠的元代貴族(周汛、高春明《中國古代服飾大觀》,頁13)
此外,後代帝王的儀仗中,皇帝身後常打着兩個羽扇,略高於頭,是否爲上古“皇”的變相,也值得研究。

圖六 楚祖吴回(祝融)像(長沙出土楚帛書,見陸思賢《神話與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原標作“顓頊”,誤)
(二) 由遠古楚民俗與印第安人遺俗看三皇時代氏族聚落首領的冠飾
南方的楚國,由於春秋以前相對獨立發展,又由於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漢書·地理志下》,頁1666。所以在長沙出土戰國帛書圖像中,留下了反映史前階段楚人始祖冠飾的圖像: 圖像上的人有三個頭顱,右胳膊已斷(見圖六)。《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又云:“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無右臂。”*袁珂《山海經校注》,頁413,412。顯然,畫面上表現的正是三面一臂的吴回。《史記·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吴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史記》卷四〇,頁2027。
可見,帛畫上的人物,正是史前時代楚人的祖先吴回。*帛畫上三面一臂的人物學界定義爲顓頊,誤,應爲祝融。“楚祖高陽”是指祝融,非指顓頊。顓頊是楚與秦的共同遠祖,祝融是楚人的始祖。《國語·鄭語》言楚爲“重黎之後”,《國語》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510。又云:“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頁511。“融”即祝融,羋姓即楚人。《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載楚武王以不祀祝融與鬻熊而滅之。《禮記·喪服小記》説:“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其祖是鬻熊,其祖之所自出(遠祖)自然是祝融,司馬遷將高陽與顓頊相混,誤。參拙文《吴回·南嶽·不死之鄉——探索有關楚民族的一個神話》,刊《民間文藝季刊》1987年第1期,頁67—73;《離騷辯證·高陽·祝融·吴回》,收入拙著《屈騷探幽》(修訂版),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頁303—305。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人物三個頭上都有四條長形飾物,顯然爲羽飾。這樣看來,至五帝時代,至少南方有的氏族或中心聚落的首領仍戴此種羽冠。王政《戰國前考古學文化譜系與類型的藝術美學研究》一書第十章第四節《域外民間文化中的羽飾》對澳洲、北美洲一些原始民族中的羽飾有較多的論述,可以參看。
可以使我們對“三皇”時代氏族、聚落首領的冠服有一個具體想象的,是北美印第安人酋長的冠飾。我看到一些北美印第安酋長的照片,其頭上都是用幾十釐米長的彩色羽毛編成一圈(見圖七)。美國1933年拍電影《小天使》中印第安人酋長的帽子也是如此。另一部美國電影《白羽毛》中印第安人酋長的帽子是: 用一樣長的彩色羽毛駢聯編成約人身兩倍長的帶子,其正中作成圓形,戴在頭上,兩頭在身後對稱垂下,羽端向外,顯得特别威嚴。我想這應該是有民俗學根據的。今印第安歌手所戴帽子上也插着美麗的長羽(見圖八)。史哲《土著人的隱秘世界》一書第四章《印第安人的昨天和今天》所附印第安人酋長、演員和儀式上的頭飾,就有八幅頭上插着各種漂亮的羽毛。*史哲《土著人的隱秘世界》,北京,中國民航出版社,2004年,頁140—194。據近代和當代許多地理研究成果證實,西伯利亞東北部在一萬年以前的冰凍期,有一條狹長的陸地橋,使亞洲與北美的西北部(今美國阿拉斯加州)相連接。很多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民俗學家一致認爲,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爲蒙古人種的後裔。亞洲蒙古人種的一部分最早是從這裏先後遷移到北美洲的,後來也有從水上乘船過去的,成爲今天印第安人的先民。這方面的研究論著很多,毋庸贅述。*參喬健編著《印第安人的誦歌》第一部分《美洲與亞洲文化的遠古關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華國勝《加拿大印第安文化與亞洲文化關係簡析》,刊《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2期,頁262—263。那麽,印第安人這種冠飾同中國史前時代氏族首領的羽冠有關,亦不足爲怪。

圖七 印第安酋長(見史哲《土著人的隱秘世界》,北京,中國民航出版社,2004年,頁169)

圖八 南美厄瓜多爾的印第安三人樂隊中的成員馬可(《光明日報》2012年5月14日第12版)
郭沫若先生説“畫羽之冕亦是後起”,更早之時應是“插羽於頭上而謂之皇”,指出了“皇冠的形成過程,即由頭飾向冠飾的轉變”,是很有道理的。聯繫上古岩畫和一些原始民族的冠飾來看,很可能在伏羲氏以前只是在頭上紮了長而美的羽毛,後來纔固定於皮弁之上。總之,由於“皇”這種羽冠爲炎黄以前首領所戴,後人便以“三皇”統稱傳説中我們祖先所經歷這三個階段中傑出的首領;儘管説春秋以前只有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之傳説而無“三皇”之稱,但也不能説這種稱説毫無根據。劉起釪先生《幾次組合紛紜錯雜的“三皇五帝”》一文云:
本來“皇”字在早先的文獻以及金文中,只是形容詞或副詞,爲尊大、美善之意,常用以形容上天、上帝和祖先。到戰國中後期,把神話中的帝堯、帝舜等作爲人間帝王來稱呼,而戰國羣雄中的强者也爭想稱帝,天帝位號歸了人王。於是人們開始把常用以形容天帝的皇字移作天帝的位號,因而《楚辭》的《離騷》裏有了“西皇”,又以“皇”字直稱天帝,《九歌》裏有了“東皇”、“上皇”,《橘頌》裏有了“后皇”,皇成了上帝的稱謂,以前叫“帝”、“上帝”或“后帝”的,此時叫“皇”、“上皇”或“后皇”了。*劉起釪《古史續辨》,頁107。
這是尚未弄清“皇”字的本義,未對先秦有關文獻作全面清理和科學、細緻的研究,也未關注與之相關的大量民俗學材料而形成的誤解,現在看來顯然是大可商榷的。
五 從史前玉器和商周青銅器看“三皇”的圖像
冠是身份的標志,而首領、君王之冠更是獨一無二的象徵。直至今日仍有“王冠”、“加冕”之説(如英國的女王)。上面我分析了“皇”字之義,論述了三皇羽冠在先秦時及此後周邊少數民族以至印第安人酋長冠飾上的遺存,想可以消除一些在“三皇”問題上的誤解。下面從史前階段氏族、聚落首領的冠服,探索史前時代氏族、聚落首領的形象在上古玉器、青銅器中的存留與演變。
(一) “三皇”服飾的圖騰標志性
《列子·黄帝》言“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83—84。如果這裏只是説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我們還可以只從神話方面去理解;但其中也説到夏后氏,就不能只從神話方面解釋了。我以爲這應從氏族的圖騰標志方面去理解。東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文選》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6年,頁515。《路史·後紀一》羅苹注引《玄中記》云:“伏羲龍身。”*《路史》卷一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83册,頁73上。《山海經·海内東經》:“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袁珂《山海經校注》,頁329。《山海經》所反映與其他典籍的記載暗合,則《列子·黄帝》中“蛇身人面”指伏犧氏、女媧氏而言,“牛首虎鼻”指神農氏、夏后氏而言。由《山海經》、《列子》所載可知,伏羲氏龍身或鱗身的傳説産生很早。馬克思説希臘神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9。遠古時代既不可能有文字資料留下來供我們了解,則結合考古材料正確地解讀有關的神話,是我們認識遠古社會歷史的手段之一。
學者們都認爲伏羲氏是以龍爲圖騰的。龍本是馬的神化(大約到神農時代又被加上了兩隻角,有了牛的部分形象)。不論怎樣,既然被神化,便與尋常之馬不同。上古之人看到魚蛇能憑虚游於水中,便想象神馬可以騰空而行。因而,被神化的馬便是鱗身。上古之時最美麗華貴的皮弁是以珍貴羽毛爲飾,華美威武的衣服也多用獸皮做成。遠古之時有一定地位或以勇武稱者,秋冬當以有花紋的虎豹之皮或其他色澤鮮亮的獸畜之皮爲服。但當時人們生活資源的很大一部分來之於狩獵,所以這些獸畜之皮並不太珍貴。水中鱗類的皮卻因其難取,每張皮的面積又小,集合爲一件衣服很不容易,故更顯珍貴。周代以前國君、貴族的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者,亦以其稀罕之故。我以爲伏羲氏首領在特定場合所着外衣可能是用漂亮結實的魚鼉或蟒蛇之皮做成,穿上它全身閃光,也不易射穿,更顯其威武不凡。文獻中載伏羲氏“作結繩而爲罔(網)罟,以佃以漁”,*《周易正義·繫辭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51上。看來其以龍蛇爲圖騰是有原因的。因之,其首領以魚鼉蟒蛇之類的皮爲衣,更體現出首領對氏族的代表性。
關於神農氏形象的傳説,典籍中也有反映。司馬貞補《三皇本紀》言神農氏是“人身牛首”,*《史記》附録二,頁4024。《繹史》卷三引《河圖挺輔佐》言“伏羲禪於伯牛”,*《繹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65册,頁80下。同《列子·黄帝》言其“牛首”是一致的。則神農氏應是以牛爲圖騰者。那麽,神農氏(烈山氏)的衣裘應是用牛皮做成,皮弁上同樣以羽毛爲修飾。今在商代的陶俑中,尚可見到牛角形冠飾(見圖九),只是上面没有羽飾。北美印第安人以牛爲圖騰的氏族,其長者的帽子上不僅有牛角,也有羽飾,只是羽毛不太長,位置也有變化(見圖十)。這至少可以成爲我們對神農氏首領冠飾進行推斷的一個參考。《周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彭林整理《周禮注疏》卷三七,頁1206。裘冕爲上古天子祭祀所着。前面説過,祭祀儀式上的服飾一般比較保守,往往是前代服飾的遺留。《周禮·夏官》中的記載應多少反映了史前階段氏族首領冠服的狀況。

圖十 印第安部族以牛爲圖騰的長者(史哲《土著人的隱秘世界》,頁178)
中國史前階段氏族、聚落首領戴有特别冠飾的圖像在上古時代的玉器、青銅器中尚能看到,只是由於以前很多問題没有弄明白,長期形成的某些誤解影響着人們的思維,所以未能有清楚的認識。
商周青銅器上圖案化的所謂“獸面”,今通稱“饕餮紋”。最早使用這個名稱的是北宋吕大臨《考古圖》。其卷一癸鼎下云:“中有獸面,蓋饕餮之象。”*吕大臨、趙九成《考古圖 續考古圖 考古圖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7。其後宋徽宗敕編的《宣和博古圖》亦取此説,後人相沿,遂成定説。考吕大臨之所據,乃《吕氏春秋·先識》中的幾句話:“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956。但是,此處所説周鼎上的“饕餮”,究竟是特指某鼎上的一個圖案,還是總稱商周鼎上作爲主題紋飾的所謂“獸面”圖案,還很難説。商周之時“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669—670。其中在重要部位突出加以表現的未必即是饕餮。看《吕氏春秋》一書所論,亦非只有饕餮: 《達鬱》言“周鼎著鼠,令馬履之”。《慎勢》言“周鼎著象”。《離謂》則云:“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倕爲堯之巧工。所謂“齕其指”云云,應是反映了上古之時的某一傳説。《適威》云:“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頁1382,1121,1188,1291。“竊”,據陳奇猷先生之説,爲“禼”字之重文,商人之祖契,字本作“禼”。“有禼”即其上刻鑄有契的形象。以此來看,《吕氏春秋》所説的周鼎上所刻鑄,多有上古人物的像,“饕餮”只是圖象中之一種。吕大臨之説顯然是以點帶面,雖然他是用推測的口吻説“蓋饕餮之象”,但對後代博物學者形成了很大誤導。

圖十一 良渚文化玉琮上羽冠人圖像(《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

反山除一座墓之外,其餘各墓均有一件同玉琮圖像上部基本一樣的玉飾,頭戴羽飾冠,臉呈倒梯形。身體部分的佈局大體相近,但具體圖形有很大不同,並不表現爲有目、有口的獸面,而是兩個胳膊伸開,各抓住一只大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的同志因這些玉飾出土時均在頭骨一側,認爲是具有神靈意義的頭像,命名爲“冠狀飾”。我以爲這不是一般的飾物,而反映着對祖先神的信仰。《山海經·大荒東經》:“有困(因)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袁珂《山海經校注》,頁351,352。吴其昌《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云:“‘困民’之‘困’,乃‘因’字之誤。此二字本極易誤。‘因民’、‘摇民’、‘贏民’一聲之轉也。”見《古史辨》(七)下,頁357。下面説到“王亥托於有易,河伯僕牛”等。玉飾所表現即商代卜辭、《古本竹書紀年》中説的商先公王亥。“因”爲“殷”字之借。但王亥爲湯之八世祖,當夏代中葉。而良渚文化在公元前3300—前2250年間,在夏代以前。《山海經》中關於王亥的記述,只説明了先商文化也是源遠流長,有所繼承的。反山玉飾上的圖像應反映着比王亥時代更早的傳説。那麽,我們就完全可以認爲它是神農時代或炎黄時代某一聚落傑出首領的圖像。
反山出土玉琮人像頭上羽冠下緣的長條上也有圓圈圖案,表示羽飾是插在皮冠上的。身上突出的雙乳的標志,顯示了女性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當然,也不排除部落首領在突出對雙乳的表現時,巧妙地將上身的服裝圖案變爲某一獸面,以乳爲眼睛而成爲氏族圖騰的可能。《山海經》中説的形天氏“以乳爲目,以臍爲口”,*袁珂《山海經校注》,頁214。有可能就是這種含義。從這個角度説,李學勤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這個玉琮爲我們提供了認識中國史前時代氏族首領形象的實物依據。
我指出反山玉琮圖案上設置眼睛一樣兩個圓圈的本意,便解釋清楚了何以要在人像的前胸繪製圖騰圖案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何以形成“兩個面孔”的人形的問題。我以爲玉飾上的人像都是遠古氏族首領的圖像,同古埃及法老的頭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是我們至爲珍貴的國寶。玉琮上的圖像和很多玉器、銅器上的主題圖案,則突出地表現了圖騰的部分,而簡化、淡化或乾脆省略了人的頭像,這應同社會意識的轉變有關。
(三) 從上古摩崖、玉器與商周青銅器看三皇的圖像
上古摩崖、玉器和商周青銅器上的羽冠人面紋表示一種特殊的權力和地位,這由西北、西南大量頭飾羽毛的上古岩畫和玉器上的圖形可以證明。雲南滄源岩畫中,頭上有羽飾的很多(如圖十二、十三)。餘杭反山的一個玉鉞上部靠刃口處有一圖形,與玉琮上的完全一樣。又臺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斧,上面的羽飾非常突出,並可以看出有兩支對稱的孔雀毛。上古時代斧鉞是權力的象徵。《尚書·牧誓》周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然後誓師。《顧命》寫康王繼位的儀式上也是“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黄懷信整理《尚書正義》卷四,頁419—420;卷一八,頁735。《史記·殷本紀》云:“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記》卷三,頁124。春秋以前,鼎同是權力的象徵,所以有楚莊王問鼎之事,古代君王禮服上也繡着斧形圖案。那麽,作爲斧鉞、大鼎、琮上主題圖案的這種羽冠人面圖像,應顯示着至高無上的權力、地位和神靈輔佐的意思。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二、十三均見王政《戰國前考古學文化譜系與類型的藝術美學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4)
與此相近的,還有1963年在山東日照兩城鎮發現的玉錛。此件玉錛的下部兩面也有接近於商周時代所謂饕餮紋的圖飾。如李學勤先生所説,此圖案“頂上有飾羽的冠形”。此外,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墓葬中,出土了幾件與此圖案相近的銅飾。玉琮上人物胸部好像“以乳爲目”的那個獸面圖像,馬承源先生和李學勤先生都認爲可能是當時龍的形象。*馬承源以爲遼寧西部發現的紅山文化龍形玦,如把龍的臉部平面展開,與反山玉琮上的獸面非常近似。説見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317。李學勤説見《良渚文化玉器與饕餮紋的演變》,《走出疑古時代》,頁89。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只是,我以爲並非所有的“饕餮紋”都是由龍形象而來,有的是由其他的圖騰演變而來,如河南安陽1004號大墓出土的商後期方鼎,其正中顯然是牛形圖案(見圖十四)。甘肅靈臺出土“丩”銘銅方鼎上也顯然爲牛形圖案(圖十五)。*初世賓《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頁106。如果説龍圖騰與傳説中的伏羲氏有關,則這個牛形方鼎上的圖案應同傳説中的神農氏(烈山氏)有關。應該指出,即使伏羲氏、神農氏代表的那個時代結束了,但作爲一個氏族及其文化還是會傳承下來的,將同軒轅氏、陶唐氏(堯氏族)等其他氏族的文化共同發展,或相互融合。虞舜被夏禹所代,但其子商均受封,其後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又封舜之後嬀滿於陳;商朝雖亡,而微子奉其祀,宋爲其後,故《商頌》得傳於後世。有關伏羲氏、神農氏的重要史實會傳至後代,原因與此相類。

圖十四 商代牛方鼎,河南安陽侯家莊出土(宋鎮豪《中國風俗通史·夏商卷》,書前彩頁)

圖十五 西周銘銅方鼎,甘肅靈臺縣白草坡出土(楊重琦《隴上珍藏》,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169)

圖十六 商代大禾人面青銅方鼎(宋鎮豪《中國風俗通史·夏商卷》,書前彩頁)
胸部有圖騰圖案的圖像在以後的玉器和銅器上不見了,但在銅鼎的主要部位以人像爲主題圖案的例子至商代仍可見到。如湖南寧鄉出土商代後期的人面方鼎,我以爲就是這種習俗的遺留(見圖十六)。在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不少有人面圖案的器具。如天水師趙村出土一馬家窯類型陶罐,其顯著部位有一個人面。這些人面像都應從宗教和社會組織的方面去認識,很可能是某氏族、聚落首領的像。明白這一點,對於我們進一步揭示夏代以前的歷史具有重大的意義。《墨子·耕柱》中説: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鼎成,三足而方……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422—426。
《左傳·宣公三年》亦云: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於商。*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669—671。
在三代,鼎是作爲王權的象徵的。前一個王朝滅亡了,後一個王朝繼承它。至於上面所鑄圖象究竟爲哪一個聚落或氏族的祖先,已不太考慮。這就是商代銅鼎上作爲主題圖案的獸像或人像不止一種的原因。
六 中國史前史與三皇時代的社會與文化
“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烈山氏)”,本是對中國遠古三個大的氏族或聚落的稱謂。《列子·黄帝》即以“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並列言之。而傳説中這三個不同時期氏族的經濟發展狀況及社會文化上的特徵,大體上反映了中國史前農耕聚落期和中心聚落期,*關於中國遠古由村落向聚落再向國家的轉變,參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上編第一篇第一章《文明社會的標志與國家形成的軌迹》。該書將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上第一批原生形態的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畫分爲三大階段: 即由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發展爲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爲都邑國家形態。農耕聚落時期在中國有前7100—前5000年的彭頭山、磁山、裴李崗、老官臺、河姆渡的農耕聚落和半坡、姜寨之類的遺址。秦安大地灣一期、二期文化也應屬此一發展階段。所以後來也以之代指我國遠古時期所經歷的三個歷史時期,如《六韜》中言“三皇之世”、《尸子》中言“燧人之世、伏羲之世”,《商君書》、《莊子》並言“神農之世”。
先秦文獻中關於三皇時代的社會與文化狀況也有所記述。《六韜·五音》云:
古者三皇之世,虚無之情以制剛彊,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駢宇騫、李解民、盛冬鈴等注《武經七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35。
後面四五句是説,當時人們認識客觀世界是憑藉金(金屬類)、木(植物類)、水、火、土(土石類)相生(助長)、相克(控制)的道理,已知用天干(來自十進位計數法。因人手有十個指頭,用爲最早的計數工具)、地支(來自一年十二個月,由對月亮圓缺的觀察而來)相配計算時日。*因六十甲子中有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故稱“六甲”。其中説當時人“虚無之情以制剛强,無有文字”,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文子·上義》云:“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文子疏義》卷一一,頁472。《戰國策·趙策二》:“宓戲(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范祥雍《戰國策箋證》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050。“誅”的最早的意思是懲罰和申斥,古文字爲言字旁後轉變爲殺戮之義。
先秦文獻中關於三皇時代的社會狀況,對燧人、伏羲、神農分别論述者更多。下面分别對有關材料加以鈎稽論説。
(一) 燧人氏
傳説中的燧人氏同發明人工取火有關。我們祖先對於人工取火意識的形成和經驗的積累,應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不是由某一個人突然發現的。先民是怎麽知道可以人爲地産生火焰?這同先民們打磨工具有關。打磨石器時産生火花,使他們認識到石塊相碰相磨可以産生火。敲擊中産生的火花無固定方向,又一閃即息,當時人恐怕難以將它們引爲火種。到中石器時代,人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較多的經驗,智力也有所發展,不但會設法從打擊石塊中取火(如挑選敲擊後容易産生火花的燧石,以野棉花、植物乾葉之類附着燧石以取火等),且已開始打磨工具,在一些石器、木器上鑽孔。鑽燧取火、鑽木取火的方法便産生了。《世本·作篇》中説:“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世本八種》,頁107。這同前引《管子·輕重戊》燧人“鑽燧生火,以熟葷臊”的説法一致。看來燧人氏是發明了鑽木取火的氏族。《尸子》言:“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二十二子·尸子》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頁374上。又言:“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同上書,頁374中。《韓非子·五蠹》言:“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説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陳奇猷《韓非子新校釋》卷一九,頁1085。
距今約一萬多年的山頂洞人已有各式各樣打磨得比較精緻的石器,遺址有灰燼,並有燧石器和石珠殉葬。此時可能已有了取火、儲火的辦法,但難度很大。山頂洞人有公共墓地,並且身上撒着赤鐵礦末,則當時已進入氏族社會,並有一定的原始宗教意識。那麽,至數千年後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原地區普遍進入母系氏族社會,形成大體平等的初期農耕聚落形態,則專門的取火工具、取火方法應已形成。首先發明了便捷有效的取火工具和取火技術的氏族,便是後人所稱的“燧人氏”。儘管它並不一定有後來的炎帝、黄帝那樣大的活動範圍,但它在那個歷史階段中代表了先進的文化,所以人們用“燧人氏”來指稱它所代表的那個時代,無論從哪個方面都是説得通的。
據學者們的普遍看法,新石器時代早期仍以打製石器爲主,以漁獵、采集爲主要經濟,已發明了弓箭,産生了初級農業和畜牧業。如上面所言,鑽燧取火和擊石取火的經驗來之於打磨石器和在石器上鑽孔。燧人氏是我國遠古史上最早開始加工石器的氏族。我國先秦文獻中列燧人氏於三皇之首,正與此相合。燧人氏是我國新石器時代初期代表着最先進生產力的氏族,不用説它也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個氏族。
中國境内發現的中石器時代遺址有内蒙古呼倫貝爾盟海拉山的松山、山西大荔沙苑、河南許昌靈井、河北陽原虎頭梁等遺址,時間約相當公元前一萬年至七千年之間。在山西沁水下川,發現有自舊石器時代晚期到中石器時代的遺存,時間距今一萬年左右。湖南澧縣彭頭山發現新石器早期農耕聚落遺址,距今約九千一百年至八千二百年左右。這些大體相當於傳説的燧人氏時代。《韓非子·五蠹》言“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陳奇猷《韓非子新校釋》卷一九,頁1087。便與這一時期的經濟狀況相當,當時經濟上主要以漁獵和采集爲主,農耕尚處於初級階段。
(二) 伏羲氏
“伏羲”本是氏族的名稱。文獻中也寫作“宓羲”、“虙羲”、“宓戲”、“庖犧”、“包犧”,上古之音同。伏羲氏的興盛時代是在燧人氏興盛時代之後,但它們並不一定是前後相承的關係,也不一定在同一區域之内。《山海經·海内東經》云:“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袁珂《山海經校注》,頁329。這同漢代《詩含神霧》“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太平御覽》卷七八引,頁364上。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伏羲鱗身”的説法有些關聯,反映了伏羲傳説的分化情況。又傳説伏羲“生於仇夷,長於成紀”,而“徙治陳倉”。*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榮氏遁甲開山圖》,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47。陳倉其地在今陝西省寶雞市。又《左傳·昭公十七年》“陳,太暤之虚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391。其地在河南淮陽一帶。則根據先秦所傳,伏羲氏是由西北(今甘肅隴南、天水一帶)向東遷徙的,經濟上應是農業、漁獵、飼養相結合的。又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有:
曰(粵)故(古)大能雹戲,出自□(母)華胥,居於雷□(澤),厥田漁魚,□□□女,……乃娶尾□子之子曰女皇,是生子四□,是襄天地,是格參華。*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64。
這同漢代緯書《詩含神霧》“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犧”之説大體一致。*趙在翰輯《七緯·詩緯·含神霧》,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58。至於“尾”其地,新出版清華簡《繫年》的第三章:“飛廉東逃於商蓋氏,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於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41。李學勤先生以爲“邾”即今甘谷南部與禮縣北部相接的朱圉山。則遠古尾其地,亦距此不遠。這與文獻所載伏羲生處相合。
前引《管子·輕重戊》言:“虙羲作,造六法以迎陰陽。”郭沫若《管子集校·輕重戊》引聞一多先生之説,認爲“八卦古有六法之稱(六爻之義蓋本如此)”。*郭沫若《管子集校》,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頁400,1289。可見,《管子》中這句話反映了較早的傳説。《尸子》卷下曰:“虙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又云:“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二十二子·尸子》卷下,頁374中。
《世本·作篇》載:“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又曰:“伏羲作琴。”*《世本八種》,頁107,108。《易·繫辭下》曰: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周易正義》卷八,頁350下—351上。
《文子·精誠》曰:
虙犧氏之王天下,枕方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者絶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如往。*王利器《文子疏義》卷二,頁73—74。
“八節”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可見當時對季節氣候的變化已有了基本的認識。人們長時間地看日出日落、月圓月缺及一年四季的變化,以及不同季節天上星斗的運行情況,已積累了一定的曆法與天象的知識,對草木榮枯、水土凍消的循還規律等都有了一定的認識,也開始了原始的農業。所謂“以佃以漁”,即又種地,又漁獵。當時人們的很多創造是從各種自然現象和常看到的事物中受到啓發,就連長度單位尋、尺、寸等也是先民們根據人自身有關部位的長度而定的。《説文·尺部》:“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又《寸部》:“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説文解字注》,頁175下,67上。可見《繫辭》所説的“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云云,同後世神化的所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兩回事,不能認爲是無根據地拔高和美化氏族社會的人物,而應看到它確實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真實。《莊子·大宗師》:“夫道……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又《繕性》:“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莊子集釋》卷三上,頁246—247,卷六上,頁551。《楚辭·大招》云:“伏戲《駕辯》,楚《勞商》只。”*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21。則戰國時代有些關於伏羲時代社會狀況的傳説,甚至有傳爲伏羲時代流傳下來的歌曲。聯繫《世本》所謂“伏羲作琴”來看,應是完全可能之事。《荀子·成相》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荀子集解》卷一八,頁460。這就反映出戰國之時對伏羲時代的社會治理方式有些較具體的傳説。
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我們的先民已經會作繩索、織網罟,有一定的計算知識,並有原始宗教。“八索”最早爲紀事的工具,即所謂“結繩記事”,但也是和數的觀念聯繫在一起的。《周易集解》引虞鄭《九家易》:
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458。
這是反映了古人結繩記事的一種手段。記事之繩有八,從中國自古代將數之奇偶和凶吉相聯繫的傳統習俗來看,我以爲古人是以垂繩的單數記凶事、偶數記吉事。《周禮·天官·宫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鄭玄注:“奇衺,譎觚非常。”*彭林整理《周禮注疏》卷三,頁102。《史記·李將軍列傳》:“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史記》卷一〇九,頁3454。可見中國古代以“奇”即單數表不好、不順利,而以“偶”、“對”、“雙”、“麗”表吉利。後來由結繩而産生占卜之具,也是以奇爲凶、爲不順,以偶爲吉、爲順利而形成。

《周禮·春官·外史》云:“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彭林整理《周禮注疏》卷三一,頁1027。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論左史倚相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340。《八索》未必即講八條繩索占卜之法;因爲沿用舊名是史官的陳法。但“八索”後來又成爲“八卦”理論的一個分支,應是保留了較原始的占卜之法。在甘肅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距今約七千八百年)遺址中,發現有刻畫符號,有陶片磨成的紡輪坯,陶器上多有網狀繩紋,則當時已具備産生八卦前身“八索”的物質和智力基礎。
同時,大地灣遺址901號房址僅前堂面積就近一百三十平方米,還有後室和東西兩個廂房,共同構成一個大型建築。其正門朝南,左右有對稱的側門,東西牆上又各有側門通向廂房。正門進去一個大火塘,直徑超過兩米半,殘高約半米。其地面壓實磨光,如今日所鋪水泥地面。看來,這個火塘不是用於一般取暖或炊事,而是宗教或其他儀式所用。這個堂,也應是進行宗教儀式和召集會議之用。那麽,在當時已産生了具有較高權威的氏族、聚落首領,集中而議事。傳説的伏羲時代,當農耕聚落獲得第一步擴展、完善和内聚的時期,即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階段的後期,也即新石器晚期的前段,距今約八千至七千年左右。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至半坡文化之前經濟上以農耕、漁獵、飼養爲主的時期,應在這個時間範圍之内。磁山—裴李崗文化也屬於這一時期。
(三) 神農氏
《易·繫辭下》又云: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斫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正義》卷八,頁351下。
這段文字不僅指出了神農時代已能製造專用的農具,而且有了交换農産品和生産、生活用具的市場。《國語·魯語上》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國語》卷四,頁166。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503。《禮記·祭法》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吕友仁整理《禮記正義》卷五五,頁1802。“厲山氏”即烈山氏,“厲”“烈”一音之轉。所謂“烈山氏”即神農氏,古人刀耕火種,“烈山澤而焚之”,*《孟子注疏》卷五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3上。故稱這個善於耕種的部族作“烈山氏”,稱其最後的一位首領爲“炎”帝,“炎”也是由烈山火種的特點而來。後來有的學者以爲“炎”反映着炎熱的氣候特徵,認定爲南方部族,完全是望文生義,不可徵信。戰國之時關注農耕的神農家起,故人們又稱烈山氏爲“神農氏”,後以其意思明了而成對烈山氏的普遍稱呼。“烈山氏”是神農氏較早的稱説。因戰國以後文獻中稱作“神農氏”,故本文也以“神農氏”稱之。柱應是烈山氏的一位傑出人物,故夏代以前人奉之以爲稷神。上面文字反映了神農時代的種植無論糧食作物還是蔬菜作物,都已達到多樣化。《太平御覽》引《周書》云: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懇(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太平御覽》卷七八,頁366。
“天雨粟”自然是流傳中産生的神話,反映了其氏族在農作物品種的選擇、培育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績。據《周書》所言,當時已掌握了製陶和簡單的冶煉工藝。製作出斤、斧和耒、耜、鉏(鋤)、耨等農具,可見農業生産已經較前發達,穀物的種類也比較多。《六韜》引“神農之禁”云:“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羣書治要·六韜》,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525。《管子·形勢解》云:“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又前引《輕重戊》云:“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二〇,頁1183。又《尸子》云:“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二十二子·尸子》卷下,頁374中。這實際上是説當時已進一步掌握了自然規律,能順應天時。又云:“神農耕而王,所以觀耕。”*《太平御覽》卷八二二引《尸子》,頁3663下。説明氏族、聚落的首領特權還不大,仍然參加耕種活動。周天子每年的藉田,是這種古風的遺留。因爲周人也是以農耕而起家的。《尸子》又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與昏也。’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二十二子·尸子》卷下,頁374中。這是説神農氏並非每位首領都德能兼具,只是當時人民淳樸,易於管理。這是符合史前社會的實際的。其中言神農氏七十世,自然是大略言之,後世以一世三十年。上古之人壽短,以每世二十年計,則七十世一千四百年上下。燧人氏距今約一萬至八千年前;伏羲氏距今約八千至六千三百年前;神農氏距今約六千三百至五千年前。*從世界上古社會發展的狀況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看,時代越早,社會的經濟、文化、人的思想觀念發展變化越緩慢。故按三皇的順序,燧人氏時代應最長,伏羲時代次之,神農時代又次之。神農氏末期首領爲炎帝,即有黄帝起而與之爭戰,進入部族首領更遞較頻繁的五帝時期。關於三皇各段之時間,文中只是考慮到上述因素的大體估計。《商君書·畫策》云:“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又《開塞》云:“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07,53。《文子·上義》引《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王利器《文子疏義》卷一一,頁494。《吕氏春秋新校釋·愛類》略同,頁1472。這些與上文引《周書》中那段文字一樣,對當時社會經濟與社會制度、首領與廣大聚落成員的關係等作了概括的論述。《文子》中用了“天下”一詞,這也是後人對傳説的神農時代有所懷疑的原因之一,認爲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産生統一了中華大地的帝王。其實,“天下”一詞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上的含義並不相同。在神農時代,也就只指人們所見到的天底下那一大片地方;至夏商時代,主要指中原與黄河流域,也包含江南和西域之地;春秋戰國以後又不斷擴展。至於包含五大洲四大洋,則到清代以後。對此,我們不能像人們對“皇”字的含義一樣,以今天的觀念去理解。
《莊子·盜跖》云:
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莊子集釋》卷九下,頁995。
這是説神農之世人民生活安靜而滿足,處於母系氏族社會的興盛階段,尚盛行走訪婚(大體同於南方一些少數民族直到近代尚保留的阿柱婚)。*這種婚姻狀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甘肅省武都縣坪芽鄉藏族中尚盛行。1970年我到坪芽公社招生,發現學生的家庭主要成員中都填的是母親和舅舅,而没有填父親的。校長告訴我們,那裏成年婦女的配偶只在晚上去住,白天勞動在他自己家,同女方家庭無經濟上的關係,對孩子也没有撫育的責任。我覺得這是北方所存史前婚姻狀態的活化石,同南方少數民族的有關資料俱可以彌補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之不足。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允許我對存在於西北的這一古老習俗作詳細調查。文革後我即到了蘭州,對此未能進行社會調查,深感遺憾。
《世本·作篇》:“神農作瑟。”又其《帝系》云:“神農樂曰《扶持》。”*《世本八種》,頁7,83。這是説當時已有了音樂藝術方面的活動與創作。
應該説,這些記載是反映了中國母系氏族公社繁榮時期的狀況的。當時經濟上已進入以較發達的以種植農業爲主的階段,並産生了畜牧業。如果同考古的成果聯繫起來看,則大體上相當於仰韶文化時期與大汶口文化早期,屬新石器晚期的後一段。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説,應屬初步分層與分化的中心聚落時期。
戰國以後人之所以稱烈山氏爲“神農氏”,是言其農業技術高,種植農業得到空前發展。戰國時農家如許行等人自稱其學説爲“神農之言”。*《孟子注疏》卷六上,頁2705中。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文》,將見於《管子·揆度》的《神農之數》同見於漢唐之書的《神農之法》、《神農之教》、《神農書》、《神農占》俱視爲“三皇”中“神農”之作,是只看名稱的簡單化處理。這些文獻顯然是戰國時農家言,雖亦總結了以前的一些農業經驗,但産生時間遲得多。弄清了這個問題,不僅可以對戰國時農家的學説有具體的了解,也不會因神農時代不可産生那樣的著作而否定歷史上神農之世的存在。
(四) 餘論
在傳説的三皇時代,中華大地上有很多的狩獵與農耕聚落。《莊子·胠篋》中與伏羲氏、神農氏並列的有容成氏等。前些年刊佈的上博簡《容成氏》中列舉的遠古氏族有容成氏、尊盧氏、赫胥氏、喬結氏、倉頡氏、軒轅氏、神農氏、木韋氏,壚氏等,*參《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50,293。《漢書·古今人表》中也有所彙集,如《莊子·大宗師》中與伏羲並提的狶韋氏,《莊子·盜跖》、《韓非子·五蠹》中列於燧人氏之前的有巢氏等。有巢氏很可能是南方氏族,*參王文清《淩家灘文化應是“三皇”時代的有巢文化》,《東南文化》2002年第11期,頁32—36,並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縣淩家灘遺址第三次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第11期,頁1—12。難以斷定其大體時代。上述氏族中,有的可能是存在於三皇之世的。後代所謂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烈山氏),是舉不同歷史階段之影響大者、强者,他們分别在一定階段中形成一個中心,分别代表了中國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不同時期的歷史。
以上對“三皇”的有關文獻傳説、“皇”字的本義、遠古時代氏族首領的冠服在後代祭祀冠服、舞蹈冠飾、知天文者和貴族、武士等的冠飾,以及周邊少數民族首領、北美印第安人酋長冠飾等當中的遺存,及遠古氏族、聚落首領的形象在上古玉器、銅器上的反映,作了一些探討。總之,我認爲“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本爲遠古氏族、聚落之稱,因其在經濟發展和文化方面的特徵分别反映了中國農耕聚落階段和中心聚落階段的歷史。後來的傳説中將這三個時期的創造發明皆分别集中於一人之身,故也用來指這三個氏族的傑出首領。“皇”本爲堯舜之前氏族、聚落首領所着羽冠之名,故春秋戰國時人們把傳説中的燧人、伏羲、神農統稱爲“三皇”。
我不認爲中國上古時代有過後代帝王那樣的“三皇”,但關於燧人、伏羲、神農是流傳有自的,春秋戰國時人稱他們爲“皇”,有民俗學的依據,在當時也有更多的文獻學的依據。有氏族、聚落,就有氏族、聚落首領。三皇五帝時代氏族、聚落首領的形象在史前的玉器、陶器和商周時代的銅器上有所反映。這是我們以後的研究中應予充分注意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