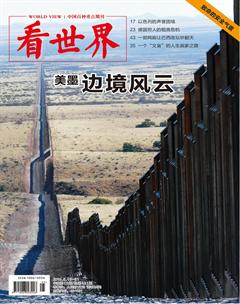伊拉克:IS阴影犹存
天气很好,清澈明晰。他们说,只要你向四周看看,你会发现周遭很安全——只要你能看到村子边一排排的树木,还有沙漠边缘最后的几处田地,以及夹杂其中的灌木丛。
但在冬天,白昼很短。一旦黑暗接替短暂的黄昏,从天而降,一切色彩和动作都会被统一的黑色所吞噬,恐惧也随之来临。这就是加里布居民所说的,并急切催促你尽快动身离开这个村子和地区的原因所在。
因为夜晚时分,恐怖又会重新回到这里。

村民们说,有时候狗会吠叫发出警报;有时候第二天早上会看到一些有人来过的痕迹;而且经常会在晚上听到大声嚷嚷的男人的声音,他们叫嚣着要杀掉那些反对“伊斯兰国”(IS)的人。
去年10月初,伊拉克军队收复了极端组织控制的最后一个核心据点,位于基尔库克西南部的哈维佳区。在打了几天的小仗之后,政府军宣布IS势力被彻底肃清。然而,对当地人来说,IS一直阴魂不散。
加里布位于哈维佳北部靠近扎布河的地方。这个村庄的名字的意思是“奇异的,异域风情的”。加里布原住居民有3000人,战后回归的只有500人。由于害怕夜间被IS袭击,牧羊人们都躲得远远的。光复后好几个月里,夜里没有电,没有光,恐惧的噪音从未中断。
那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盘踞在加里布的IS武装分子对这个村子简直是门儿清,大到每一条路,每一栋房子,小到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狗,他们都清清楚楚。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这个村的村民,彼此是亲戚,是邻居。这些人中以村边的纳西夫最为臭名昭著,大家都很怕他,他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时就已经聚集了一波追随者了。
部分IS武装分子在去年10月的小规模冲突中丧生,其他几个人逃到了土耳其。留下的人还在周边四处晃悠,他们沿着扎布河和底格里斯河进入到丛林之中,或是躲进马哈茂德山脉和沙漠山谷之中。早在IS倒台之前,这些人就已经修好藏身之所,挖掘隧道,储藏物资了。
他们又回来了
现在,他们晚上会回来,要么走路来,要么乘船而来,悄悄地回来复仇。村民们不得不轮流放哨,并在每栋房子上都装上了灯,这样谁过来了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過如果就此以为白天是安全的,那就太大意了。侯赛因·阿拉夫中校的儿子阿里就是在白天膝盖中弹的,他的两个表兄比他伤得更惨。

由于害怕夜间被IS袭击,牧羊人们都躲得远远的
腿断了之后,阿里只能躺在基尔库克的一个房子里,在2014年他们全家逃离基尔库克时,他可没想到有一天会以这样一种状态回来。为了防止纳西夫他们再回来,阿里他们把纳西夫的房子给拆了,因为这个人在阿里他们眼中就是个害人精。
在侯赛因父子出生的那个时代,加里布像整个伊拉克一样,有着明确森严的等级体系:逊尼派统治这个国家。这个传统从奥斯曼帝国时代开始,到一战后英国人将这里的三个行省合并为现代伊拉克以来,都是如此;在之后的萨达姆时代,也是如此。
哈维佳的逊尼派如同土皇帝一般,尽管他们很多人都是农民,但依然受教派庇护。阿里·侯赛因一家跟萨达姆的第一任妻子的家族颇有关系。他们那会儿喜欢谈论本家叔叔、后来当上伊拉克情报部门官员的谢里夫·穆罕默德,而这位叔叔后来还模仿起萨达姆·侯赛因的做派。
但随后伊拉克因为两伊战争和科威特战争陷入混乱局面,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仅仅三周就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谢里夫·穆罕默德直到最后一刻依然还在为萨达姆高唱赞歌。而那些他们眼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资本家纷纷为美军充当“带路党”。眼看着时局要变天,随着伊拉克最后一支武装部队被解散,这些曾经的统治阶层开始变身。
几乎在一夜之间,曾经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变成了待宰的羔羊,这些被村民们嘲笑,被情报机关怀疑的极端主义者开始变得无法无天。在加里布,不管是哈维佳还是其他村子,这些人开始明目张胆地加入极端组织。虽然他们是官方通缉的恐怖分子,是美军追杀的目标。但是时局舆论开始转变,即便是在巴格达,也有很多伊拉克人对美国人各种不满。
在加里布,后来成为IS头目的侯赛因·纳西夫成为了这批政治失意者的旗帜人物,他到处派发来自沙特的传教磁带和DVD,并将自己的年轻追随者转移到地下。村子里的人说,纳西夫后来辍学了,他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但这个人很聪明,美国人曾多次将他拘留,但他在巴格达有很强的背景,总有支持者帮他保释。
最终,在2014年夏天,他又回来了,不过不再是以犯人身份回来的,而是新的统治者。他穿着金色长袍,在30个表兄弟组成的私人安保部队的簇拥之下,回来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可以决定加里布所有人的死活,这种滔天权势一直持续到去年10月。
纳西夫家的流血事件
去年12月的那个周三下午,阿里回忆说,他和其他人一起走进了纳西夫曾经住过的房子。房子已经空空如也,他们推倒了橱柜,碗碟打碎了一地,然后继续下一栋。下一栋还是空的,不过阿里看到村民把房子给烧了。
“一开始,我们高喊:打倒IS!”他说,“然后我们中最年长的阿卜杜拉赫曼·谢里夫说:把枪和手机给我,我也要去看看!我们当时就一把AK-47,我们还捡了一些石头。”

留下的lS武装分子还在周边四处晃悠,他们沿着扎布河和底格里斯河进入到丛林之中,或是躲进马哈茂德山脉和沙漠山谷之中
阿卜杜拉赫曼在前面带路,纳西夫家的门已经敞着好几个星期了。不过门后面堆了一些石头,以防老是被风吹开。村民们把门推开,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这时传来一阵汤和新鲜面包的味道。然后阿卜杜拉赫曼打开了最后一扇门,这是通向厨房后面储藏室的门,也是IS武装分子的藏身之处。就在这时,那些武装分子突然冲了出来,“他们看上去像怪物一样,头发和胡须蓬乱冗长。他们当即开火,”阿里说,“阿卜杜拉赫曼当场中枪倒地,死了。侯赛因大声喊着:我来拖住他们!大家快跑!快跑!”
阿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他瞥见自己的表弟正站在前门,张开手臂,手里攥着一块石头。阿里听到了枪响,然后只顾着埋头逃命。后来他们找到侯赛因时,他的眼睛和胸膛各中一弹。“我当时也就离着有30米远,”阿里说,“有个人拿枪瞄着我,啪,打中了我的膝盖。”
枪声惊动了整个村庄,村民们都跑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只能缓缓靠近,因为远处还有枪响。IS武装分子相互掩护着逃离。阿里把自己藏在半米高的土墙后面。“那个开枪打我的男人朝我跑过来,并蹲在了墙的另一边。”
阿里逡巡在墙边。“我看到一滩血开始往外飙,那都是我的血。他记得那些IS分子声嘶力竭地吼道:“这就是把我们赶出家园的报应!”阿里说,他们至少来了五个人,他都能认出他们的声音。他说,蹲在土墙另一侧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奥马尔·纳西夫。作为IS“安全机构”的负责人,纳西夫曾经担任阿巴斯及周边地区的处决者。这项工作令他非常骄傲,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听他吹嘘过:“如果需要的话,我连自家兄弟的脑袋都砍,砍头可是一种享受呢。”
有一次,大家回憶起纳西夫在时的往事时说道,纳西夫三岁的女儿每次在他回家时都会跑过来紧紧拥抱他。但是有一次,他在执行完处决后回到家中,身上的血腥味还未散去。女儿明显动作慢了很多,她慢慢走近,没有抱自己的爸爸。之后整整一周都没有靠近过纳西夫。
阿里说,天气开始变得愈加黑暗,愈加寒冷;但是IS武装分子还在不停地开枪。不过随后,悍马越野车的轰鸣声突然传来,伊拉克军队驱车赶来。顷刻之间,AK-47的枪声夹杂在14.5毫米重型机枪的火舌中,喷薄而来。政府军来了,极端分子们彼此招呼着撤退,一个接着一个在枪声中逃之夭夭。
阿里依然危在旦夕。所有人都认为阿里肯定会死的。“如果我当时挥手,士兵们会立刻朝我开火。”这些政府军士兵经历过太多次伏击,心理都有阴影。阿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双手颤抖着给村里的一个朋友发短信:“告诉政府军我正躺在土墙后面,离悍马就30米。”发信息的时间是下午6点37分。
大家终于找到了阿里,然后开车把他送到医院里。与此同时,政府军士兵不得不立即前进:因为有农民发现七个IS士兵静静地漂浮在扎布河上。这一次,政府军没打算活捉这批人,而是打算把他们全部干掉。
谁也不想被找到
恐惧在伊拉克以各种形式四处传播。在哈维佳的三年多时间里,大多数人对IS武装分子非常害怕。这种恐惧感一直萦绕在心头。不过这种恐惧感似乎是可以进行折算的,比如阿德南·谢里夫的两个兄弟被杀后,他就对这个恐怖组织毫无丝毫畏惧了。
去年秋天,当政府军打到这个地方时,IS负隅顽抗,不过打到加里布时,这群恐怖分子一溜烟都跑了。有意思的是,就在逃跑前几个小时,纳西夫还在大声演说:“我向你们发誓,胜利离我们们越来越近了!我发誓!”然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是政府军还要继续进军,只有当地部族民兵驻守了下来。于是恐惧再度袭来。一个牧羊人描述他的一段遭遇。某天晚上,正在村外和自己的羊熟睡中的牧羊人突然被人叫醒,他发现自己已经被10个IS恐怖分子围住。他们问:“政府军在哪儿?你有手机吗?多少钱?把它卖给我们!”
牧羊人说自己需要这个手机,如果手机没了,自己啥都干不了了。“不,不,”这群人生气地说,“我们给钱的!”这群人像喝醉了一样。然后突然间又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没拿走手机。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侯赛因两兄弟的追悼会正在进行,连着三天,不断有人来悼念他们。来了很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接受采访时愿意透露姓名,“如果IS的人知道我们来这里,肯定会杀了我们的。”一个老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