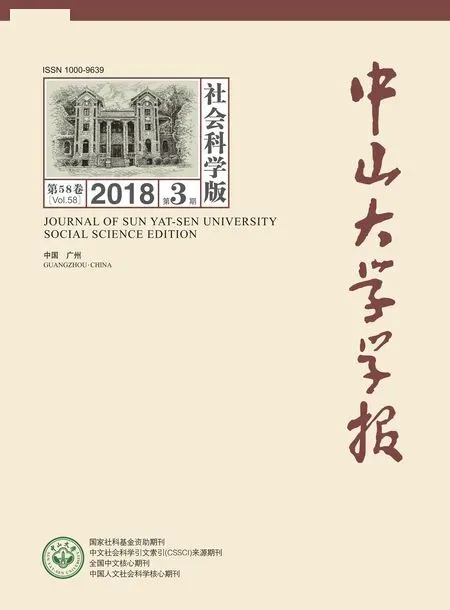鲁迅视野中的香港悖论*
朱 崇 科
鲁迅与1927年香港的遭遇既是一种偶然,也是必然:如果不是他从厦门到广州而是直接到上海,又或者他从广州不是去了上海而是重回北京终老,可能就与香港擦肩而过,但实际上这都是假设。毕竟1927年,鲁迅三次涉足香港,而且事后都有文字记录:1月17日他由厦门大学转赴中山大学途中驻足香港,18日晨离港,有关经历描述收入《而已集·略谈香港》中;2月18—20日,鲁迅由许广平等陪同前往香港作了两场演讲,分别是18日《无声的中国》(收入《三闲集》)、19日《老调子已经唱完》(收入《集外集拾遗》);9月28日,许、鲁二人离粤赴沪,又一次途经香港,有关感想收入《再谈香港》(收入《而已集》)。除此以外,鲁迅还有多篇杂文涉及香港,如《谈“激烈”》(收入《而已集》),《述香港恭祝圣诞》、《匪笔三篇》(收入《三闲集》),《“抄靶子”》(收入《准风月谈》)等。从此角度看,香港承载了鲁迅先生过于丰富的联想、判断,甚至可能迷思。尤其是结合后来香港在各个层面的强势崛起与慢慢由盛而衰,鲁迅的论述变成了让(港)人爱恨交加的文化遗产。
相较而言,有关鲁迅与香港的关系研究亦相对丰富,但主要议题如下:
第一,到底是谁邀请鲁迅赴港?一般以为,根据《鲁迅日记》,邀请人当为香港青年会,但后面的说法有所不同。主要探讨者包括记录者刘随的《鲁迅赴港演讲琐记》*见香港《文汇报》1981年9月26日第13版。,认为是当时香港大学的黄新彦博士邀请;而刘蜀永的《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见《香港文学》1993年第10期。,提出是赵今声邀请的;中山大学教授李伟江则在《鲁迅赴港演讲始末考》*见《鲁迅世界》(广东)2001年第3—4期;后收入氏著《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持类似观点等。相对晚近的论述则见于张钊贻《谁邀请鲁迅赴港演讲?》*见《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他认为赵今声之说虽有漏洞,但更符合可能的历史状况;而林曼叔则在《鲁迅赴香港演讲经过的几点质疑》*见《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中,认为赵今声之说漏洞百出,刘随之说更可靠;而后张钊贻又撰文《赵今声邀请鲁迅访港一说的若干佐证——回应林曼叔先生的质疑并分析黄之栋的辩解》*见《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进行回应、反质疑与辩解*张钊贻的系列论述收入其论著《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第二,讨论鲁迅杂文中香港作为“中介空间”的意义,可参看陈欣瑶《船舱、街道、客厅——鲁迅杂文中的“中介空间”》*见《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当然还有其他散见于书中的论述,包括鲁迅之于香港形象建构的负面性等,以下会论及,此处不赘。
上述研究增益我们的认知,但也可以继续开拓思考,为何香港之于鲁迅如此重要?鲁迅对香港的认知到底有着怎样的洞见与不见?在鲁迅对香港的迷思中,又有着怎样的悖论?而耐人寻味的是,鲁迅的香港遭遇两次都和广州*有关分析可参拙著《广州鲁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有关,具体关涉为何?
一、鲁迅的香港中介
如前所述,鲁迅对香港的认知算不上是经过长期调查或居住得来的丰富/准确的实践经验,却偏偏多次提及且振振有词,颇有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感;同时,恰恰是因为涉之未深,鲁迅对香港的论述中既有超越性洞见也有一些不见/盲点。由于对香港缺乏充分的历史现场感悟与现实体验,因此想当然地产生“中原心态”。“他们将在国内适用的思想原封不动地搬到香港来,视之为天经地义,这其实也是中原心态的不自觉反映”*赵稀方:《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88页。,值得我们仔细探勘。
(一)中华高度:以香港观照中国
毫无疑问,被尊称/谥号为“民族魂”的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现实存在、未来发展等都有着相当浓烈的关怀和大爱倾注,关于香港的发言及书写,因此也首先是他这种精神意志的体现。当然,如果拓展开去,鲁迅思想的关注范围不只所谓的“中华高度”,而实际上具有更强的超越性和开放性。他对中国传统、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思潮都有反思、批判和部分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一言以蔽之,鲁迅的思想是属于世界的。但限于篇幅,此点并非本文焦点,我们还是先立足于其中华高度的角色和意义。
1.名实的辩证。从鲁迅对中国关注的角度看,香港首先是此视野中的对象和组成部分。如人所论:“鲁迅在香港的两场演讲,内容很严肃,也不单讲给香港人听,反正能入场的香港人并不多,他要借这个英国殖民地南方小岛,作为他对自己国家的关注与提醒——香港历来都能给人提供许多发言空间。”*小思:《选文思路》,小思编著:《香港文学散步》新订版,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 第27页。可以理解的是,在1927年2月18日的《无声的中国》中,他首先批判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对当时中国人个体及群体发展的滞碍:“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⑧ 鲁迅:《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5页。不难看出在新的民族主义视角把脉下的中国痼疾。为此,他也想在香港烧一把火,鼓励青年们奋勇前行:“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从这样鼓励中不难发现鲁迅的世界眼光。正是要让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才有期待,有焦虑,有批判,也有鼓励。

19日的《老调子已经唱完》继续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糟粕(所谓“软刀子”)的大力破除和庄严宣判,同时也警惕外国人对此类中华文化的褒扬,并犀利指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鲁迅:《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6页。甚至在《述香港恭祝圣诞》一文中,同样也以文言文吊诡地对香港尊孔以及弘扬“国粹”进行嘲讽。这符合新文化运动前后,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持猛烈批判的态度及原则。
2.香港个案。如人所论:“鲁迅终竟是鲁迅,无时无地不关注着中国人,特别是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和坎坷命运。”*林曼叔:《鲁迅赴香港演讲经过的几点质疑》,《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毕竟鲁迅笔下的香港,作为当时的英国殖民地自有其变异和特殊性,即使单纯从华人及其境遇的视角也可见一斑。其中相当经典的论述则是来自于《再谈香港》:“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565,447页。鲁迅先生担忧和呈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沦陷后的惨况。这是宏观视角,揭露的是殖民地政治运行机制和土人的悲惨境地。
如果从相对微观的视角,也可以看出鲁迅敏锐的后殖民(postcolonial)视角。统治者貌似文化大一统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强调,实则等级森严,主次区分,内外有别。我们不妨以“搜身”为例加以说明。《略谈香港》中,鲁迅提及英警搜身讲英语的西装男,鲁迅评价道:“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565,447页。将之与更早时期的中国历史事件相比,显示出殖民统治中的等级森严和特权意识,相当辛辣。《“抄靶子”》一文中,香港成了与上海对比性的存在:“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竟谓之‘抄靶子’。”*鲁迅:《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第215页。表面上看,鲁迅对香港的批判程度轻些,实际上大前提就是大力批判殖民地/租界的不平等/歧视恶习。易言之,鲁迅对香港殖民地身份/景观的批判有一种片面的深刻:它既有自己的问题,同时又可能成为大中国的典型未来。
(二)中原心态:以中国诠释香港
有论者指出:“通过与‘上海’进行参照,鲁迅杂文以类似‘移情’的方式辅助其香港经验的匮乏,试图探入‘香港’深处别获洞天。借此而发的曝露与讥刺往往立足于报章奇闻,显示出情非得已抑或有意为之的‘隔靴搔痒’。而恰是‘隔靴搔痒’的尴尬位置,方才使鲁迅杂文跳出香港场域的干扰, 在诸多层面上‘一语中的’, 而身处多重中间位置、肩负多重中心/边缘身份的香港空间,也在鲁迅的杂文书写中成为一方醒目的‘异托邦’。”*陈欣瑶:《船舱、街道、客厅——鲁迅杂文中的“中介空间”》,《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平心而论,鲁迅对香港的不少认知可谓隔靴搔痒,甚至也有误读,简单而言,可以称之为 “中原心态”。
1.“畏途”香港。整体而言,根据鲁迅的自我描述,其后两次香港之行颇多不快:比如演讲前的干涉,发言稿刊登时候的审查,还包括遭受刁难(据说没有给小费贿赂),再加上鲁迅心中原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爱国心炽热,导致他很多时候因为敏感和愤怒,而对香港的描述戴上了有色眼镜,往往显得缺乏平常心。
比如《匪笔三篇》从香港《循环时报》择录三则消息。他自己写道:“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无任欢迎。但此后拟不限有韵无韵,并且廓大范围,并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鲁迅《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44页。易言之,他的摘录更多是负面材料,实际上这三则消息分别涉及了:撕票绑票、以吕洞宾名义讹诈钱财、流氓威胁群殴女招待。毫无疑问,这都是相当恶劣的行径:杀人放火、坑蒙拐骗、(性别)暴力抢劫。但不必多说,这也是以偏概全。
2.繁复香港。某种意义上,将对传统文化猛烈批判、新旧文化高度对抗的大陆新文化运动模式搬到香港语境中来自有其限制,毕竟彼时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已近30年。从更宏阔的语境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在大中华区其实有各自的特点与模式,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在当时的马来亚,推动新文化运动最得力的人士恰恰是操持文言文、视野开阔的旧派文人,香港的状况也有点类似。如赵稀方所言:“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国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一味讨伐中国旧文化,不但是自断文化根源,而且可能会造成旧文学灭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赵稀方:《小说香港》,第90页。
考察《略谈香港》中引述香港总督金文泰的有关粤语文字,其第二条讲述的其实是如何把相对繁难的中国国故变成有利于后学学习的轻便学问,第三条则是将中华传统发扬光大,推广到世界范围中去。这其实和鲁迅一贯主张的 “取今复古”理念惺惺相惜。易言之,剔除传统糟粕的韧性实践,在新文化立足未稳时高扬批判大纛是对的,但去芜存菁地处理传统也可以同步共振,只是不要沉入故纸堆、迷恋旧尸骸即可。
鲁迅误读香港的另一原因在于,他缺乏对殖民地国人/华人的更为深切的“理解之同情”。殖民者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固然有借助有关糟粕奴化华人的险恶用心,值得警惕。如他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所言,“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鲁迅:《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326—327页。。但现实往往是更复杂的存在。相较而言,无论是彼时的香港还是马来亚(含新加坡),大多数殖民地华人本身往往地位低下(如苦力等),他们必须在主流/官方文化以及异族多元文化的挤压中找寻并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不该忘记,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本身也必须是溯源自中华文化传统的,而同时中华文化传统也往往成为当地华人反抗奴化、葆有中华性(Chineseness)*有关分析可参拙著《“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的重要凭借。“清末怪杰”辜鸿铭(1857—1928)青年时已拥有很深的西方文化造诣,后来确认自己的华族文化身份后疯狂迷恋中华文化传统,乃至矫枉过正到令人瞠目的病态个案,可以部分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这并不是鲁迅第一次在保持对殖民地思考的洞见之余的不见和偏见发作。1926年,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他和校长林文庆(新加坡峇峇华人)之间的冲突亦有此方面的原因。其中当然有经济、人事和学术政治的纠缠,但有一点,鲁迅并没有设身处地或换位思考殖民地华人建构中国性的不易与悖论。这更是一种文化冲突——鲁迅坚持否认了传统的合法性,借此来捍卫新文化来之不易且并未牢固的地位,而这当然与需要以中华传统安身立命的林文庆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个差异乃至冲突其实更是两种思想模式的对抗*具体可参拙文《林文庆与鲁迅的多重纠葛及原因》,《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二、香港的鲁迅迷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鲁迅和香港的关系却因了香港的崛起、兴盛、1997年回归和部分衰落而又变得起起伏伏。但很多时候,有关认知并不因为后顾而显得高明,在香港语境里也不乏对鲁迅认知的迷思。当然反过来,也可以部分彰显鲁迅自身的迷思。
(一)鲁迅如何把脉/升华香港
如前所述,鲁迅对香港的描述和批判既有其中华高度和敏锐洞察,同时又有其中原心态观照下的误读。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文化穿透力,他的书写效力被放大。而在1997年出版的《否想香港》一书中,香港本土学者开始反思并批判鲁迅。在《再谈香港》中,“最重要的地方在于鲁迅首先指出,除了华夷以外,香港还有‘第三种人’,无论是‘高等华人’还是‘奴气同胞’,他们实质上都是因为洋人的统治而变了质的华人,他们自然也成了鲁迅鞭挞的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跟着的论述里,出现的不单是华夷有别,攻击的目标也不一定是夷人,甚至不单是变了质的华人,而是普遍的香港人”*引文为王宏志撰写,见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 第50页。。在他们的论述中,全体香港人都遭受了鲁迅论述的波及。
不必多说,这种香港本土认同的崛起与重新定位自然会对他者(含刻板印象)进行深入反思,毕竟鲁迅对香港的描绘中掺杂了不少恶感,恶化了香港的形象,使之成为了一个“恶托邦”。但同时,我们更要反思鲁迅之于香港的升华意义。
1.如何再现香港?需要指出的是,在1920年代呈现出一个客观真实的香港并不容易,鲁迅先生以其个人体验(尽管不无误读)再现了香港,为香港的历史镌刻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从相对单薄的香港文化史建构层面来讲,是鲁迅的影响力顺便提升了1920年代香港的知名度——恰恰是鲁迅等文化名人的南来,对香港场域的填充,部分涤荡了“文化沙漠”的蔑称;同时坦白言之,找寻香港文化的本土源头并不容易,甚至有一种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的虚妄。唯其如此,本土文化建构者还不如好好地借鉴/利用香港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或节点的价值。反过来退一步说,鲁迅不无片面的对彼时香港的呈现也是其本来面目的一种,因为它亦有藏污纳垢之处。
2.鲁迅风格。有论者指出:“鲁迅杂文对于‘香港’的处理方式投射出鲁迅杂文的一类写作方法:通过对于中间物的发现、选择与叙述,完成个人经验的‘越界’与日常生活的‘杂文’化。在这一写作方式中,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经验,越界成为支撑政治书写与文化启蒙的利器之一。”*陈欣瑶:《船舱、街道、客厅——鲁迅杂文中的“中介空间”》,《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鲁迅杂文的一般风格往往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是杂文篇幅所限,或者是杀伤力效果的考量,或者是写作习惯使然,鲁迅对所知有限的香港呈现、批判和投射观点不得不借助其他时空的体验与感悟,比如上海、广州,乃至历史文化知识。同时,由于香港又是英国殖民地,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鲁迅对香港的审视又多了几分严厉乃至苛刻。这也是出于“爱之深,责之切”的关怀所致。在我看来,懂得这一点后,鲁迅之于香港更应该是可资借鉴的资源与文化财富。
(二)香港如何阻隔鲁迅
如果反思鲁迅对香港的恶感来源,我们不难发现,彼时的香港其实也屡次阻隔鲁迅。
1.审查制度。如人所论:“(1) 香港殖民地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仍然执行省港大罢工时制定的新闻检查制度;(2) 审查不单是新闻,也包括副刊;(3) 审查的内容不止针对民族主义与殖民地矛盾斗争,也包括保守文化与文化革新的矛盾斗争;(4) 审查的落实已不限于出版前的审查,而是已落实在香港中文报纸编辑的自我审查上面。”*张钊贻:《谁邀请鲁迅赴港讲演?——新材料的考辨与问题的再辨正》,《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鲁迅在1927年香港演讲时遭遇过审查。在《略谈香港》中他写道:“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③④ 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446,497—498,565页。而在《谈“激烈”》一文中,他又借助广州执信学校学生经过香港时的遭遇对此加以批判。鲁迅引用了原报章文字:“搜获激烈文字书籍七本。计开:执信学校印行之《宣传大纲》六本,又《侵夺中国史》一本。此种激烈文字,业经华民署翻译员择译完竣,昨日午乃解由连司提讯,控以怀有激烈文字书籍之罪。”③

而在《再谈香港》中,鲁迅又详细描述了他在海关检查时被刁难勒索的经过,最后揭底牌时茶房提醒他“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于是鲁迅感慨道:“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④平心而论,1927年9月底的鲁迅,面相在盛夏时更显得枯瘦(如图,在广州西关,1927年8月),加上人长得矮小,的确容易引起误会。但这种来自殖民地异族统治者的歧视与勒索,恰恰是让敏感的鲁迅加倍痛
恨的,所以他的描写与挞伐也毫不客气。
2.广州比照。如前所述,鲁迅到香港的三次实地游历都和广州有关,也可以视为广州鲁迅的封套(开端、进行与延续)。
鲁迅的第一次香港经历是从厦门到广州前的经停,易言之,鲁迅到广州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期待和爱人许广平团聚,虽然限于老师身份,他给出的更冠冕堂皇理由是和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革命阵线*具体可参拙文《爱或革命的偏至——鲁迅1927年来穗动因考》,《粤海风》2014年第2期。。所以,鲁迅对于途中的一点不愉快,会因为这种思念和日益逼近广州而相对淡化乃至忽略的。
鲁迅的第二次赴港是在他脚伤未愈的情况下前往的。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传播新文化知识的热忱和爱国心切,而另一方面,不容忽略的是,陪同兼翻译的恰恰是爱人许广平。之前的脚伤其实就是鲁迅“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爱情发作——游玩时从越秀山高处跃下伤足。实际上,彼时的广州鲁迅寄居在熙来攘往的大钟楼上,缺乏跟许广平单独相处的空间,所以香港之行其实也为许、鲁的爱情焦虑*具体可参拙文《爱在广州:论鲁迅生理的焦灼与愉悦》,《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找寻一个出口。颇有意味的是,在《略谈香港》中,鲁迅还专门表扬了那个船员的好心——提醒鲁迅注意安全并确保他无事。
鲁迅的第三次遭遇香港是他离穗赴沪的经停。此时的鲁迅和许广平静悄悄地离开广州,对于在上海的前景可谓前途未卜,甚至忧心忡忡。而有关“查关”不只是一个程序或过场,甚至还有些故意刁难乃至歧视的意味。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再谈香港》中的愤怒,这也是他对香港恶评最盛的一次。甚至到了《谈“激烈”》中亦有广州和香港的对比,两地文化、语言相似,但统治结构不同,借此凸显殖民统治的罪恶。
但无论如何,鲁迅依然是疗治香港历史文化薄弱的一副好药。虽然好比一把利剑,他亦有因锋芒毕露而伤及无辜之处。陈国球曾经写道:“香港,我们的一代,就是这么一个失去自己身世的孤儿。我们的记忆,或许于大家族中话聚天伦时,不无少补;我们的失忆,正好把这段野外求生的经历忘记。香港,本是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陈国球:《借来的文学时空》,《读书》1997年第7期。认真地想一想,鲁迅的香港书写何尝不该化为香港(人)自我/本土的精神资源呢?
结 语
在鲁迅和香港1927年的遭遇中有着相当耐人寻味的悖论:虽然鲁迅到港只有三次,但关于香港的论述却丰富而集中,表面上看恶评居多。在我看来,香港之于鲁迅颇富悖论性:一方面,他借助香港观照中国,并在香港场域发声,呈现出中华高度;另一方面,由于他对香港了解不多,又有中原心态。但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之于香港至关重要:一方面,他巧妙把脉其问题并升华了香港的地位,包含文学史/文化史地位,尽管不无深刻的片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香港曾经阻碍或伤害过鲁迅。整体而言,今天的香港必须好好借鉴/利用鲁迅这个丰富的精神资源,充实并且坚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