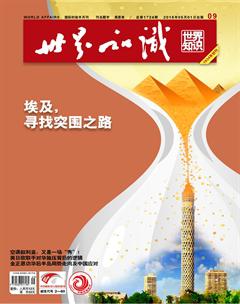从饮食习惯看中日文化差异
雷玉虹
生食与熟食——地理差异造成的文化差异
稻作文化是指稻作农耕以及伴随这种农耕而出现的一些相关文化现象。虽然日本的稻作文化源于中国,但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差异,中日两国已经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

日本皇居。
大米在中日两国都常常被作为主食,但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两国民众在饮食习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人喜欢吃凉的米饭,热腾腾的米饭出锅后要搅拌凉了做成寿司、饭团,并将其作为招待客人的高级料理。而且这种习惯从儿童时代就开始养成。幼儿园里小孩子吃的午饭便当都是凉的。从超市、便利店买的饭团、便当通常也是不用加热就直接吃的,过新年所做的菜肴也是做好后放在精美的食品盒内凉着吃。吃凉米饭在日本是普遍现象,而不能吃冷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的孩子自小就被灌输饭要热了才能吃、吃冷饭会生病的观念。如果将冷饭拿去款待客人,那是一种失礼行为。
中日两国民众在吃鱼的习惯上也有很大差异。日本人喜欢将鱼切割后直接生吃,或仅仅只是加点盐甚至连盐都不加整条烤着吃。在日本的高级料理割烹料理中,款待客人的最高礼节之一,是奉上由活的鲷鱼做成的生鱼片,叫生造鲷鱼。将活鱼的肉切割好后放在鱼骨上,看上去还是鱼的形状,但却可以将鱼肉一块块地夹下来蘸着芥末酱油吃。如果那条鱼的嘴还在一张一合地动,说明鱼新鲜,也代表主人对客人的诚意。这与中国人吃鱼的方法截然不同。在中国人的主流观念里,吃生鱼是不卫生的、野蛮的。拿生鱼肉去款待客人,在中国人的传统饮食文化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中日两国民众都以大米为主食,所以吃饭时都需要以菜肴与之相搭配。但在菜肴的烹调过程中,两者的喜好又有很大区别。中国人是“用味蕾”吃,比较注重菜本身的味道。而日本人则是“用眼睛”吃,更注重菜的外形是否美观。中国菜的主要做法是加上各种调味料的煎炸炒煮,虽然味道有差别,但从技术层面上来看,饭店里的菜与家庭里的菜的做法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日本料理中的家庭料理与饭店的割烹料理、料亭料理,不仅在味道上差别很大,在做法上也是截然不同的。日本料理中的生鱼片的味道不仅仅取决于材料本身是否新鲜,还取决于厨师的切割技巧如何。经过严格训练、技术娴熟的厨师切割出来的生鱼片,与没有经过训练的切割出来的无论在外观上、口感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割烹料理中厨师的技巧表现为其刀工的娴熟程度。日本高档菜中的怀石料理,讲究的是如何将素材的单一味道料理出来。而中国的大菜,不论是八大菜系中的哪一派,还是通常小饭店里的菜或是家里的菜,都是加入各种佐料,讲究的是最终出锅时的味道。中日菜肴的不同可以从中国的麻婆豆腐与日本的一品豆腐略见一斑。麻婆豆腐中放了大量的香辛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我们把做好的麻婆豆腐送进嘴里时,我们感受到的是香辛料的味道,而不是豆腐本身的味道了,因此香辛料的如何搭配就显得很重要。而日本的一品豆腐则只是在生豆腐上加些调味料,我们吃到的还是豆腐的味道,因此,对素材的要求就显得比较高。
总之,中日两国的饮食习惯是有巨大差异的。这种差异可能源自两国之间地理、文化的不同。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戴国煇先生认为日本是一个四周被海水包围的岛国,海水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消毒池,起到杀菌的作用。同时日本属海洋性气候,一年四季天气温和,气温不会发生剧烈变化。而且新鲜的鱼从船上到餐桌的时间比较短,能保持鱼肉不腐烂变质。气候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独特条件为日本吃生冷食物提供了可能。而中国属于以陆地为主的国家,国土辽阔,大部分地区离海比较远。由于运输上的限制,也因为气候上的原因,使得中国人将不吃生冷食物作为保持健康身体的生活智慧世代相传。可见,不同的生活习惯源自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不同的人文环境。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中日两国人民往来的频繁,彼此在饮食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增多。现在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能吃到原汁原味的日本寿司,新鲜的日式生鱼片也成了中国百姓桌上的美食。同样的,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不仅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烤鸭,还能尝到新鲜的上海大闸蟹与荠菜馄饨。许多日本人喜欢上了中国菜,饺子与拉面已成为不少日本人的日常主食之一。科學技术的进步,使得通过人工手段改变自然风土的条件成为可能。饮食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中日两国普通民众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当然这种交流并不足以解决彼此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横饭与竖饭——中日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日之间在饮食习惯上还有横饭与竖饭的差别。饮食习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反映。中日两国由于地理历史上的差异,形成不同的食物爱好与生活方式,也造成了两国民众之间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上的巨大差异。日本作家堀田善卫先生曾在1973年出版的《讨论日本中的亚洲》一书中提到横饭与竖饭问题。现在,横饭与竖饭已经被用来比喻日本式与外国式两种不同的处世方式。在这里的横是指横式文字,竖是指竖式文字。日本的书籍报刊通常是采用竖式文字方式排版印刷的,而其他国家的书籍报刊通常是用横式文字方式排版印刷的。因此横竖两种不同的文字排版印刷方式在这里也被用来比做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方式。竖饭是指日本人同伙一起聚会吃饭时,大家拼命喝酒,吵吵嚷嚷,边喝边闹的情形。日本社会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日本人平时必须循规蹈矩,只有在每年的新年会、忘年会以及其他一些公司或部门内部举行的聚会上,上下级、前后辈才可以平等地一起喝酒猜拳。这种只限于自己人内部、吃竖饭的方式被认为是日本人发泄日常工作生活压力的一种途径,在这种场合即使胡说八道、喝醉酒也不会被追究责任。所以在岁末时日本的地铁站里经常见到喝醉酒倒地而睡的工薪族。这在日本人眼里是见怪不怪的事。
横饭里的横是横式文字的意思,也指横式的人际关系,在日本也被用来指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相对正式的饭局。据说,即使被日本国内认为比较国际化的驻外商社员工、外交官等,也会感到这种正式饭局是一种负担。虽然离堀田善卫提出横饭与竖饭的讨论已经过去了40余年,可今天的日本社会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曾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翻译、现众议院议员大野功统曾专门在自民党总部以“要在国际社会中生存,横饭优于竖饭”为题进行演讲,主张日本人为了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应该改变喜欢在日本人的圈子之内交往的吃竖饭方式,积极地与用横文字的外国人交往,吃横饭,通过交流獲取有用的信息。吃横饭与竖饭这种饮食文化的差异引起的行为差异已经被提到日本是否真正走向国际化的政治层次。
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之间的吃饭则大体是横饭型的。中国人比较喜欢横向的人际交往,参加各种聚会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拓展横式的人际关系。因此,中国人大多不但不会对与陌生人吃饭感到局促,而且通常还把与陌生人吃饭当成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也许因为是为了扩展交往而与朋友吃饭喝酒,因此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喝醉酒、胡说八道,就有可能会失去个人尊严,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所以,中国人的吃饭通常是一种社交的行为,而非仅仅是一种释放压力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喝醉酒倒地睡在大街上不仅是失礼行为,也会伤及自己的名誉。
对此,戴国煇先生提出横饭与竖饭不仅是横文字与竖文字的问题,也可以说还是指以横的关系吃饭还是以竖的关系吃饭问题,反映的是中日两种社会之间不同的思维方式。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社会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日本人把等级制看作是正当的而且可行的社会结构,并以此作为解决各种问题的出发点。日本人喜欢吃竖饭,表明了日本社会内部是一种竖式的人际关系,在这里下级要服从上级、后辈要服从前辈,同时上级、前辈又对下级、后辈负有一定的责任义务。这种竖式的人际关系使得日本的公司或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得到增强,同时也反映了日式的承担责任的方式,即通过集体负责的倾向,减轻个人责任。竖饭被活用,拥有强化组织机能的作用,这是日式文化的特点之一,但这种竖式的人际关系是以牺牲个人的主张与权利为代价的。而中国则是讲究横式人际关系的社会。与日本社会相比,在中国,个人的主张比较能够受到社会支持,个人的责任也比较能够受到重视。两国在家庭财产分配上的差异,也佐证了这一点。中国的家产诸子均分制与日本的家督继承制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社会更看重的是个体的利益,所以中国父母的财产大多采取子女均分的方式。而日本社会更看重的是集体,即“家”这个组织的利益,所以日本的财产一般由长子或幼子继承,而不是子女均分。
沉默与做声——中日社会的差异
中日之间除了饮食习惯、思维方式不同之外,对自然的感觉、金钱的感觉、语言的使用习惯乃至美感等都是不同的。日本的木式建筑、家具大都使用本色,日本的皇居、神社的建筑大多也使用原色,朴实无华。而中国人大多喜欢在家具上漆上各种颜色。中国的庙宇皇宫大多喜欢涂上富丽堂皇的颜色。从以黑白两色为主基调的精致的日本皇居与以红黄两色为主基调的金碧辉煌的北京故宫的强烈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两个国家文化上的差别。日本被称为国宝级文物的京都古庙里的土色茶碗的质朴与北京故宫里色彩绚丽的瓷器表现出了两个民族不同的审美观。中国人喜欢鲜艳的、富丽堂皇的颜色,除了与我们多姿多彩的文化有关外,还可能因为中国是以陆地为主的国家,很多地方风沙较大,如果房屋与艺术品不涂上明亮的颜色,就可能被尘土吞噬而失去美感。而日本人喜欢素朴的原色也可能是因为日本属于海岛国家,尘土与风沙比较少,所以原木质朴的颜色之美能够得以充分体现出来。
日本社会还存在一种沉默文化。虽然日本也有少数民族,但大和民族占绝对优势。日本国民与文化主要是大和的民族与文化。可能因为语言是相一致的,日本国民的面孔脸型也差别不大,思维方式大致相同,因此彼此之间心灵相通,相互交流对话似乎就变得不太重要,沉默也成为了一种文化。日本的电车里非常安静。日本的大学课堂里学生发言也不是很踊跃。日本人在很多场合说话含糊,令外人摸不着头脑,但是日本人之间却能理会其中的意涵。由于日本社会等级森严,每个人都生活在信奉“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竖式社会秩序下,强调个人自我主张不利的观念似乎得到社会全体的默认。在这种情况下,对话与提出个人主张的机会就变得很少。因此,许多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都感受到一种来自外部的被强烈要求匿名生存的无言的压力。
而在中国社会中则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一说法,强调的是需要大声说话表明自己的主张,强调自我的存在。中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不仅国土辽阔,方言众多,各个地域之间、民族之间风土人情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价值观念、性格也有差异。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重价值观念的社会里,如果不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彼此之间就很难理解与沟通,就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此,中国人习惯于社交式的对话及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主张。有人指出,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移民社会的美国相似,如果不大声清晰地发言主张自己的权利就不能生存。对此,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学者冈仓天心曾在《东洋的理想》中提出,中国与欧美相近,个人主义得到承认。很多日本人感叹中国人与欧美人相似,都能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主张,所以比较容易与欧美人沟通。但日本人说话比较含糊,与外国人沟通时常会导致误解。连日本政府高官都觉得在与外国政要交往时存在沟通的问题,普通百姓更不用说了。
中日同属亚洲,同为黄种人,且两国地理上邻近,中国的汉字也在日文中得以使用,但无论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都多少有些陷入同文同种之窠臼、忽视对方相异之处的倾向。中日两国人民在许多问题上的思考方式、价值取向都有很大差异。日本许多研究中国的著作非常精细,资料收集也很全,但对中国的看法总体概括起来,却有“瞎子摸象”的感觉,把握不到问题的全貌。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可用“雾里看花”一词来形容,缺乏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研究与理解。中日两国官民在交往过程中,只有彼此都认知到对方的“异”,增进对对方的了解,准确地理解与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与目的,才能防止误解与误判,进而努力争取达到“同”的共识。
(作者为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