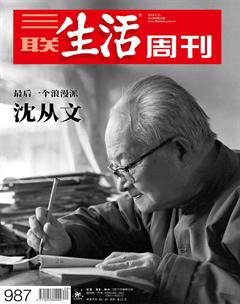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
维舟
战争中的平民
要表现一个大时代,最好是通过讲述一些个人(甚至最好是小人物)在那个年代的遭遇与命运——至少,在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中,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做法。然而,一直以来,历史写作却很少采用这样的手法,传统的历史书写偏重记录上层人物的功绩,现代史学则往往执着于通过宏观的整体性把握,来寻觅某种“历史发展规律”或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动力。按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只有诸如地理条件、社会结构这样的“长时段”因素才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至于短期内的政治事件都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朵朵浪花——个人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历史能产生多大影响?就算是牛顿在看到苹果落地的那一瞬间猝死,迟早也会有另一个人发现万有引力的存在。
不过,现代社会的精神其实背道而驰——一如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性就是短暂、转瞬即逝、偶然”。2014年,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历史学宣言》开篇就模仿马克思的口吻写道:“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强调长时段历史眼光的重要性,反对碎片化的研究和不顾长远影响的短期主义行为,这当然是对的,但一个现实是:对很多人来说,“历史的必然性”太过乏味,他们倒是对乱世中小人物跌宕起伏、充满偶然性和意外的命运抱有无限的兴趣。
历史人物的命运看似不过是个人的一些遭遇,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却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人们普遍对剧烈变动时期的“乱世儿女情”特别感兴趣,恐怕正在于它呈现了日常生活和抽象原则中不会出现的极端情形。不仅如此,我们也能从普通人具体而微的遭遇上感同身受地体会到那个时代的各种力量。

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及其著作《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正因此,《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显得与各种描述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大异其趣:它呈现的是23个高度真实的历史人物命运,根据其留下的资料缀成,其中“没有任何编造”。但除了真实性这一点之外,它读起来与其说像历史,倒不如说更像一部散点透视的历史小说。作者说得很清楚,书中力图呈现的“不是很多事实而是些个人,不是很多过程而是体验,不是很多发生的事件而是情感、印象和氛围”。一些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小人物在战争中第一手的目击记录,恐怕也更能让我们明白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哪怕你对战争本身无感,但或许对当事人的这些感受也会有共鸣。
顯然,在此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呈现出来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选择这23个人并不是因为刚巧只有他们留下的资料够完整,因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料档案早已汗牛充栋,但作者并未着眼于那些大人物,相反选择的基本上都是平民。这不仅是因为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更能引人共鸣,也因为一个特殊的时代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通常是军人们的事,平民一般不卷入。
这倒不仅是因为战士的荣誉感或道德观使然,也因为在以前的战争观里,屠杀平民既算不得英勇行为,对打赢战争也没什么用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殃及平民,开启了地狱之门,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但这种观念仍然存在。1917年5月25日,德军12架哥达双翼机空袭英国南部小镇福克斯通,造成290人伤亡,成为史上首次针对平民的战略轰炸,但英国战争大臣德比伯爵告诉上议院说,空袭没让英国损失一兵一卒,因此这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然而,“一战”中大量涌现的各种新型杀人武器(如机关枪、战略轰炸机、坦克、发射毒气弹的迫击炮和常被人忽视的铁丝网)使战争明显变得更机械、更非人性了。这不仅大大加强了对士兵和平民的无差别杀伤力,还意味着要赢得一场战争必须动员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这一负担当然落在平民肩上,他们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了。
这可是人们起初做梦都想不到的。欧洲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除了像普法战争速战速决的几场有限战争之外,差不多已经安享了一个世纪的和平,人们几乎无不乐观地相信理性、繁荣和进步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塔奇曼在《八月炮火》和《骄傲之塔》中所描述的,当时的西方上层人物普遍低估了受压抑的非理性力量在战争中爆发出来时所蕴藏的破坏力,要不然他们肯定会事先阻止这股最终让他们王冠落地的力量。普通人的反应也差不多,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完整,并且生活也总要继续,因而卡夫卡的日记现在读来有几分过于冷静的荒诞感:“德国对俄国宣战了。午后,我还去伏尔塔瓦河畔的游泳浴场。”但不然他还能怎么样呢?
战争中的梦游者
个人史的另一大好处是能让人体会到丰富的历史细节:1914年载满士兵的火车开行极慢,甚至慢到“在火车上常能采摘铁轨旁的花朵”;在英国,开战后街道变得异常冷清,像“配给”“集合”这样的军事术语渗入日常谈话当中;德国的学校里,爱国的校长禁止学生们在校使用外语;女性忽然开始流行穿军装。有残酷的细节(由于军法禁止带家属上前线,一个法国军官枪杀了坚持要和他一起走的妻子),也有荒诞的细节(曾是罗曼语教授的德军一等兵,和身为战俘的法国索邦大学教授因为对古普罗旺斯语诗歌中的虚拟语气用法吵起来)。不同国家的公民长久以来都被教育得太过深明大义,以至于把国家荣耀、民族意志看得比个人的生存更重要。如果说早先的年代很“美丽”,那么悲剧就是将美毁灭给人看。正是在这种非理性的争斗中,才开始有人起来怀疑所谓战争的意义。
正由于这样的心理落差,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一代欧洲人都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书名中的“美丽与哀愁”在很大程度上也委婉地暗示了这种想法:那个逝去的黄金时代值得追怀,随后的疾风暴雨则让人只剩下“哀愁”。
前些年一部描述“一战”的历史著作将当时的欧洲交战国统治阶层称为“梦游者”,但公平地说,当时的普通人也一样在“梦游”,而这种状态说到底并不是他们无知、平庸,而是因为人类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形:冲突空前剧烈、事件太过复杂,而需要驾驭的力量也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因而最终的结果几乎是所有人都不曾料到也不想要的——即便是战胜国,恐怕都希望宁可没有这样一场战争。这与其去责备当时的人愚蠢不知所措,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自己产生的非意图结果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缺乏经验应对。
当然,战争之所以打成这样,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它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尽管之前长期的繁荣进步给了人们安定和平的日子,但对很多深处底层的人来说,却意味着很难有望翻身。战争尽管粉碎了人类持续不断进步的信念,但正如本书所言,它也承诺了要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正是有些人欢呼的原因:因为这场战争代表了一项承诺,承诺巨大而激进的变化将会发生。”不幸的是,我们在历史上再三看到,这种行动固然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往往又会带来一些更为棘手的新问题。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没有熬到变革发生的那一天就倒下了。战争最惨痛的破坏力在于,在那种年代,最先倒下来的通常是一个社会的精华人物。《柏林记忆》以日记形式真实记录了“二战”时期德国柏林的生活,其中有句话让人难忘:“碰到这种时候,艺术家最难熬。年轻的若没有死,也全部被征召入伍,年纪大的全躲了起来。不消说,他们的观点是最与众不同的,所以不论如何,都很难生存下去。”这话当然也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个人来说,他们在那样一个剧变年代中选择大抵很少,而且不由自主,因而往往都很艰难。如果要记忆,那这或许就是这段历史中最值得记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