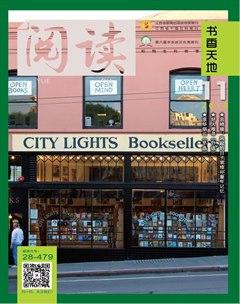理想村
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美国小说家、诗人。一生发表了大量体裁多样的作品,包括系列小说“兔子四部曲”“贝克三部曲”以及一些短篇小说集、诗集和评论集等。其中,《兔子富了》和《兔子歇了》使他分别于1982年和1991年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我们当然早就知道理想村的存在,只是担心在茫茫丛林中,飞行员菲德尔和米格尔无法找到空地降落。不到一个月前,一架补给机飞往更南端的路德教会。途中,黄昏降临,惶恐的飞行员飞向海边的灯塔。飞机把他带到了费罗山脉,在那里飞机坠毁,残骸(我们从天上看的)和煤场的废料混在一起,简直无法辨认。由米格尔驾驶的第二架飞机,更在云中和地面失去了联系。那些奇怪的云朵,都是由此地冒着蒸汽的河流直接蒸发形成的,天空看上去仿佛爬满大蛇。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米格尔不过是把电台调到了一个播放雷鬼音乐的频率,这个频率是由奥罗山脉中一个大型反政府组织不间断播放的。
我们降落了15分钟后,米格尔驾驶的塞斯纳飞机在天空出现了,只有虫子那么一小点儿,飞得也是那么不起劲。我们欢呼。甚至连当地的族长也欢呼起来,尽管他在城市做按摩师时历经无数苦难,并且要顾及自己的身份。
飞机的引擎早已熄灭,我们的行李—背包、冰酒容器—也早在机翼下拥挤不堪的地上堆成了小山。这时,族长和牧师才有些不情不愿地迎上来问候我们。降落处是村子的主街,飞机的后涡流吹掉了圆锥形屋顶上的茅草,很快引擎的噪音打断了人们的午睡。两位牧师,其中一个身材高大,面色苍白优雅,讲口齿不清的西班牙语。相比之下,另一个神父矮些,黑些,混血儿的天性躁动着,令他像久羁之马,跃跃欲试。族长当然有着纯正的印第安特征,尽管因为多年的城市生活而多少有些磨蚀。他围着鹦鹉羽毛制成的、敷衍了事的围腰,戴着彰显身份的猴皮臂章,还穿着一件灰色三件套马甲。花了些钱,米格尔跟着一群孩子把红色条纹的塞斯纳停到停机的地方。有几个孩子光着身子,有几个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之前去过的那些不理想的村子里的孩子相比,无一例外透着健康、欢乐的劲头,又不涉心机。这里没有乞讨,只有幼儿乌黑的眼睛里才微微看出一点对我们的装扮或女性成员时髦光鲜的城市打扮表现出的好奇之情。
我们被带到住宿的地方,几个男人正用他们独一无二的结绳法,把我们的冰酒器吊到房梁上。他们动作麻利,甚至我们当中的结绳专家奥塔格也望尘莫及。这个在藤蔓和纤维上建立起文明的部落,早在30年前就以结网、架桥和结绳记事的技艺震惊了早年的人类学家—他们的棕色手指一阵忙活,快结好时,一声大笑便从被绿烟叶染了色的嘴里冲口而出,一半是挑衅一半是庆祝。
我们休息了一下,然后被带着进行期望已久的观光。我们参观了洋蓟地和几亩棉花试验田,参观了一排大作坊,女人们正用村里的发电机驱动织布机,大批量生产传统图案的布匹。
我们还参观了一排小作坊,老人们用木棉树雕刻一成不变的长吻浣熊、水豚、美洲虎、蜈蚣,这些东西将在千里之外的机场纪念品店出售。
这样的工业,高个神父用他那柔软的加泰罗尼亚语解释道,当然远非完美,因为如此生产的雕塑,被认为有损万物有灵的神旨。我们在这儿是过路的。这些老人—神父用手掠过排架和老人们半秃的脑袋—只能雕刻祖先留下的样式。下一代人,他希望,能更多地摆脱传统,雕刻既有民族特色又能表现人类共同福祉之美的东西。这样的雕塑在机场商店里是否流行还有待观察。
“我们就是靠着摸索走到这里的,”他说,“我们并不轻视折中的道路,我们只把最终的目标奉为信条。”
毋庸赘言,最终的目标是自由、平等、博爱;工人掌握生产方式,从压迫下解放出来。简而言之,强权得到约束的社会。小个子牧师笑了,站在洋蓟地里,带着混血儿的精神劲儿。他头上的树叶繁茂,阴影愈加浓重。他的胖手半握着,一时间在袍子前形成一个奇怪的形状,像是那种优势没有得到约束的无形社会结构。
我们在河里游泳。河两岸的植物高大得一成不变。“很多热带物种,在自然的塑造下看上去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的植物学家费尔南多解释道。“假设有一位火星来客,”他接着详尽地解说,“哪怕他在冰极点上降落,他也会发现大量的微生物和苔藓—多到疯狂、歇斯底里的程度—这就是生命,在这个宽厚仁慈的星球上。”
当我们裹着毛巾,穿过村子中心宽阔的露天广场,我们看到了很多光滑的大石头,毫无章法地放在吃饭的茅屋和孩子们上课的茅屋间。夜色降临,这些大石头投下长长的阴影。路易斯,我们的人类学家,推测这是某种仪式或游戏时用的筹码。他离猜错不远,忧郁的族长愉快地解释说,这些石头是村里的年轻人用来测试力量的。我们稍稍地客气了一番,他们就把现任冠军叫了过来:一个相当胖的男孩,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印上图案的T恤衫。在同伴的怂恿下,他才像女孩般扭捏地走过来。他向看上去最重的一块石头走去—以一个冠军不动声色、漫不经心的步伐,突然他气运丹田,用力一拉,巨石便倒立起来。这时,石头看上去更重,阴影也显得更长。男孩蹲下来,抱起巨石,好像父亲在孩子快跌倒时把他抱起来。他试着抱着重物站住,周围所有观众都同样紧张地一声不吭。第一次,他失去了平衡,不得不突然扔下石头,往后一跳,免得砸到脚趾。第二次,他先把石头放在大腿上,然后用力顶起来,石头好像某种滑动的大型寄生物,寻找他身体的入口。终于,他脸上羞怯的微笑被紧绷的表情一抹而去,他把怪物扛到了肩上。他转过身,面向观众,然后才把石头往地上一丢。砰然一声巨响,随之被观众的喝彩声吞没。男孩转眼便没入荫蔽处,算是一种自谦,表示他的功夫并非得力于本人,而是天赐神助。
族长和两位牧师见证了表演,也看到我们都满心欢喜。于是,他们接着安排了一个吹筒枪的节目。于是,他們接着安排了一个吹筒枪的节目。一位看上去颇为精干的老者—罗圈腿,几颗门牙为了好看拔了下来,两颊还各有一条V字型的饰纹—用带着穗子的飞镖,击打广场上几步之外的小目标(一片折起的叶子,一个乒乓球)。吹筒枪至少有十英尺长。随着夜晚的寒气包裹住我们潮湿的身体,我们的影子也被明显拉长了。鸡皮疙瘩各自带着它们极小的影子,出现在孔基塔的大腿上,而汗毛也像热带异鸟的羽毛在埃斯莫拉尔德的小臂上直竖起来。尽管如此,当被邀请尝试一下吹筒枪时,我们还是欣然从命,用鼓着气的腮帮子和谬之千里的击射,惹得观众阵阵发笑。
需要强调的是,整个过程都是在得体而美好的轻逸中进行,这在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文明间是不太常见的。观众迅疾无声地散去,很快,香甜而辛辣的炊烟,在空气中飘散起来。明亮的圆月出现在还是蔚蓝色的天空上,我们也回到住处,准备享用美食了。
月光把一大片苍穹都染成了淡紫色,连星星也隐没其中。远远看去,四周丛林的边缘很低,像海洋上的天际线。想想看,像我们这样的谈话,一千多英里之内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多么奢侈啊,这人性宁静的庄重。
当牧师们起身去休息,我们又拿出一瓶酒。我们散着步,却像下课的孩子,让散步变成了一场奔跑。在月光的照耀下,村子的街道仿佛拓成了起飞跑道那么宽,它向我们暗示着速度。于是,我们的步伐也快了起来,抑制的笑声变成了气喘吁吁的狂喜。我们飞着,佩普、奥特加还有劳乌尔,我们的语言学专家,在前面领路。孔基塔和埃斯莫拉尔德手拉着手,咯咯笑着,步履轻盈地跟在后面。费尔南多、我还有萨尔瓦多,我们土生土长的农学家,则不慌不忙地殿后。
我们到了丛林高耸密集之处便停了下来。那些藤蔓交织的树冠,向我们弯下身子,如同巨人殷切的头颅。在黑暗之墙的后面,我们可以听到生命咔哒作响的低语,而瀑布不舍昼夜的轻柔咆哮则响在我们左边远处的河中。树墙之后,深远的丛林如同頭顶的夜空,看上去近乎无限。一回头,我们看到跑道,就像飞行员在着陆前的一瞬所看到的。遗世而独立正是这个理想村的立意所在。倘若离得不够远,那么,政府的黑手就会伸过来,那么,族长也就不必撇开按摩师而系上那条羽毛腰带了。
可以想见的是,那晚我们在吊床上睡得并不安稳:每一个动作都会导致一阵令人痛苦的摇晃,连把身体趴过来也不行。清晨,在月落和日出交界的黑绸般的时刻,窗外传来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不停的窃笑声。我们知道,匆忙难看的离别时分到了。飞行员带着一夜狂欢之后的倦怠,同时又为嗡嗡地飞越那无尽的绿色丛林而担忧。族长没穿上灰马甲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显然对那套文明礼仪毫无在意。他给了孔基塔一条貘牙做的项链,埃斯莫拉尔德则以折后价购得一个长吻浣熊雕像。我们不停地挥手告别,当两架飞机一起斜飞过广场干涸的土地,飞过河流,飞向远方。
直到几个星期后,为向政府报告,我们重新检视日记,才发现每个人是多么庆幸能够离去:人,何必到天堂去住。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村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