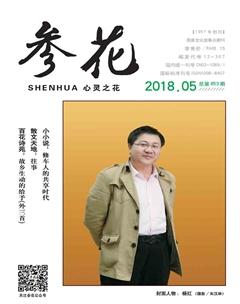关于群众戏剧创作和表演中审美距离的一点思考
摘要:俗话说: 距离产生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写道:“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首诗成为描写庐山壮美风光的传世佳作。而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庐山《题西林壁》中写的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见距离对审美的重要作用。审美距离是布洛提出的一种学说,即在审美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客观现象无从与现实的自我产生联系,才能使其充分显示其美的本色而更富有美感。“审美距离”研究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美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审美距离既伴随审美过程,也增强审美感受。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审美距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同一审美主体出现的审美差异,对于群众戏剧创作和表演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群众 戏剧创作 审美距离
一、时间距离
戏剧既是空间艺术也是时间艺术。随着时间的变化,其审美体验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对戏剧内在本质的审美判断都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如有的作品原来看是美的,隔段时间再看,变得不很美了。有的作品原来看是不美的,而今天再看却变成美的了。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很多优秀作品,如《红岩》 《地道战》 《党的女儿》《刘三姐》等作品,都曾为人们带来过巨大的精神鼓舞和艺术享受。而今再现于观众面前时,其艺术震撼力就大不相同。这就是时间距离的拉长,包括传统道德教育的缺失,以及审美取向的分歧、审美标准的差异,使人们的审美判断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现象反映在年轻人身上尤为突出。再如《智取威虎山》 《永不消失的电波》 《小兵张嘎》 《红楼梦》等,一批作品的重拍,甚至几次的重拍,并不是因为原来的作品不好,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审美意识、审美情趣有了新的变化,审美角度、审美取向也出现了差异。可以说,这种差异和不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活的改变而改变的。
时间距离,反映在戏剧创作本身的另一种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如戏剧结构中的幕与幕之间,场与场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或人物上下场之间的顿歇等。这类时间距离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戏剧反映社会人生提供相对合理的时间过程。如戏剧情节的发展,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物思想、性格、精神与行为的变化等,必然在时间上有个相对合理的发生、发展过程。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过程,才能更好地打开观众丰富的想象,让他们去思索,去体味,去延伸。这比舞台所直接表达的更加广阔、更加深远,也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距离的设置,也是为观众进行戏剧审美展开的最美妙的窗口。
时间距离在戏剧表演中尽管占有的时间相当短促,但它对于揭示人物的心理冲突、激情、矛盾,灵魂的震荡和人物命运,对于揭示戏剧情节,情势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雷雨》的第三幕,四凤的母亲逼迫四凤起誓,从此以后永远不要再见周家的人,“孩子,你要说,你要说。假若你忘了妈妈的话……”四凤不顾一切地:“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哦,我的妈呀!”随之一头扑在母亲怀里。伴着雷声轰然滚过,舞台上呈现一个大停顿——时间距离。演员充分利用这一停顿深刻地展示各自积压心底的苦痛,于无奈、无助中的情感挣扎和母女间难以说出又不得不为的心理纠缠与矛盾。這一停顿,不仅没有使戏剧冲突停歇下来,反而使戏剧更加复杂、深化了,并为推进剧情、酿成全剧最大冲突和高潮埋下了伏笔。这种时间的顿歇,无言的沉默,往往比激情的爆发更加有力,更加沉重,因而也更具戏剧强大的震撼力。
二、空间距离
任何一种艺术,当创作主体面对创作对象时,主客体间一定会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对这一距离把握是否得当,关系到创作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当然,距离的远近同审美效果的好坏并不是成正比的关系。演员同观众间存在着的空间距离,不是演员随意可以调整的,而是需要演员主动去适应,不让这种距离美遭到破坏。如舞台上常常出现一些场面和段落间的过渡,或人物的大段独白,或较为平淡的生活过程与细节等,有可能让一些观众因不耐烦而离去。那么,演员该如何通过表演不让观众离座而去?这就需要演员拿出最大的热情,情绪饱满,精神振奋,没有丝毫的懈怠,全身心真诚地投入到角色的生活中去,并不时而又恰当地变换节奏,尽可能合理地增添或强化一些动作、表情、手势与语言的色彩,给观众带来哪怕是极微弱的新奇感与惊叹,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和兴趣诱导到戏剧的情境里,不让他们的兴致降温和瞬间的专注偏离。总之,就是要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舞台的魅力,让观众与表演者在同步的体验中,感受到空间距离为他们带来的美感。
保持这种审美距离稳定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其戏剧的基本观念,在舞台上制造出“再现生活真实的幻觉”,把观众带领进舞台所创造的另一个新奇美妙的世界,同角色一起品味剧中的苦乐悲欢,从而实现其演剧艺术的审美理想。
三、心理距离
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体现的就是一种心理距离。这种距离的形成大都以人的情感为主导,所以又可称为情感距离。艺术创作的过程始终渗透着浓烈的情感,并将这种情感灌注到艺术形象中。没有情感,艺术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没有情感,这种距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当然也就谈不上审美了。诗人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都是由心理距离构成的艺术观照。而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则讲了把心理距离拉远,心里清净了,才能发现、体悟到事物的真谛与美妙。
戏剧创作中的“仿真”与“似真”是两种戏剧观指导所形成的完全不同的艺术形态。两者同观众间构成的心理距离及其审美感受,也存在较大差异。“仿真”强调的是将生活真实地再现于舞台,即创造真实的幻觉;“似真”强调的是剥开生活真实的外表,追求生活本质的真实,人的心灵深处的真实,即创造“似与不似之间”的真实幻觉。前者,所追求的心理距离是越近越好,好像剧中的一切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周围,我见过、我熟悉,因而感到亲切、贴近,给人以审美的满足与愉悦。后者对心理距离的追求却是适当拉远,不要陷进现实生活,不再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到人和生活的本质层面去。剧中所发生的一切,未来可能发生,或经验中不曾发生,不会发生,我不曾见,我陌生,因而令人感到意外,感到惊奇。比如大量的科幻小说、科幻影视等。它给人的审美感受,更多的是新奇、刺激、兴奋,以及由此产生的幻想、思考、想象、憧憬。
人的审美心理是复杂的,而且经常在变化。这种变化,常常表现为一种追逐群体的倾向性。如时装审美,昨天喜欢蕾丝滚边儿的,今天就爱好加带绒毛的,昨天时兴黑白分明的,今天流行五彩缤纷的。对美术作品,有人喜欢写实的,有人青睐写意的,还有人迷恋抽象的。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群体,即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对同一审美客体会是不同的,是具有审美差异的。因此,戏剧创作者应适时地了解人物在审美需求与情趣上的变化,使自己的作品与时代需求的变化合拍,以便使审美距离的把握与观众的审美需求相适应。
比如以《乡村爱情》为代表的乡村生活题材电视剧的流行,以《港冏》为开端的冏系列电影的火爆,以《甄嬛传》《芈月传》等后宫戏的持续升温,赵本山小品的潮起潮落,等等。每一次新潮的出现、更迭,事前都有大量的专业人员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查,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对作品经把脉后做出适应性的调整,才使作品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始终把握在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度”上。
心理距离在戏剧创作中的另一种形态是戏剧结构中的“悬念”。它在戏剧中不仅仅像章回体小说那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是几乎贯穿在剧中情节发展、回旋、推进的全部过程。如果把构成情节发展过程的事件、矛盾和冲突比作江河洪流,那么悬念就如参差错落,明暗崎岖的礁石。情节的流动常常在险峻的礁石间穿越奔涌,时而有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时而有涟漪层层,浪卷回旋。有戏剧家甚至称:一出戏,就是一连串的悬置和危机。学者余秋雨从戏剧审美心理学角度对悬念做如下解读:“一切戏剧技巧,最终无不出于对观众心理的把握,那么,其中又以悬念最为明显。‘悬者,乃观众之‘念……这种技巧要求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拉开距离,从而使观众的注意力在这个距离内保持住……”设置悬念的目的,全在于保持戏剧演出与观众心理距离的稳定。保持这一心理距离,就是为了唤起观众对剧情发展的极大关注,引发他们对演出的浓厚兴趣与热情,满足他们对剧中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情节、人物及其命运等种种事物的心理期待,以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
如何保持心理距离的稳定?这就需要演员在舞台上或银屏幕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泣一叹,都应给观众以新颖、新奇和惊叹之感,都应赋予角色以新鲜的生命活力和角色独特的个性风貌与特征,让人物形象透射出神奇的艺術魅力。这样才能使观众牢牢地被吸引在剧场里,心甘情愿地随着剧情与人物命运的变化,体验着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尽情地享受着艺术带给他们的喜悦与满足,这应是作为演员维系与观众审美距离的最佳方式。
四、文化距离
在审美距离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文化距离。文化距离所指的不只是审美主体各自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高低,而是因民族、种族、国别、地域和地区及其历史、民俗、信仰、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所呈现出来的审美距离。如一般汉族观众看傩戏、藏剧、壮剧、傣剧等,就很费力,甚至根本听不懂、看不懂;中国的戏剧小品、相声拿到西方国家,也很难被接受;南方的滑稽戏、方言剧所特有的诙谐、幽默和妙趣横生的笑料常常让南方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而北方人看了却一脸地莫名其妙。再如莎士比亚的剧作,近百年来经多位翻译家译出了多种版本,至今还有翻译家仍在重新翻译。其目的就是为使中国读者与观众更好、更乐于接受,同时,更深切地领略沙翁那博大而又深邃的思想,丰厚而强烈的情感,及其语言闪烁出的美妙光辉,以便解决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惑。
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由于所在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生活习俗和语言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形成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民众所特有的生活方式、观赏习惯、观赏情趣和观赏需求。他们喜欢什么,接纳什么,又排斥什么,是要伴随戏剧创作不断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拉近这种文化距离?关键在于能否让戏剧创作中的一切“外来”因素“化”为本土观众易于接受的作品,使之落地生根。首先,要了解和掌握剧中的文化差异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并具体找到它是从哪些问题、哪些环节和细节中体现出来的。其次,要确定这些差异之“点”究竟在什么位置上。否则,一切工作将乱无头绪,无从着手。再次,要深刻理解每个“点”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义,它在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它又是通过怎样一种艺术方式和特色表现出来的。最后,筛选出与之相对应的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戏剧表达方式与技巧。由此形成两种不同文化与艺术的融合。如沪剧移植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京剧移植的《奥赛罗》,话剧改编的《李尔王》等,就是运用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语言方式,及其舞台表达方式、舞台环境、场面、造型、服装、音乐、人物呈现,等等,都是将异国戏剧作品中的大量“外来”因素化为本土观众乐于接受的戏剧作品。这或许为解决戏剧创作中存在的文化距离,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或大可借鉴的途径。
随着当代戏剧的崛起,人们对各种戏剧与形态的探索,其审美意识逐渐提升,也迫使其审美距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在同一台戏里,就可能有现在时,过去时,未来时的交叉、颠倒、组合、重叠或穿越,有现象的、心理的、想象的、幻觉的、潜意识的、梦呓的,或完全是主观虚构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而演员的表演也必然随着剧情任意往来,自由进出。可以在台上,在台口,也可以在台下,到剧场的任意一个空间去表演,甚至被悬在空中,或被翻转身来头朝下做些什么,更有一些剧目演出把歌舞、音乐、造型、杂技、吟唱、哑剧、集体朗诵、局外点评、介绍、解说等其他门类艺术的表现形式,融汇到戏剧演出中来,力图寻找到戏剧审美的最佳距离,取得理想的审美效果。
对于上述种种实践、探索,有人认为“戏剧舞台就是表现,只要能表现的,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有人说“杂交即可出新”;或有“重在揭示本质的真实”;或有“深层心理的直观”;或强调“揭示人生哲理”……众说纷纭。但不论怎么说,总体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当代戏剧演出所呈现的审美距离,已从昔日的传统戏剧演出所建构的审美距离中脱离出来,衍化为一种新的形态,即,它不再是稳定不变始终如一的,而是呈现为一种兼具弹性与跳跃性,流动多变和多层面的复合式审美距离的形态。
审美距离是一种客观存在,如同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对于同一个审美客体来说,不同的审美主体会有不同的审美感受。因此人们才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总之,戏剧舞台上无论展现什么,怎么展现,用什么方式展现,也无论它怎么千变万化,只要舞台艺术存在,观众存在,其审美距离就不可能被破除而消失。戏剧舞台艺术正是由于它所特有的艺术感染力、思想说服力和情感震撼力,及其审美距离的存在,才使得观众在艺术的感悟中获得情感之愉悦,让精神为之振奋,心灵为之净化和提升。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别有洞天。
(作者简介:谭秀梅,女,本科,天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级,研究方向:群众文化)(责任编辑 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