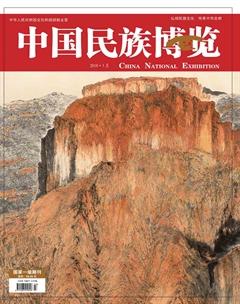从舞剧《水月洛神》谈舞蹈的意象创造
肖恒莉 邓晨霞
【摘要】“意象”属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诞生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个门类艺术的发展。中国舞蹈同样是受到了其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水月洛神》是取材自中国的文学作品,整部舞剧如梦如幻,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审美的艺术境界,引起人们的想象。本文将以《水月洛神》为例来分析舞蹈当中的意象创造,希望能给从事舞蹈界的工作者帶来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水月洛神》;舞蹈意象;意象创造
【中图分类号】J723 【文献标识码】A
一、舞蹈意象的内涵
所谓舞蹈意象,就是舞蹈演员通过肢体动作在舞台空间和时间中创造出的一种超以象外、虚实结合的舞蹈景象,这种舞蹈景象是由具体的“象”和虚幻的“意”共同组成,舞蹈动作的外表形态是具体的“象”,舞蹈动作的内在含义是虚幻的“意”,通过连贯的动态舞姿表现出来,便能够引发观众的审美力和想象空间。
“象”因其直观可感性而具有“显意”“尽意”的功能优势,舞蹈正是凭借鲜明的动态视觉形象而使其情感的表现得天独厚。[1]“意”是“象”的最终目的与升华,舞蹈表演者用动态舞姿创造出虚象。不过“意”是通过“象”而产生的,因此,没有“象”就没有“意。在“象”和“意”的关系中,要以写意为主,利用有情感的动作姿态来结合,追求型外之意,有限中出无限,做到“意”与“象”的有机统一。《水月洛神》就是演员通过熟练的动作与完美的表演营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引领观众由实象体会到意象,激发联想。由此可见,舞蹈意象的创造在舞蹈作品中的重要性。
二、几种创造舞蹈意象的手法
(一)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
以意象造型立象外之象,这是指利用具有高度概括性、感染力的舞蹈动态造型营造出意象的一种手法,此手法适宜于营造氛围比较宏大、气势阔大的舞蹈意象。
舞蹈动态造型的意象创造主要依靠舞蹈动作,此时的动作必须是浓缩、提炼了舞蹈的精神本质和丰富内涵,它来源于生活动作的概括化、变形化、抽象化和艺术化,这些舞蹈动作能够启发人们的思考、想象和联想。因此,有时候一个动作、一个姿态足以胜过千言万语,舞蹈便是通过动态造型意象表达出那些言语不能完美表达或无法表达的事物,所谓“言之不能尽者,象能显之”[2]。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舞蹈作品进行分析。在《水月洛神》中的第三段,以曹植与曹丕兄弟俩人征战沙场为发展背景。舞台上消沉的昏暗的灯光里,出现了战乱之中的甄宓在周围充满的血腥与苦难里奏琴。在古琴声如泣如诉下,眼前,一群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垂头丧气、悲痛不已,每一次呼吸与沉气都夹着沉重的悲伤。随后,由甄宓有感而发的作词吟诗中,舞台上连续出现一系列打动人心的造型群雕,跪地、揩泪、佝偻难行的舞蹈造型,使观众仿佛看到了战争中的纷乱与无助,感受着战争给平民百姓的身心肉体带来的无情灾难。这段舞蹈以独到的舞蹈动态造型意象营造出特有的氛围和意境。它那沉暗的色彩、悲痛的情调、沉郁的节律,无不渲染出战乱中无辜苍生的重负和心酸。
(二)借自然物象写主观情思
借自然物象表主观情思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主要手法之一。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比兴”手法来托物寄情——咏梅花以感叹自己的人格;以雎鸠天性比淑女之恬静。以致后世的中国绘画中有名的“四君子”(梅兰竹菊)都是寓意个人高尚的品徳。而在舞蹈艺术中也是如此。
自然界中的物象总是习惯性地被人民赋予其具有一定的内涵,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容。清代画家石涛曾说:“山之得体也以位,山之荐灵也以神,山之变幻也以化,山之蒙养也以仁,山之纵横也以动,山之潜伏也以静,山之拱揖也以礼,山之纡徐也以和,山之环聚也以谨,山之虚灵也以智,山之纯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这段话说明了各种形态的自然物象反映了不同的精神内涵。然而,绝大部分的自然物象都是有“形”有“意”的,以“形”传“意”便是舞蹈创作意象的基本方法。例如,在《水月洛神》中,编导是以三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洛神赋》为蓝本,故事伊始,不管是诗篇中还是舞剧中的神女都是虚构与遐想,在皎月下,云水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如此虚无飘渺、如诗如画的梦境唯有用月与水这满含令人玩味不尽的意蕴来呈现意象了,水之温柔、明畅;月之皎洁、高雅,水月之间,荡起涟漪,幻想出意境,生起爱慕之情。《水月洛神》的编导正是借用水月物象,抒写了曹植内心的情感波澜和主观情思。
(三)以具体物象象征性质的不断改变营造新的意象
赋予舞蹈物象以特定的象征意义或不断改变其象征意义以营造新的意象,这是舞蹈艺术创造意象的一种特殊手法。
《水月洛神》整部舞剧的亮点之处要数其中的十二块墙体的妙用。这十二块墙体正面是汉代石刻的图案,反面则是明亮的镜子。随着墙体的自由移动、巧妙摆设,十二块墙体由始至终作为“虚象”贯穿全剧,在舞台上营造出层出不穷的舞蹈意象。
十二块墙体首次出现在战乱时期,曹植偶然与甄宓的相遇,此时的“十二虚象”在剧中渲染出宫廷的森严;
接下来,是曹植眼中只有甄宓不可占据的美,“十二虚象”穿梭其间,成为曹植内心的“屏障物”,对甄宓的美遥不可及;
当曹植、曹丕和甄宓三人错综复杂的关系成为流言蜚语充斥着整个后宫时,“十二虚象”是掩护宵小们的“宫墙”;
曹丕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境,预感曹植会给自己带来威胁时,“十二虚象”化为曹丕的“心境”,无时无刻都倒映出曹植的身影;
最后,曹植被贬为地方官史,与甄宓诀别时,“十二虚象”作为分割他俩各在一方的“围墙”。
《水月洛神》一剧中,“十二虚象”以不断改变其内在含义的物象流动其中,每一次的变幻就产生一种新的意象,勾起新的联想。这种以实引虚、以虚托实的手法,增强了舞剧的艺术效果,使舞剧的意象创造更为新颖。
(四)通过虚拟创造内心视象
艺术被定义为虚实相结合的客观现实世界。同样,舞蹈艺术也不例外,用虚拟物象描述人物内心世界,用舞蹈语言虚构成人物思想与精神,是舞蹈创造意象的得天独厚之手法。
化实为虚,意味无穷,有利于提高舞蹈艺术的境界。正如清人笪重光所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在舞蹈创作中,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务必要有化物象为情思的思想,即是把客观真实的舞蹈语言化为主观思想与表现。如在《水月洛神》中的第五段,曹丕府中莺歌燕舞、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身处其中的甄宓却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感慨战乱中的女人生如浮萍,漂浮无定。昏暗微光的舞台上,是甄宓柔弱无助地求脱与挣扎,她怜悯天下苍生,祈求天下太平,并且渴望自己能够得到自由。临近高潮,舞台正中间的甄宓被一群客观存在的男舞者包围成半圆形,这群男舞者表现了甄宓不可视的内心世界,为甄宓的“心灵视象”,是“虚”。尽管甄宓反复周旋、跳跃,她始终无法翻越、逃出坚实不催的男舞者的包围。编导正是通过舞台上的客观物象展现着甄宓内心的忧愁和抑郁,十分明晰地呈现出她烦恼不安、思绪万千的情感世界。
将内心深处情感外化为可视的方法,在舞蹈艺术创编中是较有特色的,同时,也是观众能较好理解与接受的。
(五)利用道具的象征功能创造意象
中国舞蹈艺术创作善于使用道具来扩展意象空间,道具作为人体以外的延伸媒介,具有超然的象征意义。在符合舞蹈劇情需要的情况下,适当地借助道具的艺术功效来协助舞蹈作品的完成,有利于拓展舞者的舞姿动态,还能使舞蹈作品更具丰富的意象内涵,从而提升舞蹈作品中的情感世界。
例如,《水月洛神》剧中的古琴,这一道具运用得非常恰当、巧妙。在战乱时期里,甄宓厌恶着战争给生灵带来的涂炭,抚琴于灾区中,曹植便是通过琴声读懂了甄宓的心声,由此结为知音。在这里,道具“古琴”起到了很好的沟通媒介作用,它是人体以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延伸媒介,在剧中创造了舞蹈意象和环境气氛,是古琴让他们相知,揭示了悲剧爱情故事的开始。
三、舞蹈意象的价值和意义
苏珊·格朗曾说过:“演员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出一个能够使我们真实地看到的东西,而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一种虚的实体。一种舞蹈越是完美,我们能从中看到的这些现实物就越少。”她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美学对舞蹈艺术创作的认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人认为,舞蹈意象本来就是追求虚实结合,似与不似的艺术创作,当今很多令人口交称赞的优秀舞蹈作品里,意象都在里面充当着必不可少的重要创作手段。那些通过虚实相结合演绎出的作品,更能虏获观众的心,带领观众跟随舞蹈而浮想翩翩。
还是《水月洛神》,这部舞剧既是舞蹈家情感的完美表现,又具有美到极点的“诗情画意”,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可以说,舞蹈意象不仅仅是舞蹈编导的基本追求,更是中国意象艺术最为典型的代表,用流动的体态表现出中国艺术之意象精神。只有创造出韵味深长的意象才会引发观众的想象,让观众产生共鸣,从而产生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袁禾.中国舞蹈意象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2][清]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 北京:中华书局 , 1980.
作者简介:肖恒莉(1993-),女,汉族,广东省东莞市,硕士,研究方向:舞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