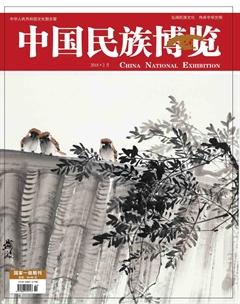甘青地区史前祭祀遗存研究
罗丹婷 周岳
【摘要】对甘青地区史前礼仪祭祀和丧葬祭祀两方面的梳理,该地区普遍存在着原始崇拜。从埋葬形式可以看出各个文化之间存在着对死亡理解的普遍性。同时又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各个地区文化之间产生了差异。
【关键词】甘青地区;礼仪;宗教;祭祀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各地由于自然条件各异,因而导致原始的宗教观念在不同地区与不同部落之间也产生了差异,原始社会的文化形成必然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同地区和不同部落之间相对封闭,文化交流较少,在人类对自然敬畏的共性之下,还形成了以各个部落为中心的自成体系的具有个性差异的原始宗教观念。本文论述的空间范围大体上包括甘肃大部和青海东部,时间范围涵盖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诸文化。甘青地区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根据属性差异可以分为两类,即礼仪祭祀和丧葬祭祀。
一、礼仪祭祀
史前礼仪祭祀遗迹是指古代先民在祭祀祖先、祈免灾祸等活动下遗留的考古遗存,它是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人们对自然存在敬畏并由此产生信仰,祭祀活动也就随之而来。地画“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献祭的根源便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的无把握、未来的不可知,对于所犯罪行上的良心上的咎责;而献祭的结果,目的则是自我感—自信、满意,对后果有把握、自由和幸福。去献祭时,是自然的奴仆,但是献祭归来时,是自然的主人。”
目前在对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F411发现的地画(图一)含义解释,学术界的观点主要围绕“人物所持何物”和“框内所画何物”两方面展开。“地画中有人物和动物图案。上部正中一人,头部较模糊,手中似握棍棒类器。正中人物右侧,仅存炭黑残迹,系久经磨擦脱落,推测也应为一人。正中人物左侧,也绘一人,左臂向上,弯曲至头部,右臂亦下垂作手握器物状。在正中人物下方,绘一黑线长方框,框内画两只头向左的动物。”考古报告认为,地画可能有祖神崇拜的意义。画面上方的人物是祖神,下部方框内的动物是供奉神灵的牺牲。画面表现的不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共同的祖神,可能是氏族小家庭的一种崇拜偶像。并认为地画体现了原始社会晚期以男性为主导的三位一体的家庭组合方式。画面上方人物一手放于头部,一手握着器物,两脚交叉而站,仿若起舞。故而笔者认为人物所持的棍棒状器物应为祭祀所用的法器,方框所画为放在盒子或台面的贡品,地画上的人物在举行祭祀神灵献上牺牲的仪式,整个画面表现了史前祭祀过程中的丧舞仪式。
“远古时期大型房屋有各种不同的用途, 有的是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集会房屋或男子公所, 有的是首领住宅, 并非所有大型房屋都是供许多家庭集体居住的公共住宅。”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的F901,建筑宏大、主次分明且与一般房址出土物不同,不见日常用具和生产工具,在同区域近千平方米的范围内也不见同时期遗迹。在赤峰东山咀红山文化也曾发现类似房址,遗址北部有一平台式祭坛,南部有两三个以鹅卵石砌成的石圆圈,附近出土有人体塑像,祭坛与石圆圈之间有一空旷广场,遗址四周没有居住遗址。两处房址的相同处在于,遗址建筑排列有一定布局,“大房子”内没有发现与生活生产相关的工具,房址周围空旷且没有居住房址,故而推断该遗址为宗教祭祀中心,主要是用于部落氏族的集会和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的场所。
无论是考古发现的祭坛、祭祀用具,还是有痕迹表明的祭祀活动,都体现了人们出于在自然面前的无力感,而寻求一种超自然神力的仪式。在民和阳山发现的12座圆形土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墓地的西南角,坑内有人为打碎的陶器、动物残骸、大小不一的石块以及被火烧过的痕迹。从圆形土坑的分布和坑内摆放的物品来看,应是一种在葬后为缅怀死者而举行仪式时的祭祀遗存。类似遗址在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过两处,一处是用河卵石铺成的长方形石块建筑,选用20多块大小均匀的河卵石铺砌相当规整,在遗迹西南约1米处,发现一具完整的狗骨架,在狗骨架下,整齐地平铺着一些陶片,附近还有一座墓葬。另一处是用河卵石铺底的圆坑遗迹,石圆坑附近还分布有墓葬。由此推测应是与墓葬相关的墓祭遗址。
在大何庄、秦魏家、师赵村皆发现了“石圆圈”遗迹,它是利用天然的扁平砾石排列而成,附近分布着墓葬,圆圈的旁边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这些“石圆圈”遗迹或许是在埋葬仪式前事先埋葬,用以陪葬的牺牲。在大何庄、皇娘娘台、秦魏家,东灰山发现了或多或少的卜骨,它们有的分布在石圆圈附近,有的放置于陶罐中。林声在对彝、羌、纳西族的调查中提到,羌族和纳西族只用羊的肩胛骨,彝族有时采用牛或猪的肩胛骨,但仍以羊的为主。在甘青地区发现的卜骨基本都系羊的肩胛骨制成,在经过刮削、灼烧等步骤后进行占卜之用。另外在武威皇娘娘台发现了10余片出自窖穴,未经烧灼,只有轻微刮痕的牛、羊、猪肩胛骨,或为还未使用的占卜材料。看来这时的卜骨制作技术还比较简单,占卜技术还处在原始阶段。作为宗教活动的占卜,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中的用牛、羊或鹿的肩胛骨占卜的卜骨标志着这一阶段原始宗教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也说明这一时期社会上应该已经出现一批脱离生产劳动的人,这些人是专门从事宗教占卜活动,应该是部落氏族的首领。
在阳山发现的喇叭状陶器,根据形制推测应为陶鼓。在《畲族考》有一段对陶鼓的描述,“人死刳木納尸,少年群集而歌,辟木相击而舞。”在祭祀神灵、送别死者的宗教活动中,陶鼓发出的声音可以起到上达于天,下警醒地的作用。在阳山发现的陶器下口沿外侧有一圈乳钉小钩和钻孔,或许可以在举行活动时背在身上,方便跳祭舞时使用。而陶鼓的使用者也就担当了与神灵沟通的职责,执掌着祭祀等一切与神灵相关的活动。在永昌鸳鸯池发现的石雕人面象(图二)精致小巧,上部有孔,便于携带,发现时放置于死者手臂上。在河北迁西东寨也曾发现过一件双面石雕像,石质为红色砂石雕刻,人面成椭圆形,背后有四个系孔。这种人面像便于携带,或与陶鼓有相同含义,是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并且可以表明佩戴者是举行祭祀活动首领的身份。
二、丧葬祭祀
“原始部落的任何风俗的形成,都与他们的原始观念有关,而埋葬习俗则体现了原始人对死亡的理解,是原始宗教观念的直接反映。”丧葬祭祀,即指甘青地区先民在埋葬尸体时,在对尸体的摆放、随葬等方面体现的祭祀行为。从甘青地区有关史前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关于葬俗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尸骨散乱,有明显人为破坏的痕迹。
在甘青地区广泛盛行的二次葬是指,对死者的尸体和遗骨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扰乱的葬法。陈洪海对甘青地区除陇东以外的二次葬进行分析,认为师赵村石岭下类型墓葬应为甘青地区二次扰乱葬的源头。二次扰乱葬自半山-马厂类型开始盛行,在循化苏呼撒、乐都柳湾均达半数以上。齐家文化时期,二次扰乱葬比例最高的是青海互助总寨,武威皇娘娘台、乐都柳湾等地也有发现。进入青铜时代后,二次扰乱葬成为了辛店和卡约文化的主要葬式。故而有理由认为,二次扰乱葬的存在与人们的意识形态有关,其中必定蕴含了当时人们对于尸体和死亡的认知。
高东陆认为,二次葬是对埋葬了一段时间的墓葬进行处理,即将墓口打开,把尸体拉出来扯乱,然后再将扰乱的尸体随填土回填,最后再将头骨埋入墓内。二次葬多设置墓上标志,一般放置石块,方便寻找墓葬。在二次开挖,对墓内人骨进行处理时,有时在墓内对尸骨进行处理,有时在墓外。有时甚至将人骨和葬具一同进行焚烧,即火葬墓。火葬墓中尸体摆放姿势基本上看不出。从对卡约文化的遗址发掘中可以看出,二次扰乱只对墓主人实施,不惊动人殉,由此也可证明二次葬应是尊重缅怀死者的行为。二次开挖对尸体进行扰乱时,应该伴随着宗教祭祀活动,一些墓口和填土中的草木灰应为祭祀所留。二次掩埋是二次葬的最后一步,散落的人骨随葬陶器和墓上标记一同随意埋入填土。
笔者认为,二次扰乱葬的出现应与原始先民的早期宗教观念或者对死亡的理解有关。从考古发掘报告中可以发现,有些墓葬中扰乱了尸体的身体骨骼,头盖骨却完好无损。“灵魂可以自由离开躯体,但是必须依附在某物之上,它同尸体联在一起,而当皮肉腐烂和消解时,它就走入骨头里去,主要是头盖骨。”推测这种葬式可能是源于人们思想中存在着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观念,打破骨血,从而使灵魂得以脱离肉身,由此获得重生,达到死后与家人团聚的目的。
在甘青地区的史前墓葬中,空墓是一种特别的现象。民和阳山发掘63座空墓,占墓葬的40%,民和东灰山四坝文化墓地空墓22座,占9%。空墓即只有随葬品无人骨,墓穴的形制、排列、随葬器具摆放有序,显然绝非埋葬时的遗漏疏忽,可能因为死者未入土或埋入他处,在尸骨不存的情况下仍设置墓葬,放设随葬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及对死去人的敬畏之心。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来看,甘青地区墓葬尸体的摆放方位也存在着共性。永靖大何庄的齐家文化55座小孩墓,死者均头向西北;永昌鸳鸯池头向东南方的占69.8%;土谷台墓地头朝朝东的墓葬占45.2%;红古下海石马厂类型墓葬人的头向多向西,占总墓葬死亡72.7%,分布间距不相等。这外侧有规划性的公墓是以东北部最高处为中心点,向外一层层地弧形分布;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墓坑方位以南北向为主,埋在台地缓坡上的墓葬头向均朝台地中心。秦魏家墓地墓主头向朝西北向的墓葬占77.5%。可知最晚自半山—马厂开始,先民们就已经通过埋葬时头部的朝向位置表达一种埋葬习俗。在一个聚落中死者的头向一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向心性和凝聚力,他们可能朝向敬畏的方向,祈求上苍可以在死后依旧对他们加以庇护。
在秦安大地湾仰韶早期发现的6座瓮棺葬,基本没有墓坑,多是将瓮棺竖向放置,瓮上扣一盆,钵为葬具,且盆、钵底部多见一小孔。云南纳西族的火葬是在埋葬时,把骨灰袋底部剪开,或抽出底线,使口部和底部均与外界相同,便于灵魂出入。秦安大地湾的瓮棺葬在底部留孔或许也是为了便于灵魂可以自由出入而专门设置。
人殉是指用活人来为原始氏族的首领或地位特殊的人的一种殉葬方式。在徐家碾寺洼文化的墓地中有8座墓,发现了用人殉葬的现象,占总墓葬的7.8%。被殉者除个别外都属于孩童和未成年的男性。在8座墓葬中有6座墓的殉人埋在墓穴的壁龛内,壁龛都设在墓主人的脚旁。殉人的尸骨上没有发现绳子等捆绑的痕迹,应都是事先处死后埋入。有些墓的殉人缺头颅骨,或头颅砍断后放置在身体上,或将尸体拦腰砍断成两截。湟中下西河墓地也有20余座殉人的墓葬,人殉捆缚跪状置于墓道西北角或西南角,并随葬一无耳花边小罐和一段牛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葬在对墓主人进行二次扰乱的时候,并未惊动人殉,由此也可看出人殉的地位和墓主人之间的差异。
“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色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它的宗教里。”在干骨崖墓地中,超过50%的墓内放有砾石,少者一两块,多者数十块。有的放置在石椁内或石椁一侧,有的直接叠压在石椁之上,更多的是将大块石砾压在死者胸前、腹部和下肢。人们将死者用大块石砾压住,似乎反映了对尸体的恐惧,用石块压住尸身,以防逝者打扰生者,祈求生者的平安。这种葬俗应该与干骨崖墓地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墓地所在的丰乐河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砾石,或为墓内积石的材料来源。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并不完全具有通用性,除了人类对于自然天然的敬畏外,还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随着地理环境的不同变化,对敬畏事物的处理方法也有些许差异。
三、结语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宗教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意识到精神世界极为匮乏的条件下产生的。它表现了人们在面对大自然的无能为力下寻找心灵寄托的方式。在甘青地区史前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中可以看出,祭祀等宗教活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埋葬祭奠死者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这说明在史前时期,人们信任宗教带给他们的对抗自然的力量,并由始至终地贯彻到他们的生活中,由此指导他们的的生与死。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宗教祭祀的形式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在徐家碾寺洼文化和湟中下西河卡约文化墓地发现的人殉,这不仅体现了先民们相信灵魂不灭,希望死亡后仍有人陪伴。而且体现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开始出现,不同地位的人埋葬形式產生了差异。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4(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