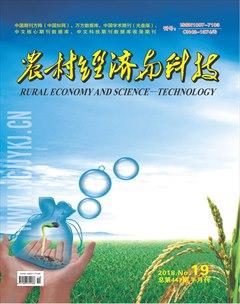传统思维方式与当代农村治理
杨永超
[摘要]从初民社会的原始思维,到现代社会的科学的系统综合思维,每一步发展,都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进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历经了数千年的洗礼,早已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农村,传统思维方式是主流思想,即便是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也仍然对人们的活动起着支配作用。农村基层治理必须把握好农村传统思维的每一方面,结合实际,正视传统,批判继承,推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传统思维方式;农村治理;宗族观念;鬼神思想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大多数。农村是一个保守的地方,所有中国的传统因素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这就是乡土气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左右甚至主导着当代农村的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原有治理体系,但终究也无法彻底根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从古至今,农村治理体系都体现为政治建构中最基础一环,农村治理的基础性决定了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充分重视农村问题,“只有当一个个小村庄也能够参与政治,国家的大政才有真正广泛而牢固的基础。”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是农民,所以必须以农民为中心才能有效推进当代农村治理进程,因为“农民既能起着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着高度革命的作用。”重新审视传统思维方式对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1 求“稳”心态与农村治理
中国古代传统思维对于“出世”的态度是极为谨慎的,“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这也是当今许多中国人都奉行的处世之道,不“出世”必然要求安分守己,克己复礼。这种思维方式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沉淀,在今天的广大农村地区仍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导致了农民的一种追求稳定的无为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被异化,成为处理任何一切事务的一条准则,但又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是伤害。
中国农村曾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漫长岁月,这样一种极不平等的社会形态能在中国维持两千多年,凸显了小农经济的社会稳定性,这其中最核心的还是求“稳”的小农心态的作用,而这种思想在今天极易被扭曲,给乡村治理带来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后,农民被广泛吸纳进入基层政权的治理过程,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内撤社建乡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村出现了农民与政治逐渐“疏远”的现象,一方面,人民公社的撤销和乡镇政权的建立,使政府“远离“了农民;另一方面,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农业生产而非以往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政治运动 。巨大的反差让人感到意外,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历过人人都讲政治的年代的人来说,对于这种“疏远”更是费解的。政府的“远离”和农民再次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没有了强力的政治动员,农民受到政治的冲击也小了,致使农民求“稳”的传统心理回归。
针对政府“远离”农民的现象,国家建立并不断健全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来激发农民的政治参与,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原有的人民公社的某些政府职能。在很多地方,村委会实质上是属于乡镇政府的一个下级机构,贯彻执行乡镇政府的政策,代行政府某些职能,如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稳定等。但即使这样,不少地方仍然出现农民与村委会的疏离,很大程度上固然是农民的传统思维求“稳”心理的作用,但也是基层自治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致,如某些基层干部脱离农民包办一切,行政过程长期不公开,不真心实意为民办事等。农民在这些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对于政策实施不再积极,甚至对农村基层治理采取漠视态度,农村治理必须依靠农民和农民对基层治理的冷漠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农村治理所要处理的头等大事。
农民的保守性使得其对于自身利益的得失是十分关心的,对待任何事物时往往最先要顾及自己的利益,而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且又无力捍卫时,容易选择两种方式,一是默不作聲,任其发展;二是誓死捍卫,不惜代价(如聚众闹事、上访等),一般如无必要,前者是大多数情况下的第一选择,使得对其他事物更加漠视;后一种选择和倾向则对农村治理形成不小挑战,给基层维稳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农民是传统乡土社会的代表,在充分尊重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农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使基层治理制度运行合理化,保障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都是必要的。农村基层治理要依靠农民,主动拉进农民与治理组织的距离,基层干部队伍廉洁化、高效化,必须给予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好处,增强获得感,打消农民自身的偏见,解决农民的困扰。
2 宗族观念与农村治理
家族是传统乡土社会的纽带,在传统政治生活中,家族历来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宗族观念和宗族意识早已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观念,宗族观念有着它的物质载体如祠堂、族谱等,物质载体容易遭受破坏,但作为内在的观念上的宗族观念则不可能被根除,在当代社会里,宗族观念和宗族意识已经难有过去那么根深蒂固,但是一有可能,它势必会再次兴起,如近些年来不少地方开始兴建宗族祠堂、编修族谱、祭拜祖坟等。
以血缘为纽带,加之地缘关系的影响,使传统社会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差序格局,而这一格局的中心就是家族,家族将作为单个个体存在的人以血缘关系连成一个“社会圈子”,差序格局的实质是家庭本位主义,“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中心是自己,这也是典型的自我主义。而家族则实现了把一个个自我串联起来,一个个家族又最终组成了传统农业社会。
家族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人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家族的束缚,在家族的框架内,借助家族的力量,每个人的力量都被放大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今天,家族关系在现代化浪潮下一定程度上是被新的人际关系所替代了,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家族观念在经历了建国后一段时期的冲刷之后又有了兴起的趋势,正式的宗族组织在建国后纷纷被取缔(需要指出,宗族观念在农村是从来没有消亡过的)。在农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家族观念也一直是基层治理所必须面对的,传统社会以家族长老为核心的家族治理模式被更加现代化的民主治理所替代,但家族作为一个“实体”仍然存在于广大农村地区。尽管当代宗族观念在孝道、敬老、邻里团结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宗族观念的兴起,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首先,宗法思想中的家长制、保守主义,已不再是今天社会的主流,势必阻碍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果这种落后宗族观念进入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以及基层政权内部,那么会导致家长制和官僚主义作风、官官相护和以权谋私、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人代法和以权代法等乱象。宗族势力对基层自治组织也构成了冲击, 主要表现在:①在部分群众中,宗族的凝聚力比基层政权的凝聚力要强;②村级班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宗族之间权力分配的舞台;③隐形的族长在地方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取代支书、村主任, 操纵乡镇党政主要领导;④宗族势力在某些问题上敢于与基层政权公开对抗。宗族势力对基层管理组织的侵入,将落后腐朽思想带入治理体系内,使农村基层治理处于“人治”状态,有悖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初衷。
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发生的变革,国家政权只延伸到乡镇一级,而农村则以基层民主自治的形式来实现自我管理。政府“远离”农村而“悬浮”于乡镇一级,造成了农村政府权力的真空状态,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加速, 而整合则严重滞后, 新旧体制之间此产生摩擦、出现断层,从而形成空隙和真空地带, 这就为宗族活动提供了机遇,给了宗族势力以可乘之机,宗族势力侵入到基层自治组织内部。在宗族观念支配下,农村基层治理成为了家族牟利的排他性工具,基层治理陷入危机,农民对于宗族势力操控的基层自治组织敢怒不敢言,选择敬而远之,对基层治理更加“漠视”。
再次,宗族观念下,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不能进行,容易形成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主义,从而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在不同的宗族之间,由于人为的宗族观念隔阂而不断分裂,导致宗族纷争,邻里不安;在同一宗族内也存在着矛盾,宗族内部矛盾往往成为邻里纠纷的主要动因,因为宗族内部矛盾往往关系到个人具体利益的得失,使得这类矛盾更加难以调和。
取締宗族观念和宗族意识是不现实不可行的,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有其好的一面(如家风传承),但宗族观念的极端化也给农村社会安定带来了隐患,也增加了农村基层治理在维稳方面的难度,在此背景下如何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应对新的宗族观念兴起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新挑战。
3 鬼神观念与农村治理
鬼神问题历来就是扑朔迷离十分复杂的,不同时期、民族、地域都存在对于鬼神的崇拜,鬼神观念也代表了人们思想深处最神秘的部分,常见的鬼神崇拜如人死为鬼或为神,鬼入地府,神归天堂,这才有了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神佛的敬畏。不同地域对于鬼神的崇拜又有很大差别,而鬼神观念往往与宗教因素挂钩,最终成为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首先,“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之天、地。曰命运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何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儒家思想中对天的崇拜几乎影响到所有中国人,也是中国古代对于天的主流看法。对于鬼神的敬畏不仅在于传统文化中鬼神数量之多,更是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神魔传说充斥于坊间,人民始终相信鬼神真实存在,鬼神也就成为古代统治者促进社会稳定维护统治的工具。
其次,鬼神观念又引出了“报应”的思想。“中国宗教中一个深植的传统即是相信自然或神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也都是每个中国人深知的道理。报应作为一种宗教概念被人们所接受,往往是通过皈依与鬼神来实现,鬼神的崇拜为“报应”提供了思想基础。不论儒释道还是西方宗教对“报应”都不排斥,这对社会成员来说是行为规范,人们相信有“报应”一定会来到,即便是在此岸世界看不到,也会在彼岸世界看到。
鬼神观念扎根的农村,农民相信有皇天鬼神报应的存在,往往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会预想未来的“报应”,似乎是用功利性的心理去看待每一件事,以此来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这也会导致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于一切事物的冷漠,认为一切自有伦理,人无法改变某些事情。那么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农民往往有这样的心态,对基层管理事务不积极,对即使是对某些自己认为的“恶行”也呈现冷漠态度,把一切都寄托与“报应”,又使得农民对政治事务参与的不积极程度更严重,容易造成慵懒的风气。
鬼神观念也是封建迷信和邪教的温床,虽然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普遍提高以及国家加大了对邪教的打击力度后,但某些不良用心者利用农民的鬼神观念,将战场转向农村,穿着宗教外衣大肆宣扬封建迷信和邪教思想,以牟取暴利。这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但又因为鬼神观念的掩护下,宗教外衣的包装,使得其难以被发觉,而农民更是难以辨别个中真假而频频中招。
鬼神观念是具有宗教气息的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之所以能深深扎根于农村即有它的合理性。它往往带有较强的腐朽性和落后性,但也是中国传统宗教的缩影,是人们信仰的皈依,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产物,孕育出了独有的中国文化。农村基层治理中在取缔封建迷信和邪教的同时要做到保护鬼神崇拜的文化产物,对农民的思想做正确的引导,这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如何甄别和加以保护在具体工作中是十分复杂和严峻的。
4 总结
传统思维方式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从目前的社会开放性来看,传统的行政方式已经难以有效满足农村社会矛盾解决的需要,因此,农村基层治理需要改进工作理念,重新审视传统思维方式在农村中的发展现状、作用和地位。就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各个地区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而传统思维方式始终是农村地区的主流价值之一,走近农民才能依靠农民做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基于当前农村的现状做出相应调整,以传统思维方式为推力而非视其为阻力,走出当前农村治理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13.
[2] [美]塞缪尔·亨廷: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7.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8.
[4] 高鑫.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忽视[J].真理的追求, 1995(6):31-33.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5.
[6] 杨联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升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