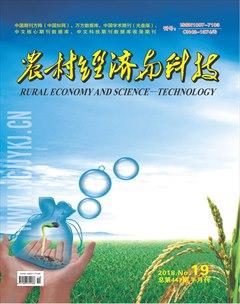政府与农民关系困境探析
柳家志
[摘要]人民主权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共识,解决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在民国初期和抗战期间,政府只是重视重点城市和战略要点的经营,广大农村长期得不到政府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却是生于斯长于斯,深知农村的强大生产力和生命力,明确对农村地区的治理和建设。在新时期,研究政府与农民关系不仅是经济命题,也是重要的政治命题。
[关键词]政府;农民;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可以做两部分来解:一是政府政权在农村的存在,即实现有效治理;二是农民对于政府信任和认可,即实现全面发展;政府对待农民的态度取决于政权的合理合法,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取决于政府治理是否利己,两者都来自于国家和个人理性。台湾学者林语堂曾说“中国人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指导着自己的各项活动。而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孕育了中国的个人主义。”所以,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决定了农民与政府关系的复杂,政府与农民关系的探究也更具意义。
1 政府方面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和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并不排除二者在各自具体利益上的差异性和矛盾性。由于在当前的改革时期,新体制尚未完全确立,而旧的体制亦未完全终结,这种新旧体制胶着状态使得政府与农民关系产生了新的扭曲。在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之中,代表国家力量的政府相较而言更具优势,并无所谓平等可言,这也就是异化理论在政治当中的鲜明体现,为实现政府与农民关系的良性发展,国家治理就必须达到能够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提高农民的政治自尊以及社会地位的效果。但现实却是,由于政府自身的能力和社会现实等各方面的局限,政府的治理效果并不明显,关系也需要不断得到修正。
1.1 定位不清
农村,传统意义上是指以农业作为主要生产生活的聚集地。傳统的中国农村存在手工业的商品交换,但是是以劳动生产为主要目的。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农村的边界远远小于传统意义上的,现在大量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集镇等因为生活面向城市经济已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地区,农村脱离了片状区域形成了团块状的区域。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下,农民被划归为生产小队。所以习惯上农民仍将自己置于小队的内部,在村内事务和组内事务常常出现队长的参与。相较于村,农民更愿意进入队内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诉求,大量的“壮劳力”流入城市和城镇寻找就业机会,造成村内的空心化。大量的人员以岁末年初为时间节点进行大规模的流动,由于经济原因,小学基础教育的留守儿童和年龄在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成为村内事实上的主体,同时村内还有大社员和精英存在。由于近年来返乡创业政策的推动,部分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拥有城市理性和城市思维的返乡新农民,对政府作为的要求也更加高。所以很明显的不同的群体,需求的不一致产生了利益分层,政府能否在新时期发挥政治智慧对“旧”农民与新农民的利益诉求给出合理的界定与分析,才是实现农民利益的现实性思考。
再有,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央政府可能会接收到来自村民的声音,能否摆正在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和农民关系问题上的责任到位至关重要。中国采用的分税制体制,造成了事权与财权的相分离,而很多的国家扶持政策需要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所以很多惠民利民政策的实行周期较长,政策的结构链被斩断,影响政策的打包推行和递进效果发挥,必然导致政策效果的失利。
1.2 推进城镇化与对农民的保育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仅是户籍和地域的转变,更是生活方式和经济再生产的变化。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更多的偏向于非农人口的增加,却没有打造出足够的非农产业来解决非农人口增加的尴尬。中国城镇化“大”的逻辑致使城乡边界被不断压缩,伴随而来的是对农村生产方式和法则的挤压,由于土地财政和拆二代的经济敏感,是对农民“不劳不获”的生存尊严的挑战,也是无法共享土地升值的不满。对农民的保育是建立保证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战略下的对策。由于我国地理差异明显,机械化的大农业在丘陵和山地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而庞大的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的支撑需要,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农业种植人口,在国家治理中能否兼顾这一部分劳动者的经济公平就更值得思量。
1.3 治理的行动逻辑
贺雪峰认为行动逻辑也就是行动规律,即指通过考察政府和社会在面对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时采取了怎样的行动策略,采取这些策略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中又隐含了什么样的规律。在贺雪峰与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书中提出,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遇事情不讲原则的策略主义和有问题消极不作为的捂盖子之举,也明确指出“不出事”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导致出大事。“不出事”的逻辑中饱含短期性的行为取向和重结果轻过程的价值倾向,所以,政府行动在“不出事”行动逻辑运行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不合乎法理的操作。“不出事”并不是什么问题什么矛盾都没有,只是没超出政府的掌控范围,最关键是不影响政府的政绩。(谢正富,2014)在权力授予的逆向和晋升锦标赛的机制下,“不出事”的逻辑更趋强化,“不做不错,做多错多”成为官场法则和政治前途护身符。
1.4 发展路径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但形成的原因和程度各有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距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为了尽快形成自身的工业体系,许多国家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城乡经济的对立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期都具普遍性,也或者说是必然性,农业经济的弱质性决定了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劣势。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路径有其特殊性,赶超的国家战略奠定了二元结构的基础、城乡分离的制度固化了二元结构、公共资源的倾斜配置增大了二元强度、改革开放的战略取向增强了二元结构的长期性,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巨大差距、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发展不同步、城乡劳动要素不平等、生产方式二元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不协调等问题,造成农村的人为贫困。(刘明慧,2008)这种贫困是损伤农村发展肌理,掠夺发展机会,工业的强制剥夺和竭泽而渔的后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能否解决长期贫困的不满和促进农村新发展是政府与农民关系改善的经济前提。
2 农民方面
2.1 臣民文化
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政治文化被定义为针对政治客体(政党、法院、宪法、政府等)的“取向性模式”,包括对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方面,以及作为政治角色作出自我认知与感情和评价的种种取向。作为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阿尔蒙德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狭隘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马玉娟,2005)中国经历了悠久的封建集权时代,在传统中国,以往数千年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个人对家庭、国家、社会的绝对认同,形成了个人消融于群体的臣民文化。简单地说臣民文化就是就是人民潜意识里对政府的顺从态度,从上文提到的“管”的需求也可略知一二。比如人们对政府政策的出台很关心,包括自己会在这个政策中的利益损益问题,但它绝对不会想到用自己的合法权利去干预或者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去。简单看,似乎民众对行政力的依赖性强,更便于管理(至少表面看是这样),但其实正如“超稳定社会”孕育着最大的不稳定一样,在一个公共精神孱弱的社会,在公民文化不易生长的地方,社会管理绩效最低,它的行政代价也必然极为高昂。它一方面造成行政成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行政力对社会和市场的渗透和干预必然且多且滥。本应由社会或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终由行政力来操办,使行政意志无处不在。于是,行政力量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担当着主体,成为一切社会事务的主角,成为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无限政府”,而“无限政府”的本质是“无宪政府”,“无限政府”必然超越权力的边界而使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导致国民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之间产生隔膜。政府在公共舞台上奔跑和表演,国民则是舞台下打着哈欠或瞌睡的观众。(秦德君,2013)
在我国现阶段,臣民文化已经不再占据十分主流的地位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使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有了独立的意识。而对于臣民文化这一传统文化现今虽已非主流文化,但由于其存在历史之久远,实非短时期内就能改变的事情,在中国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民还是在臣民文化的影响下与政治发生关系。对于清官圣人的政治期盼就体现了臣民文化的潜移默化,“为民做主”恰好就是民主的对立面——集权。人民缺乏自我表达和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意识,只好将希望寄托在权威的政府人员身上,希望他们能代表群众的共同利益,有清官能为民做主这其实就是自动放弃了政治权力,使权力集中于政府人员身上,这无形中就强化了官员、臣民的意识,使两者产生分化,最终导致人民权力的丧失。在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中本身就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农民,在臣民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中比较劣势就更加突出,也就更加消极。
2.2 生活面向
贺雪峰认为生活面向是指村民建立自己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时的面向,在传统社会,尤其在农村地区,在稳定和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面向具有高度的内向性,有着稳定而明确的共同体及集体意识。(贺雪峰,2013)改革开放之后,由打工潮和升学热为两大引擎的牵引,农村居民流动不断加快,在生活面向方面从单一稳定的内向型分离出外向型的生活面向,此類个体对共同体和集体意识趋于淡薄甚至无视。(杨小华,2016)同时认为农民存在着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以及基础性价值等等,在市场经济不断进入的乡村,农民的价值边界被不断突破,生活面向也更趋于城市,打破了村庄价值生产机制,蕴含极大的不安分,这种不安分不是简单的行为体现,而是相对剥夺感下的心理“冲动”。农民的价值理性选择面向城市,离开了乡村本土而选择了城市“漂流”,正是这种进入城市的价值冲动导致了农民入城后的“无根性”。在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打破的前提下,农民的愿望更多的是被粗陋认为是逐利性行为,而不是农民价值追求的正当。其次,农民入城除了增加社会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导致农村的空心化,空心化的农村不仅让政府认为价值投资和资源投资的不必要和无力感,也使农村留守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2.3 经济理性
农民也是关注自我利益的理性人,会选择成本支出最小,收入最大的收入方案。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高歌猛进,对传统乡村社会造成冲击。经济理性被解读为农村市场经济后的产物,但不得不说这是经济学者的学科自豪打造的狭隘视角。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传统靠天吃饭的农村,农民对于什么地种什么作物都有合理的安排,这种理性更多的适用于农业生产,但却是农民早期的理性思考。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带给农民是与国争利而不是与国谋利。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无论是臣民思想还是定国安邦的奉献精神,都是让利与国,农民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结合。市场经济是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个人理性激烈表达,所以与国争利、与众争利成为农民行为新常态。在政府治理中,农民抢先关注是与己有利否,与民协商和公共决策的公共产品的非排他也为农民提供制度武器,致使国家政策也常常演变成为经济拉锯,政策效果不佳。
3 小结
诚如上文所说,农民的不安是为打破城乡分野下唯血统论以求取社会尊严和政治认同的斗争,也是反制贫富不均的努力。政府对农民的诉求应有清楚地认识,旗帜鲜明的态度,真正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腰杆挺起来,头抬起来才是政府积极作为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刘明慧.城乡二元结构的的财政视角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2] 谢正富.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3]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 使树菁中国基层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5] 邱贵明,蒋国河. 政府与农民关系的互动与调适——“八十年探索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述评[J].中国农村经济,2008(3).
[6] 俞弘强.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相关成果的考察[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5).
[7] 杨海坤,樊响.论乡镇政府与农民关系的优化——从改善制度环境的角度切入[J]. 江淮论坛,2015(06).
[8] 秦德君.“臣民文化”的历史困境[N].深圳特区报,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