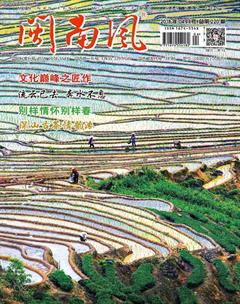摩托车后座
林少华

家里打小最贵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那辆老式摩托车。
“坐好了吗?”摩托车后座上的我和母亲点点头应了声“好啦,出发!”父亲随即左手抓住离合器,娴熟地抬起左脚,踩两下挂挡,右手一转油门,迎面就吹来一阵凉爽的风。
自打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以卖菜为生。摩托车是载货的工具,换了一辆又一辆,仍旧不改它在父亲身边的地位。农村道路的坑坑洼洼以及长期运载大量蔬菜,摩托车很快就滋生了咿咿呀呀的咯吱声响。那时候,家家户户的男主人几乎都有一辆摩托车,我们放学早,回家围着灶台做完饭,细致地盖起来,等父母回来一起吃饭。那个時代的每个孩子练就最厉害的就是听声识人,这周边几辆摩托车就有几种不同的声音,一听摩托车的声音,我们就能知道哪家的主人回来了。等到父亲的摩托声出现在村头,我就会飞一般地跑出去,在巷子口等他刹车,未来得及停稳车身,我就一骨溜爬上摩托车后座,抱着父亲的腰,迎着夕阳,一起回家。
一提冬季,回忆的不是冰冷而是满满的暖流。按照惯例,我们每周必去十公里开外的县城看望爷爷奶奶,这个习惯从未改变,冬天也一样。瑟瑟的寒风在街上呼呼地刮过,吹起了地上的落叶,各家的窗户紧紧实实地关着,似乎人们都不迎接这位“威风凛凛”的寒风。
一辆摩托车,三个人。爸爸是司机,在最前面,我夹在中间,妈妈在后面,这样的排列持续了十多年。冬季里,摩托车的车把上总是套着一副黑色的加棉手套,车座左右两侧因为长期运载重物磨损出深黄色的棉面;后座两侧,为了载蔬菜而加上去的铁架刚好成为垫脚板,矮矮的我上车也就毫不费力。上车后,我环着爸爸的腰,将小手插入他的军大衣口袋里,妈妈抱着我,将她的手环在我和爸爸的中间取暖。
这个时候是我被宠溺的时候。我把小脸蛋埋进爸爸厚实的背板,骑着摩托车两小腿一张一合如骑马一般,想象自己奔驰在草原上,英俊潇洒。口中跟着车身颠簸节奏伴着车的吱呀声念念有词满腹梦想。就这样,我小小的身躯,在父亲的臂弯里,母亲的怀抱里,甚是温暖。
雨季是大人们最不喜欢的季节。恰逢从奶奶家出来下雨,后座的时光对我而言却更为兴奋。父亲的雨衣是一人式的大雨衣,我和母亲就窝在父亲的雨衣下。母亲弓着背,将我揽在怀里,我看不见周围的景色,总会时不时焦急地询问到了哪里。后来学会了默数转了几个弯,地板上有哪些矮标识,自学成才知道方位。雨季,父亲听不清我的叽叽喳喳,我就开始自娱自乐玩起水来。雨水顺着雨衣曲线,从我两侧流下一条长长的链条。我喜欢用小手掌去接待它们的到来,它们就会顺着手臂,亲昵地跑进我的胳肢窝。脚上的喜悦也不曾停止,泥泞的道路,时不时调皮溅起水花,打湿裤脚,留下土黄的泥巴花。然而,体质虚弱的我,很容易因此感冒,这导致母亲要时不时把我的小手压回雨衣下,抱得更紧实。
后座上的时光,随着我们的外出求学日渐减少。不管是春风和煦,艳阳高照,亦或是冬日冰霜,一如既往来来回回循环反复。十几年的日子,犹如飞梭一样。长大,在不知不觉间。人说在父母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而我们的眼中,自己已经长大,父母却渐老。
那日,毕业回家的我,高举毕业证书,一脸笑容地说:“妈,你坐中间,我们去给爷爷奶奶报喜去!”让母亲坐在我和父亲的中间,静静地闭着双眼,紧紧地圈住她的腰,牛皮糖一样粘住她的背。
后来,实行摩托车限载,那辆摩托车成了父亲的短途代步工具。家里也早已换上小车,一人一个座位坐得舒坦,也不怕风吹日晒、严寒酷暑。只是这十公里的路途上总觉得少了些许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