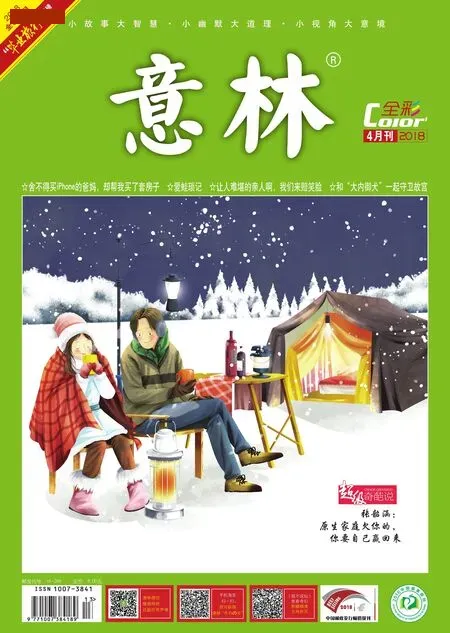让人难堪的亲人啊,我们来赔笑脸
□ 南在南方

看程绍国写的《林斤澜说》,有一章写林先生和汪曾祺先生的莫逆之交。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作者提起游鸥海时,一个年轻姑娘挽着汪曾祺,走在后面的汪的妻子施松卿对作者说:“老汪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女孩子。你看你看……不过,我不嫉妒,真的没有嫉妒,哈哈哈……”2000年,在北京林斤澜家附近的建国门客栈,我说起这件事,林斤澜感慨地说:“老施脑血栓,瘫倒在床上,还疑心曾祺和保姆有关系。有一天,保姆问她晚饭吃什么,老施竟说:‘吃逼!’(原文如此,抱歉)曾祺对我说的时候直摇头,说:‘你换一个词也可以嘛,比如说:吃屁。’”
忽然眼热,不说施松卿当年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美人,也不说汪曾祺喜欢女孩子,而是病中汪夫人说的那两个字,这两个字无疑令人难堪,可若说这话的是我们的亲人呢?
比如我在《我妈》里写道:我妈笑起来像灰兔子,灰白的头发,露出仅剩的两颗门牙!不过兔子不流口水,我妈有时要流口水,可谁也拦不住她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完之后要说一句:“要是有啥药,把我的笑给治了就好了。”我说:“你只管笑,比哭好!”我妈自从中风之后,就爱笑。我说:“妈,你笑啥咧?”我妈说:“想着有一回下雪咱屋一只鸡摔了一跤,爬起来,一拐一拐地跑了……”话音未落,又笑起来。
很多时候,我妈管不住自己的笑,家里有客正说话,我妈忽然笑了,常常让人莫名其妙,自然,我们得解释一番,这样客人才释然。因为,我妈坐在那儿,看上去好好的,正常人一样嘛。
生活里头,亲人让人难堪的事总是免不了。
有一年夏天,我坐公交车,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小伙子坐一起,小伙子明显不对劲,脑袋拧着瞅后座一个女子,这个男人就扳他的身子,扳他的脑袋,他明显地挣扎,还要拧过脑袋,呆呆地瞅着那个姑娘。中年男子跟女子轻轻说:“对不住啊……”小伙子第三次转身,伸手指着女子的胸说:“爸爸,好大奶!”
那女子忽地站起来,指着小伙子,恼怒的嘴唇颤抖着……
中年男人再一次道歉,脸上绛红着,好像有点轻微的抖动:“对不起,娃有病啊。”那女子余怒未消说:“有病,你领着他出来瞎转?”中年男人诚恳地说:“不是瞎转,去看病……”
周遭的人就劝姑娘息怒,那男人将小伙子的脑袋搂在怀里,这时,小伙子不挣扎了,只是安静地靠在他爸怀里。
他没有责怪儿子一句,或许责怪并没有意义。
我们无法知道自己将会有怎样的父母,就来到世上了。父母也不知道将会有怎样的儿女,就养育了我们,就算是一块石头,他们也要焐热我们,有时候,我们让他们难堪。
父母曾经是庞然大物,只是后来,总有令人难堪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由着他们让人难堪,我们来赔笑脸。因为这样的时日,也许不会太多。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说:你和死亡好像隔着什么在看,没有什么感受,你的父母挡在你们中间,等到你的父母过世了,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你不知道。亲戚,朋友,邻居,隔代,他们去世对你的压力不是那么直接,父母是隔在你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把你挡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