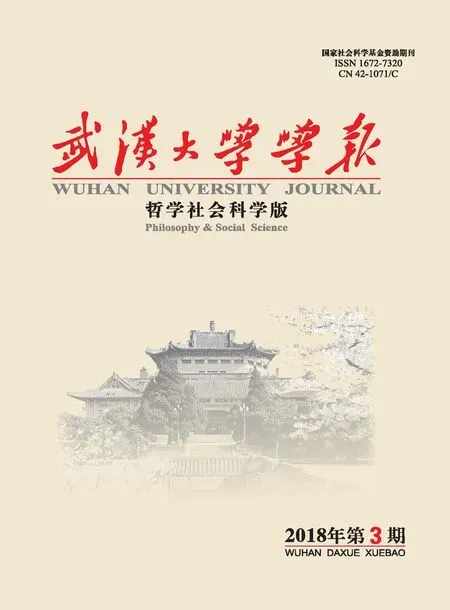公海元叙事与公海保护区的构建
马得懿
一、引言
晚近以来,建立公海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 on the High Seas)以应对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管理、科学研究以及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正日益为国际社会所青睐。公海保护区一度成为区域甚至全球海洋治理的新工具和新形态。然而,构建公海保护区从来都不是单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它更体现着一种海洋资源的国家控制权利和管理能力[1](P45)。公海保护区的构建,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从理念、内容和执行层面,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可以解读为自由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习惯权利与条约义务的关系以及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的关系[2](P10)。毫无疑问,从理念、内容和执行层面来审视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具有理论层面上的合理性。但是,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实践复杂性表明,公海保护区在完成既定目标的同时,亦面临根本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诸如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合法性问题,即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国际法基础问题。在2013年7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俄罗斯曾经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提议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表示质疑[3](P12)。故此,公海保护区构建所依赖的国际法原则需要澄清。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海域。因此,要想用全球统一的方式来解决海洋问题非常困难[4](P89)。更何况,现有国际法框架之下的公海保护区体制存在诸多制度性空白①严格地说,本文所提及的公海保护区并非全部属于公海保护区。某些海洋保护区基于特殊的海洋区域,诸如“地中海行动计划”下的特别保护区,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来衡量,该保护区所涉及的海域并非属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义上的公海。。公海的国际法地位和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复杂性,决定全球性公海保护区体制的构建是一种奢望。因此,尝试探索公海保护区发展趋向则显得尤为必要。
为应对上述两个基本问题,本文将公海保护区构建的问题置于公海元叙事这一视阈之下。公海元叙事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前期的学术基础。早在1924年,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佛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cois Lyotard)就把元叙事界定为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5](P1-2)。我国学者在元叙事的基础上,将此理念引入海洋秩序的研究之中而提炼出海洋元叙事,即关于海洋秩序的叙事。当今海洋法律秩序是在历史上关于海洋空间、资源、战场这些叙事的影响下形成的,海洋大国的海洋叙事能力一直是影响海洋事务的一个持久因素[6](P63-85)。故此,公海元叙事是旨在系统地阐明公海秩序的合法化表达。依赖公海元叙事的基本模式,以探究公海保护区构建的核心基础和发展规律问题,便具有可行性和重要价值。公海保护区的构建置于公海元叙事视阈之下,为理解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提供另一种进路和视野。
二、公海自由制度张力的逐渐发展与公海保护区
公海自由与海洋保护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亦可以转化为如何正确诠释公海自由制度张力的问题①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的规定,公海自由意指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以及科学研究自由等。当然,公海自由的行使受到一定的限制。。公海自由在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1982年《公约》)框架下得以固化并得到不断发展。
(一)公海自由制度张力的逐渐发展
17世纪之初,胡伯·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对海洋自由的论述与他对人类财产权演变的分析紧密相关。当格劳秀斯提出海洋开放原则时,他深信渔业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7](P38)。进而,出于维护荷兰的国家利益之考虑,格劳秀斯认为,根据国际法,任何人可以自由航行到任何地方,自由贸易指向一切对象。然而,英国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m)发表的《闭海论》(Mare Clausum)完全站在格劳秀斯的对立面。400多年前格劳秀斯与塞尔登之间的对抗,实际上隐含着公海自由与限制公海自由之间的对抗。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思想一度占据上风而流芳千古,并且最终被1982年《公约》固化为基本原则。某种意义上,格劳秀斯与赛尔登的对抗奠定了公海自由制度张力的思想基础[8](P1-17)。
海洋法内部存在一定的张力。詹姆斯·克拉斯卡(James Kraska)在《海洋大国与海洋法:世界政治中的远征》(Maritime Power and the Law of Sea:Expeditionary Operation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提出“海洋法的张力”,认为当前沿海国与海洋大国之间的张力主要集中于专属经济区[9](P55)。人类利用海洋实践催生的公海自由的含义不断丰富和发展,公海自由的制度张力亦越发复杂。公海自由的制度张力分别经历了第一层级张力、第二层级张力以及第三层级张力三个层次。
1.公海自由第一层级张力。公海自由第一层级的制度张力,也是公海自由的传统张力,主要指在理解和行使公海自由中所形成的沿海国利益与海洋大国利益之间的冲突。自从人类社会步入20世纪,人类对海洋开发和治理的能力日渐增强,世界上少数海洋大国染指海洋领域的深度日益增强,而部分沿海国的海洋意识也逐渐萌发且渐次意识到海洋的战略地位。由此,沿海国的扩权意识和行动逐渐加强。为了规范各国兴起的“蓝色圈地运动”,1928年国际社会开始起草和审议一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即《领水公约(草案)》,开启国际社会以国际法来规制海洋区域地位的先河。这也预示着人类利用国际规则来利用、开发与管理不同区域海洋的开始。伴随着特定海洋大国开发海底、底土以及大陆架能力的增强,人类逐渐将开发海洋的触角延伸到深海,其重要标志就是1945年美国发布《杜鲁门公告》。《杜鲁门公告》的发布对世界上沿海国产生强烈的反响,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以不同方式宣布对领海以外的大陆架及其上覆水域的资源提出权利要求。
为了协调沿海国利益与海洋大国利益之间的冲突,1958年国际社会形成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体系,其中之一便是1958年《公海公约》。1958年《公海公约》明确了公海自由的基本涵义,并且建立“领海—公海”二元海洋体制。1958年《公海公约》反映出沿海国利益与海洋大国利益之间的对抗,尤其是在领海宽度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2.公海自由第二层级张力。公海自由第二层级张力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发达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由于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体系没有解决领海宽度问题,同时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国际社会开始启动联合国海洋法第三次会议,历时9年的第三次海洋法大会形成1982年《公约》。1982年《公约》以“一揽子协议”(A Package of Deal)体系构建公海自由的国际法体系,并且发展了公海自由的范畴①1982年《公约》第87条丰富和发展了1958年《公海公约》下公海自由的范畴。。显然,1982年《公约》及其公海自由的发展,主要根源在于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非殖民化运动的高涨、联合国等国家组织的推动以及世界能源新秩序的形成[10](P27-28)。此阶段公海自由体系的形成,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发达国家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与公海自由第一层级张力相比较而言,公海自由第二层级张力的主要特征不仅仅局限于沿海国与海洋大国之间,而且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包括部分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等。不仅如此,公海自由第二层级张力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饱受争议的核心问题——专属经济区的地位,至今尚未明确②1958年《公海公约》下的“公海”为“不包括一国领海或者内水的全部海域”;而1982年《公约》没有明确界定“公海”。然而,在起草1982年《公约》过程中,“公海”是否包括专属经济区的问题则引发很大争议。[11](P8)。
3.公海自由第三层级张力。海洋全球治理日益受制于海上航行秩序、海洋非传统安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的养护与利用以及国家安全等因素的制约,故此,不断衍生出公海自由第三层级张力。公海自由第三层级张力,主要指国家管辖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在行使公海自由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在行使公海自由方面的利害关系,行使公海自由的形式和内容应当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12](P165)。1982年《公约》意识到“公海自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范畴。行使公海自由必须受到约束,公海自由的概念不是进行战争、耗竭生物资源、污染环境或者不合理地干涉其他国家船舶合法使用公海的许可证[11](P16)。英国诉冰岛渔业管辖权案中,国际法院认为,1958年《公海公约》是对“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原则”的宣示,这些原则包括国家行使公海自由时必须“合理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13](P22)。1982年《公约》第88条明确了“公海应该只是用于和平目的”,然而,该《公约》既没有界定“和平目的”,也没有明确允许的海洋军事使用的类型[14](P404)。这导致各国在解释“和平目的”上产生较大歧义,这也是加剧公海自由制度张力程度的原因。
由此,在海洋治理上形成了国家管辖与国际合作的严重对立问题。为了缓解国家管辖和国际合作之间的张力,根据1982年《公约》第87条、192条、194(2)以及196条,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诸如国际海事组织,先行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和国际航道安全领域,尝试国家管辖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协调问题。尤其,晚近逐渐兴起的公海保护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公海自由制度张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公海保护区的类型和目的,比较集中地反映出公海自由与限制公海自由之间的关系。
(二)构建公海保护区的实践与公海元叙事
1.公海保护区的主要实践。公海保护区源于海洋保护区。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大约公元9世纪,在太平洋西部和印度洋一些群岛国,当地渔民尝试采取特别捕鱼方式或者“禁渔区”来节制捕鱼活动[15](P854-875)。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的重要性,明确保护区作为实行管制和管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一般来说,2012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海洋保护区的界定具有较大影响③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定义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CICN)的定义:“任何通过法律程序或者其他有效方式建立的、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环境进行封闭保护的潮间带或潮下带陆架区域,包括其上覆水域。”。后继许多海洋保护区的区域性国际法框架吸收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关于海洋保护区的定义[16](P12-14)。公海保护区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框架和基础必须超脱于海洋保护区的概念[17](P213-219)。目前体制之下,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与管理机制比较复杂,呈现出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多元介入的格局④根据1982年《公约》第197条,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定和制定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者区域性基础上,直接或者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
公海保护区的制度基础得益于国际海事组织在治理海洋环境污染和航道安全方面的经验。根据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和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之规定,国际海事组织有权采取防止国际航运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区域性管理措施,并且有权划定“特别敏感海域”(Particularly Sensitive Sea Areas)[18](P41-50)。为了强化和固化国际海事组织的一系列举措,根据1982年《公约》第211条第(6)款,亦设计一系列制度,以完成特定海域环境与生物资源的保护。一般地,“特别敏感海域”的设立并不局限于专属经济区,一国的领海和特定海域诸如海峡、公海都可以成立“特别敏感区”。1975年地中海沿海国制定“地中海行动计划”并签署《巴塞罗那公约》;1992年比利时、丹麦、英国、法国以及欧盟共同签署《保护东北部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各国展开合作以保护东大西洋环境;1995年地中海沿岸国通过《巴塞罗那公约议定书》强化必须遵守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内环境保护措施等;1999年11月25日,法国、意大利与摩洛哥根据《关于建立地中海海域哺乳动物保护区的协定》,共同建立派格拉斯海洋保护区,旨在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免受人类活动的干扰①上述海洋保护区设立的国际法依据分别是1975年《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和沿海区域公约》、1992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以及2009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等。。
1980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为南极海域的保护区构建提供了有效的国际法根据。2009年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通过一项措施,决定设立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保护区,该保护区禁止一切捕鱼活动,与渔业活动有关的科研活动需遵守一定的保护措施[19](P1-8)。在前期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基础上,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实践得到一定的推广和扩展。2013年,南极海洋资源养护委员会依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该保护区的建立历程比较曲折,主要是在南极资源养护委员会是否有权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这一问题上各国存在分歧[20](P18)。海洋大国以建立公海保护区为契机介入公海的管理动机明显,这引发了相关国家的不满和忧虑。2017年11月30日,国际社会通过了《防止北冰洋中部公海无管制渔业活动协定》(下文简称《协定》),旨在规范和治理北冰洋中部公海渔业资源。这是北极国际治理和规则制定的重要进展。《协定》不减损各方依据1982年《公约》享有的公海科学研究自由等[21]。虽然《协定》尚未明确建立北极中部公海保护区的举措,但是该《协定》的临时措施基本上反映出与公海保护区基本功能相一致的理念。
国际社会推动公海保护区的构建,依稀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构建公海保护区的可行性和沿海国合作程度上,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具有由易到难的基本轨迹。作为半闭海的地中海海域,地中海沿海国借助欧共体的协助和斡旋,以富有特色的“地中海行动计划”为行动指南,构建了富有成效的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作为海洋地位极为特殊的两极地区——南极海域和北极海域,国际社会认为,南极罗斯海海洋保护区和北极中部公海都不同程度地承载着“国际利益”,构建保护区的国际认可度较高。
2.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元叙事方式及其检视。上文所阐释的公海自由及其制度张力的三个层级,为进一步理解公海元叙事模式下的公海保护区构建提供基础和前提。
其一,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之间的动态性冲突。
构建公海保护区的实践,一直伴随着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公海上,船舶通常受制于船舶登记国即船旗国的管辖。根据1982年《公约》第211条和220条的规定,1982年《公约》的制度设计过于维护船旗国的利益,导致船旗国、沿海国以及港口国之间的利益一度失衡。1982年《公约》框架下沿海国的权利与义务配置不足以应对沿海国保护本国的海洋遭受到船舶污染的风险。1982年《公约》赋予沿海国行使保护本国利益的前提是“沿海国遭受重大损害或者有实质性损害的威胁”,这显然不利于沿海国有关利益的维护。事实上,沿海国的安全利益并不仅仅限于海洋环境污染的防范;更何况,公海的海上威胁很容易危及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毗连区乃至领海海域[22](P202-203)。
为了应对公海保护区构建中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之间失衡的问题,国际社会出现了扩大沿海国管辖权的趋向,并出现了沿海国管辖权的滥用问题。晚近以来,重新塑造船旗国与沿海国之间管辖权的平衡问题,逐渐由若干重要全球性或者区域性国际组织来承担,尤其是国际海事组织被赋予历史重任。在国际海事组织主导之下,一系列有力举措得以执行①国际海事组织分别实施了分道通航制、强制引航制以及船舶报告制、船舶交通系统以及无锚区等相关措施。,这些举措协调了沿海国管辖权扩张与国际社会利用公海的权益之间的冲突。历史经验表明,当国家的海洋能力出现显著增长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扩张将不可避免,公海自由也必然受到相应的限制。总之,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之间的动态性冲突是公海保护区构建中面临的矛盾之一。
其二,“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国际法状态。
无独有偶,1982年《公约》注重各个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但是,作为1982年《公约》非缔约国是否应该遵循此原则呢?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之相关规定②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者权利。”,似乎1982年《公约》非缔约国并不受制于1982年《公约》的约束③国际法院的相关重要判例也支持了此种观点。诸如,荷花号案和北海大陆架案都不同程度地认可此种实践和理论。。然而,1982年《公约》第3条、17条、52条、61条以及87条等在赋予权利或义务时没有采用“缔约国”的措辞,而是采用“国家”的措辞,甚至“所有国家”或者“所有国家的船舶”的措辞在1982年《公约》中多次出现④比如1982年《公约》第 2条第1款提到的是“沿海国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a coastal State),而非“沿海的缔约国”;第3条使用的是“每一国家”(every State);第 17条和第 52条使用的是“所有国家的船舶”(ships of all States);第 61条第 2款使用的是“所有沿海国”(the coastal State);第 87条使用的是“所有国家”(all States)等等。。深入挖掘和考察上述1982年《公约》所采用的措辞,至少可以从某种角度上推论出1982年《公约》具有不仅仅是为缔约国,同时也具有为非缔约国而制定或编纂的倾向和意图[23](P261-262)。就公海保护区的构建而言,如果某一国家游离于某一公海保护区所赖以建立的国际法框架之外,那么该国并不必然完全不受公海保护区体制的约束。然而,公海保护区构建面临的重要现实在于,某些海洋国家以公海保护区的区域国际协定的非缔约国为由,充分利用习惯国际法而享有国际法权利,但刻意不承担相关国际法义务。此谓公海保护区构建中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国际法状态。通过区域性国际条约发展公海保护区的基础越来越扎实,但部分国家仍然可以通过不签署或不承认相关国际条约的方式坚持传统的公海自由。公海保护区既有养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也应当允许可持续利用,而不能“只养护,不利用”[2](P95)。质言之,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必须应对习惯权利与条约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公海元叙事视阈下公海保护区构建所面临的基本课题。
故此,反思和检视公海保护区构建中元叙事方式问题成为必要。就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之间的冲突而言,1982年《公约》在认知和处理海洋环境的整体性和流动性风险上存在缺憾。1982年《公约》所涉及的船旗国和沿海国的海上管辖权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沿海国的管辖权从海岸线到公海由强变弱,而船旗国的管辖权从公海到领海由强变弱。然而,海洋的整体性,尤其是海洋生态的流动性与国际性,对其管辖的程度并不必然与1982年《公约》框架下管辖权变动规律同步。世界上某些重要的敏感公海保护区具有跨越不同法律地位海域的属性,导致无论是船旗国管辖权,抑或是沿海国管辖权,都面临着复杂的局面。晚近以来,由于船舶悬挂“方便旗”航行盛行,导致船旗国管辖权面临复杂局面。虽然在法国诉英国马斯喀特三角帆船案(Muscat Dhows)中,常设仲裁法院宣布的“决定授予谁悬挂其旗帜的权利,以及制定管理这项授予权的规定属于主权国家”被认定为一项基本的原则[24],但是,“方便旗”盛行导致国家与船舶之间的真实联系(real connection)难以建立。1982年《公约》只是一般性要求船旗国在行政、技术和社会事务方面对船舶有效控制即可,而船旗国控制其船舶在公海上捕鱼的具体义务比较模糊[25](P89)。
就公海保护区构建元叙事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国际法状态而言,最为典型的情境是某些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框架的非缔约国,在充分享受习惯国际法赋予的权利的同时,刻意规避或者漠视其应该承担的国际法义务,进而造成公海保护区构建中“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国际法状态。然而,权利义务已经成为国际关系行为的最终表现,以国际法形式承载的权利义务体系已经成为国际关系规范体系的主要部分[26](P173-181)。根据有关国际法实践,非缔约国是否可以基于习惯国际法规则主张权利,然而该权利是需要满足履行义务才能享有的。这一点在尼加拉瓜案中得到重视[27](P11)。目前,公海保护区实践并没有完全解决某一相关国家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国际法状态,导致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协定下权利与义务配置不平衡的局面,进而威胁公海保护区所依赖的国际法的稳定性。
三、公海保护区构建的新动向与国际法基础
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实践动向呈现出新的趋势,梳理这些新趋势具有必要性。同时,深入探究公海保护区构建所赖以存在的国际法基础,构成全面认知公海保护区构建的重要环节。
(一)公海保护区构建的新动向
1.沿海国管辖权的膨胀。公海保护区框架下沿海国或者提议国的管辖权日益膨胀成为公海保护区构建的新动向之一,其重要标志是渔船登临权日渐成为执法的重要举措。尽管公海上存在着普遍管辖权,但是长期以来,渔船登临权的实施并不普遍。依据1982年《公约》第110条和国家实践,公海登临权的适用具有严格的条件。2001年《鱼类种群协定》生效后,公海登临权的概念得到发展,公海登临权适用于公海捕捞渔船的实践日益增多。同时,中国渔船成为行使公海登临权的主要对象(如表1所示)。1982年《公约》没有具体规定养护公海上生物资源的执行措施,而是由有关国家之间通过缔结合作协定来解决相关问题。1992年《北太平洋溯河鱼群养护公约》是第一个将登临权适用于公海渔业资源养护的渔业协定,并授权任何成员国有权登临从事被禁止的捕捞活动的船舶[28](P14-35)。沿海国管辖权膨胀的另一例证是2017年厄瓜多尔强制适用本国法律审理的“福远渔冷999”案①2017年8月13日,一艘中国籍渔船“福远渔冷999”因为被发现涉嫌非法占有和运输鲨鱼,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被当地执法人员扣押。同年 8月 25日至 27日,厄瓜多尔根据本国《整体刑事组织法》(The Intergol Criminal Organic Code)第247条之规定,判处20名中国籍船员1至4年的监禁。。通常,海洋保护区因为其跨度不同法律地位的海域,导致其法律地位亦存在复杂性。该案船舶涉嫌运输和交易保护物种,而且该船舶在经过海洋保护区时没有报告相关机构。厄瓜多尔法院实施排他性管辖权,并且判决涉案中国船员违反该国的刑法[29]。该案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存在很大争议,尽管涉案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海保护区,但国际司法和各国实践有力印证海洋保护区包括公海保护区沿海国的管辖权日益膨胀成为一种趋势。

表1 2011-2016年中国渔船被登临情况[30]
2.治理公海保护区的“低政治”公约的勃兴。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在特殊海域推行“低政治”国际公约,尤其是国际海事组织利用“低政治”航行规则所依赖的程序优势,逐渐在特殊海域构建“低政治”公约治理模式[31](P75-84)。由于国际海事组织在特殊海域推行具有强制性适用的“低政治”公约治理模式取得积极效果,近年以来,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或多或少追踪此种趋势。事实上,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航运规则的强制性导向,以应对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前文提及北极中部公海适用的《协定》的基本框架,向国际社会表明,处于特殊地位的公海治理新模式某种意义上亦代表当前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发展趋势之一。该《协定》框架尚未明确构建北极中部公海保护区,但是《协定》展望未来建立正式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前景。为了避免北冰洋公海“临时性禁渔”变成“永久性禁渔”,《协定》规定“初步有效期限”,为未来建立正式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奠定基础。这是该《协定》颇具特色的亮点——“日落条款”[32]。特殊海域的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多以“低政治”公约的方式展开,比较巧妙地实现公海自由与限制公海自由的平衡。
3.公海保护区蕴含的其他价值。西方某些海洋法学者或者政治家眼中,海洋秩序的“领海—公海”二元论是最佳安排。专属经济区在今天通常被描述为自成一格(sui generis),该区域内某些权利和责任的分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33](P107)。作为1982年《公约》最具有革命性的创造,专属经济区导致1982年《公约》体制之下的“公海”迥异于1958年《公海公约》体制之下的“公海”,导致专属经济区构成公海自由的巨大绊脚石[34](P849)。专属经济的某些制度安排包括1982年《公约》框架下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极有可能在公海保护区的构建中得到体现和隐含。世界上两个特殊海域海洋保护区问题,暗示着公海保护区具有深层次的蕴意和价值,至少在海洋划界上具有一定的潜在功能。其中巴伦支海的商业鱼群的管理体制,暗示着公海保护区构建的重要价值。1976年冬季和1977年春季,挪威和苏联分别设立各自的200海里管辖权,挪威设立经济区,而苏联设立临时捕鱼区。随着经济区和捕鱼区的建立,海洋边界问题成为巴伦支海大陆架划界谈判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苏联和挪威意识到该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故此,挪威和苏联同意在部分争议区作出临时安排——经济区灰色区域。在灰色区域内,挪威可以对那些拥有挪威颁发许可证的挪威船只和第三国船只进行检查,而苏联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船舶[35](P10-11)。经济区灰色区域,不但具有海洋保护区的角色,而且在缓解海洋划界冲突上起到积极作用。
另外一个例证是地中海海洋生物保护区。作为半闭海的地中海地缘政治比较复杂。不仅如此,地中海沿海国存在着海洋划界及其他的利益冲突。“地中海行动计划”通过建立特色海洋保护区,有效地回避海洋划界争端而促进了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的合作。对于争议海域,特别保护区的建设需要由行动计划缔约国协商一致决定,并由行政机构负责[36](P268)。依据这一特色方案,地中海地区建立了一个国家管辖外的特别保护区——海洋生物保护区[37](P23-28)。由此观之,地中海某些海洋保护区在实现海洋保护区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同时承担着缓解半闭海海洋划界等争端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公海保护区的构建为未来海洋划界争议的解决提供建设性的思路。
(二)公海保护区赖以存在的国际法原则
1.善意原则。公海保护区构建的新动态,为重新审视公海保护区所依赖的国际法基础或原则提出诉求。1982年《公约》第十六部分以“一般规定”的形式强化善意原则①1982年《公约》第 300条规定:“缔约国应善意履行根据本公约承担的义务并应以不致构成滥用权利的方式,行使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管辖权和自由。”。奥康奈尔认为,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是一项基本原则,由此引出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和其他特别的和直接的与诚实、公正和合理相关的规则[38](P124)。公海保护区的构建相当复杂,要求公海保护区提议国、缔约国、沿海国乃至第三国都应该秉承善意原则来履行相关义务并享有相关权利。正如法国学者M.维拉利所强调的那样,任何人忽视善意原则都是构成整个国际法结构基础的一部分,都可能使国际法降为一套空洞无物的法律形式[39](P57)。为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序言中认为,善意原则是举世公认的,且公约中多次提到“善意”之措辞。在海洋划界中,国家首先应善意开展协商,寻求与其他相关国家达成共同协议,而一切单边行动有违背1982年《公约》精神②除了国际法实践之外,1982年《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就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作出规定,明确海洋边界应由有关国际协议划出,以便得到公平解决。。一个成功的公海保护区应该是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分歧,并在优先区域发展公海保护区模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2月20日至2015年3月18日期间,由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审理的“毛里求斯诉英国仲裁案”,是对公海保护区构建应该坚持善意原则予以固化的典型例证。虽然涉案的查戈斯海洋保护区并非严格意义上公海保护区,但是,该案引发的核心问题为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提供有益启迪。该案中英国声称查戈斯保护区的建立将促使海洋学、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水平,并且显示英国保护海洋环境的责任,特别是管理鱼类种群的义务。然而,毛里求斯和群岛原居民则对英国表示强烈反对。毛里求斯依据1982年《公约》第287条和附件7提出仲裁请求,即英国不是1982年《公约》意义上的“沿海国”,无权单方面在查戈斯群岛设立海洋保护区。同时,英国设立海洋保护区行为的真正目的并非保护海洋环境[40](P126)。“毛里求斯诉英国仲裁案”所涉及的海洋问题很多,但是该案主要涉及一国设立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问题,即国际法基础问题。由于该案包括海洋领土主权争端的因素,导致该案的初步管辖权和实体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但是,如果抛开该案其他争议不谈,就查戈斯海洋保护区建立的合法性问题而言,该案进一步固化了“善意原则”构成海洋保护区建立的国际法基础。虽然仲裁庭最终没有直接揭露和批评英国在建立查戈斯海洋保护区中存在的其他目的,但是在该案审理中,James Kateka法官和Rudiger Wolfrum法官认为,英国在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意图上有所隐瞒且违背善意原则[41]。
2.“弃权理论”的适用。“弃权理论”是公海保护区构建中应对公海自由与限制的另一产物。20世纪30年代,过度捕捞致使渔业资源不断衰竭。一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捕捞业而提出“弃权理论”。所谓“弃权理论”,基本动机是迫使其他国家放弃对特定渔业资源的捕捞权,从而实现本国排他捕鱼[42](P43)。1952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国际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在科学证据表明加大该鱼种捕捞力度无法维持该种群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缔约国应该放弃捕捞该鱼种。为防止日本取得对大马哈鱼的绝对捕捞地位,1952年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三国签署《北太平洋公海渔业国际公约》,该公约便吸收“弃权理论”。各国对“弃权理论”的态度不一,但是基本上都持有相对谨慎的态度。一些传统渔业强国都认为,该理论实际上是渔业资源的分配机制而非养护措施,故而违反公海自由原则[43](P140-144)。至今,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并未完全将“弃权理论”视为建立公海保护区应该坚持的国际法原则,这是国际社会基于“弃权理论”的适用基础并不明朗的考虑。事实上,世界上一些重要海域的划界至今没完成[44](P2289-2900)。因此,这极容易造成海洋大国利用公海保护区这一机制而攫取公海的利益。为此,“弃权理论”的适用极有可能造成滥用限制公海自由的极端行为。
然而,公海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而近乎造成竭泽而渔。根据有关国际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特定公海海域的渔业资源前景不容乐观。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高度洄游种群、跨界种群以及公海离散鱼类种群面临过度捕捞局面(见表2)[45](P495)。表2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海资源的捕捞量急剧增加[46](P64)。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有明确证据显示世界海洋野生鱼类的捕鱼量已经达到最大限度,鱼类种群已经处于过度开发或资源枯竭的状态。故此,国际社会有责任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公海保护区的构建。

表2 高度洄游种群、跨界种群和公海离散鱼类种群统计(%)
为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公海保护区构建中“弃权理论”适用的条件,即有选择性地适用“弃权理论”,将其作为构建公海保护区应该遵循的国际法原则。针对部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已经不能胜任新挑战的情况①比如,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由于受到选择退出程序(opting–out-procedure)的制约,导致该组织的执行力不足。,可以尝试在不同类型的公海保护区适度适用“弃权理论”。国际社会有必要认真总结和梳理公海保护区的差异性,进而实施区域层级规划,以便进一步细化“弃权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公海保护区类型。因为,1982年《公约》第118条呼吁各国必须互相合作以设立分区域或者区域渔业组织,这也是在不同类型公海保护区强化有选择适用“弃权理论”的国际法基础。
四、结语
公海治理构成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一环,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并将之视为海洋治理的新模式和新工具。无论构建何种类型的公海保护区,国际社会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公海自由与限制公海自由之间的协调与平衡问题。由此,重新审视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公海元叙事的基本视域,即公海保护区构建中船旗国管辖权与沿海国管辖权之间的动态性冲突和公海保护区构建中“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国际法状态。在反思和检视公海元叙事的实践基础上,本文密切联系近期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实践与经验,认为公海保护区构建呈现出以下新趋向:公海保护区框架下沿海国管辖权的日益膨胀,治理公海保护区的“低政治”公约的勃兴以及公海保护区蕴含的其他有待挖掘的价值,尤其是特殊海域公海保护区在缓解海洋划界对抗上具有的重要法律价值。基于公海保护区构建的新动向之考虑,构建公海保护区所赖以的国际法基础和原则应该不断被完善和修正,而善意原则和有选择适用“弃权理论”构成了公海保护区构建的国际法基础和原则。
1982年《公约》在1958年《公海公约》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公海自由的理论与实践,但是1982年《公约》框架下的公海自由属于开放的,国际社会治理公海的实践必然催生公海自由之“其他自由”。某种意义上,公海保护区承载着国际社会利益与各国的利益。不仅如此,公海保护区的构建必然也是各国提升公海治理话语权的重要契机与途径①事实上,中国近海和管辖海域面临着与日俱增的油污风险。这种风险随着海上贸易运输和海上资源开发活动的活跃而变大。在中国特定的管辖海域设立海洋保护区,日益成为海洋治理的重要和有效的举措之一。。因此,各国在总结各类海洋保护区建设基本经验基础上,大力探索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方略显得极为必要。
公海保护区的构建不仅是不断挑战和修正传统海洋法理论的过程,而且,其也承载和蕴含着相关海洋国家的战略利益。海洋强国日益意识到公海保护区构建在推动公海自由内涵逐渐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尤其认识到在公海保护区的构建中带来的诸多海洋战略利益,诸如海洋管辖利益、资源利益、科研利益、制度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等。故此,探索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方略要充分顾及国际社会利益。与此同时,海洋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逐渐形成本国方案,以战略性和前瞻性视野审视公海保护区的构建,提升海洋秩序构建的叙事能力。
[1]Douglas M Johnson.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Ocean Boundary-making.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
[2]张磊.论公海自由与公海保护区的关系.政治与法律,2017,(10).
[3]格雷厄姆·凯勒.海洋自由保护区指南.周秋麟,张军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
[4]朱利安,罗谢特,吕西安·沙巴松.海洋保护区的区域路径:“区域海洋”的经验//海洋的新边界看地球.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让-佛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6]牟文富.海洋元叙事:海权对海洋法律秩序的塑造.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7).
[7]Hugo Grotius.The Freedom of the Seas.trans.Ralph van Deman Magoきn,James Brown Scott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8]马得懿.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与北极航道秩序.太平洋学报,2016,(12).
[9]郑凡.海洋法中的张力与美国的海洋政策.太平洋学报,2015,(12).
[10]屈广清.海洋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1]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研究所海洋法研究室.现代国际海洋法——世界海洋的水域和海底制度.吴云琪,刘楠来,王可菊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12]路易斯·B.宋恩.海洋法精要.傅崐成,邓云成,蒋围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13]England v.Iceland[1974].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
[14]Boleslaw A.Boczek.The Peaceful Purposes Clauses:A Reappraisal after the Entry into Eあect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Halifax:Ocean Yearbook,1998.
[15]Rakotoson,Lalaina R,Kathryn Tanner.Community-based Governance of Coastal Zone and Marine Resources in Madagascar.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2006,49(11).
[16]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Guidelines for Applying the IUC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to Marine Protected Areas:Report of Switzerland:IUCN,2012.
[17]Ronan Long,Mariamalia Rodriguez Claves.Anatomy of a New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for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First Impressions of the Preparatory Process.Environmental Liability Law,Policy and Practice,2015,23(6).
[18]张晏瑲.论航运业碳减排的国际法律义务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当代法学,2014,(6).
[19]桂静.不同维度下公海保护区现状及其趋势研究——以南极海洋保护区为视角,太平洋学报,2015,(5).
[20]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Home(CCAMLR).Report of the Second Special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CCAMLR,2013.
[21]蔡霞.国际磋商各方就防止北冰洋中部公海无管制渔业活动协定文本达成一致,超前给北冰洋公海捕捞贴上封条.中国海洋报,2017-12-05.
[22]M.Cuttle.Incentives for Reducing Oil Pollution from Ships,the Case for Enhanced Port State Control.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1995,17(2).
[23]马学婵.1982年海洋法公约适用于非缔约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制与社会,2017,(7).
[24]France v.Muscat Dhows[1982].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
[25]Bertrand Le Gallic.Using Trade Measures in the Fight Against IUU Fishing,FAO Fisheries and Argricultre Cirlular.Rome:Rome Press,2012.
[26]高潮.国际关系的权利转向与国际法.河北法学,2016,(11).
[27]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ILA).Statement of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Report of ILA:ILA,2000.
[28]李杨.公海非法捕鱼的国际法律管制.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3,11(2).
[29]惠新.中方回应“福远渔冷999”号被扣案.中国渔业报,2017-09-04.
[30]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中国渔船被登临情况统计报告[2017-11-14]http://www.china-cfa.org/.
[31]李伟芳,黄炎.极地水域航行规制的国际法问题.太平洋学报,2017,(1).
[32]周超.国际磋商各方就《防止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文本达成一致.中国海洋报,2017-12-05.
[33]Jon M.Van Dyke.The Disappearing Right to Navigation Freedom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Marine Policy,2005,29(2).
[34]G.Kulleenberg.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ome Perspevtive.Ocean and Coasta Management,1999,849(4).
[35]盖尔·荷内兰德.北极政治、海洋法与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巴伦支海划界协议在俄罗斯的争议.苏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
[36]Author.Protocol Concerning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the Mediterranean[2017-11-01]http://195.97.36.231/dbases/webdocs/BCP/ProtocolSPA95_eng.pdf.
[37]邓颖颖,蓝仕皇.地中海行动计划对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启示.学术探索,2017,(2).
[38]John F.O’Connor.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Law.Aldershot:Dartmouth Publishing Co.Ltd,1991.
[39]M.维拉利.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刘昕生译.国外法学,1984,(4).
[40]吴士存.国际海洋法最新案例精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
[41]Mauritius v.United Kingdom[2010].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PCA),2011-03.https://pcacases.com/w eb/send Attach/1570.
[42]Soji Yamamoto.The Abstention Principl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s.Washington Law Review,1969,43(1).
[43]王小晖.论新参与方的公海捕鱼权.江汉论坛,2016,(9).
[44]Charney J.I,R.W.Smith.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Dordrecht:Maritinus Nijhoあ,2002.
[45]Jean-Jacques Maguire.The Stage of World Highly Migratory,Straddling and Other High Seas Fishery Resources and Associate Species.FAO Fisheries Technical Paper,2006,22(49).
[46]Wysokinsky.The FAO Fisheries Technical Paper:The Living Marine Resources of the Southeast Altantic.Rome:Food&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