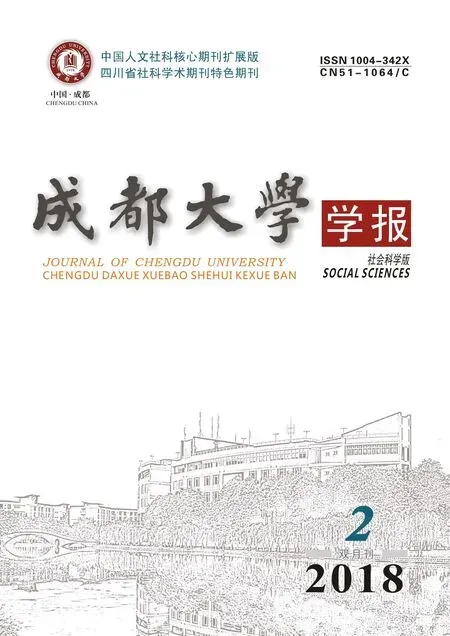杜宇时期蜀地农业初探
辛 艳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杜宇氏是继蚕丛、柏灌、鱼凫氏之后,在蜀地立国的第四个王朝。它在蜀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开明王朝以降蜀地文明的更加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杜宇氏如何取代鱼凫氏,成为蜀地共主,文献并无言及。但从《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看,杜宇氏与前三代在政治统治方面亦有很大的差异①。不论怎样,杜宇氏的到来,为蜀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一点为文献所盛称。杜宇王朝强大的国力,是与他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史籍所称杜宇对推动巴蜀地区农业生产有卓越功勋,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蜀地传统的稻作农业得到普遍推广和治水患兴水利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上。杜宇由此被尊为巴蜀农神。
一、杜宇“教民务农”与先秦时期蜀地稻作农业的普遍推广
就杜宇王朝的史迹,蜀地本土文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较蚕丛、柏灌、鱼凫前三代更为详尽,使我们得以更全面管窥其经济文化面貌。《蜀王本纪》云: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望帝。治文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1]414
《华阳国志·蜀志》以此为基础亦有取舍: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至郫邑,或至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意,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 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2]101
合上述两段史料观之,《华阳国志·蜀志》大体上是依据《蜀王本纪》的。但所记史实差异之处亦明显,主要体现在对杜宇及其妻女利,以及开明氏族群的来源的认识上。常璩以“理性”史观自居,标榜“则为怪异,子所不言”[2]521的正统史观,对《蜀王本纪》中所谓的荒诞不经之说予以多方修正。《蜀王本纪》所载杜宇“从天堕”,杜宇妻女利游江源“从江源井中出”,开明“死而复生”的史迹。在常璩看来,此类神话色彩极强的题材皆不可信。但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蜀王本纪》记载的蜀地上古传说,包含了真实的历史素材,对充分认识杜宇、女利、开明族群的来源,提供了重要材料。因此,《蜀王本纪》提供的蜀地历史文化方面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就杜宇王朝的存续年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常氏显然是受华夏正统论的影响,将杜宇王蜀的时间延至“周之叔世”。根据蒙文通[3]44和童恩正[4]69两位先生的研究,杜宇王朝主要活动于西周至春秋之际,甚为合理。学界一般认为十二桥文化是杜宇王朝的文化遗存。十二桥文化是以十二桥、金沙遗址为典型代表,包括指挥街、方池街、岷山饭店、抚琴小区等遗址在内的一系列文化遗存,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而成都金沙遗址是继广汉三星堆遗址之后,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古蜀文化中心遗址,是杜宇王朝的“都邑”所在。遗址布局合理、功能系统完备,其间分布有宫殿区、一般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5]出土遗物数量庞大、规格较高,包括金、玉、铜、骨、石器以及数以吨计的象牙等礼仪性用器,说明这是古蜀国的又一政治文明中心。如此规模的政治文明中心的形成,必然是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物质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下。因此,十二桥文化反映出的蜀地农业文明繁荣景象与为蜀地农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杜宇是分不开的。
上引《蜀王本纪》载杜宇“从天堕,止朱提”,说明杜宇乃朱提人,其族系为濮越族。汉代朱提即今云南昭通一带。据研究,云南地区农业起源甚早,是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的亚洲栽培稻起源中心之一。[6]看来杜宇入蜀,从云南地区带来了栽培水稻及其种植技术,是完全可能的。当然,稻作农业传入巴蜀地区,可能不止一个方向,也不止一次。前文已有论述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在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就有一定的发展。而杜宇入蜀的这一次,可能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理念,大力促进了稻作农业在巴蜀地区的普遍推广和提升,蜀地农业经济由此取得重大突破性发展,故有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之说。文献所称杜宇名“蒲泽”和都“郫邑”,意为迁往成都平原低湿之地,可能也与发展水稻之类的温湿作物有关。扬雄《蜀王本纪》、许慎《说文解字》、左思《蜀都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等书亦言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并成为唐宋文人的咏诗题材。杜鹃鸟为农候之鸟,一般在稻田插秧农时鸣叫。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虽然是传说,则包涵有杜宇与蜀地稻作农业发展的真实历史素材。
近年来,成都平原的植物遗存浮选结果,也反映了杜宇时期仍然是以蜀地悠久的稻作农业为主,辅以粟和黍的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成都市郫县菠萝村遗址是一处商末周初的聚落,该遗址“宽锦”地点2011年浮选出的农作物种子有稻谷、粟和黍三种。[7]稻谷数量占农作物总数的69.64%,出土概率高达88.46%;粟的数量占农作物总数的5.73%,出土概率是42.31%;黍的数量占农作物总数的0.1%,出土概率为7.69%。无论从稻谷数量在农作物总量中的比重,还是从出土概率看,稻谷都占绝对优势,而粟和黍处于次要的地位。金沙遗址金牛区5号C地点2007-2008植物遗存浮选亦有类似的结果,[8]出土稻谷的数量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77.6%,粟的数量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22.4%。上述浮选结果有力地证明了作为杜宇王朝的考古学遗存的十二桥文化,仍然是贯之于蜀地以种植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悠久的农业种植传统。
杜宇王朝农业的发展,还得力于其妻朱利族群的联盟。《蜀王本纪》载杜宇妻:“名利,从江源井中出”,此条内容又见于东汉末年来敏《本蜀论》,谓杜宇妻为“女子朱利”,并直接称其“自江源出”,省去“井中”二字[9]1045。江源,指的是禹羌族世居的岷江上游地区。与水和岷江密切相关的朱利及其族群,也应该是出自擅长于早期农业和水利的西羌[10]。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了近百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营盘山、波西、沙乌都和布瓦寨遗址等若干规模庞大者,均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聚落,充分揭示了此区域农业起源很早的史实。有着悠久农耕传统的朱利族群与杜宇的联姻,共同推动了杜宇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此外,《蜀王本纪》所称朱利“从江源井中出”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凿井技术在蜀地的出现与发展。水井的出现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开辟新的水源,使人们能够离开江河湖泊到更广阔的地方去发展农业,是“原始农业”迈向“灌溉农业”的关键性一步。

杜宇王朝是在农业经济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影响深远。《华阳国志·蜀志》云:“巴亦化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杜宇不仅对蜀地农业有重大贡献,而且还影响到了四川盆地东部巴国农业的发展。由于杜宇“教民务农”的卓越功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的风俗一直残存到近代。在民国时期,四川农村中还有不少地方有“土主庙”,就是用来供奉这位“杜主君”的[12]23。正如蒙默先生所说“教民务农”的杜宇氏,看来对古代四川农业的发展做出了相当贡献的。[13]22
二、考古所见杜宇时期蜀地农业的发展
杜宇王朝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蜀地的考古发现中亦有充分的揭示。以十二桥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是古蜀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十二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大规模木结构建筑的发掘。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迹分布范围广(面积达1300平方米)、布局讲究,正好濒临郫江故道而建。其中的大型滨水木构“宫殿”建筑群,反映了蜀地干栏式建筑技术的成熟[14]。这种建筑技术使人们能得以居息于低湿临水之地,却不为潮湿所困,无疑说明了蜀人对水的认识水平和治理能力有了较大提升,因而能有效地开发滨河地带。十二桥文化水利技术的进步无疑促进了农地的扩大与农业文明的繁荣。作为古蜀国的又一中心“都邑”的金沙遗址,其内至少包括古郫江水在内的四条古河道由西北蜿蜒流向东南,这种城与水互相交错的格局,反映了依水兴建的古城对水的利用能力的增强。金沙遗址区内还发现有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渠遗迹[15],说明这一时期农田水利设施的进步,蜀地可能出现了灌溉农业。纵然先秦时期蜀地的治水技术逐渐走向成熟,但在李冰建都江堰前,成都平原面临最大的自然灾害仍是洪灾。文献和考古材料揭示,杜宇王朝可能不只一次遭受水患。从十二桥遗址木构建筑的保存情况和各种迹象分析显示,十二桥遗址应是毁于洪水[16]19-20。杜宇王朝晚期,正如《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所记,又曾遭遇到一场特大洪灾“若尧之洪水”的威胁。杜宇任命擅长于水利的滨水族群开明氏治理水患。开明氏不负所托,最终顺利完成了这次艰巨的治水使命,为蜀地农业文明的持续繁荣提供了保障。
十二桥文化出土的农业工具种类明显增多,亦反映其农业经济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十二桥文化出土的石质工具,可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磨制石器仍是以小型的斧、锛、凿、锥、镰、铲、杵为主,大多通体磨光,制作精细。打制石器主要为盘状器、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锄、斧形器、石网坠等器形。方池街古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占80%以上,其中盘状器数量最多,达108件[17]。盘状器是一种可用作砍砸、切割和削刮的具有多种用途的石器。根据石器的微磨损痕迹分析,发现盘状器、削刮器等大部分打制石器的加工对象为竹、木类植物。由于这类加工对象对工具损耗大,石器的使用寿命短,用量大,只要实用,就不必进一步磨制加工。[18]这类工具的多见与早期成都平原的生态环境有关。早期成都平原为大量的植被覆盖,森林繁茂,杂草丛生,大量的耕地尚待开发。盘状器、削刮器等打制石器不仅可用于砍伐林木、开垦荒地,发展种植业,而且还可用于采集、渔猎,弥补早期农业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桥文化还新发现有象征早期农业发达农具的木耜和鹿角器。金沙遗址出土了1件木耜,长141厘米,由一块整木做成,形状似现在的铲子,[19]118-119是用作翻土的农具。木质农具在青铜时代是重要的农业用具,由于木质工具易腐烂,不易保存,所以迄今考古发现的木质农具较少。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亦发现有骨质农具——鹿角器。由于成都平原是由岷江等河流冲积而成的,土质疏松,与较笨重的石质工具相比,木质、骨质工具是当时翻土、松土的优质农具。此类工具更容易深入土层,有利于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木质、骨质两类生产工具的出现,无疑说明杜宇时期蜀地农业生产取得的进步与发展。
由于杜宇时期蜀地农业的发达,家畜饲养业也发展很快,中国传统的六畜在这时已经驯化成功。十二桥遗址发现的能确定为家畜的有猪、狗、黄牛和马。[20]其中以猪为主,猪的死亡年龄在10-16月龄,说明饲养家猪的主要目的便是屠杀食肉。十二桥遗址还发现一根鸭的肱骨,但不能确定鸭是否已经被畜养了。成都市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地点出土动物骨骼中家畜包括猪、狗、马、牛、羊等,同样是以家猪为主。[21]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动物骨骼[22],据研究,属于家养动物的有家犬、马、黄牛、家猪、家鸡。按最小个体说统计,家猪为30个个体,在动物总数所占比例最高。金沙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23],可以确认属于家养动物的有猪、犬、牛、水牛、马和鸡等,尤以家猪的数量最多,约占75%。上述诸遗址发现的家养动物遗骸表明,商周时期,蜀地已经畜养了猪、狗、牛、羊、马、鸡等家畜、家禽,可谓六畜齐备,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稳定的肉食来源,侧面反映了蜀地的农业经济繁荣。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杜宇入蜀并结合蚕丛氏的后裔,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重大举措,使以成都平原为腹心地带的蜀地,农业生产呈现出繁茂的景象。《山海经·海内经》载: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郭璞注:“播琴犹播殖,方俗言耳。”
“都广之野”的地望在哪?据近代学者蒙文通先生考证[3]162-165,《山海经》是巴蜀地区的文化典籍,为先秦时期的作品。全书所言的“天下之中”指的就是巴蜀地区。而《山海经·海内经》则是出于古蜀地区的作品,成书在西周中期以前。其中的“都广”即“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在四川西部。看来,“都广之野”其实指的就是成都平原,这已是学界共识;“后稷”本为周始祖弃,因“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24]112,而逐渐被尊为中国农神。蜀地作为农神后稷的归葬之处,反映了成都平原农业高度发展的史影。“百谷自生”表明成都平原农作物种类繁多,有菽、稻、黍、稷等品系,这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膏”,郭璞注解为“味好皆滑如膏”,说明成都平原所产的菽、稻、黍、稷等谷物质量上乘;“冬夏播琴”反映的是成都平原开始了双季种植农业。《山海经》记载这一农业生产的繁茂景象,可能正是杜宇在成都平原大力发展农业之后的实况。[13]22
注释:
①《蜀王本纪》称前三代蜀王引退时皆“神化”或“仙化”,反映了浓厚的宗教神权政治色彩,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数量庞大的大型祭祀重器也印证了这一点;而有关杜宇王朝的史料,则突出强调在其耕战治水的贡献,带有明显的务实特点,十二桥文化也没有发现如三星堆文化那样大规模神权至上的遗物。这说明,杜宇王朝在国家形态方面较鱼凫王朝的神权政治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扬雄.蜀王本纪[M].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8.
[2]刘琳.华阳国志新校注·蜀志[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3]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5]朱章义,章擎,王芳.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J].四川文物,2002(2).
[6]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J].社会科学战线,1984(4).
[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菠萝村遗址“宽锦”地点2011年浮选结果及分析[J].成都考古发现,2012:488-496.
[8]姜铭,等.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J].南方文物,2011(3).
[9]王国维.水经注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0]彭邦本.杜宇王朝的存续年代与农业发展略论[J].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26-32.
[11]李钊.试论开明王朝的嬗替与先秦时期蜀地农业发展的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9):216-222.
[12]李殿元,李松涛.巴蜀高劭振玄风:巴蜀百贤[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13]蒙默.四川古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14]李绍和.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J].文物,1987(12):1-23.
[15]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以成都平原先秦文化为中心[J].中华文化论坛,2006(1):5-11.
[1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十二桥[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7]徐鹏章.成都方池街古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3(2):297-316.
[18]王毅.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J].成都文物,1988(1):32-35.
[1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M].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20]李绪成,李升,何锟宇.十二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报告[J].成都考古发现,2005:458-474.
[21]何锟宇,等.成都市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地点动物骨骼报告[J].成都考古发现,2012:273-294.
[22]朱才伐.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23]刘建.金沙遗址出土脊椎动物及古环境研究[D].成都理工大学,2004.
[24]司马迁.史记·周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