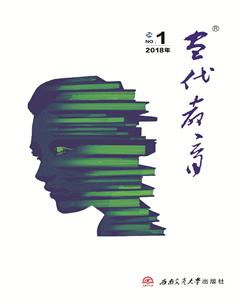让蚊子读懂乡愁
吴华
“蚊子读懂了我的眼神/虔诚里有种漫无边际的深邃/正如曾经淹死希望的河流/汩汩地流淌着希望”。泓洁的诗歌,充满了孤独和哲思。在某个酒醉后的夜晚,他突然清醒的那一瞬,完成对这个世界的重新审视。在新闻战线打拼多年,蓦然回首,发现世道总是貌合神离。希望之河淹死希望,只有蚊子才能读懂他的乡愁。
纳雍盛产诗人,如空空、徐源、王家洋、闵云霄等熟悉的名字,当然,这其中还应该加一个人的名字——周泓洁。
和泓洁认识,并非因为诗歌。
在2006年左右,我和閔云霄、苏江元、周泓洁搞了个叫“贵州热线”的BBS。按照今天说法,我们四人应该是联合创始人。有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感觉。四人年龄相仿,单身、记者、文艺青年,偶尔还写些诗。
但那时候我几乎都没把泓洁当诗人,我和云霄、江元,写了诗不管好坏就往网上贴,泓洁没有。后来,我们接触渐渐少了,导致我几乎都把泓洁写诗这事给忽略了。
2017年9月的一个清晨,接到他的电话,紧接着看到了他的许多的诗稿,这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惊喜。
泓洁的诗和人一样,比较沉稳、朴实、率性、随意。没有华丽的辞藻,他通过知性书写和辨证体悟,在生活的浮尘里,力图展现生命本源和生活的本真。
赵卫峰把贵州新诗分了三个阶段:一是六十年代传统性的“乡土抒情”;二是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及其影响下的多元共生、同源多流局面上的“意识形态抒情”;三是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的“复合抒情”时段。
按照这种分类,泓洁的诗应属“复合抒情”。他的诗确有“你用最冷色调涂抹北方的空气/我匍匐在铁轨上深情凝望你”极具现代画面感的现代气息,也有“像这样的黄昏/不止一次被母亲的勤劳打动”传统而平静的叙述。
由于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他只能通过诗歌、童话和梦幻遥寄相思和乡愁,命中注定了他必须在无序的跑道上漂移。他在《贵州政协报》《法制生活报》及多彩贵州网都工作过,因此诗歌中散发着一些职场情感的宣泄。由于心情的起伏,他的心情的好坏像钟摆,在诗歌的高和低之间来回摆动。在诗里,他耕植的那些硕果被人摘走,爱神赐予的种种善意,因此变得模棱两可,这或许就是他生活、情感或者职场里的某种场景移植的隐喻。在诗中,泓洁有时候对生活充满迷茫和无奈。他写道:
“风不停地吹
楼道里的钢管扶手也跟着嚎叫
小区的夜晚不再宁静
一些人哭了一些人笑了”
但总体来看,他的诗歌更多是写土地、种子、母亲、亲人、家乡、英雄,当然还有薄雾和白雪、花朵和爱情。
在街边的流浪歌手那里,他找到了异乡人的共鸣,在《1999,访城市歌者》中写道:“城市霓虹灯忽闪着疯长的情欲/某个阴暗角落流浪狗和吉他手依偎在一起”“没有人计较你的性别/没有人追问你的身份”。作为一个乡情浓郁的异乡人,很难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找到自己的归宿感,因此当遇到类似遭遇的人,音乐让他们同频共振。
虽然如此,周泓洁并不悲观,他的生活不是想象中乡下人进城的黑白片,而在他努力和勤奋下将自己活得多姿多彩。“你轻轻飘起的发丝撩拨我宽厚的手掌/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这种朦胧的情愫让很物质的城市生活变得富有诗意。是的,于他来说,生活如果没有了酒和诗意,那他如何在梦里的村庄栖居,蹲守一个人的温暖?
村庄在他身上打下太深的烙印。在诗里,烟雾始终笼罩着农村,烟雾始终笼罩着他。在烟雾里,他歌唱父母、歌唱友邻、歌唱情敌、歌唱能歌唱的所有一切。在烟雾笼罩的村庄里,他或许有过一份“小芳”式的情或梦。他多么希望,家乡的烟雾缭绕永远不再散开,星星和月亮按照时序轮转,趟过那条长长的溪水,和水草和爱人,坠入爱河。
炊烟往往让山村更具诗意,但他始终用烟雾,或许山村的炊烟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只有在烟雾中,他才能听见了树叶的咳嗽声。
泓洁具备了媒体人对事物的洞察能力、对事物的思考,没有停留在表象,有时已经深入到了“内核”,他将日常性表达兼容了传统诗歌的含蓄、典雅、优美。在他眼里,细雨算得上不速之客,常常扮演洗车工,每次出行拖泥带水,树叶被车轮暴力碾压,加剧了腐败。
媒体人在夜色里走得多了,往往需要找一个亮处,方能观照自己的信仰和灵魂,而诗歌便是他们夜色中的火光。
出于对新闻的敏感,他以鸽子花的名义为见义勇为好老乡王家勇写诗,为倒在凝冻路上的协警朱清写诗;他希望这些身边英雄“躺在善良的故事”里。
或许正是新闻素养,“真”成为了泓洁的诗一个重要特点,他将自己的坦荡和率性写进诗里。“2009,车过北京西/一次偶然邂逅暧昧至极/恍入我终生回忆”。在某个周末,他甚至预谋了“婚外情”:“最后一页稿纸交给爱/留下钢笔。孤独地/等待新的命题”,他幻想“坐在情人的大排档/妻子喋喋不休PH值小于7/雨越下越暧昧/风越吹越煽情”。
这些近乎隐私的情感琐事,泓洁毫无顾忌地把它写进诗里。可以看出他诗里的“真”,从这点来说,比那些技法“老辣”、口是心非、辞藻华丽的“大诗人”更难能可贵。把醋意写成“PH值小于7”这种调侃,则展现出他生活中的冷幽默。
客观地说,泓洁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诗人,他的诗句并不刻意,有时甚至会留下一个记者的“职业病”,过于地追求表达清楚,让诗歌缺乏了一些必要的节奏感和跳跃感。有时候他自顾自己表达,倾盆大雨般地把自己的情感宣泄出来。这些看似缺点,其实是周泓洁的诗歌基因。如果没有这些“基因”,那么这些诗歌也就不属于周泓洁了;如果都有了统一标准,那么周泓洁的诗和北岛、于坚的都一样,那又有什么意义?
“一定是阳光找不到出路,她要/晒干所有的爱情?”这样的诗句只属于他——周泓洁。周泓洁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关键的时候,他能够用一两句恰到好处的词句,点燃诗歌,照亮自己。
只有谦卑的诗人才能成为大师,只有大师才能让诗歌穿越时空,击中你我的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但愿泓洁不显山不露水,继续构建出属于他自己的诗歌秩序和精神秩序。
但愿某天清晨,他又会给我们一个超越今天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