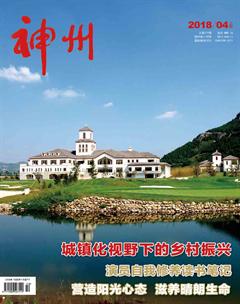试析陈独秀的绘画艺术观
高俊松 朱胜甲 陈云云
摘要: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政治地位毋庸置疑。但同时,他又具有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美术情怀。他早年受家族的影响就接触大量的绘画作品,生平广交美术界好友,并且提出伟大的“美术革命”的艺术革命主张,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变革,将西方艺术特别是写实主义精神引进中国美术,由此改变了中国绘画的格局与发展,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走向。
关键词:王画;美术革命;绘画艺术观;中国绘画
陈独秀(1879——1942年),原名干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及首任总书记。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确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陈独秀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指引中国人民从思想文化上展开对封建伦理制度及一切守旧顽固势力的批判和讨伐。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很多学者一直致力于陈独秀的研究,从中共党史、政治、文化、社会背景等各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作为一个学者,陈独秀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有着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其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不仅仅只是他的兴趣爱好;其对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有着深厚的学术研究与独到的见解。
陈独秀早年就接触过大量的绘画作品,尤其是其后来所批判的“王画”。陈独秀嗣父陈衍庶为清廷官员同时是位画家,对书画有着深厚的艺术造诣,被黄宾虹誉为“左清晖”。陈衍庶一生酷爱书画,擅长描绘陈独秀“美术革命”中所批判“王画”王石谷风格的山水,家中收藏的书画颇多,所以陈独秀敢言“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虽然陈衍庶后来与陈独秀形同水火,几近决裂,但不可否认,陈独秀所受的早期教育都受到陈衍庶的深刻影响,并且从陈衍庶家中收藏的书画作品中,陈独秀对中国绘画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教陈独秀读书的胞兄陈庆元和二姐夫姜超甫也得陈衍庶亲传而善工丹青,其风格也授受王画衣钵如此被四王画风所包围。在这种家族艺术氛围熏陶下下,陈独秀对绘画艺术很感兴趣,以至于陈独秀一度也嗜好书画收藏。陈独秀一方面对于王画的感性认识极为深刻,另一方面也在这个特殊的家世关系中很容易对王画产生某种逆反心理,其对陈独秀早期有着重要艺术熏陶,给予陈独秀早期对中国绘画开始就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与体会。从陈独秀的家世背景来看,可以肯定的是,陈独秀在这种家庭背景下,對中国绘画一开始就不陌生,并且对中国绘画、特别是“四王”的绘画有着直接的体验与体会,对其有着本质上的理解。
陈独秀属于个性明显,敢言敢行,性格张扬的人。章士钊曾列出天下难交之友中,耿介执拗的陈独秀排名第一。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和对绘画艺术的兴趣,陈独秀一生中也交往了许多书画家朋友,其与苏曼殊、黄宾虹、刘海粟、潘玉良等等又有着深厚的友谊。柳无忌在《苏曼殊及其友人》中称“郑同荪曾讲曼殊的朋友,恐怕要算仲甫(陈独秀字)最久最厚。”1902年,陈独秀和苏曼殊相识于东京青年会。而后,苏追随陈至上海《国民日日报》。陈与苏二人在艺术、诗歌、书法、文学、佛学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在精神交流与思想沟通方面,二人可谓是互相称赏、互相褒扬。在这二人的相互交往当中,陈独秀对苏曼殊的影响是深远的。苏曼殊的绘画的画面感是极富诗意的,这和她的诗学灵性是有关系的。而陈独秀作为教苏曼殊作诗的先生,可见对其艺术造诣和思想成就方面的影响之大。1904年左右,黄宾虹就在安徽公学从事教务工作,并且与陈独秀来往较为密切,他们谈革命,谈艺术,谈思想。在赵志钧的《画家黄宾虹年谱》中,提到:“入夜则闭门摹画,校中同事,竟有不知其能者,引为大奇。”以后成为一代山水画宗师的黄宾虹,其投身反清革命,及艺术磨砺有成,也颇受陈独秀思想和人格的影响。陈独秀照拂过一位濒临绝境的女性,即后来成为画家的潘玉良。潘玉良在与命运抗争中努力学习绘画,陈独秀继续帮助她于1918年考入上海美专。在特定的年代被可以抹去的陈独秀种种印迹外,于潘玉良两件绘画作品上的题跋幸而留存。从题跋看,陈独秀一直寄望的“以洋画精神改造中国美术”,亦即中西交融的表现形式,在潘玉良的画作中得到了贯彻和体现。陈独秀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奠基人,与美术家的交往,肝胆相照。在艺术思想方面,在美术革命中都体现了对中国美术所持的审视态度与复兴期望,以及民主科学构建现代思想文化的信念。而不得不提的一位就是刘海粟,陈独秀一位交情颇深的朋友。在刘海粟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大量关于陈独秀的文字。刘海粟创办上海美术高专的时候,二人因机缘巧合得以接触,在后期交往中,此二人在对艺术思想的见解,对当下政治文化的分析中愈加互相欣赏,并且在很多领域方面都有接触。潘玉良能够上上海美术高专也是通过陈独秀去介绍的,陈独秀将潘玉良引荐给刘海粟,让其得以在上海美术高专上学,这对于潘玉良来说可谓是她迈向艺术这条道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刘海粟在日后的学习中对潘玉良也可谓是照顾有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潘玉良本人的才华当得此赏识,另一方面就是可能因为陈刘二人的互相信任。其次在刘海粟的很多画作当中,作为好友的陈独秀都有题字,这也充分说明陈刘二人的交往密切。刘海粟在当时上海美术界可算得上是一枚标志性的旗帜,陈刘二人的交往,对双方的绘画艺术观以及他的艺术素养都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在这样的一个身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基础之上,陈独秀才在1919年提出“美术革命”的文化主张。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主张,显现出作为一名思想家、政治人物的陈独秀对绘画艺术的高度认识,以及其对绘画艺术发展犀利的提出了个人的观点与主张,对中国绘画的发展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陈独秀对绘画艺术的独到见解和深厚的艺术修养。陈独秀“美术革命”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一场以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与洋画写实主义的对立为焦点的中国美术前途的争论。首先,陈独秀在“美术革命”中,严厉的指出了中国绘画的弊病与问题,提出要革“王画”的命,王画指的是以清代文人画家王石谷为代表的四王的画。指长期以来,腐朽的封建主义绘画“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提出中国画要改良,必须引入西方写实主义的精神。其次,陈独秀一直反复强调“写实主义”,一方面是从绘画技法的角度出发,主张写实的绘画技法,要求画家淡忘甚至是摒弃文人画轻形重意的这种绘画技法,而应当去追求以形神兼顾为主的画法;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更为提倡的是绘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希望当下的画家可以以一种客观的身份,持有客观的角度去再现现当下社会的面貌和现状,去揭露和纰漏社会的所属的实情,为陷入危难的中华民族发出反抗的呐喊声。用他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就是要将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用到文学艺术上。虽然现在看来他们当时提出的想法并不完全正确、科学,但对于一个正在探讨中国未来命运走向的大时代,他们的想法、言论像一颗火种,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美术,中国画改良问题的大讨论。此后,更有许多人,如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等的继承与发展,造就了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画坛。受故乡邓石如老先生的影响,陈独秀从小就研习书法艺术,并且精于六书,正因此,他对书法的字形等有着独到的见解。由此看来,作为一位政治人物,陈独秀对中国绘画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将中国绘画的改良与发展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部分来考量,是将“美术革命”与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界革命等一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与反叛精神,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画的变革,将西方艺术特别是现实主义油画引进中国美术,由此改变了中国美术的格局,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走向。而“美术革命”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人们渴望发展、进步、创新的思想变革,它对后来中国画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中也凸显陈独秀对绘画艺术的高度认识和政治敏锐。
从陈独秀早年的家庭教育及家庭氛围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传统中国书香门第的家族家风,虽然陈独秀后来背叛了这一腐朽的家族,并与其一刀两断,但不得不否认,陈独秀其早期深受这种中国传统科举思想下的教育,也为这种文化艺术氛围所感染,从其家人的绘画传统来说,陈独秀不可能不被这种家族氛围所感染,其对中国绘画的认识与认知以及自身的艺术素养也从这时开始建立起来。走出家乡后,其与国内艺术才子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再加上学术视野的开阔,陈独秀开始形成其个人的政治观点,同时其绘画艺术观也在逐步成熟。其逐渐的开始审视中国绘画的发展问题,将中国绘画的症结归结于“王画”的盛行,强调要用西方写实主义精神来改造中国绘画,要在文艺界进行“美术革命”。能大胆的提出这一论断,首先是建立在陈独秀对传统中国绘画的深刻认识上,正因为他对传统中国绘画发展的深入了解,对西方绘画写实精神的深刻认识,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头人的陈独秀才敢于提出要革“王画”的命,要改良中国绘画。正因为陈独秀的“美术革命”,中国绘画的发展出现了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并影响至今。
藤固在其《中国美术小史》中的一段话:“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就是混交的时代。何以故,其间外来文化侵入,与其国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结合,而调和之后,生出异样的光辉。”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多位艺术家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从而形成特定的的时代产物,从艺术这个领域去分析是极其丰富且高质的,其对后世美术界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陈独秀总结了自己的绘画艺术观在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必然过程,其中既有推动社会发展的这一积极性,也有当下时代背景所导致的规定性。他整个一生所历经的思想和事业,恰处于时代和社会的转型时期。当有着五千年文化底蕴和传承的华夏,在遇到西方走在时代前沿且演变几百年的开源文化时,碰撞出前所未有的“新纪元”。陈独秀毅然推陈出新,宝剑锋从磨砺出,空前绝后的完成了新旧思想的更迭与融合,此高度和速度绝无仅有。为其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添加了浓重的一比,并作为典范流传后世!
参考文献:
[1]《陈独秀传》上、下,任建树 唐宝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2]《陈独秀年谱》,唐宝林 林茂生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3]《画家黄宾虹年谱》,赵志钧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 年版。
[4]《吕澄集》,黄夏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5]《蘇曼殊全集》(全五册),柳亚子编,上海北新书局 1928 年版。
[6]《存天阁谈艺录》,刘海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年版。
[7]《“艺术叛徒”刘海粟》,石楠著,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8]《画魂潘玉良》,石楠著,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9]《陈独秀与中国名人》,朱洪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10]衰败想象与革命意志——从陈独秀“美术革命”论看20世纪中国画革新思想的起源于洋《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
[11]试析陈独秀等人的“美术革命”的思想内涵 黄瑞欣《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2]独秀文存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项目来源:2017年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从当代绘画的发展看陈独秀的“美术革命”》编号:SK2017A320
作者简介:高俊松,安徽怀宁人,安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朱胜甲,安徽六安人,安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陈云云,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