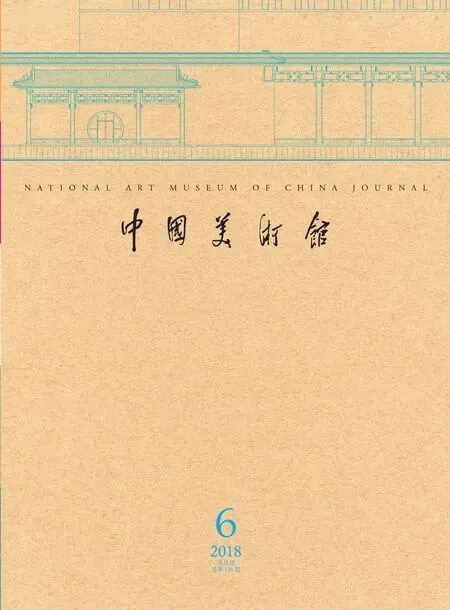“江山如画—金志远、徐孅伉俪艺术展”研讨会纪要
本刊编辑部 整理
2018年9月6日,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中的又一重要展览“江山如画——金志远、徐孅伉俪艺术展”于中国美术馆开幕,并于当日在学术报告厅举行了研讨会。江苏省文化厅原副厅长赵绪成、南京艺术学院原院长冯健亲、江苏省美术馆原馆长宋玉麟、江苏省国画院原副院长喻继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左庄伟、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胡宁娜、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喻慧、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杨耀宁、江苏省国画院傅抱石纪念馆馆长黄戈、人民美术出版社原总编辑程大利、江苏省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原院长萧平、《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裔萼、公共教育部主任徐沛君等出席并参与了讨论。会议由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张晴主持。
冯健亲(南京艺术学院原院长)

冯健亲
我是搞油画的,来评论国画有点困难。但七八十年代画画的人比现在少得多,所以那个时候美术家协会的一些活动,包括出去采风,是不分油画还是国画的。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金志远、徐孅,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批画家。这一批画家和较我们年长的那批老画家之间有一些差别,尤其是新金陵画派要反映现实生活,中国画要画一些人物,对于老画家来讲有一个改造的过程,一个转变角色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隐约看出这种痕迹,但在金志远、徐孅作品中,这种痕迹就比较少,融汇得比较自然。
坦率讲,如果不是这一次展览,他们两位的作品我不会看得这么多。因为这次活动所以特别关注了他们的作品,我觉得我这个判断还是正确的。他们的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山水里面出现的桥、火车,结合得比较自然,这种表现跟对自然对社会的认知是有关系的,我讲的承上启下也是这个关系。到“文革”结束以后又转了,创作观念转变为强调本体,把反映现实的功能整个丢到了一边。现在再来看他们的作品,再来重新审视这一段创作的历史,对于我们当今的创作是非常有价值的。现代艺术我感觉有点走到头了,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当年的作品,反而有一种鲜活的感觉,它里面是有精神的。所以我在此呼吁,对这一代画家的创作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更进一步的研究,真正认识他们对于中国现代美术史所起到的作用。

研讨会现场
赵绪成(江苏省文化厅原副厅长)

赵绪成
有一句俗语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林子里的一只鸟。艺术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父母给予这个人的一切,这是基础,也是根源,然后再加上外在的环境。所以,我看金志远和徐孅先生的画,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是吃淮扬菜长大的,也是做淮扬菜的,十分地道。我对金志远、徐孅伉俪的过去没有太多了解,但是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聊天很舒服,这种舒服现在看来是一种平实、平和,是一种温暖的感受。
70 岁以后思考人生、艺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怎么都行,不行也行,因为未知无限;怎么都不行,行也不行,因为已知有限。一切都在行与不行之间,永远都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无所谓行与不行,都在酒里,都付笑谈中。
喻继高(江苏省国画院原副院长)

喻继高
今天参观画展,令我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我第一次见到金志远是刚刚毕业到了江苏省美术工作室,那时候金志远在创作连环画《刻字老人》,后来又创作了工笔画《毛主席在山村》。后来才到了画院。从现在的作品来看,金志远和徐孅夫妇都是饱含着政治热情,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文化生活,不断地下乡,不断地创作。所以,他们的作品代表着这一历史时代的精神面貌。他们生活非常艰苦,为了画画顾不得自己的生活。那个时候起早贪黑,晚上吃过晚饭还要画到很晚才回家。他们为后人留下这么多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金志远和徐孅两位画家都是非常有才华,也是非常有创作激情的,通过这次展览,我们看到他们从1954年至1985年这段时期内创作了这么多的作品。把这一批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我觉得非常恰当,也非常有意义。现在再去找那个时代的作品,可能很难了。那个时代的很多画家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一生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美术馆能把这一批作品收藏起来,是非常可贵的。
我和金志远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和邻居。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同一个年代看着他们画出来的,知道什么时候画的,怎么画出来的。刚才我看见《采菱》,后面的小伙子回过头来很含蓄,有点害羞地看着他的对象,画得非常精到。我当时跟金志远说,等到正式作品画完以后,草稿给我留个纪念。后来草稿我也没拿到,画了好几稿,还是最开始的这张最好。说明创作有时候好的作品真是偶或一得,他的第一稿是充满了感情画的。还有一张《养鸡姑娘》也画得很好,不知道被哪里收藏了。
他们的创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一次展览又给了我们很好的学习机会,看了以后,既高兴、激动,又感觉可惜,引起了很多回忆和怀想。我会永远把这两位好朋友记在心里。
宋玉麟(江苏省美术馆原馆长)
我的感受跟大家一样,到了展厅以后首先感到非常亲切,又非常激动。第一,这些作品大部分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作品。第二,自然就会回忆到金志远和徐孅两位先生。感谢金田把金志远、徐孅夫妇的艺术作品公之于众,让大家能够看得到,放在家里是不行的,应该入藏中国美术馆。

宋玉麟
我认识金志远、徐孅老师早在6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中学。我是共青团员,每年暑假要回到画院参加社会实践向徐孅老师报道。她是国画院的书记,安排我在画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时候画院的笔会特别多,老先生们都来,当时没有墨汁一说,都是发动很多小孩子磨墨,暑假结束时候给了我很高的评价,都是徐孅老师亲自写的。
金志远老师比徐孅老师大一岁,他们都在54 岁相隔一年英年早逝。这个展览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我父亲和金志远老师合作的《劈山引水》。我从小就对这张画记忆很深,今天才知道最好的一张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我认为这是艺术史上比较完美的一幅画,人物各种姿势,各种动态,劳动的场面非常生动。我之前看印刷品以为这张画很大,今天看到原作发现作品很小。我父亲的配景也不错,有很多北宗的技法在里面。老先生画画的时候线条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原作上都体现了出来,上墨又没有盖住,很自然的那些痕迹都在上面。这种创作的状态就是今天所谓的干净、完美、漂亮。还有很多题款是我父亲的字,看到很亲切。在我回忆里,徐老师和金老师礼拜天也好,平时下班也好,跑到我父亲的画室里交流,有时候会让我父亲题款,说明他们当时的情感应该是很深的。
他们这一辈人注重写生。金老师的写生本很高一摞,每一张写生都可以说是一幅作品。所以,他的创作基本上都是从写生过来的,这个特点非常明显。另外,他们很注重日常生活中别人不注意的细节,像一瞬间的细节表现,都是平时大家不在意的,但很生活化、很生动的情景,他们通过仔细的观察描绘了出来。他们在艺术技巧上今天看来有时不太完美,但他们的创作是生动和真切的,这种真切恰恰是我们最缺乏的,情感性的东西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得够充分。他们的创作为什么感动人,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去了,把自己的心思都用在画画上面了。所以,作品不在大小,也不在于技巧一定要完美到什么程度,关键是真情实感。
他们作为伉俪画家,艺术创作上肯定是相互影响的,还会共同画画。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他们俩都是从五六十年代的人物画家到了70年代转为山水画家。作为山水画家,他们相对来讲比新金陵画派余彤甫、丁土青、张晋、张文俊要晚一些,金志远老师没有进入到新金陵画派这批画家的前九里面,主要原因是他最早是作为人物画家,从70年代开始才以山水画家的身份出现在画坛。而新金陵画派主要以山水为主,当时也没有安排他们参加两万三千里写生。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又转向山水了。最重要的作品就是金老师和我父亲为毛主席纪念堂合作的一张《韶山朝晖》,当时的影响比较大。我觉得金志远老师和徐孅老师是金陵画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但很可惜他们去世得很早。他们最好的时光就是“文革”那段时期,被耽误了,再加上两位先生早逝,但还是留下这么多的作品,足见他们的勤奋。现在通过这次展览把这批画交给了中国美术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程大利(人民美术出版社原总编辑)

程大利
一想起金志远、徐孅两位先生就非常亲切,他们是让人敬重的一对伉俪画家。我有幸在1981年的时候为两位先生编了一本画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们两个人给我的印象永远是轻声说话,待人非常有礼貌,教养是一代人的教养,儒雅、诚恳、朴素,一点虚势夸张都没有。虽然就是一个册子,我来回跑了很多趟,最后请林老写题签。我前天把它找出来了,发现金志远先生每个字都补过了,七个字每个字都挖一遍,肯定是前面发现某一个字不理想,他挖了一个,接着发现还有不理想的,再挖。我觉得将来就这个原件可以写一篇文章,它背后有着文化的、人格的意义,反映了那一代人的工作精神。
金志远和徐孅是新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知道钱亚宋魏,还知道一些老先生,紧接着就是跟喻继高先生同辈的金志远、徐孅,还有比他们年龄大一些的陈达、尚君砺,他们不仅对江苏绘画,对全国的绘画贡献都是很大的。如果说当时长安画派在学习传统上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个新路就是走出了一种粗犷的高原黄土之风的话,那么新金陵画派走出的这条路更多留下的是对江苏、对吴门画派、对元明清绘画文人气息的继承,对笔墨内美的继承。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首先给我们的感觉是重意境,内美的第一个元素就是要有意境。接下来就是语言,笔墨语言一定要留有余地让人去推敲,去琢磨,去品味。黄宾虹说“画求内美,不务外观”“画中内美非常人所能见”,这个常人就是不动脑筋的人或者不感兴趣、毫无感觉的人。这是中国画跟西洋画两个不同的表现方式,两棵大树不一样,结出的果实不同,两条大河各自归海,流经的道路不一样,两种文化源流滋养出来两个结果,各得其美,各有所长,没有孰高孰低。可惜这两位杰出的画家早逝,他们没有机会像我一样走遍世界各大博物馆,未免太过遗憾。
金志远和徐孅两位先生所处的时代充满了政治运动,他们学习的就是批评传统,不能躺在传统的温床上睡大觉,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突破传授,寻找新时代的语言。这有错吗?一点没错。今天我们有机会把元四家、明四家一个一个分头出版,现在想看一张龚贤的画很容易,但龚贤在“文革”期间是不能看的。他们好多作品是在批“黑画”期间画出来的,这两位老先生是在不正常的年代里头真诚的艺术家。一方面他们是20世纪上半叶艺术家的优秀代表,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局限和扭曲抛掷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阴影在两位先生这里都存在,这是无法回避的。尽管如此,我们在金志远先生和徐孅先生的画中还是看到了真诚、情感、纯粹,看到了他们一丝不苟,追求笔精墨妙的表现。
他们没有碰到后来吴冠中先生提到的形式问题,因为接着我们就改革开放了。有一个词叫“拨乱反正”,还有一个词叫“解放思想”。那个时候我正在编《江苏画刊》,对形式的推广和推进是那一代画家没有碰到的。这两位画家如果能够活到今天,必定是不可限量的,可惜的是他们在最美好的年龄离开了。但他们还是留下了这么一批优秀的,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作品。我们今天确实是碰到了好的时代,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的观点是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不拒绝、不排斥一切外来好的东西;在吸收外来养分的时候,绝对不能把我们祖先千锤百炼留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丢掉视而不见,这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有人批评得非常好,“胡画”,这两个字是深藏道理的。中国画讲究的是自己的语境、笔墨,自己的艺术规律,我们在金志远、徐孅两位老先生的画中就可以看到他们严格地遵守了笔墨的艺术规律。所以,画上有他们的体温,有时代的印记,有20世纪上半叶整个的历史脉络。
金田能够继承父母亲的精神,做了这样一次捐赠行动,难能可贵,我们这些老朋友还可以借此机会聚一聚。这批作品入藏中国美术馆,可以说是得其所哉。
萧平(江苏省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原院长)

萧平
我刚才在三个展厅里徘徊,思绪万千,想到几十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在眼前。我讲几点:
第一,今天金田兄妹把金志远、徐孅两位先生50 多张画无偿捐献给中国美术馆,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境界。把这批画捐献给中国美术馆,对父亲的这批遗产来说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安置之所,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同时也给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讨的机会。
第二,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画家,开始都是在“美术工场”工作,然后调金志远先生到中央美术学院,是调干生。徐孅先生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华东分院,就是后来的浙江美术学院,学习4年。毕业以后,1988年结为夫妇。金志远先生早期学画水彩,也画过油画、漫画、年画、宣传画、领袖画等,无所不画,甚至还布置会场。当时的美术工场是什么都要做的,他们是非常能吃苦的一辈人,对工作兢兢业业,甚至夜以继日,再加上生活条件差,克勤克俭,就也是他们五十几岁就去世的一个原因。今天回忆起来是非常可惜的,两个纯粹的、真诚的把丹青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正处壮年的艺术家就这样走了,除了怀念,也值得我们反思。
第三,新金陵画派的形成非常值得研究。江苏画院1956年开始筹备,除了亚明先生、魏紫熙先生可以画人物以外,大部分都是画山水、花鸟的。傅抱石先生当时主要是画古典人物。那个大时代是中国画面临存亡绝续的时期,有人说中国画“不科学”,包括徐悲鸿先生都讲过,山水画有恢弘的历史,但现在它不能为政治服务,毫无用处。这一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江苏画院开始是从江苏各地邀请画师、副画师、助理画师,都是以传统的山水花鸟画为主的一批画家,除了傅抱石先生、钱松喦先生、余彤甫先生知道一些西洋画原理、原则,接触过一点西洋画之外,大部分没有学过西洋画。而金志远、徐孅两位先生恰恰都在正规学校学习过,接受的是新式的艺术学院的教育。所以,他们早期的画主要是以人物为主,这批人物画跟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的毕业生都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回到南京,慢慢地被改造,逐渐地开始跟这些老画家融合。
江苏画院的这一批集体创作或者几个人的创作非常能说明问题,金、徐两位先生在跟老先生的接触过程中慢慢地把中国画的传统汲取了过来。所以到了70年代他们就开始变了,往山水画转。徐孅不仅往山水画转,还包括花鸟画。在这些接触或合作中,既保留了他们在艺术院校中学到的造型能力、应变能力,同时也吸取了很多老先生的优点。《劈山引水》这张画非常协调,看不出是两个人画的。那个时候大家对待艺术是真诚的,这样一种态度让他们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成为了学习过程。他们早期的作品,可能感觉到自己的书法水准还不够,所以往往会找一些老先生题字。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不少宋文治先生,还有钱松喦先生、魏紫熙先生的题字。七八十年代之后,就会发现作品全部是他们自题,书法有了相当的提高。新金陵画派从草创慢慢发展,过渡到成熟,这样一个阶段中,他们也不断在学习,慢慢地成熟起来。他们是不是对传统就没有认识了?不是的,在他们心中一直是两条线,一条是中国绘画的传统,一条是大自然,到生活中去。
金志远先生有一方印“得之真山水”,他的山水画一大特点就是写生。他是扬州人,但扬州八怪跟金先生是凑不到一起的,扬州八怪偏于纵放,但八怪之后扬州的画风也在变化。清代中期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画家,都是从华喦那里取径,用的是小笔头,不用大笔。我看金志远先生取的就是这个路子,也用小笔。他画松树提取了王蒙的一些画法,用繁密的小笔。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午是理论课,下午是绘画创作,晚上是写生。他们不是没有理论的,金志远先生就非常喜欢谈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他们夫妇两个人性格不完全一样,徐孅先生比较爽直,快人快语。她是常州人,清初常州画家恽寿平影响清代画坛300 多年,在常州更是蔚然成风,尤其对女性的影响非常大,画史上清末民初时期的常州女画家大都学恽派。而徐孅先生初中毕业就考上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然后再到美术工场,最后调到华东分院,又回到南京。她的用笔跟金志远先生不一样,更接近沈周,笔是直直的,金志远先生倒是秀润的。整体来讲,他们都是以写生为主,比如他们合作的年画《歌声荡漾到船归》当时影响很大,《送饭》也得了奖,双勾画法很有创意。
他们20 岁开始创作,54 岁去世,中间还有“文革”10年,20年的时间留下这么大批的画作,值得敬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新金陵画派的成长历程。
左庄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左庄伟
老人在一起容易回忆过去,年轻人都讲未来。在座的除喻老以外,好像我算比较大的,我跟这两位画家相处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我1960年毕业,做学生的时候就跟他们有过接触,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他们的为人和作品。
刚才冯老的讲话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和观念,萧平先生的评价也能代表我们对他们艺术的认识,另外有几点我想强调一下。
第一,金志远和徐孅的艺术风格应该是整个国家艺术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体现。过去一般对人物画是比较重视的,当时我们画画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要求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走这样一条艺术道路。如萧平先生分析,在南京,相当一批民国过来的老画家基本上都是画山水和花鸟,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画家更多的是强调造型能力,以人物画为主,表现的手法、方法基本相似,年画、连环画、宣传画,都是画人民的生活,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这一代的画家大的风格基本都是相似的。在一些作品的表现上,山水只是一个配景或者作为环境出现,基本都是以人物为主体形象。艺术家自己的个人风格并不鲜明,写生一般都是江南的景、江南的人,一个画家画得好,其他的画家基本都按照他的路子去画。比如亚明画的苏州人物,在江苏影响很大。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走出来的画家基本都是以人物为主,包括魏紫熙,主要是年画、连环画,这种形式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人物造型、人物风格大体相似,这是由时代大风格决定的。
第二,整体来讲,江苏在解放初期一段时间里,如果要画山水,那些老画家功力还是不错的,但用过去传统的技法去表现现代生活并不协调,比如宋文治画过中山陵,用的是古人的笔法和技巧,中间有一队少先队员扛着小红旗点缀一下,表示这就是新生活。我印象当中那时讨论过,认为这种表现是旧瓶装新酒。那个时候江苏的美术界大概由江苏美术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南京艺术学院,还有江苏画院,这几个不同方面的力量组合起来的,有中有西,影响着江苏画坛,所以在一个时期里艺术观念、艺术道路、艺术效果都是朝着大同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现在看这些画,如果不签名的话很难判断出自谁手。另外,当时强调集体创作,那个年代不讲名利,也不讲拉帮结派,强调集体创作、集体智慧,强调共同的艺术观、共同的表现。时代的风格影响了个人的风格,个人的思想情感跟时代的思想情感是结合在一起的。再者,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知道那个时候大家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确是怀有真情实感的,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和社会的情感也是一致的,所以作品里不管出现什么样的人物,确实可以反映一个时代人民的精神面貌,丝毫没有虚假的成分。年轻人或许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我们很清楚,金志远和徐孅两位先生的作品是充满真情实感的。
第三,新金陵画派应该说是江苏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形成的“江苏艺术风格”,扩大一点讲就是江苏派。代表人物是“九老”,最主要的代表是傅抱石先生、钱亚宋魏,后来江苏的理论界、画界一致认为张文俊先生应该也在其中。当时对新金陵画派的界定在理论讨论上有几个说法,一个是时间地点,时间是1961年,人物是国家画院的两万三千里写生,集中在山水,当时认为这是代表事件,人物和花鸟没有更多地考虑进去。无论从艺术观念、艺术道路还是艺术的表现效果上,基本都是大同小异。所以,金志远先生应该算在新金陵画派大的范畴里面。
归纳起来,我认为江苏美术的发展一直是沿着一条既跟国家、时代并驾齐驱,又有江苏特点的道路行进的,那就是继承传统、深入生活、贴近时代。这也是新金陵画派一个重要的主旨。当年亚明复出以后,开始在江苏抓传统学习,包括金志远、徐孅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他们在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中都会向传统靠近,我们能看到在他们的画里已经注意到了笔墨的问题。我不反对走现代,也不反对当代,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传统还是一定不能丢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金志远和徐孅两位先生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贡献,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尚辉(《美术》杂志社社长、主编)

尚辉
金田把二老的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这是对20世纪中国美术收藏极大的丰富。感谢中国美术馆能够比较全面地收藏金志远和徐孅的作品,不仅满足了家属的一种愿望,更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尤其是为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绘画的变革提供了更加细腻深入的样板。

研讨会现场
这个展览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重新审视新金陵画派,它的生成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几“大老”,考察金志远和徐孅的创作年代、成名年代,恰恰是和新金陵画派的酝酿和立派是同期的。所以,用“继承”这个词我倒觉得并不完全准确。他们共同参与了新金陵画派的酝酿和发展,只不过后人更看重新金陵画派的山水,而忽略了当时和新金陵画派共同成长的人物绘画。我们顶多说到了魏紫熙,但是今天看了金志远和徐孅的作品,最精彩的还是他们早期的人物画。那个时候人物绘画表现现实生活的确是很难的,大家都知道汤文选的《婆媳上学》,一下子成为中国画变革最重要的一件作品。《第一张选票》也是很重要的,表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做主人。很显然它们和传统的人物画相比在精神立意上,在形象塑造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总是和传统笔墨结合在一起的。
金志远和宋文治合作的《劈山引水》,刚才宋玉麟先生说山画得很好,如果金志远一堆人画不好,山也画不好。这一堆人现在看还是很精彩的,你可以说它来自于速写,但我觉得速写是搬不进画面的,很显然它有对人物组合、对笔墨浓淡不能说是很高妙,但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发展。再看看徐孅的《送饭》,里面的人物形象从人物的结构到正面和侧面处理,尤其是一些光膀子的人物形象的处理,很显然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人物造型的理解,或者说造型和笔墨的一种运用。
刚才大家都谈到了,金志远到中央美术学院得到了徐蒋体系人物绘画的训练,所以早期金志远、徐孅的人物绘画乍看不易分辨,但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金志远对人物的结构画得更干一些,强调得更突出一些。徐孅是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今天看她的画还是特别的精微,一点一滴都处理得干脆利落,都画到了。颜文樑的画风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到了徐孅还不好定论,当然后来她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也是我们认为浙派人物绘画崛起的地方,徐孅去的这个时代也恰恰是酝酿浙派人物绘画的时代,当时方增先、李振坚也试图把花鸟画勾花点叶式的人物造型放进去,从徐孅的作品中能看到这个意思,但也不是十分明显。有一点可以讲,在新金陵画派生成的阶段,用人物表现现实生活是第一位的,山水还要向后推迟一二年。正是因为有像金志远、徐孅这样用传统中国画来表现现实人物,大胆进行中国画创新的画家,推动了新金陵画派在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变化。当然至于他们中间是如何接受的,还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美术史研究。比如说他们和亚明的关系,时间的前后,不能草草定论,至少我们从他们的作品里可以分析得到新金陵画派在人物绘画上的发展,在血脉上曾经受到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这两个画人物体系的影响,所以才使得金志远和徐孅的人物绘画在当时的江苏特别突出。当然新金陵画派山水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金志远和徐孅也慢慢走上了山水画的道路,至少是山水和人物相结合。这一点徐孅是很好的典范,她特别精于构思,比如60年代的《茶亭》。我发现今天的人不太会画带有情节性的画,但徐孅的《茶亭》是主题性人物绘画的精品。虽然这件作品宣传得很少,我们都不是很熟悉,但我们看到它的时候,还是会承认这是一幅经典作品,尤其在人物的形象处理上。在江苏画人物画,久而久之都会被山水画同化,不仅如此,用笔用墨的技巧和方法都会被同化。所以,徐孅的人物形象除了勾线,人物的头发或者是衣着也会有一些山水笔墨的处理,增加了更多韵味。
徐孅的作品还引导我们特别去关注70年代末中国画的变革。这部分作品,今天研究美术史的人经常一笔带过,因为紧接着是改革开放,我们很快进入了既受西方现代主义冲击,又向现代主义学习的阶段,强调大笔块的水墨或者形式构成。他们两位没有赶上这个时代,也使他们在70年代的绘画艺术成就凸显而出。金志远和徐孅最重要的作品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画出来的,他们一直忠实于如何表现生活,把生活中的情趣表现出来,而不是图解政治。不是表面上的莺歌燕舞,而是表现人的情感,表现丰收者的喜悦,以此来抒写自己的情怀。比如《洞庭桔红》也是一幅精彩的作品,尺幅很小,但是境界场面很大。这件作品之所以吸引人,首先就是它的构图非常精致。她画的是江南水乡的农业丰收,有水稻,有船来运粮食。她另一幅作品《金秋十月运粮忙》是以俯瞰的角度来画船上丰收的稻谷,也有在桥上画桥底下运粮的场景。《洞庭桔红》画的是远远的船上丰收的场景。同样的主题,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徐孅善于运用构图的变化,这种构图的变化和她的视角变化是紧密相关的,她处理得非常好。70年代末画《梅园新村》的人很多,包括钱松喦。徐孅的《梅园新村》把梅花绽红一片画成近景,远景是梅园新村的建筑,梅和建筑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她很注意一些细微的处理,比如画稻谷,很多人画稻谷不经看,徐孅用的是勾线的方式,借鉴了传统的树法。她对中国画不是那种大跨度、大跳跃的断裂式的变革,而是细微的,仿佛潺潺流水,在不知不觉中把写实的人物造型,透视的变化、构图的复杂和传统的笔墨有机地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对传统中国画一个很好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
金志远先生则似乎完全转向了山水画。他的山水画和我们所认识的新金陵画派一般的笔墨是比较接近的构建。比如散锋皴,大面积用水渲染的方式,使烟雨的变化更加自然,这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新金陵画派第一代、第二代画家所基本持有的公共审美范式。当然金志远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散锋皴必然涉及到一种刚劲的笔法。我同意刚才大家谈的,在笔墨上徐孅体现出一些男性的风格,金志远更加温婉一些。如果说他们两人的个性之间相同性占多数比例,小的区别就是徐孅在用笔的方法上和金志远有差异,她更多是用碑学的点掇方式使画面更加温润,金志远用散锋皴,则略显苍劲。徐孅画的江南水田,金志远画的云台山水,同样都是绿油油的调子,但比较起来,他们在构思的方式和用笔上还是有区别的。同样是画水乡,徐孅画得更加水墨淋漓,而金志远用细的散锋皴勾皴近前的树和中景的水乡民居。可以想像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写生而获得的素材,但是在提炼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艺术风貌上就有所差别,尤其是使用中国绘画语言的时候的确稍微有所不同。
金志远和徐孅让我们对新金陵画派的生成和发展有了新的认识,至少新金陵画派中的人物绘画是我们在研究新金陵画派的时候被忽视的。我们对新金陵画派的认知,随着我们对一些作品新的认知,一些展览的举办有了刷新。历史是有不同侧面的,我们常常能看到哪些作品,有哪些人物和作品被遮蔽了,艺术史终究是客观公正的,好的策展人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带给我们新的视野。我相信这次展览的举办是为我们带来新视角,重新认知新金陵画派的重要契机。
胡宁娜(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

胡宁娜
前面几位老师谈的我特别有同感。有几个原因,一是金志远老师和徐孅老师是我们国画院的前辈;二是我跟金田是这一届主席团的成员;三是我们都是“画二代”,所以有很多的同感。
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太熟悉了,然而到今天我才细细地看两位老师的画。刚才讲到中国画分科,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画来讲,我还真分不出他们是山水画家、人物画家,还是花鸟画家。现在很多画家,是我擅长画什么我就画什么,而那个时候的画家,是需要你画什么你就画什么。我觉得金老师和徐老师是全才,而且画得很专业。比如码头的船,现在画人物画的可能就会回避掉,最多当做配景,但是他们的画是前景。山上的很多树比如大的松树,如果不是专业山水画家不敢把树摆在前面。所以,现在想来我的父辈那一代人真的是了不起。
黄戈(江苏省国画院傅抱石纪念馆馆长)

黄戈
金志远、徐孅老师的展览带给我一个思考:今天的年轻一辈对他们的研究以什么样的语境来切入?我们以前对新金陵画派的研究到了现在的知识背景和环境下,应该重新进行怎样的审视?我前两年参与了一个金陵画派美术馆的方案工作,未来我们的研究应该不仅仅是傅抱石、钱亚宋魏,而是一代一代新金陵画派的发展脉络。我也去看了今年苏州的双年展,为什么去看?我的想法就是如何把现代的语境和策展方式以及表达方式嵌入到我们所要表达的主题中。我一直在对这方面的课题对进行深入的思考,希望通过我们这一辈的努力,继续把老一辈的精神发扬光大。
裔萼(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

裔萼
这个展览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提起新金陵画派,大家一般都知道“五老”,其余成员因为各种原因不太为人所熟悉。而这次新金陵画派两位重要的艺术家金志远、徐孅的作品大规模面世,非常难得。所以说这个展览是一个具有钩沉意义的研究展。
和他们的同辈艺术家一样,金志远、徐孅在自己的创作盛年,艺术创作却面临着种种限制,堪称戴着镣铐的舞蹈。思想上面临着深刻的改造,画法上需要和新题材新内容相结合。他们处身时代的大潮之中,依然能够葆有一种质朴和诗意的情怀,以平实之笔表现普通劳动者,尤其是表现江南水乡人民的日常劳作和丰收的喜悦,充满诗意之美。他们的作品朴实、秀雅、清新、隽永,自具风貌,代表了新金陵画派人物画的最高水平,也丰富了新中国的绘画史。
徐沛君(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

徐沛君
金志远和徐孅两位画坛前辈的成就很高,风格也很统一,可以从很多方面,譬如艺术特色、个性面貌等角度加以解读,得出丰富的结论。最能打动现代人心灵的,还是弥漫和充盈其中的浓郁的田园诗情。比如金志远有一幅作品《晨露》,描述农民到田里干活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之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画作题目用的是“晨露”,我不知道是不是借用了陶渊明的诗。陶渊明是隐士,但他也描述劳动。金志远和徐孅两位前辈在描绘劳动的时候,把古人的田园诗意和现代人对劳动的尊崇和歌颂融合在一起了,画面充满田园诗意境,也带有对劳动一种发自内心的歌颂和欢愉。这一点最能够打动人心。
画作中的农耕劳作手段正在日渐远去,“田园”及田园诗意也在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成为一种历史及美学象喻。现在再看他们的作品,是后工业化社会、网络化社会对传统田园诗意的一种深情回溯,这种情愫可以打动现代人,也一定可以打动以后的人,它既是一个时代劳动形式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对一种文化意境的永恒的追求。
张晴(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今天的研讨会就像刚才尚辉讲的,很生动,好像回到了江苏国画院,其乐融融。能够把大家请来在这里聚会是不容易的,多年之后必定是一段佳话。
第一,20世纪被遮蔽的艺术家有很多。通过研究这两位老先生的艺术,提醒了我们未来将要做些什么工作。你们今天的叙述,我们记录下来,以后可以好好研究,把新金陵画派研究透,然后再到中国美术馆来做展览。如果能够把新金陵画派这些老先生的故事都讲出来,我们随后再学习、研究,这个贡献就大了。
第二,感谢金田先生把自己父母亲的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这是一种胸怀。他说,今天把父母亲的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我的心也放下了。这句话是他发自内心的。他有两重身份,一是家属,一是江苏美术馆的副馆长。所以,他很清楚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归属何处才是真正的落地。

张晴
第三,通过对金志远和徐孅二老作品的研讨,我们对新金陵画派有了再认识、再发现,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学术任务。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新金陵画派在20世纪美术史上的贡献也将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表述。
最后,我代表中国美术馆再次感谢金田全家对我馆的捐赠。希望更多的人对中国美术馆进行捐赠,我们要做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的陈列,有很多作品我们是没有的,如果大家都能积极捐赠,我们的工作将会加速走向完善。
——中国美术馆藏文学插图精品展
——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藏明清肖像画展
——中国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广西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