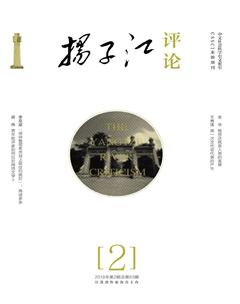呈现之余的期待
叶橹
在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活动中,江苏作协、《扬子江诗刊》不但举行了多达20次的系列研讨活动,还约请了江苏一些知名诗人编选了上下两卷的《江苏百年新诗选》。这两卷厚重之作,广泛地收录了百年新诗发展进程中江苏籍和长期在江苏工作的诗人的代表性诗作,也有一些因与江苏有着某种特殊关联的诗人作品入选,充分地体现了编选者的独到的目光,也证明了他们为此而付出的心力。
纵观这两卷本的诗选,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主事者的胸怀和魄力。在全国性的各类诗选中,江苏以独具的眼光从地域性特点出发,精选了305名诗人的诗作,不仅显示出江苏诗人的宏大队伍,更体现了他们在百年新诗发展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地域性”的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宏观中的微观、微观中的宏观的诗歌观察视角。就全国范围而言,某一地域中的诗歌现象,可以说是宏观中的微观,而对某一地域中的不同诗人的创作现象进行研究,则无疑是透过诸多诗人的微观现象而综合出该地域的宏观格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卷本的《江苏百年新诗选》无疑具有这种双重性的品格。人们既可以从中看到江苏诗人在中国诗坛的独特地位,又可以在对这些诗人的具体观察和研究中,总结出江苏诗歌的某些艺术特色和风格。所以我认为,这两卷本的诗选,可以说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巨大意义的工作。它既提供了一种史料,又为人们从事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起着导引的作用。
作为新诗历史发展进程的见证,这两卷诗选中所记录的,自然是江苏诗人们的创作实绩。那么,我们可以从诗人们的创作中,读出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首先,在新诗的初创阶段,我们欣慰地看到,以陈衡哲、刘半农、刘延陵、陆志韦、宗白华、朱自清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都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敏悟者。五四时期的追求个性解放,把个人融入社会的奉献精神,最早地体现在这些诗人的创作之中。女诗人陈衡哲作为最早出现的女诗人之一,后来因为主要以历史学的研究而淡出诗坛,但她的《鸟》一诗,却在新诗初创时期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诗以最鲜明的对比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一只在狂风暴雨中“找不到一个栖身的场所”的鸟的遭遇,而此时一只在“金漆的栏杆”后的“笼鸟”,却怀着“是忧愁,还是欢喜”的复杂心态看着这种情景。等到风雨停了,它看着那些“随意飞去的同胞”,不禁发出了心声:“我若是出了牢笼,/不管它天西地东,/也不管他恶雨狂风,/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直飞到精疲力竭,水尽山穷,/我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这样的诗性表达,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那一代青年人对自由的向往,为挣脱精神束缚而不惜粉身碎骨的气概。而刘半农的 《相隔一层纸》的对贫富悬殊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样表达了追求享有物质平等的正义呼声。向往自由,追求平等,从五四迄今,一直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息息相通的社会思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体现了诗人们的信念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在刘延陵、陆志韦、宗白华这样一些诗人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闻到一些现代意味的气息。他们可以在世俗生活中体察到一种微妙的感知。《水手》是刘延陵的代表作,也是新诗史上的名篇。它传达的是一个“水手”对妻子的怀念,但却在前后两节诗中,以蒙太奇的手法呈现了“他”在现场和想象中的思绪和场景。陆志韦的《子夜歌》更可以说是一首非常迷人的短令:“夜深了么?看天河渐渐的白。/琥珀光拥护这满山的松柏。/窝里的小鸟没有一些声息,/只有我那,脚踏着路旁的荆刺。”从遣词造句到意境的呈现,把一个诗人的精微而细致的感觉,表达得何等的迷人。至于宗白华那些优美精致的短章中蕴藏的诗性哲理,更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我之所以把这样几位诗人的“现代意味”专门作为一个话题,是因为在其后继起的一些诗人中,更进一步地发扬了他们的优点,从而在新诗史上建树了可以称之为丰碑式的作品。
以《距离的组织》之艰涩和《断章》的优美与多义而闻名的卞之琳,毫无疑问是新诗史上无法绕过的大诗人。这次在诗选中选的另一首《古镇的梦》也堪称拔萃之作:“小镇上有两种声音/一样的寂寥:/白天是算命锣,/夜里是梆子。”为什么单单从这两种声音里听出了寂寥,不妨细品诗中的演绎。像辛笛的《航》,纪弦的《狼之独步》,吴奔星的《我沿山涧以彳亍》,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与表达上,无不体现一种独具的韵味与节奏。这种体现诗的语言日渐走向现代的风度,正是造就诗的内涵愈益丰富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这样一批极具现代意味的诗人中,我想专门提及一位女诗人。她是沈紫曼即沈祖棻。她是知名学者、教授,对我国古典诗词的研究极具开拓性,自己的旧体诗词创作可谓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水平。在诗选中选了她的五首现代格律体新诗。仅从这五首诗中,我们即可窥见她在探索现代格律体新诗创作上达到的成就。她的创作似乎证明,写现代格律体的诗,是需要有旧体诗的造诣的。这种造诣不是体现在如何让新诗成为旧体诗的变体,而是要在语言韵味和格律节奏上充分融汇消化,溶入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意识。她的诗没有固定的模式,每行的字句也只是大体整齐,绝不因凑齐字数而削足适履,也不因追求统一而滥施以水充油。她的诗应该给我们现代格律体的追求和探索者以有益的启迪。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坛,由于面临政治环境的改变和舆论导向的关系,使众多诗人在创作上进退维谷。但我们仍可以从屠岸的《稻明波》、沙白的《水乡行》、忆明珠的《春雨》这些写于不同年代的诗作中,读到诗人们从大自然的景物感受中浓浓的诗意。这些以对大自然的景中有情的诗,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诗人的精神寄托。而闻捷作为一位重要诗人的出现,则是以对爱情的抒写而获得名声的。寄情山水和对美好爱情的讴歌,本是历来诗歌中的重要题材,但是在特定环境中,这类题材频现佳作,而众多描写现实生活的诗,却未能经受住艺术标准的检验,成为时间的淘汰物,应该是一种深刻的教训吧。
1980年代以后中国诗坛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无疑体现在江苏诗坛上。新时期出现的韩东、车前子、小海等诗人,可谓得风气之先的诗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车前子的《三原色》、小海的《北凌河》等,都是一些给人留下鲜明深刻印象的佳作。除了这些已被世人所知的诗人之外,人们还应该注意到诸如收入诗选中的佳作:长岛的《纸上的声音》所呈现的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无声的抗争;庞余亮的《在人間》对历史的沉痛记忆;丁捷的《太师方椅》对“传统”威仪的暗讽;如此等等。
诚然,1980年代以后的江苏诗坛所呈现的勃勃生机,不是这样对个别诗作的点评所能概括的。从这两卷本的诗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仙逝或仍然健在的老一辈诗人,他们的大部分优秀之作也是写在1980年以后,而许多后起之秀的中青年诗人,更是成为江苏诗坛的主力军。特别要提到的像西川、胡弦、张作梗、朱朱、沈浩波、黄梵、育邦等人的诗,不仅已经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影响,而且还正走在继续创新并潜力犹在的道路上。这些人有的虽不在江苏工作,但他们身上有着江苏的基因,有的则是从外地移居江苏而为周围的环境气氛所感染,成为江苏诗坛的新鲜血液。诗选中选入这两类人的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这皇皇两卷的诗选对诗人和诗作的选择中,我们不但看到了编选者们的苦心和良知,更能体悉到他们的洞察诗歌艺术美质的眼光和能力。
首先,对于百年中复杂的诗人和诗作的选择,是需要查阅大量原始资料的。有一些人,譬如郭绍虞,我以前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史研究专家,并不知道他写新诗。诗选中选了他四首诗,都可算是精品,特别是《静默》一诗,那种在“一跳一跳心弦颤动的声音”中体察和感悟到“但这是何等的静默呵”的情境与诗境,非一般人能体察和表达出来的。要知道,那还是新诗的初创阶段。另外像对已经在台湾生活数十年的一些诗人诗作的寻找,如舒兰入选的《乡色酒》和《鸟》,其对乡愁的表达,既简练又含蓄,深符由点及面的诗的联想的规律。把一些不广为人知的诗人和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是这部诗选的一大功劳。
其次,编选一部规模如此宏大的诗选,必然会面对一种“悖论”。在对诗人和诗作的选择上,究竟是看人说话还是以诗为本。有一些 “名气”很大的而诗却不怎么样的诗人,同一些“名气”虽然不大诗却写得很好的詩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从诗选的现在这种格局看,我以为是基本符合实际状况的。原因在于,编选者基本上是就诗说话的。自然,由于受到既要照顾到人的存在,又因诗的不可能多选的矛盾,编选者还是不得不削足适履地对很多诗人作了定量的限制,这应当说是无可奈何中的抉择吧。不过由于编选者的艺术审美眼光的不同,很可能会对某些诗人的诗作的选择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选本不是对诗人的诗作的全面评价,因而不可能把他的优秀之作全部选上。所以我认定,这种选本具有另一种功能,就是当你读了他的诗并产生兴趣,是可以有意识地去找他其它的诗来读的。这就是诱导的功能。
再其次,由于百年新诗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曲折,以及诗人个人命运经历的复杂性,在诗人的诗作中存在着某些艺术价值的不同,因此应当允许这种差别的存在。我们不能因为某些诗作在艺术价值观上的抵牾而采取排斥和打压的态度。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诗人具体的生存环境的影响,往往会使诗人在某种情境之下发出一些肺腑之言,而这些肺腑之言却不能用“正能量”之类的原则加以衡量的。试举叶圣陶《黑夜》一诗为例:“便是太阳光,/也自有他烛照所及的极限吧?/惟是黑暗是广大而无边。/我竭力睁开了眼睛,/但是,看见些什么呢?”这是一首非常有生存感受的诗,如果以所谓“正能量”来评判它,或许就会成为宣扬消极悲观的诗。评诗既要考虑到它写作的背景,更须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心性。我以为,叶圣陶的这首诗,即使是放在今天来写,也是体现了一种哲理的思考,而不会是什么“毒草”。
最后,我还想专门说一下选好诗和什么是好诗的问题。因为一再有人说新诗是没有什么标准,许多人也因为自己的无知也在跟着信口开河。新诗的确没有像旧体诗那样的平仄对仗之类的标准,但它的优劣是可以凭对诗性的呈现和表达而得以判断的。我不能说这部诗选中的诗都是好诗,但是它的确从史料性的意义上反映和体现了百年江苏诗人的概貌。其中也真实地呈现了一些新诗的名篇佳作。对于这些名篇佳作的认定,我认为必须以历史的和艺术的眼光加以判别。的确存在着某些曾经被误认为名篇佳作而后来被历史所否定的情形。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判断一首诗之是否为佳作和名篇,需要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加以考察。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艺术水平,才能产生什么样的诗歌。有一些人往往因为生活在当下而习惯于以当下的艺术眼光来评价历史,这并不符合科学的态度。历史所呈现的真相是,从初创阶段而逐步走向现在,新诗可以说是依然走在路上,但历史是现实的一部分,是它不可或缺的基因。所以我认定,它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所创造出的经典,都是可贵的文化财富。有的曾经被认定为经典之作的诗,可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它的文化基因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存在于当下的诗歌创作中。有些人发出的言论,好像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成熟而优秀甚至伟大的诗人,这种言论除了败坏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而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效果。我相信人是从无知走向有知,从幼稚趋于成长的。我们对这两本诗选所应该采取的观察态度,犹如在看一群诗人是如何在探求的道路上彳亍前行的姿态。有曲折坎坷,有成果收获,未来的道路依然会漫长而曲折。人类的生存之道不就是这样的吗?
坦率地说,在当下的现实中,能够做出决定出版这两本诗选,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了。因为它本身会产生许多矛盾,诸如入选不入选和选多选少之类的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什么诗能入选或不能入选。如此等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已经证明了编选者的辛劳没有白费。也许这些被选入的诗作,未必就是能流传的好诗,但它的意义不是树碑立传,而是呈现一种整体面貌。不过我也相信,其中有少数诗作,可能是未来研究中国新诗史的人不能不提及的。能有这样的期待,应该就是值得安慰的了。
我个人在阅读这两本诗选,也受到不少的启迪。以往虽也读过其中部分诗人的诗作,但从未感到江苏这个群体队伍的如此庞大。特别是在读那些活跃在当下诗坛中的诗人的诗作,隐隐地感到他们中有些人,会成为我们时代诗坛的中坚。我们能不能期待他们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罢。
2017.12.18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