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本三题
金荞麦
野莱蓁蓁的小院,终于被拾掇得清清爽爽。
经霜后的红叶李更加艳红,宛若乡野里醉酒的村妇,妩媚中飘逸出阵阵妖气。一场声势浩大的雪并未摧残它们的容颜。在洁白的雪的掩映下,它们格外娇媚。大约是地气的温度尚未升到一定的地步,红梅和白梅似乎一若往常。经过它们的身旁,我总要瞟上几眼,留意一番。不过雪下过之后,它们的肌肤似乎涂抹了春天的色晕,白雪覆盖下的节枝处,隐隐地显现出骨朵的嫩芽,看来春节前后必定是要盛开的。当然,小院里也还有其它的树木,譬如桂树、桃树、水杉、香樟、春秋竹等。不过,它们似乎在春天里都不是我心目中的主角。
主角究竟是谁呢?其实,它已经对你吟吟地笑了——一种微笑,一种淡雅的微笑。这微笑多么像春天水面上细微的涟漪,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笑个不停。它就是被抛弃的金荞麦。每次看到它们,我既欣喜又内疚。欣喜的是我每天还可以看到它们的容颜,心里便有了一种慰藉,而内疚是因为我带它们来到小院,最终又被我不明不白地抛弃,成了流浪的孩子。
我必须先说说它们的到来。
那是2010年的秋天,我发现岳母家厨房外面的空地上有两丛旺盛的植物,一丛是墨绿的薄荷,一丛是绿中泛出丝絲缕缕红晕的金荞麦。两种植物对我来说,曾经司空见惯,可在城市里实属少见。吃过薄荷糖的人,自然对薄荷的气味不会陌生,但金荞麦是许多人不认识的,也少有感知的,但它是我童年记忆中最重要的植物之一。我家老屋西垛的墙角处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柿子树,径直高度超过了屋脊。每当柿子成熟时,柿树便成为鸟儿的乐园。它们毫无畏惧地抢先(鲜)在我们之前,将一些即将成熟的柿子啄得十分狼藉,不堪入目。闲着没事时,我就呆在树下,端详鸟雀如何糟蹋红彤彤的柿子。祖母见我如此没心没肺就持着竹梢子恐吓我——你看到鸟雀吃柿子,怎么不赶走它们呢?可祖母的竹梢子,每次只是蜻蜓点水似地落在我身上,不像母亲打人没轻没重的,恨不得一下子把你送到阎王爷那儿。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确实错了,为了将功补过,便搬来竹椅子放到柿子树下的金荞麦旁。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竹夹板,闭上眼睛,晃悠着二郎腿,通过听觉来判断柿树上的情形。鸟雀一来,我突然打响竹夹板……看那鸟雀仓皇遁去的情景真是令人痛快!可金荞麦被我糟蹋尽了。有一天,村头的黄家媳妇问祖母要点金荞麦,说是做什么妇科病的偏方。祖母便领着她进了我家的菜园子。到了墙角处,看到狼藉一片的金荞麦,祖母真的是好生气哟,却又舍不得惩罚我,只是自己使劲地跺着小脚,就像碓石在石臼里捣着糍粑一样。
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奇的人,一看到黄家媳妇低眉顺眼,一副羞涩的样子,我就觉得这金荞麦一定跟女人有关系。于是,我跑到村东头的麒麟溪旁找到袁开成,他是我心目中的大能人,只要有什么不懂的东西问他,一准有正确答案的。即便一时困惑,他还可以翻看那本破破烂烂的厚厚实实的《药科植物大典》。
袁开成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你们家的金荞麦是一种红茎品种,块状根茎更是宝物,尤其是它们生长在百年瓦砾中,沾有阴柔之气,再加上你们家的金荞麦与艾叶生长在一起,互为作用,其药效更加显著……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家的金荞麦与艾叶生长在一起呢?他笑吟吟地摸着我的头说,一个村子的人,谁不晓得你们家有金荞麦啊——我还为你治过脱肛呢。
什么是脱肛?我好奇地问。
袁开成便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是怎么回事,羞得我当时无地自容——你才脱肛呢!
你别站在那里发呆傻笑了,赶快挖吧。岳母递给我一个铲子,示意我用铲子掘取一些薄荷和金荞麦。当天,我即将它们带回了校园,就手种植在办公室前面的小院里。没想到金荞麦的生命力特别顽强,生长也特别旺盛。一个春秋下来,它们便疯狂地生出郁郁葱葱的一大片,尤其是红色的茎干翻越路牙,在水泥地上匍匐前行。燠热的夏天,它们正好吸收了地表的炎炎之热,减少了大量的太阳辐射。这样一来,办公室里确实感到凉爽多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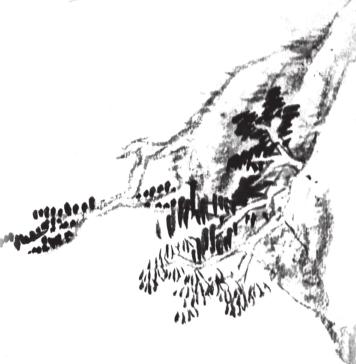
后来有一天,总务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学校要拾掇拾掇这个可以演《聊斋》的小院了,希望我尽快处理掉那些金荞麦。我当时几乎没什么犹豫地就告诉他,处理掉吧,我不要了。事实上,我也确实没地方移植。你想想,偌大的城市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做主呢?就连我老家百余年的老宅下面的土地也不属于我。我的天空我做主,我的土地我做主,那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拥有土地,是中国人遥远的梦想。
经过两个星期的土地平整,小院旧貌换新颜。刚翻耕过的土地,呈现出大量的虫子和微生物,新鲜的泥土散发出草木根须的芬芳,连小院上方的空气都甜滋滋的,更应该是鸟雀们争先恐后的乐园。果不其然,鸟雀闻讯,奔走相告,呼啦啦地来了几十只。有黑鸟,有黄鸟,也有灰白相间的“畚箕”鸟。它们不惧人色,只顾埋头啄食,大快朵颐,个个是大腹便便,摇摇摆摆地飞走了。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几个月之后,播洒的三叶草种子便绽出了嫩芽,遇雨更是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小院终于有了都市的气息。尽管我个人挺喜欢草莱参差、野性十足的原来小院,但毕竟不适合都市学校。我啧啧称赞,逢人便夸。正好某杂志社编辑要我一张近照,我便毫不犹豫地将新垦的小院作为背景了。
我很快适应了这个拾掇得十分精致的小院,也从心理上接受了这个小院。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发现三叶草丛中又生出了多棵的金荞麦。一开始,它们探头探脑,从三叶草里举起紫红色的嫩苗儿,像星星之火。然后它们一天天地变化起来,一天天地生长起来,大有燎原之势。我担心它们过于露脸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果不其然,学校领导终于看到它们显赫的身影了,好像要安排工人将它们彻底清除。
我怀着一颗歉疚的心,走到它们的身旁,不无责怪地说,为什么不低调一点呢?它们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像犯了错误的学生,羞愧难当地低下了头。为了保障它们的安全,不至于在三叶草中过于招摇,我在午休时分悄然地潜入圃中,用锋利的刀片将它们抹蔸儿割去了。果然,这之后没人再提起它们了。它们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安全,我也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也算是对我当初负心的一种忏悔与补偿吧。
三叶草
三年前,城市的山坡引种了耐旱的三叶草。它们或亭亭玉立,擎起掌状的三出复叶,每片叶子中央部位荡漾着锯齿状的白晕,仿佛微笑的浪花;三片叶子上的三道白晕组成一颗洁白的心,时刻对蓝天或大地表白纯情与真诚。它们或匍匐在地,生长出发达的须根,时刻吸纳地面上蒸发的丝丝水气,努力翻越护栏般的路牙,向更远处的空地伸展。那些埋伏在草丛里的石头,蠢蠢欲动,好像从来都没有安分过。它们一直与三叶草争夺地盘,此消彼长,你进我退。这期间,雨水帮了石头的大忙,总是让蓬勃的三叶草暂时地低下头颅,拜伏在石头的脚下。石头们或大如卧牛,静静地反刍,居高望远;或小如窥兔,目光如烛,机警地睃巡四周,一有风吹草动,便学习鸵鸟,将脑袋隐蔽在草丛里,任由脊背遭遇不测。
我总是在晨露瀼瀼之际,漫步在山坡的小径上,穿越郁郁葱葱的三叶草地界,到三台山上做深呼吸。在这段路程上,我消耗的时间大约半个时辰,因为是漫步,就少了匆促,而多了彷徨或遐思。更多的时候,我必然要回头张望的,一心想看看披着霞光的三叶草,是如何无所顾忌地吸纳天地之精华;或者观赏三叶草上方萦绕的彩虹,是如何裹挟并俘虏那些状若卧牛或窥兔的石头的。此刻的石头反而比往常要生动得多,不再是僵化的化身,而多了動感,甚至色彩也变得迷人了。我想这石头的归宿竟然如此美妙,一定是前世修炼而得到的善果。
当我从三台山上款款而下时,半晞的朝露,洗却了昨日的风尘,三叶草展现出最新最美的丰姿。如果是仲春时节,三叶草多棱的花梗,高高地擎起半球形的花序,几十朵白里透红、红里发紫的微型喇叭花儿,团团簇拥在一起,远看恰似一朵。微风一吹,清香扑鼻,吸引着三台山上众多的蜜蜂,前来采蜜,乐此不疲。
无独有偶。一年前,与三台山毗邻的办公小院,一改往日的草荒莽野,也播种了密集的三叶草,跟马路对面的山坡上的三叶草遥相呼应。经过园丁的精心培育,它们非常茂盛地生长起来。那些残存的野草,譬如蒲公英、紫丁兰、苦马、青蒿、大黄等,不得不甘拜下风。即便偶有露头,也必遭围剿,从此小院的草坪变得单一而纯粹——春风不二,唯三叶草是尊。
我对三叶草真正的了解,也应该是从办公小院开始的。过去只识其面,不知习性。知其美,却不知所以美。原以为三叶草适合一切有土壤的地方。其实不然。三叶草虽然耐干旱与贫瘠,却喜欢阳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它们往往难以生存,譬如浓密的树阴下,三叶草的种子是很难发芽的;即便发芽了,也是很难成活的;即便成活了,也是很难成长的。我所在的办公小院东边,植有密集的水杉、红叶李和樟树,地面终年难得阳光,撒在下面的三叶草种子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依然寥若晨星,病恹恹的,苍白着脸,没有健康的绿。这真的让我长了见识,原来植物也是阴阳有别的。三叶草开花时节,整个小院馨息弥漫,就连鸟鸣也散发着令人开窍的清香。尤其是清晨,做值日的学生,总是把这里当作世外桃源。应该说,小院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也是锻炼的好地方。它不仅僻静,而且植物多多,空气清新,实乃都市难得一隅。多少年来,我几乎每天早晨都能看见一对退休的夫妇,来到院子里,做体操,拉单杠。最近每每遇之,他们总是说,三叶草真好!是啊,三叶草真好。在没有三叶草之前,小院里草莱蓁蓁,杂乱无序,往往硕鼠纵横天下,野猫肆虐无忌,真是聊斋的很。偶或夜间亲临,灯光黯淡,树枝摇曳,极可怖,令我毛发竖立,心生鬼狐而惧之。
某个清晨,我来得特别早,正值学生清扫路面。他们将扫帚一起扔在地上,个个弯下腰,在三叶草丛中寻寻觅觅。我问临近路面的一位女孩子:“你们在干什么呢——三叶草都被你们踩坏了。”她羞涩地朝我笑,显得拘谨的样子。看我没有离开的意思,便嗫嗫嚅嚅地告诉我,他们在寻找四叶草。我顿时恍然大悟。看来他们是即将离开学校的初三毕业班的学生。他们认为谁找到了四叶草,谁就是幸运儿;找到的四叶草越多,谁在中考中取得的成绩就越好。这之后,每天早晨总有几个孩子在清扫地面之后,弓腰哈背地于三叶草丛里寻寻觅觅……我也不再干涉,并且衷心地祝愿他们心想事成。
五一长假,正好结束了阴雨连绵的天气,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我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写了一个短文之后,便到小院里散步,晒晒太阳。阳光下的三叶草,花香特别浓郁,多棱花梗格外挺拔,小萼如钟,花瓣交叠。低处传来“嗡嗡嗡”的声音,分明是蜜蜂。低头一看,果不其然。我掏出手机,不停地跟踪拍摄。在拍摄过程中,我突然看到一柄四叶草,异常兴奋。然后转移了兴致,像学生一样,成了低头寻觅族。为了寻找更多的四叶草,我绕小院一圈,端详得十分仔细。我一共找到九柄四叶草和一柄五叶草!我把这个好消息通过微信发给女儿。她说,你把那个五叶草采了,晾干,寄给我做书签吧。当我回头再来寻觅时,已然不见它的踪影。好在有照片为证,不然读者朋友会说我诓人呢。
翌日清晨,我再次来到小院。霞光普照,水气氤氲。远远的,我一眼就看到那柄新绿的五叶草——它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没有弯下腰……我要留着着,让更多的孩子们看到它,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苘麻
清溪河畔有一片野生的苘麻。从春天的萌芽到夏天的蓊郁,几乎没有什么过路人迟疑留意,乃至驻足观察,直到叶腋间绽放出五瓣环绕簇拥着黄色花蕊的小黄花,才有人掠它一眼,但天气炎热,也无心逗留。从夏天的繁花到秋天的挂果,这是一个充满迷幻的过程。我在西城漫步时,经常看到一些年青人坐在河畔,偶尔欣赏一番身边的花朵或花朵形状的萼——它分布在尚未成熟的半球形蒴果周围。秋风扫落叶,苘麻也不例外。落叶归根,一柄又一柄,一片又一片,它们在河畔翻滚,偶或被风吹到水面,随波逐流,或在水面上打着旋儿。偶尔有体力不支的蜻蜓停憩在上面,它的翅膀成了风帆,小舟似的叶片就加快了滑翔或漂流。可半球形状的蒴果依然悬挂在草本上,格外令人瞩目,仿佛一幢幢吊脚楼,在秋风里摇晃,里面安居着快乐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便是收缩了的褐色的种子。进入暮秋时节,蒴果渐渐失去水分,仍然保持蓬松的外壳,干枯的花萼均匀地分布,形成半球的切面,那些红褐色的种子,有如铃铛里的弹子,风一吹便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仿佛秋风轻吟,是谓秋声之一种。

到了冬天,这些干枯的蒴果缓缓地开裂,種子便在寒风中摇落,发出咝咝的声响,有点像摇滚曲,又像砂砾炒豆子,反正那声响就是无比的美妙。这种无限缩小版的猪腰子(猪肾)形状的种子,在摇滚中挣破了蒴果的缧绁,杂乱无章地撒落河畔,等到第二年春天,一沾染温暖而上升的气息便萌出更多的苘麻幼苗,绿油油的一片,浑身都是毛绒绒的,有点像构树叶子,植株也有点像嫩小的构树,只不过一个是亚灌木状的草木,一个是地地道道的木本。娇嫩的叶片上吸附了大量的亮晶晶的露珠,熹微初露,这些晶莹剔透的露珠色散出万般美丽的彩虹,有如我小时候玩耍的玻璃瓶底儿里面的七彩霞光;当朝阳斜斜地射过来,气温渐渐地升高,毛绒绒的叶片上就会升腾起紫色的水雾,而且轻轻地摇摆,袅袅不绝,真的像一只只毛绒绒的小鸭踱着稚嫩的步伐,一歪一歪的,拙姿迷人。
其实夏天的苘麻最是旺盛而美丽。一是它们的亚灌木状的形态基本确立,每棵苘麻都能营造一片清凉,为那些小动物们,譬如昆虫、飞蝶、青蛙等,提供了一个纳凉避热的小天地。二是夏天的花朵最妍丽,黄得妖娆,不仅花是黄的,而且蕊也是黄的,如果苘麻密集成片,那黄灿灿的视野一定会迷乱的,甚至产生美妙的幻觉,仿佛进入梦乡。三是夏天苘麻的蒴果也像灯笼花儿一样,尤其是绿色的萼片恰似花瓣,绿的绿,黄的黄,相互映衬着各自的妖娆。只是夏日里白昼溽热不堪,傍晚又多有蚊蚋,不便长时间流连其间。不过,我倒喜欢趁朝露未晞的早晨赶到清溪河畔,一睹苘麻的丰腴之态和壮美之色。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漫步到清溪河的末端,选择有苘麻的地段,席地而坐,眺望远处的秋浦河。我想合流同域的秋浦河身旁也一定密布这种古老的植物,诗意而又实用的植物。当年,我游走秋浦河的时候,一心想着李白酿造的诗意,而没有过多地注目两岸的植被,特别是不起眼的小科植物,更想不到小时候常见的野苘麻,有那么多的实用功能。当然,今天的人们几乎渐渐地淡忘了苘麻的历史功劳。我们都知道,中国种植棉花是宋代以后的事,而且棉花种子是从印度传入中国中原的。据考证家们说,宋代以前的汉字中没有“棉”字,只有“绵”字,这表明棉花是宋代引入中国的。我对这个问题曾经抱有怀疑的态度,可惜我不是做学问的,无法有力地辩驳——如果印度早有棉花,那么唐僧西天取经时,怎么就没有带回这个不亚于经书的“伟大之物”呢?不说了,扯远了。这之前,中国人穿的衣服都是苎麻纤维和蚕丝纺织的,前者多为百姓所用,后者多为富人拥有。再往前推,譬如《诗经》时代,就有许多百姓人家采折苘麻浸泡、漂洗,取得粗纤维,编织衣裳。《诗经》中有“衣锦檾衣”,这“檾”便是苘麻。另外《诗经》中的“东门之池,可以沤苎”中的“苎”,我个人认为,这“苎”不仅仅指的是苎麻,也包括苘麻在内。其中的“沤”字,倒为我们了解古人如何用苎麻和苘麻制作衣裳的。当然,“沤”的技术有高下,生产的布匹理所当然也有精良与粗鄙之分。总的来说,那个时代的衣服多为麻衣,十分简陋而粗糙,精良者多为贵族所拥有。所以才有诗人后来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感慨。
至于苘麻的其它实用功能,我是记忆犹新的。在此说说一二。
除了织布制衣,苘麻还可以通过沤制、漂洗、脱皮、晾晒,得到纤维,即苘麻丝。这些晾晒后的苘麻丝作用可大了。水上人家可以用它裹上他物缝补船体的缝隙,再上泥子,然后油上桐油,防腐,防漏。农家可以用苘麻丝制作绳索,系在箩筐等农具上,承受重力;妇女也可以用它搓绳纳鞋,或系一系腊鱼腊肉什么的。我老家麒麟畈的家庭主妇,常用箬叶剪鞋样儿,用浆糊裹苘麻丝做鞋底板儿。这些实用功能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倒是麻果点花令人记忆犹新,想起来内心还一阵阵地小雀跃。
所谓的麻果,就是苘麻的干蒴果,一般在入冬时节摘取若干,用丝线串在一起,挂在灶房里或廊道顶上,一俟用的时候,便取下一二。所谓的点花,是指在食物(如米粑)上印上红红的花朵儿。这印花的模子就是现成的苘麻干蒴果儿。这种半球形的蒴果切面上就是十几瓣的花萼儿,均匀分布如花瓣,将它沾染上红色儿,往食品上一按,便是一朵小红花儿了,真真切切,清清楚楚,而且凸凹有致,具有立体观感,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无论是乡间腊月,还是农闲之时,简陋的农家生活总是在巧妇手下变着法儿改善一番,平添生活的乐趣与情趣。每逢麻果点花之际,小孩子们突然变得勤快起来,还不等大人将米粑放下,就急吼吼地抢着往上烙印。烙印完了,还将米粑放在手上反复地把玩、欣赏,心里有一种成就感、喜悦感和自豪感。我曾经和妹妹为了抢着点花,将一块洁白的米粑弄掉到地上,沾上了许多灰尘,用水反复冲洗,还是不干不净的。最后还是母亲吃了这块不干不净的花朵漫漶的米粑。
想起这些温馨的往事,我又情不自禁地来到清溪河畔,一边漫步,一边采摘已经成熟的苘麻蒴果,揣在兜里,准备带回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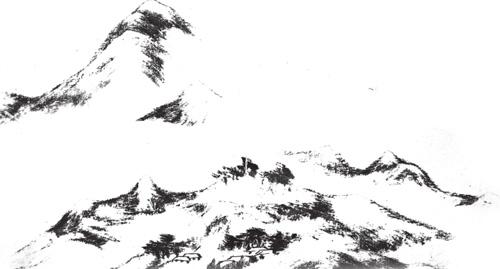
【作者简介】包光潜,男,安徽池州人,作家,诗人。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选刊》《诗林》《诗潮》《上海诗人》《诗词》《散文选刊》等500余家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并有诗歌、散文、小说入选多种文本,多篇散文入选中高考试卷。作品被《人民日报》《散文选刊》《新华文摘》《人民文摘》《读者》《意林》等近百家知名报刊广泛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