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三题
挂 青
究竟是“挂青”,还是叫“挂亲”,虽然我一时说不出原因。但我更认同“挂青”二字。小时每到清明节前日,就见母亲用石磨磨好糯米粉,做成扁扁圆圆的糯米春饼,然后蒸熟。把从火炕上取下的腊肉,洗净之后,再切成二三两左右叫“刀头”的小块,然后一块块放锅里用水煮熟,预备明天“挂青”用。而父亲,就在火塘边用铁制的半月形大人叫“钱子”的东西打“纸钱”,预备清明扫坟用。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小时候除了盼望过年外,也盼望过清明节。不但可以去扫坟,听父亲讲些风水的事情,也可以说去温习一下家史。作为一般老百姓,他们的家史不是写在书上,也不会写在书上,而是写在坟地的墓碑上与活着的人的心里。如果穷的人家连墓碑也没立上的,靠活着的人口传给后代了。如果将自己的家史口传给后代,平时为了活下去不停忙碌奔波,没有时间口传,最恰当的时期莫过于清明了。
过清明节不但有好吃的母亲做的白糯米春饼子吃,还有肉吃。虽然被祖宗“吃”过的食物,留有浓浓的“香火”味,但对于那时还愁吃的年月,无疑是美好的盛宴。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按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我是必须跟父亲去扫坟的。
扫坟的前一天晚上,父母就叫我们早早地睡,一到清明那天就得大清早起来,父亲手提着装满蒸熟的还冒着热气的白糯米春饼与“刀头”及鞭炮、纸钱、香火的篮子。腰上系着装着柴刀的木刀盒,手里拿着割坟上杂草的镰刀。我姐姐也拿了镰刀,我与妹妹什么也不拿,像欢快的麻雀,望着四处山岚起的白雾,听父亲一下说我太公的事,一下说我祖母的事,一下说我奶奶与爷爷的事。最有意思的是说我祖母,一辈子不知生了多少儿女,最后活下来的就只有我爷爷。我爷爷是怎么活下来的,连我父亲也觉得奇怪。他小时听我爷爷说,我爷爷常被祖母放在火塘的炕上或塞进大抽屉里,就去做自己的事去了。我父亲说我祖母埋的地方风水好。他说他能讲会说,能文能武。他说我长得俊,也能说会道也是祖母把我送到人间来的。并说风水宝地的坟自己会长,像植物一样,一年又一年地会长。风水不好的坟,连坟上的草也长得不茂盛。作为风水先生的父亲,总会说这些趣事。有时还说到村里某某村民聪明,是因为他家埋有“猛虎跳界”“仙鹅下水”的风水地,或是说人家家里的某某先人埋有什么“龙口”“虎口”“蛇口”或葬有什么活龙地。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中,我们也开始观察起坟边的风景来。
一到坟地,父亲与姐姐开始用镰刀扫倒坟上的杂草。父亲像剃头匠,一下就将如人头的坟地剃了个又干又净的光头,然后在坟头头顶添几根“挂青”棍。有的坟头的“挂青”棍已经在清明长出叶子来了。父亲边插“挂青”棍边说这是风水好的表现,风水不好的坟地,光插一根棍子是长不出叶来的。然后父亲指着坟前的风水跟我大讲一通,给我进行风水学的启蒙。
在父亲给我“风水”启蒙的那一刻,我望着坟前的风景,确实是让人吃惊的。有的坟前那山河的气势,真可以说“气吞山河”,那雄壮之气自不能言说。
插完“挂青”棍,父亲就让我在坟头“挂青”棍上挂上他用“草纸”打的散钱。因为“挂青”棍朝天的刚能夹进纸钱一头,已被父亲用刀“破”开了一点小缝。我们那里大人打的纸钱是一版一版的。一张书本大的“纸钱”上是又独立又相连的象征性的圆形纸铜板。这个任务基本上是我去完成,因为女的是不能上坟头的。尤其是妇女,女孩倒还可以。一般情况是不允许的,一说是对祖宗的不敬,一说是女人有“玉”气,怕“玉”坏了坟上的风水,那样会对活着的子孙带来霉运。所以姐姐妹妹只在坟周围用成版的纸钱挂在坟的东西南北与坟前“中”的五方上,叫挂“五方”,然后在坟前先插上点燃的三根香,再放上一个“刀头”肉,再摆上一些白糯米春饼,摆上三个小瓷酒杯,用酒将三个杯子里象征性地倒点酒,再在“剃开”的称为“散钱”的堆上放上几个“忠敬”。“忠敬”也是“纸钱”的一种,是叠折成四方形的“纸钱”。我们那的“纸钱”分两种,一种叫“忠敬”,一种叫“散钱”,“散钱”就是书本那么大的,不用叠折的,而是书本那样大的草纸一层层叠着打出来的。
待把这一些摆上,把“纸钱”点上,放完鞭炮,对坟头三拱手,再跪拜下去起来,口中念念有词,大意是要埋在地下的祖宗与管風水的龙神保佑我们一家人,做生意的发财,当官的当官,读书的金榜题名,然后就叫我给“坟”里祖宗与风水龙神下跪。父亲拿着“卦”,一种两片像牛角从中锯开合在一起拇指大的“卦”。扔地上后,一片截面朝天,一片截面朝地的叫“胜卦”。截面都朝地的叫“阴卦”。截面都朝天的叫“阳卦”。父亲对坟说:“保佑唐国明今年读书抢头名,打一个‘胜卦。”“卦”从父亲手里一扔下去,如果是“阳卦”,父亲就说:“噢,祖宗已实领实受,再来一个‘胜卦,保佑唐国明将来功成名就,名扬天下。”说完,再拾起“卦”合好,又朝地上丢下去,如果是个“阳卦”,父亲说:“看来今年家里六畜兴旺,财气旺,再来个‘胜卦,串连三‘卦。”反正父亲不达目的就不罢休,一直到“卦”打好。如果老打不好,父亲就会朝燃着的“纸钱”堆上添“忠敬”,口中说:“其他的各路神仙与我师傅,不要来‘造卦,不要作怪捣乱,我把这些‘忠敬交于你们,你们要保佑唐国明健康成才,健康成长。”直到打好了“胜卦”,我快要膝盖跪麻了,才让我起来。我当时似乎被父亲拉到另外一种神秘里。现在想来,当时父亲好像为了我与神在讨价还价一般。
我跪完后,然后是姐姐妹妹过来跪拜坟头。她们跪拜时过程就简单多了,父亲早已把“卦”卷进裤兜里。姐姐妹妹跪完起来,父亲就把杯子里的酒洒在坟头地里,见纸灰没有了火星,才要我们吃糯米春饼,有时里面夹有蓍草。把“刀头”放在篮子的另一头,因为祭下一垛坟时,要用另外的,不能用现在用过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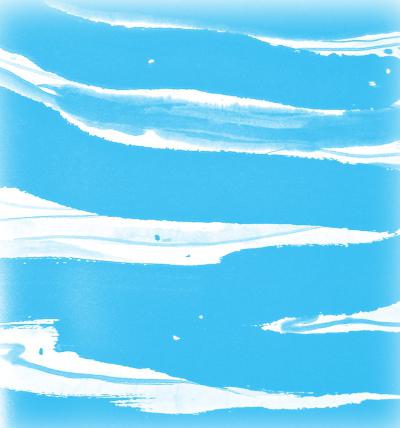
在扫坟的路上,如果看到荒坟。我们好奇地问父亲那坟为什么没人扫了。父亲就说他们已无后人,或是后人已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地到他乡去了,或是说在以前疫病流行“倒家亡”了。父亲一说这些我就奇怪。我想除了我们这些人呆在这山里,难道还有人呆在更远的山里。如今想起来,也许我故乡的历史就埋在那些坟里,那些坟也许就埋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再也无人挖掘,再也无人口传。每遇到离我家祖坟不远的一些荒坟,父亲也善意地去扫一扫,“挂上青”,摆上祭礼。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去管啊,父亲说:“那是块风水宝地。”他接着就跟我们说起好多年前因为某某挂了荒坟的“青”,那埋在坟里的人托梦给某某,帮某某中了状元的事。开始,父亲说这事我有点怀疑,但有一年我们在给祖母扫坟时,从墓碑下爬出一条蛇,父亲没有打这条朝我们伸出舌头,似在微笑的蛇,而是用棍子挑着它放在一旁。那条蛇在那棍子上就那么挂着,吐着舌头看着我们微笑,直到我们祭扫完了,它也没爬走。在父亲又把它用棍子挑到那墓碑下才没看见它了。父亲说它钻到坟里去了,说它是龙神与祖母的化身。然后又跟我们说:“以后你们要勤俭持家,子孙满堂,那样百年归后,坟前才不至于那么冷清,坟前一冷清,旁人就会说这家人家门不幸,已经绝后无人的狠毒之话的。”
从一大清早“挂青”挂到中午的时候,就回家吃母亲在家准备好的午饭,父亲就领我去二十里外“唐家”集聚之地金塔村去“挂众青”,“挂众青”就是说去扫自从这一脉开始到如今的老祖宗们的坟墓。“挂众青”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脉唐姓人的一次从四面八方来的聚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家族史口语心传的普及。我就是小时在跟父亲“挂众青”的路上得知了我最初的老祖宗是从广西全州来的,而广西全州的老祖宗是从江西,而推至更远,我的老祖宗发源地是如今的山西,唐姓这个宗族起源于西周山西的唐国。
对于我来说,清明尤其说是祭祖扫坟,不如说是一次又一次对自己家族史的温习,一次又一次对自己从哪里来的追问,更是一次又一次“孝”与“家族”灵魂对自身潜移默化的一次悄无声息地融合。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唯一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古国来说,通过清明扫坟的过程,你就可窥见许多。
四 季
山野里随着鸟的叫声什么都探出头来看热闹时,埋在土里的春笋就在春雨里长了出来,蘑菇遍山野全是。我与姐姐妹妹提着篮子大清早迎着细雨去采回来,在兼厨房烟火的二楼木板上摊开,或者直接一篮一篮地挂在火炕上,待干去了水分,最后成为最好的下饭菜。而父亲这个闲了一段时间的狮子,终于闲不住,去山林里下套,下陷阱,下夹子弄野山羊与野猪去了。有时与几个堂伯背着火枪去打来竹林里咬春笋吃的野猪。
每次村里人打野猪回来,几乎村里每家都会分到一块野猪肉。一吃野猪肉的时候,父亲就跟我们说他过去打猎的辉煌。说他打猎的师傅还是我母亲的三姨父。去山里打野猪下套,下铁夹子还要懂得“下梅山”,“ 下梅山”是一种巫术,说是猎人发动什么阴兵阴将搜山,将野猪、野山羊往那夹子与陷阱下套处赶。如果有野猪中了套,被倒挂在树上,如果踏了陷阱,就会掉坑里再也爬不出来。而夹子只要夹住它们的腿脚或嘴巴,它们也难逃命,即使逃脱了,也会留下足迹,父亲就会带人理着那些足迹在一天两天内找到它们。更可怕的是放“炮筒”,“炮筒”就是把一个塞满炸药的竹筒外涂满了野猪们喜欢吃的油,它们闻着那味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口咬下去,炸药一响,定会把它们炸得稀烂。有一年父亲放“炮筒”炸到了一个两百多斤重的“聋猪”,父亲是一个人从山林里扛到村里背后的山上,确实扛不动了,才喊母亲用竹杠去抬回来的。
山里人苦,为了点好吃的,总是使出这些在现在看来极为残忍的手段。一到获得猎物,父亲就会与人庆“梅山”,也就是向神举行一个仪式。一般是头戴着斗笠,身穿着棕皮做的避雨的“蓑衣”,对着摆着一整只生野猪或野山羊与香火通明的祭桌,边敲着鼓,一个喊着,一个回着,大多是用这样不堪入耳的话来表示喜悦。待兽骨多了,父亲就会“熬膏”。“熬膏”就是用所有的野兽骨头放火上的锅里煮,直煮到骨头全成了“膏状”,再被装进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竹筒里。冷却后,就成了胶质状,颜色是透青色的,吃时破开竹筒,吃后对身体很补。我记得我二三岁时,父亲常给我用刀切“膏”吃。
待春分清明谷雨过后,村里所有的梯田都积了水,如一块块挂在天边的明镜时,父亲就开始拿出去年夏天从山里砍回的绞去了皮、挂在火炕上的“犁弯藤”。父亲取下后开始套犁牵牛下田犁田耕种了。待春种的秧苗一长出,正好能移插的时候,父母就开始担“芋”,“芋”就是牛栏猪栏去年春种后一年积下的被铁耙拖出来堆在猪栏牛栏外的有機肥料。一担一担地用“芋筛”挑到田里。过到端午节,去深山老林溪边采回箭杆竹上发出的粽叶,包着白糯米,煮出清香的粽子吃后,插完的秧苗就要开始“踩青”了。“踩青”就是去山里采摘树木上刚长出的嫩树肉枝,一把把捆好,踩到田中秧苗与秧苗的空隙里。踩完“青”,农历“六月六”来之前的梅雨季节,我们就开始去我们以前存在过的那片深林里摘早熟的杨梅。吃后,就跟外婆家来的小姨去外婆家过“半年节”。在外婆那里叫“小春节”,是专门接女儿女婿与外甥女外甥仔去团聚很隆重的日子。
从外婆家回来后,就开始跟父母去竹林里砍竹料,破竹料了。这竹料就是刚由竹笋长高开枝,脱去笋衣,刚从竹枝上长出叶,主干刚变青时的嫩竹。在这时砍倒竹林中过密过稠的,五来尺的一节节砍断,破成一块一块的,晒到青皮干成金黄色时就捆成捆,在两捆之间穿一根竹杠,朝天的一段用一篾片连接好,再用肩挑到造纸厂的“料站”去换钱。
那几个月,只有过农历七月十五,我们叫过“七月半”,父亲母亲才在家休息。父亲打了不少“忠敬”与“纸钱”,然后将“忠敬”两个一封的用一张四方的草纸包起来,然后再用毛笔写上“敬贺某某老大人或某某老孺人多少封。孝男孝媳某某,孝子孝孙某某,孝女某某共同供奉”这些字,再到七月十五那日黄昏在路边烧了,说是让那些回家里来过“七月半”的老人好带着这些钱去扬州看戏。开始三天,就是农历七月十三到七月十五日这三天,要给祖宗们“下饭”。“下饭”就是一家人在吃饭前,父亲要在家里神龛“天地门前”该插香的插香,该烧纸钱的要烧纸钱。一般是堂屋神龛前纸钱三堆,神龛上层中间香碗插三根,两边左右一个香碗各插一根香,下层土地神龛里一支香,堂屋门前的“天地门前”纸钱一堆,插香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