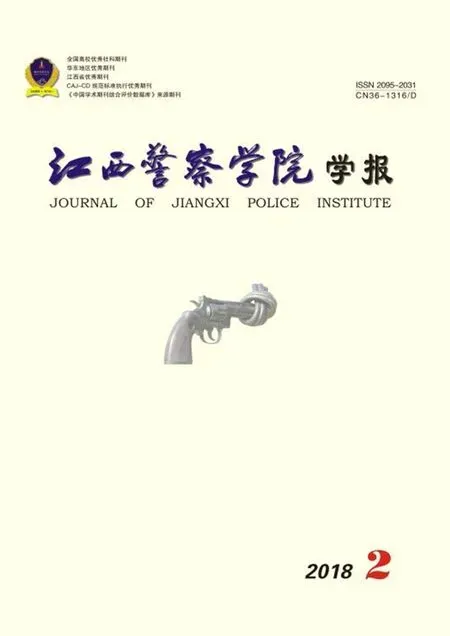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法律问题略论
王晓东
(山东警察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006 年 6 月,《刑法修正案(六)》对原《刑法》条文的第161条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但该条文修改以来的十余年,学术界对该罪的研究却寥寥无几,通过中国知网,仅能搜索到两篇相关学术论文;司法实践中使用该罪名的案例也是凤毛麟角,通过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也仅有两起案件以该罪名定罪量刑。理论上研究的热情不高、实践中利用率过低,使刑法规定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陷入囧境且面临着条文失灵的危险。而实际上,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一个适用范围比较广泛的罪名,但由于人们的惯性思维和对修订后的条文中某些法律术语的不解或者误解,致使该罪名成了“僵尸”罪名。
一、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刑法规定
经《刑法修正案(六)》修改后的《刑法》第161条规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修改前的《刑法》第161条的规定是,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的解释,修改前的罪名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而修改后的罪名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通过修改前后的刑法条文内容比对和“两高”确定的罪名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刑法的修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了信息披露的范围,这是本条修改的最重要内容。新条文增加了“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的构罪规定。通过这一修改,信息披露的范围从单一的财务会计报告扩大到了“重要信息”。而“重要信息”不仅包括财务会计报告,还包括公司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应当披露的信息范围和内容的规定,还应包括依据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事项。二是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将犯罪主体从单一的公司扩展到一切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和企业。这里所说的公司、企业,既包括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包括股票上市交易的公司和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下同)、债券上市交易的企业以及银行和基金从业人员,还包括其他有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和企业。三是增加了 “有其他严重情节”也构成犯罪的规定,将纯粹的结果犯修改为情节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所谓“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是指多次(三次以上)进行虚假的信息披露,隐瞒多项(三项以上)依法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或者因不按规定披露信息而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后又违反规定,以及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由此可见,《刑法》第161条修改后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也更具有操作性,但由于受条文术语、条文语法关系以及受修改前条文内容的影响,该罪名一直未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应有重视,致使理论和实践中鲜有研究和使用该条文的论著和案例,也使得一些本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未得到应有的处理。
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适用范围探析
受惯性思维的影响,很多人有以下三点错误认识:一是认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适用主体与修改前刑法规定的犯罪主体差不多,是有义务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公司和企业,刑法的修改只不过是扩大了提供主体和提供对象的范围,即将提供主体从公司扩大到公司、企业,将提供对象从财务会计报告扩大到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在内的所有重要信息;二是认为“重大信息”应仅限于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能够影响投资的信息,[1]与投资无关的信息不在其中;三是认为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的相对方和其他重要信息披露的相对方相同,均是股东和社会公众。
(一)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适用主体范围探析
如前所述,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适用主体较之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适用主体范围明显扩大,即不仅包括有义务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公司,还包括有义务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非公司企业,还包括有义务披露其他重要信息的公司、企业。换句话说,一切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都有可能成为本罪的主体,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个人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公司的范围,理论和实践中均无异议,即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对于企业的范围,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而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歧义。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企业,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被排除在单位犯罪之外。因本罪是纯单位犯罪,如依该解释,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对依法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就不能依本条规定定罪量刑了,而出现这种法律状况显然不合刑法的本意。如合伙企业法就规定,清算人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报送的清算报告不得隐瞒重要事实或有重大遗漏;如果提供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清算报告,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①见《合伙企业法》第 90、100、105 条。。合伙企业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所适用罪名不言而喻就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笔者认为,刑法中“企业”的范围既应包括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也应包括依法成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2]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不恰当地缩小了单位的范围,与法律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矛盾。除此之外,该司法解释还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事业单位”也被排斥在单位犯罪之外,而实际上,在我国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和事业单位②根据《公司法》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公司和事业单位均具备法人资格。。
哪些公司、企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的义务,关键是对“依法”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是法,无论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通常的理解是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订的法律和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才能称为“法”。也就是说,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设定的信息披露义务才是刑法中的义务,行政规章、地方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未经立法程序出台的国务院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等设定的义务不属于本条规定的刑法义务。
(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重要信息”范围探析
重要信息的范围是否限于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能够影响投资的信息?文献中未见有人专门进行论证。但从公开发表的仅有的两篇论文①两篇论文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略探》(杨俊发表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和《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可能性失灵》(易明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和已公开的两份判决书②两份判决书是2008年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的黄先锋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和2017年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的余蒂妮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看,所涉及的重要信息均为投资性信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规定的重要信息也多是投资性信息。
笔者认为,重要信息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投资性信息,其他一些非投资性信息也应包括在内,只要这些信息足够重要,能够严重影响 “股东和其他人利益”即可,如停电信息。笔者以“医院停电引发医疗事故”为内容,通过360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找到相关结果约43万条③https://www.so.com/s?ie=utf-8&src=hao_360so_b&shb=1&hsid=7e9191214c568f85&q=医院停电引发医疗事故。。诸多因医院停电引发的医疗事故,一般情况下是由医院承担民事责任了事,未见因造成医疗事故而追究未及时披露停电信息的供电人刑事责任的案例。笔者主张,若因供电人未事先告知停电信息,造成医院等用电人重大损失的,应当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供电人的刑事责任。笔者的依据是合同法和电力监管条例:《合同法》第180条规定,供电人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临时检修、依法限电或者用电人违法用电等原因,需要中断供电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电人;《电力监管条例》第34条规定,电力企业、电力调度交易机构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文件、资料以及未按照国家有关电力监管规章、规则的规定披露有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在上述案件中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供电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充分的。由此亦可推知,刑法中规定的“重要信息”的范围不限于类似于财务会计报告这样的投资性信息。
(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信息披露的相对方的范围探析
信息披露的相对方一般是股东和社会公众,如《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保险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其经营管理相关信息的行为,等等。但从刑法条文的表述分析,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相对方是股东和社会公众,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的相对方却并不限于股东和社会公众。修订后的《刑法》第161条规定,“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可见刑法未要求“其他重要信息”的披露对象必须是股东和社会公众;并且该条接续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可构成犯罪,而不是规定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社会公众利益”构成犯罪。一些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信息披露相对方就是特定的人或者特定群体:如《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和 《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信息;《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规定,从事供电业务的企业应当向电力用户披露停电、限电和事故抢修处理情况信息,等等。根据以上规定,企业登记机关、被特许人、电力用户等并不是股东,也不是社会公众,但却是信息披露的相对方。
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几个法律术语含义探析
修订后的 《刑法》的第161条中的一些法律术语,是造成该条文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歧义的重要原因。
(一)披露、提供的含义探析
该条中使用了披露和提供两个近义词,提供的对象是财务会计报告,披露的对象是其他重要信息。披露是发表、公开之意,从罪名和第161条上下文的语境看,披露应包括“提供”和其他披露方式。但在公司法、企业法等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的法律、法规、规章之中却未使用“提供”财务会计报告这一术语。《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将年度报告置放在商业银行的主要营业场所,并按银监会相关规定及时登载于互联网网络。从以上条文的语意上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上述规范性文件中的送交、置备、公告、置放、登载等都是刑法中“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形式。而刑法规定的“其他重要信息”的披露可以不同于上述形式,如《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第11条就规定了多种信息披露的其他方式:电力企业的门户网站及其子网站,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信息发布会,简报、公告,以及便于及时披露信息的其他方式。
由此可见,披露的概念涵盖了送交、置备、公告、置放、登载等“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各种形式,也涵盖了其他重要信息的各种披露方式。
(二)重要信息的含义探析
重要信息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重要信息。财务会计报告是重要信息的主要形式,一般是指年度财务报告。但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披露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只需提供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其他公司只需提供年度报告。如果公司、企业在法律法规的要求之外,自行提供季度报告、月度报告,则不应视为依法应当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也不应视为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即使其中有虚假或者隐瞒的成分,也不应依本条定罪。
需要注意的是,财务会计报告是包含众多重要信息的文件,财务会计报告中应当包括哪些内容由《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来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体现的内容未体现或者存在虚假体现的情况方能构成犯罪,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明确要求的内容,如企业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入,[3]无论其如何重要,也无论其有无隐瞒和虚假,根据罪刑法定原则,都不宜以本罪处理。
其他重要信息是除了上述财务会计报告之外,可能严重影响他人利益的信息,包括《证券法》第67条规定的“重大事件”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如《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规定了电力企业和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应当披露的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其他重要信息也应以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应的规定为准,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要求披露的信息如企业社会责任信息①2010年深交所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1号——年度报告披露相关事宜》要求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无论对于企业还是社会均越来越重要,根据201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2013年上交所共有391家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等不属于刑法规定的“重要信息”范畴。
由此可见,刑法条文中的“重要信息”是包括了财务会计报告在内的能够影响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应予披露的各种信息事项。
(三)法、规定的含义探析
根据刑法规定,只有那些“依法”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不按照“规定”披露重要信息,才可能构成犯罪。这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有义务披露重要信息的公司、企业的义务来自于法的规定,法的规定之外的义务不是本罪所说的义务。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可能依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提供,也可能依照企业章程的规定提供,还可能依有关部门、机构的要求提供。只有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应当提供,却提供虚假的、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才可能构成该罪;依据企业章程规定或者依据有关部门、机构要求提供,即使提供的财会报告存在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况,也不宜以本罪定性。
二是有义务披露重要信息的公司、企业要按照“规定”披露。纵观全部刑法条文,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表述有的是“违反法律规定”,如《刑法》第297条规定的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有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如第405条规定的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有的是“违反国家规定”,如第186条规定的违法发放贷款罪;有的是“违反规定”,如本罪。
根据《立法法》,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即国务院通过其立法程序制定,由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刑法》第96条,国家规定除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外,还包括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201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 “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应当由国务院决定,通常以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制发文件的形式加以规定。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制发的文件,符合以下条件的,亦应视为刑法中的“国家规定”:一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同相关行政法规不相抵触;二是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或者经国务院批准;三是在国务院公报上公开发布。而对于违反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行为,不得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
至于刑法中“规定”的范围,则无明确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规定”应当比“国家规定”的范围宽,但又不能过宽,如若将县乡级政府的规定、上交所、深交所甚至公司企业内部的规定等纳入刑法“规定”的范围显然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要求。笔者主张,刑法中“规定”的范围应当是立法法范围内的规范性文件,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法之外的规定不在刑法中的“规定”范围之中。[4]
四、结论
在信息社会,个人和企业都是通过对信息的解读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或者作出某种决策。所获得的信息是否准确、充分事关个人和企业的切身利益甚至身家性命,可见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当今社会,公司、企业的信息披露对于股东、社会公众以及其他人的利益尤为重要。但也并不是说公司、企业要做“透明人”,所有的信息都要对外披露。只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披露的信息才须披露,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披露的信息当然应被视为“重要信息”。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虽然“脱胎于”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但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我们不能随顺惯性思维的影响,仍然囿于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的适用范围。只要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而公司、企业却未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披露,致使其他人利益出现严重损失或有存在其他严重情节,即可以该罪定罪处罚。
此外,笔者认为此罪不受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重视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该罪属于轻罪,该罪的最高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加上二十万元的罚金。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存在着重视重罪轻视甚至忽视轻罪的问题。实践中轻罪大量存在却未依法受到应有的处理,这既有违刑法的尊严,又可能使触犯轻罪之人因侥幸心理的膨胀而一步步滑向重罪的边缘。因此,在法治社会,我们应当改变过去只重视重罪忽视轻罪的法律思维。重视轻罪既是严密法网的需要,也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同时符合我国刑法从“厉(严厉)而不严(严密)”向“严而不厉”发展的大趋势。[5]
参考文献:
[1]杨俊.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略探[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2]王晓东.论刑法中的“单位”[J].山东社会科学,2015,(9).
[3]薛云奎,王志台.R&D的重要性及其信息披露方式的改进[J].会计研究,2001,(3).
[4]王晓东,许瑞忠.经济犯罪侦查新论[M].济南:黄河出版社,2016:160.
[5]储槐植.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