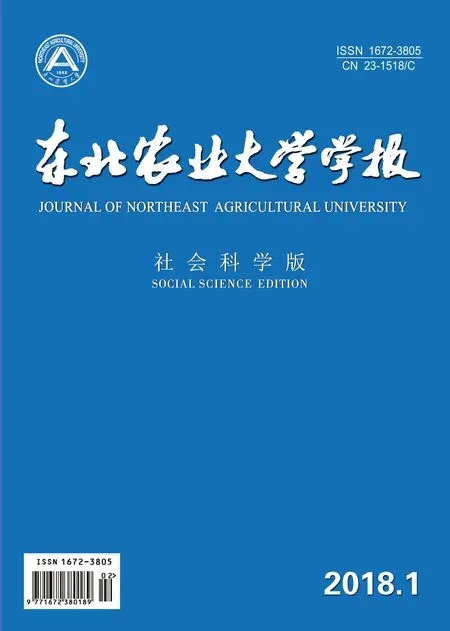消解自然主义谬误
——基于进化伦理学的解释
赵斌成诚
(山西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引言
休谟的断头台(Hume’s Guillotine)即“是(is)”与“应当(ought)”问题,已被证实迄今为止所有伦理学家遭遇到的最棘手的绊脚石之一[1]。休谟对“是”与“应当”的思考引发近代哲学重新审视伦理学。该问题出现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密不可分,在休谟所处时代背景下,其伦理思考反对宗教神学伦理思想,强调道德逻辑基础在于关于人的事实,无疑影响后世道德哲学认识,也成为现代哲学最重要命题之一。根本出发点是为阐明其道德价值观,强调情感在道德活动中的作用,以及理性在道德问题上的无能[2]。休谟思想可简单概述为:任何“是”均无法包含“应当”,即任何道德论断均无法以逻辑方法从纯粹事实性论断中推导而出。休谟斩断道德话语与事实话语间联系,这道鸿沟便成为每个试图开展道德哲学研究的学者难以跨越的阻碍。
摩尔(G.E.Moore)拓展休谟的理论,和休谟一样,摩尔的论证也反对从道德中性自然事实中推导出道德价值判断,提出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作为批判传统伦理学的主要概念。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分别论证了自然主义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他认为,两者定义的善不同。他总结自然主义之“自然”并认为:“我正在用而且已经用‘自然’表示作为各自然学科的研究对象,也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东西。可以说,它包括一切或者曾经存在,或者现正存在,或者将会存在一定时间的东西。”[3]摩尔所言的“自然”即一切自然存在的客体,而自然主义谈论的善即自然客体或自然客体集团的某一性质的替代,这似乎表明善不能与其他任何事物本身相一致。由此,摩尔推论道德自然主义不正确。
休谟的“是”与“应当”问题与摩尔提出的自然主义谬误紧密相关,从而引起整个二十世纪不休的伦理学讨论,自然主义谬误也成为继“是”与“应当”问题后区分事实与价值的新基石。当然,自然主义从未消失,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分析哲学发展影响下,自然主义关于心灵、知识、逻辑的理论被哲学家不断捍卫。但在伦理学中自然主义仍受到怀疑,即使在摩尔提出谬论百年后的今天,道德哲学论著仍需解释为什么它不可能为真。如麦克道尔(J.McDowell)做出的区分: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之前,自然是未经祛魅的自然,自然被认为包含于理由逻辑空间之中,因其自身意义而存在;自然科学兴起后,自然被祛魅,在自然的领域属于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空间,遵循的是因果律;与之相对应的是理由逻辑空间[4]。首先,自然逻辑空间包含对自然客体、因果律、经验以及对自然的描述;而知识与概念则属于理由逻辑空间。因此,“是”与“应当”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同属;其次,道德不等同于知识,不能完全按知识来源将其划分在理由逻辑空间中。道德是一个复杂命题,如何论证其来源,也成为避开自然主义谬误的必经之路。
一、进化与伦理融合尝试
从达尔文演化论中延伸而来的道德进化思想面对摩尔提出的自然主义谬误,从自然事实出发得出结论,尝试将生物学理论融入伦理学理论,是一条推动道德从形而上学向实证科学转化的进路。从演化论得到明确表述以来,各界学者即致力于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寻求更多支持演化论的证据,其中自然涉及道德与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哲学问题。而“是”与“应当”问题与自然主义谬误的责难则成为道德进化领域最棘手难题,作为一种假说性质的推测性描述,道德进化假说很难摆脱自然主义谬误。“进化的过程给我们指出了我们正在发展的方向,因此,就给我们指出了我们应该发展的方向。”[3]面对如此指责,进化论者一直努力通过哲学论证摆脱困境,尤其在进化伦理学领域,如何解释或避免自然主义谬误成为其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
十九世纪晚期,在比较“人与低等动物”精神力量的大环境下,达尔文发表关于道德进化解释,他认为:“无论何种动物,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本能,包括亲缘情感,与此同时,只要智力能力有了足够的发展,或接近于足够的发展,就将不可避免地获得一种道德感或良心,人,就是这样。”[5]虽然在关于进化过程的后续见解中,他的一些想法有明显错误,但其基本方法和思路为解释道德复杂性提供了实用框架。
达尔文试图基于包括人类在内生命进化的连续性,推论道德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无疑对过去所有用于规范行为而产生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基础造成冲击。自达尔文起,进化与伦理开始紧密联系,诸多学者将视线聚焦于此,逐渐形成达尔文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斯宾塞(Spencer)、克鲁鲍特金(Kropotkin)等。这一时期进化伦理思想普遍支持道德是自然选择或生物进化产物观点,同时在达尔文道德思考基础上有新发展。如赫胥黎认为仅有同情心不足以说明人类道德进化,道德在低等生命时期或纯粹动物世界不存在,只有人类进入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后,对群居生活有明示或默示的共同协议,且一致同意保护遵守协议者,处罚违抗共同协定者,道德才逐渐进化出来。
当时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体系尚处在缓慢接受时期,但达尔文主义关于人禽之辩的进化伦理思想已被推至风口浪尖,神创论面临坍塌,西方传统伦理基石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人们能够接受动物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但此观点转移到人类自身时便很快引起争议。最致命的反击来自摩尔,摩尔认为道德源自自然事实的理论体系犯了“自然主义谬误”错误。在摩尔而言,将自然属性定义为“好”不可行,不可分析、难以定义。面对多方质疑,进化理论体系欠缺证据使达尔文主义者无力回击,集体失声,加之因同一时代自然选择理论被极权主义利用而饱受诟病,进化伦理思想随之进入一个近乎停摆的时期。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为标志,进化伦理研究开始回温。以爱德华·威尔逊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为代表的新达尔文主义者建立社会生物学这一新学说,将进化理论与生物学理论广泛应用于文化、道德等领域研究,并提出“基因选择”学说,从基因尺度看待文化和道德进化。尽管社会生物学家声称:“科学家和人类学家理应一起思考将伦理暂时从哲学家之手转移过来的可能性并将其生物化。”[6]但社会生物学的这种综合依然未能完全摆脱自然主义谬误带来的阻碍,该时期学派内对待谬误开始出现不同态度,一些人认为这里不存在谬误,价值观可从适当诱导环境下的事实中获得;另外一些人认为,尽管这是一个谬误,但进化伦理观并不必然会犯这种错误;还有一些人对产生事实/价值区分的思想点提出挑战[7]。社会生物学的出现使进化伦理学再次复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学派内分歧增多,尤其是面对谬误的态度直接导致后来进化伦理学学派内的分支走向。
二、进化伦理学对谬误的解释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为进化伦理学总结了三条进路,分别是描述性进化伦理学(Descriptive Evolutionary Ethics)、规范性进化伦理学(Prescriptive Evolutionary Ethics)与进化元伦理学(Evolutionary Metaethics)①William Fitz Patrick.Moralit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DB/OL].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orality-biology/,2008.。三条进路对自然主义谬误的解释各不相同,实际上对待自然主义谬误的态度差异正是进化伦理学学派分支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一)描述性进化伦理学解释
描述性进化伦理学使用进化理论体系科学解释人类某些能力、倾向或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如布雷克斯(Dennis L.Krebs)认为道德意识植根于进化机制,特别用来解决道德问题和早期人类遗传基因的设计机制,在道德方面处理他们的行为,赋予其道德观念,在生存和繁殖斗争中,比早期未继承此基因的人类表现得更好。以克雷布斯理解,在早期人类祖先生存环境中,道德情感机制是被选择的,这些机制诱导早期人类以增加自身整体适应度的方式行事。责任意识源于诱发人们以亲社会方式行为的情感和动机状态;权力意识源于社会规范定义中隐含的知觉:成员如何被允许培养其福利,他们应为组织做哪些贡献;良心起源于对他人承受的社会裁决作出的情感反应。如感恩和愤怒源于对他人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作出的情感反应。正义则起源于合作交流过程中用于对抗欺骗行为的手段。当早期人类获得反思道德直觉的能力时,道德的抽象概念开始出现。
如上述总结,克雷布斯很好代表了描述性进化伦理学研究方式,即在不同层次提供经验意义上的道德进化解释,面对自然主义谬误的指责他们做出解释:“自然主义谬误试图从‘是’的事实陈述得出‘应当’。然而,我认为科学(是)和伦理学(应当)有两种不同方式。首先,人们的‘应当’判断来源于他们头脑中进化出来的心理机制——也就是他们的心理。因此,理解这些机制如何设计,以及其如何运作,为理解判断“应当”的来源提供了基础。第二,‘应当’意味着‘是’,将道德标准设置如此之高并无意义,没有人能够满足它们,正如我希望我去证明的那样,科学可以用来评估人们的道德能力。”[8]
在克雷布斯看来,科学与伦理之间存在区别,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和布雷克斯一样,描述性进化伦理学要做的并非像传统伦理学一样提出命令或设定规范,他们想通过进化理论得出“实在的道德”或“功能性的道德”。可以设想,如道德进化是早期人类通过处理对其健康行为有利并最终实现自适应目标的原因,在一定功能标准下,道德义务将仅延长与其健康相关内容。显然,大多数人感觉相对于帮助陌生人和外群体成员,他们有更强的道德义务帮助亲戚、朋友与群体内成员。然而,在派生功能标准下的道德(“应该”),可承担自身生活,独立于当前“是”的约束。如道德作用是使人们能以促进自身长期福利的方式从而促进他人福利,在祖先环境中即无需受进化心理机制影响而实现这一职能。
无需费心评估任何形式的描述性进化伦理学,因其显示的必然是简单先验证明。如按传统伦理学提出命令、设定规范模式展开批判,所有版本的描述性进化伦理学必然均是错的,它们均不可避免地走上自然主义谬误道路。但显而易见,构成行为的基础尺度和规范并非不可变动地确定下来,而是处于持续变化中,并不存在对所有时代、所有个人、所有状况均无条件适用的道德规范伦理。就此而言,进化与伦理并无绝对鸿沟,因此自然主义谬误不足以至少不能完全成为导致此学科覆灭的理由。
(二)规范性进化伦理学解释
规范性进化伦理学诉诸进化论证明或破坏某些规范性道德的要求或理论,此进路的学者使用内在逻辑论证方式分析伦理学中“应该”的理由,向传统规范伦理学提出挑战。詹姆斯·雷切尔斯(James Rachels)是此领域代表学者,他于《道德的理由》一书中分别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伦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康德理论、社会契约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德行伦理学等伦理学理论提出的理由,进而提出自已的伦理思想。
雷切尔斯认为“应当”概念起源可在事实中找到。他所谓的事实即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所具有的理性:“与其他创造物相比,人类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理智能力,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而进化。”[9]自达尔文以来,关于人类本质最丰富的信息来源之一即进化论。人类心理中最普遍特征,如态度、性格和认知能力均可视为自然选择产物。这有助于理解此类心理特征如何起作用,以及如何产生此类心理特征,简言之,我们拥有使祖先赢得生存和繁殖竞争的心理特征。当进化伦理学家从自然选择等生物学条件说明人类道德选择和行为时,以理性主义和宗教禁欲主义伦理学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学假定的构成人类道德基础的“意志自由”便受到最大冲击。
规范性进化伦理学直面自然主义谬误指责,试图通过逻辑论证方式予以反击。雷切尔斯举例论证了一个伦理推理:
如果我们不先给孩子做麻醉手术,她会非常痛苦。
麻醉剂对她没有不良影响,只会使她失去知觉并且对疼痛不敏感。
因此,应该采取麻醉。
在上述推理中,通过推理思考,进而理解此推理,即知道应如何使用麻醉剂。但此推理不涉及认知能力、情绪,以及所在社会人的信仰……也无其他方面信息可质疑应使用麻醉剂的结论。只有证明推理本身有问题,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此即道德自律意义:“其他事情不列入到应该做什么的推理。”[10]由此而言,道德仅需自身推理足矣,自然主义又起什么作用?雷切尔斯认为自然主义恰能解释为何通过推理来思考,人性通过自然选择形成,包括保护孩子的情感以及关爱他人的性情,此倾向直至他们给你一个理由去讨厌他们。因此,对实施麻醉的“情感认同(sentiment of approbation)”是通过事实思考得出的结论,通过结论表达的是应如此做。但从外部而言,能看到人性、情感、认知能力运转,以及关于儿童和麻醉相互作用的所有事实;就内部而言,即不会加以考虑,只想通过论证去思考。
显然,雷切尔斯分析的是自然主义与规范性之间的关系,他承认自然主义的道德解释存在缺陷,但不能因此全盘否认,故而提出“内部(from the inside)”与“外部(from the outside)”加以区分与联系。面对理性或道德行为相关能力被夸大情况,此为回击自然主义谬误和规范性伦理学得以立足至关重要的实质性辩论。依据雷切尔斯分析,自然主义从外部提供一种观点,但此观点缺乏从内部体验推理的规范性力量;从外部验讫之后,规范方面即消失,因当开始谈论推理并引用、评论它时,无需再说迫使行动之言。当我们限制自己通过“内部”伦理争论展开思考,对道德思维与情感之间的关系,道德术语中提到的自然特性,或其他困扰道德哲学家的难题,均无法下结论。按雷切尔斯分类,道德本身由“内部”而来,而一切道德哲学皆为“外部”产物。
(三)进化元伦理学解释
进化元伦理学选择通过和语言对比得出道德来源答案,进化理论者希望得出的理想化结论是,道德由生物习性本身决定。如理查德·乔伊斯(Richard Joyce)将道德感视作道德判断能力,认为道德判断能力系天生,得出以下结论:“语言出现为道德概念和某些道德情感(moral emotions)的出现提供一个先验制约;道德判断可以作为保证,使得个人和各层级人际关系中以提高生殖利益的方式做出判断;通过情感调节(modifying emotions)的经验证据表明,人类道德感是自然选择形成的,更准确的推断是,情感突现(projecting emotions)是我们做出道德判断能力的核心。”[11]乔伊斯反对休谟式伦理自然主义,此种自然主义意味着,获得关于进化真理的认知途径,可成为获得道德真理认知途径的手段,这于他而言确有缺陷。无论何时判断道德上的错误,均有一个完整解释,既不预设道德事实,也不作为道德事实的还原基础,这些道德判断的解释不诉诸道德事实;同时,在无其他解释情况下也需假定道德事实。因此,道德事实存在。而如何展开道德判断和行为则取决于行动者“意志自由”,有多种因素影响行动者选择。
据此解读,乔伊斯提出反对论点:“如果道德话语的规定和人们必须遵守的理由之间联系仅仅是一个可靠的偶然的话,那么道德话语是否可以继续扮演它所扮演的角色?”[12]乔伊斯认为道德话语有特殊功能,即让其他类型考虑或理由保存沉默,而实现此功能需要复杂动机。动机也许是行为或心理,如利他、尊重、顺从、合作、社会行为、道德感、道德判断等,欲了解这些内容,进化理论也许是合理工具,研究者通过进化理论和心理学与认知方面研究,试图得出的结论普遍倾向于动机源于生物本身习性,也许此类答案缺少实证证据,但至少提供一种可能性,为道德问题研究提供自然主义式科学研究径路,也将伦理学与经验科学的融合向前推进。
三、结论
在解释道德进化时,可大致如此归纳:面对自然主义谬误质疑,各进路做出解释时均将道德规范性作为“应当”,而研究对象(道德事实)则作为“是”。几乎无一例外,所有研究进路均规避自然主义谬误质疑,否认道德进化理论是简单因果联系。正如自然和心灵不能分离但也无法完全一致,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关系辩证也并非一个非是即否问题,复杂道德系统中,既有建构性规范内容,也有适应性本质。而适应性部分需通过进化理论工具找寻,也许适应性植根于人类早期祖先和动物共有的心理特征。所有正常人均有能力做出道德决策并用其引导自身行为,但此自然倾向只在有利条件下才被激活,因此在最佳条件下,规范性和事实性之间无必然矛盾。
自然主义谬误指从“是”得出“应当”的事实陈述,在当代更被凸显至科学与伦理关系问题中。科学的“是”与伦理的“应当”是融合的,首先,“应当”的判断源于大脑中反应心理状态的心理机制,此心理机制可能是进化的,通过进化理论解释“是”的心理机制如何设计和运作,可为理解“应当”判断来源提供依据;其次,“应当”包含“是”,科学与伦理不可能被完全理性分离,将道德标准定位过高以至于无人能及并无意义。科学可评估人的道德,但如进化心理学这样得出的道德也是理想标准,很难有人企及,科学目的非设定伦理标准,而伦理也不应将科学拒之门外,两者始终融合。
针对自然主义谬误对道德进化讨论的阻碍,可借鉴麦克道尔的选择,站在规避或折衷立场上。麦克道尔提出非自然主义道德实在论(弱的道德实在论),既要承认道德事实的客观向度,又能使道德事实与道德主体主观向度密切相关,即不能将道德事实极端等同于自然事实,也不能诉诸直觉主义的神秘性[14]。进化理论最直接的启示是关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真实属性的辩证,尽管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属性似乎与两者道德地位无过多联系,但间接揭示属性的本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自身。
参考文献:
[1] 唐纳德·帕尔玛.为什么做个好人很难?伦理学导论[M].黄少婷,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2] 张传有.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原始含义及其现代解读[J].道德与文明,2009(6).
[3] 摩尔.伦理学原理[M].长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 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M].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M].毛盛贤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7] 迈克尔·布雷迪.进化与规范性[C]//赵斌,译.爱思唯尔哲学手册——生物学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 Dennis Krebs.The Origins of Moralit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9] 詹姆斯·雷切尔斯.道德的理由(第五版)[M].杨宗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 Hugh LaFollette.The Blackwell Guide to Ethical Theory[M].Oxford:Wiley Blackwell,2000.
[11] Richard Joyce.The Evolution of Morality[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6.
[12]王增福.论麦克道尔的非自然主义道德实在论[J].哲学动态,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