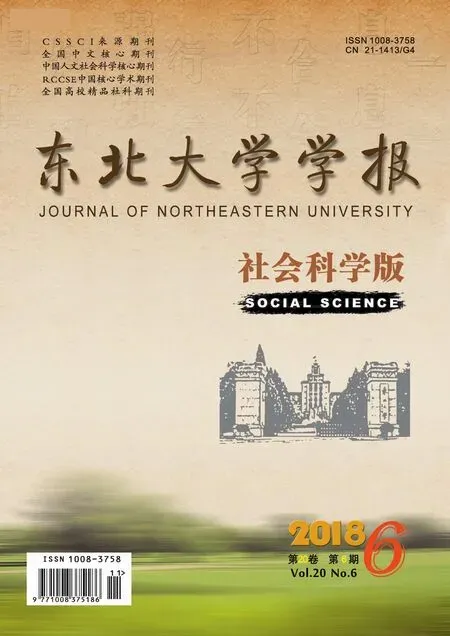古希腊技术思想与前苏格拉底时期自然哲学的关联探究
赵墨典, 包国光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对古希腊技术思想的探究,是“技术哲学史”和“技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此展开工作。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可作为哲学探讨“技术(τχγη)”问题的先导或预备阶段,后来的哲学家讨论“技术”,多是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展开,因此早期“自然哲学”可能蕴含着部分潜在的“技术”思想。笔者以“自然哲学”理论构思的视角,试图阐释“技术思想”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联意义,作为对这一时期哲学中“技术思想”的探索。本文从古希腊“技术思想”发展变化的角度,将自然哲学家对“自然生成”的构思与古希腊神话宗教、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的“技术生成”思想进行对比,试图从理论构思的层面找到两者之间的关联。
一、 “自然哲学”孕育着技术思想从神话到哲学的“转向”
古希腊前哲学的“技术思想”,寓于神话、宗教著作及文学作品中。哲学的诞生与兴盛,使得一部分神话、宗教涉及的话题,在哲学的思辨中被赋予全新意义。“技术”作为宗教神话常提及的概念,逐渐进入哲学的视界,成为古希腊哲学的重要话题。
1. 古希腊技术思想的“转向”
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关于“技术”的神话故事,神话宗教是古希腊人思考“技术”的方式,在此背景下“技术”显示出“神圣性”和“伦理性”特点。在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将“技术”作为“礼物”馈赠给了人类[1],使“技术”获得了借用“神力”的意义。这种借用“神力”的方式,在宗教意义上是“神”的附体:“神”降临身体从而开启人们的“宗教之眼”[2],让人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中看到了“正义”的规则,从无止境的劳动中看到了“美德”的品质,从“技艺”的“谋划”中看到了理性和智慧[3]。在神话宗教视角下,“技术”的思考是通过虔诚的信念展开的,“技艺”不仅意味着动用理性、花费心思,而且也是实践正义、修养品德的一种途径方式,同时也伴随着思想上的某种神圣体验。
哲学的诞生让源自神话宗教的技术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对于“技术”的思考在哲学向度上得到了重新展开,显示出强烈的“体系性”和“思辨性”。从神话宗教向哲学的视角转变中,“技术”从一种无理性的“禀赋”变成了可通过logos言说的“知识”;从一种“神”赐予的“权力”变成了人类凭借自己所取得的“能力”。最初苏格拉底反对智者的“修辞术”,把恒定不变的“自然知识”看做是取得“技术”的前提[4]。柏拉图将“技术”视做对“理念”的“觉知”[5],这种“觉知”向人类提供了理智的能力。哲学放弃了神话宗教中“诸神”的人格化形式,确立了抽象的“一神”,并从中取得了“善”之本性,因而“技术”也通过“善”取得了“神圣性”意义。亚里士多德借助“灵魂学”将“技艺”作为人类灵魂之理性品质,是被制作物取得其“外观”的“原因”。还通过“运动”理论阐释“技术”与“自然”的关系,将“技术”视为一种动变的“本原”,并从“本原”和“原因”的角度引申出人类技术活动与作为“神”之本性“善”的关系,将“技术”称作一种“外在的善”[6]。
因而古希腊的“技术思想”在哲学诞生之后即发生了“转向”,这一“转向”发生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向苏格拉底哲学转变的过程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技术”问题的哲学思考并不是凭空产生,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和智者的哲学中孕育着关于技术的哲学思考。
2. “自然哲学”的技术意蕴
“技术”在哲学向度上的展开,借助了自然哲学的“生成论”模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涉及大量有关“技术”的内容,他们的“技术思想”依赖于“生成论”这一哲学模型给出。对于柏拉图来说,无论是“感觉领域”还是“理念世界”,“技术”现象都是通过“生成”这一方式展示。在“理念世界”中,“技术理念”由“善”理念分有而来;在“感觉领域”中,“技术”活动的本质就是对“理念”的“模仿”。亚里士多德把“技术”看做与“自然”同类的“生成”运动,自然的“生成”以其自身为目的,而“技术”则是一种人为(nomos),将被制作物的“形式”作为生成的终点,其运作依赖人类灵魂对被制作物外观的预先知晓。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生成论”,虽然以全新的方式调和了“自然哲学”的运动学说与“存在论哲学”不相容的难题,但并没有摆脱“自然哲学”从“本原”到“万物”的“生成论”模式。他们将“理念”或“形式”作为“生成”的本原和原因,通过思想和理智为“生成”模式设置复杂的路径和方式。这种模式与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哲学”的生成学说是一致的。自然哲学家的“自然生成论”采取一种从“本原”到“万物”的“构造”模式,他们的“宇宙生成论”揭示出自然生成的“有目的性”特征,使得自然的秩序或法则以类似于人类理智运作方式的形式展现,自然的生成也类似于依赖某种理智的“制造”活动。因此可以说,自然哲学的“生成论”包含着人类对“技术制造”活动的体验和理解,哲学家借用了向人类理智敞开的“技术制造”过程,构造了自然之动变的解说模式,自然生成论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技术生成”。
因而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中孕育着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技术思想之所以能在哲学领域展开,与自然哲学生成论的技术意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自然哲学的技术意蕴的阐释,不仅揭示了古希腊技术观从“神话—宗教”到哲学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古希腊人的哲学构想从“宗教”模式转向了“技术”模式。
二、 “本原—万物论”与技术制作思想之关联
古希腊神话以原始神“生育”的方式诉说自然万物的生成历史,而自然哲学则采取“本原—万物”的模式探讨同样的问题。这样一种哲学的“生成论”模式以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方式将“诸神”排除在自然物生成的“历史”之外。经历了“智者”运动,自然哲学的生成论不再受到重视,而这种模式后来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重新启用,作为阐明“技术制作”理论的基础。从古希腊哲学“技术制作”理论的角度看,自然哲学的“本原—万物论”的构思与“技术制作”模式有相似性,这种模式本身蕴含着“技术”的意蕴。
1. “本原—万物论”的构思与“技术”的构思
“本原”在古希腊哲学中具有着丰富的内涵。据亚里士多德解说,本原(ρχ)有七个含义:①运动的开端。②生成的最佳起点。③事物生长或建造的起始部分。④事物生成的来源。⑤指挥者。⑥技术。⑦理解的前提[7]110。因此,本原并不是指在“广延性”上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体,而是作为动变的最初原因。“水”“火”和“气”这样的自然物被选作自然生成起点的“候选者”,并不因其微小而被当做了本原,他们必须通过特定的运动方式展现其作为自然物生成的潜在力量和意义。因此自然哲学家在众多自然物中选择并确定本原的“候选者”,其判定依据在于这样一种有特定运动方式的物体,是否能以从“一”到“多”的方式对感觉经验中的自然生成进行合理解释。
因此“本原—万物”模式的给出,首先是一种运动方式的猜想,将具有简单运动模式的“本原”置于纷繁复杂的万物的生灭变化中,构思出一种生成模式。“本原”在自然之中以“材料”的身份处于运动着的万物之中,而在思想之中则以“运作方式”和“原理”的形式实现充盈的理解。“本原—万物论”的模式是对自然运动过程和原理的描述,同时也是“构造”与“设计”活动的结果,这与人类的技术制作模式类似。工匠制作一个技术物或艺术品,总是需要围绕“样式”“材料”和“方法”进行构思,而“方法”涉及的正是让“材料”围绕“样式”生成的运动的方案。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技术制作活动的构思,描述为一种“回溯法”:从将要被制造的技术物外观出发,不断寻找实现的条件,直至找到符合当下现实的制作开始之点[7]164。技术制作活动使当下的“材料”生成未来的技术物,其“方案”或“流程”是按照“回溯法”取得的。然而“回溯法”早已蕴含在自然哲学家对本原运作方式的构思之中,自然哲学以解释自然事物的“成因”为目标,通过展示其最终能够成功回溯到“本原”的可能性,来证明“生成模式”的可行性。因而自然哲学家“本原—万物论”的构思,与亚里士多德的“回溯法”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技术活动“回溯法”的构思其实是自然哲学“本原—万物论”构造模式的概括和阐明,他们之间存在构思方法上的关联。
2. 自然的“运作方式”与技术制作活动的关联
人类最原初的宗教体验来自人对无生命事物的“物活感”[11]23,自然哲学同样包含着对这一感受的揭示。泰勒斯认为是湿润贯穿了宇宙[12]327,使得“灵魂”以“活”(ξν)的方式通达到整个世界,使整个世界“生命化”。阿纳克西美尼将“气”同时作为本原和神来看待[13]8,使得“本原—万物论”不再是“水的渗透”这样单一的机制,而是将动因归结为某种“理智”的运作方式,从而使自然不仅“生命化”,而且“理智化”。自然作为与人类同类的“生命”,其运作方式服从于自然之“理智”,这使得“理智”成为“自然法则”的依据。在自然哲学家那里,人类“理智”是获取“自然知识”的方式,同时也是技术活动的依据。在赫拉克利特残篇中,他指责毕达哥拉斯虽“博学”但并无“心智”,因而拥有“糟糕的技艺”。可见赫拉克利特认为“技艺”即是在持有“自然知识”的基础上,人类凭借“心智”对其进行运用。他们把“技艺”当做是人类“理智”的展开状态,是对作为自然“理智”的“产物”(结果)的“自然知识”的复制与对“自然过程”的再现。
由于自然之“理智”本身源自将自然的动变现象与人类生命现象的类比,因而自然之“理智”同样是拟人化之后进一步的“假设”。按照赫拉克利特的思路,当自然的“运作方式”或“自然知识”成为了人类“理智”活动的产物,那么它相应地也以人类对自己“技术活动”的认识为摹本。就“理智”活动本身而言,哲学家对自然的认识,首先应基于人类的“自我认知”。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对于自然认识,“要从对于自然不甚清楚但对于我们更加清楚的东西前进,达到对于自然更加清楚和更易知晓的东西”[14]3。那么,“技艺”作为人类“理智”学习自然、模仿自然之方式,就成了学习并模仿自己的方式了,这使得这一观念变得空洞而无意义。然而自然哲学家对于“自然”及“宇宙理性”的信念,让他们对此类研究乐此不疲。
三、 宇宙论与技术的生成模式之关联
如果说自然哲学的“本原—万物论”解决了个别之物从何而来的问题,那么“宇宙论”揭示着宇宙整体的成因。宇宙的演化是本原生成的延伸,古希腊哲学中的“技术生成”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自然哲学的“宇宙论”模式。
1. 古希腊“宇宙论”的生成机制
在古希腊,“宇宙论”(cosmology)从宇宙整体层面揭示自然之“生成”。阿那克西曼德是古希腊“宇宙论”的开创者[15]163,他的研究涉及了天体的形状、宇宙的大小、风和雷电等自然现象的成因等问题[15]89。基于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构想,阿利斯塔克等古希腊天文学家开始了漫长的对于天体结构问题的探讨。阿纳克萨戈拉通过观察陨石的坠落,得到天体是炙热的石头的结论,主张是一种“宇宙漩涡”(cosmic whirl)阻止了天体的坠落,使得天体得以按照轨道运转[15]179。“宇宙漩涡”模式使万物通过永恒“旋转”演化而成,阿纳克萨戈拉认为“努斯”处于漩涡中心产生分离,从而使万物从漩涡边缘甩出[12]456。“努斯”作为具有“宇宙理智”的“本原运作者”,将“本原—万物论”与“宇宙生成论”联系到一起,使自然物的生成和宇宙的生成在原理上达成统一。“自然哲学”与“宇宙论”的结合,反驳了来自爱利亚学派的关于世界是“永恒的”或“静止的”这一类论断[15]206,说明了宇宙是“永恒运动”且不断“生成”着的。自然中的一切运动方式,都是从“本原”的“运作”开始,不断“演化”而成的。
2. 参照“宇宙论”的技术生成模式解说
“宇宙论”使自然拥有了复杂而又变动不居的“演化”方式。伴随着对天体研究的深化,“宇宙论”模型依赖大量的运算和推理。这使自然的“运作”再难被人的理智把握,因此哲学家们开始渴望获得突破“现象”世界的、对自然整体最真实状态的“直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了他的“宇宙论”,他认为真实的大地是一个带有许多孔洞的“十二面体”[13]18-20,人们生活在洞中。人没有能力看到真实的世界,因而身在洞中却有处在平坦大地的感受[15]209,而看到真实的世界需要依靠“心灵之眼”[16]。“宇宙论”的“原理”到了柏拉图这里,就不再是自然“运作方式”的“生成”模式了,而变成了“巨匠”仿制“理念”的技术“制作”模式。柏拉图的“技术”思想与他的“宇宙生成论”采取同一模式。他认为“技术活动”和“创世活动”一样,是“工匠”对“理念”的模仿。人的“心灵之眼”是灵魂向“理念”的转向,让人凭借灵魂的理性部分看清万物的“是什么”,而后技术活动依赖“心灵之眼”注视技术物的“理念”进行。
亚里士多德把“宇宙论”作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然生成之“动力因”的探究。他的自然观念源自对宇宙不断返回自身的循环运动状态的认识。在他看来,天体在“圆周运动”的意义上作永恒运动,而地上的东西则在不断“生成”和“消灭”中循环,因而依靠“技术”的运动也处在不停的生灭变化中。在自然哲学家那里,“技术”源自对自然运动方式的知晓。与自然哲学家相反,亚里士多德把“技术”当做是自然运动趋势的“反叛”而非“符合”。他认为“技术”造成了背离自然的运动趋势,把“技术”归为“反乎自然”的“强制”的运动[14]8。亚里士多德从自然整体的运动模式推导出“技术”的生成模式,将实施技术活动的“人”作为“动力因”的提供者和“形式因”的引入者,认为“人”是技术物生成运动之“原因”。
自然变动不居,迫使人放弃将自然物作为本原、以特定运动方式构成复杂的机械运动体系解释万事万物,从而转向了“宇宙论”式的对自然运动直接的“整体性”描述。这种“整体性”视角与古希腊哲学的技术思想有着重要关联,它诱使人放弃从最微小单元、单位出发进行推理猜测,而从整体、全局的视角下以“经验”为基础概括描述,并以“类比”的方式给出解释。在这种方式下,“技术”首先被当做了时间次序上的端点,即“模板”和“原因”,这种“先验论”的方式使“模型”和“样式”成为“本原”或“起点”。如果说,“本原—万物论”采取了“技术—自然”这一循环论证的方式,既用“技术”类比“自然”,也用“自然”类比“技术”,那么“先验论”的方式即终结了这一循环论证,将二者共同归结到某一信念层面上去。在对“宇宙整体”运动方式的假设中,人失去了相对于“技术”的主体性,仅作为“生成”运动的推动力的提供者,促使事物对其自身的“仿制”,成为诸多“原因”之一;“技术”本身的“目的性”,并非来自于“人”的意愿,而是某种作为人类意愿之终极原因的“宇宙理智”。
四、 关于“努斯”的学说与目的论技术思想的关联
自然哲学将自然视做一个有“理性”、有“生命”的动变领域,将“努斯”作为此类动变的原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这种“动变趋势”揭示为“努斯”向“善”的目的性运动,从而使“善”成为一种运动的“技术活动”之终极目标。因此,自然哲学的“努斯”学说,与“技术”活动的“合目的性”存在关联。
1. 古希腊的灵魂运动论与“努斯”学说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将“运动”归因于灵魂,认为灵魂的存在是一切生成运动的前提。古希腊语“灵魂”(ψυχ)一词有着生命、精神、理智等含义[17]。泰勒斯最先把自然物运动的原因归于灵魂[11]22,认为灵魂存在于一切能动的事物中,之后阿那克西美尼[12]575与阿尔科迈翁[18]159也持有过类似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将灵魂当做“运动”之原因的做法,使人的“心智”(νοξ)或“理智”介入自然生成成为可能。自然的运动方式以“理智论”的形式得到解释,意味着人类理智与自然理智(自然运动原因的灵魂)成为同类。这种理智的共通性使人类理智可以向自然理智溯源,因而人们凭借“理智能力”取得“技术”,也有了向自然“造物”溯源的意义。
2. 技术的目的论向善解说
关于“努斯”的学说将自然运动和灵魂运动联系到一起,这使得技术的“知识”和“能力”层面的含义与“运动”层面的含义相统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努斯”与“善”建立了内在联系,从而建立了自然运动的“向善”模式,使“善”成为技术的目标。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将“宇宙灵魂”指向了“神”或“造物者”,并认为“善”是“神”的本性,“理智”造成了生命的“善”和“美”,因而“造物者”把“努斯”放在了灵魂里,把灵魂放在了躯体里[22]。在《法篇》中,柏拉图将灵魂视为“自动的推动者”,得到灵魂的“自我运动”是自然运动的源泉的结论[23]。对于柏拉图来说,工匠模仿“理念”制作,因而“理念”是“技术”之“生成”的原因。神造就了“理念”,“善理念”是所有“技术理念”的“本原”,因此技术制作活动先天地带有着“向善”这一“神”之要求的目的性意义。
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生成运动看做是“向善而生”的[11]558。他将“心灵(努斯)”分解为引导自然运动的“主动心灵”和干预人类活动的“被动心灵”[21]86。在他看来,人类一切“善”的活动皆系于灵魂之中“心灵”的运作,因此技术活动就是人依赖“心灵”追求“外在善”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中,“心灵”呈现出明显的自主性,并始终引导人们“向善”。“心灵”以“判断”的方式规劝“欲望”,通过三段论[24]指明“是”和“应该”,因此“心灵”是灵魂的规劝者。自然之中“主动心灵”造成了自然向善的运动趋势,使得自然运动朝向“善”或“不动的推动者”[25]运转;而“被动心灵”通过使人“明智”,造成人类活动的“向善而动”趋势。因此“技术”与“实践”都是人类的“善”活动,“技术”虽以“外在的善”为目的,但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追求“幸福”。
古希腊哲学的“努斯”学说,揭示了自然与人类灵魂以“善”为目的的运动本性。自然哲学将自然运动视为一种有理智的运动,将“努斯”作为有这种理智的原因,意味着一切运动都是经过理智筹划而进行的,运动本身包含着目的性。因而“技艺”作为一种人类的理智活动,在自然哲学的“努斯”学说视角下,应属于一种“努斯”活动。人类的“欲求”与“努斯”的“理智”同时赋予技术目的性,让技术不仅成为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途径、手段,同时也成为了具有追求神圣性和超越性特质的动因。因此技术基于“努斯”的运作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作为造成“自然运动”和“灵魂活动”的原因,同时其本质统一于“神学”[14]261的目的论模式之下。
五、 关联的意义
可以说,古希腊技术思想从“神话—宗教”向哲学的“转向”,是借助自然生成模型实现的,古希腊哲人对“技术”的思考,与自然哲学理论的构思有着密切关联。作为探索自然的一种思路,自然生成模式要求将经验中纷繁复杂的生成现象归结为有确定性的规律规则,使自然运动从不可预知、不可掌控状态转变为向人类理智敞开的、能够被认识的领域。人类是否持有关于自然的正确信念,需经由理论上、现实上对所知晓内容的无碍“再现”来检验,而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现实层面的“再现”都是“技术性的”,因为不论是哲学家构思哲学体系,抑或是工匠制作产品,都可视为是借助“技艺”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预设自然的可知,就已包含了对自然的“技术化”理解。这也诱使后来人将“技术”作为一种“知识”考察,“技术”作为“知识”何以可能?如何用“技术”定义“知识”?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古希腊哲学家探讨“知识论”的基础。
从“本原—万物论”到“宇宙论”再到“努斯学说”,自然哲学将运动的终极原因归结为某种理智或理性。这是一种“类比”的方式,将人类对自身思维、理智现象的认识,运用于对自然规律、宇宙理智的解释上,从而化未知为已知。这一“类比”有效的基础就在于“努斯”被同时当做人类灵魂与整个宇宙动变的来源,使得人类与整个宇宙在运动原因的意义上是同类的。进而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技艺”首先以“知识”的身份与“道德知识”进行类比,确定了其明晰性与可靠性,进而才能基于“模型”(paradeigmata)的相似关系引发出“理念”概念[26]。因此,哲学对自然生灭变化的揭示,依赖于对人类所主导的生灭变化的经验,自然的生成通过类比人类的制作而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技术视为一种模仿活动,使工匠成为自然的学习者、模仿者,这种说法揭示了“技术”与“自然”的同源性关联,而这种“同源性”关联正与自然哲学对“生成”模式的设定相关。自然哲学将“宇宙”视为复杂而庞大的理智体,使之成为人类学习、模仿的对象,这一类比使得“技术”作为一种“模仿”成为可能,也让古希腊哲学的“技术模仿”观念迎合了哲学诞生之初希腊人对理性、精神意义的渴望与凭借理智“超越”宗教束缚的使命感。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背弃了神话宗教,通过“努斯学说”为宇宙整体确立固定的演化模式,要求自然运动与人类活动一样指向特定目的和终点。“目的在动变之先存在”是柏拉图“生成论”的典型模式,在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潜能”到“现实”的“运动学说”中明确被表达出来,它不仅是自然哲学“努斯学说”追问“原因”方式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揭示古希腊“技术”动变含义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反驳了智者基于“修辞术”的相对主义哲学,让技术不作为观念产生的前提,而是作为观念的结果。技术的目的由人类赋予,当我们开始思考“技术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实际上要求的是一种“建构”,而非“回答”。这一“建构”内在包含着我们对自身之存在的理解,以此作为技术何以存在的基础。古希腊自然哲学尝试通过“努斯学说”解决自然运动的难题,但却没有将“人自己”纳入到哲学体系中去,当面见“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后来的哲学不得不向宗教方式妥协和回归。
因此,古希腊哲人对“技术”的理解,最终被整合到以“善”为核心的目的论哲学之中。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生成论”模式与古希腊技术思想的关联,不仅从“生成”的角度揭示了古希腊哲学中“技术”概念的动变意义,同时也让“人”取得了和“自然”同等的“运作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以“自然”为核心的自然哲学向以“人”为核心的实践哲学转化。“技术”作为自然哲学理论构思的经验源泉,正是经过“生成论”模式的构思与带入,才得以从“神话”进入“哲学”之中,成为古希腊哲学探讨理性、知识与人类“实践”活动等的重要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