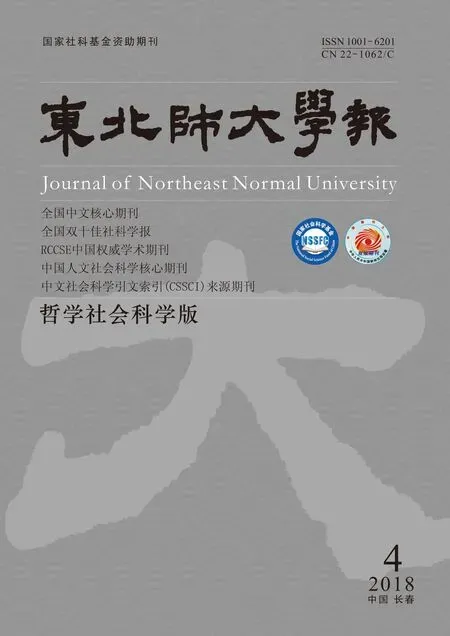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性质新探——以其安置民户、督导经济、平决府州县的职能为中心
孙 佳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调整诸京建置,改革并统一地方路制,至海陵天德二年(1150)全国普遍实行了兵马都总管府路制。学界对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是否为金朝一级地方行政建置的定性问题见仁见智。首先,德国学者傅海波[1]312、台湾学者杨树藩[2]415、程妮娜[3]112、刘浦江[4]76、史念海[5]175-176、李治安[6]369等先生持“行政建置说”,主要认为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是府、州、县之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兵马都总管府为行政机构。其次,赵云田[7]212-213、李锡厚、白滨[8]274等先生持“军事机构说”,认为金朝兵马都总管府是军事机构。赵云田先生认为路是金朝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设有都总管府、转运司、提刑司、统军司等,“都总管府为路的军事机构”,亦理民政,军政合一[7]212-213。再次,王曾瑜、张帆先生持“军事治安机构说”,认为金朝兵马都总管府是本路的军事治安机构。王曾瑜先生提出兵马都总管府长官还兼理本路首府民政[9]31。张帆先生认为金代的路不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划[10]102。最后,余蔚[11]495、李昌宪[12]950-962先生持“高层政区说”。余蔚先生认为金朝路制一直未臻完善,空间上“几种机构的辖区未能重合,区划不统一”,共同作用于府州并连接中央,应视为职能不完全的高层政区[11]495。
学界前辈的研究视角不同,前三说是基于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的内容展开探讨,后一说则是鉴于金朝多重路制的总体层面进行定义。上述诸说的讨论为金朝路制研究奠定了基础,学界前辈在探讨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性质时,或依据《金史》中《地理志》《百官志》的单向记载,或并未细致考究兵马都总管府路的制度结构和全部职掌,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被讨论。厘清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是否具有行政职能是解决各家争论的关键。本文拟通过考察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安置民户、督导经济、平决府州县等民政、民生职能,来明确金熙宗以后兵马都总管府路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建置的性质,与学界前辈的观点进行商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朝“行政路”与“职能路”的概念,以求教于方家。
一、安置猛安谋克户与汉人移民、流民
金熙宗以后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制表现为京路、都路、总管府路三种形式。京路路级官署为留守司。都路路级官署为都府,皇帝出巡时设留守司。总管府路路级官署为总管府。诸路长官皆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它们虽在官署设置上略有差异,但运行机制是整齐划一的,利于金朝中央对地方的常态化管理[13]70-78。
熙宗以后兵马都总管府路下辖的主要户口包含“猛安谋克户”和“州县户”*实际上金朝户口还包括“乣户”,即生活在金朝北部、西北部边地的游牧部落。“乣户”不是地方路制下的主流人口类型,以游牧为生,常迁徙不定。参考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猛安谋克户”以女真人为主体,另掺杂了部分契丹、奚等族人口。“州县户”指的是汉人,主要由汉族和渤海族人口组成。金朝大概每三年开展一次户口的统计与调查,经最基层的里正、主首、寨使逐户落实户主填报登记“手实”,“以实数报县”“申州”“达上司”“到部呈省”[14]1032,由县→府(州)→路→户部→尚书省。刘浦江先生依据转运司路设有户籍判官,认为“上司”应指转运司路[4]76。转运司作为掌理地方经济的职能部门,负责督促府州县进行户口登记、统计,并上报中央。兵马都总管府路作为行政建置,负责管理本路原有民户,同时还要安置新进入路内的“猛安谋克户”和“汉人移民、流民”。
(一)安置猛安谋克户
猛安谋克是金初女真人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女真建国前一年,猛安谋克组织正式成为了女真基层社会行政组织。金太祖、太宗两朝在女真内地和原辽黄龙府地区置万户路,在原辽其他地区实行都统或军帅司路,在占领的原宋地区设兵马都总管府路。此间,猛安谋克户经常被迁移到新征服地区。熙宗以后全国开始实施划一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制。金朝中央为了实现其统治意愿而对猛安谋克户进行迁移,由相关诸路安置。猛安谋克户有三个主要迁徙方向。
一是从北部、东北部地区迁至中原地区。如熙宗“创屯田军”,迁移大量猛安谋克户至中原各路,“与百姓杂处,计其户授以官田,使其播种”[15]173。猛安谋克户平时耕种屯田,战时起戈为兵。海陵贞元元年(1153)三月迁都中都,将上京地区有势力的女真宗室的猛安谋克迁移并安置于中都路、山东东西两路、北京路(大定府)、河北东路[14]993[16]197*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据《金史·食货志》田制条等史料认为海陵迁移上京诸猛安谋克的时间应在正隆元年(1156)。参见[日]三上次男「金代中期における猛安謀克戸」、『金代政治·社会の研究』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3年版、第197頁。,以清除上京地区宗室异己残留势力,同时加强女真势力对新都及京畿附近区域的控制。世宗即位于东京辽阳府,入主中都时随扈军猛安谋克内迁,为了巩固皇权,大定二年(1162)又命东北“咸平、济州军二万入屯京师”[14]124-125。二是在中原地区部分路之间迁徙。海陵正隆时曾将中都部分猛安谋克迁至南京路,以备征宋[14]109。世宗时撤除“海陵时无功授猛、克者”[14]1626,新授猛安谋克“并令就封,其谋克人内有六品以下职及诸局承应人,皆为迁之”[14]995。世宗、章宗朝实行移民和括地政策,来缓解猛安谋克户贫困化的问题。世宗在河北、山东地区对猛安谋克户进行移民和土地置换,并鼓励农耕,如“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东平之境”,“摘徙山东猛安八谋克于河北东路,置之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诏无牛耕者买牛给之”等[14]1987。三是金后期南迁。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四月,蒙军南侵,迅速占领了金朝北部大量府州县。宣宗贞祐二年(1214)四月,山东、河北诸郡多失守,河东州县亦多残毁[14]304。五月,宣宗迁都开封府。“乣军溃去,兵势益弱,遂尽拥猛安户之老稚渡河,侨置诸总管府以统之”[14]998。八、九月,宣宗在南京路归德府、开封府附近设山东西路、大名府路、河北东路行总管府[14]312-313,管理从山东、河北、山西迁入的猛安谋克徙军户[14]2378,使其形成重要的军事防线,反映出了此时金朝内缩战线、守卫汴京的军事策略。行总管府是金朝后期一种临时性军事建置,不是地方路级建置[17]112。宣宗兴定五年(1221)十二月行总管府废罢,这些南迁的猛安谋克户复由南京路管辖。
(二)安置汉人移民、流民
金太祖、太宗时期地方诸路需要安置降附的原辽、宋府州县人口和政府行为的原辽、宋府州县移民。熙宗天眷元年(1138)改制,完成了女真政权的封建制度变革。皇统五年(1145)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14]993。在调整京府州县制度的过程中,除了安抚和管理本路原有府州县民户之外,兵马都总管府路还要安置以下四类新进入本路辖境的汉人移民和流民。
一是安置迁都所召集的汉人移民。金朝曾依次历经过会宁府、大兴府、开封府三个国都,不断南移。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时,金朝中央需要加强新都建设,征调民户以充实国都。海陵迁都中都大兴府后,曾下令“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14]1863。金朝后期战乱迭发,蒙元势力崛起,大举南侵。贞祐二年(1214),宣宗迁都南京路开封府,“听民南渡”[14]306。二是安置政府行为的汉人移民。如世宗大定初年,“山东、河北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处,民多失业”,南京路陈、蔡、汝、颍州地区临近南宋。海陵正隆征宋时,这些州县受战火侵扰,导致地广人稀、经济凋零。因此世宗采纳曹望之的谏言,“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14]2037,将山东、河北的部分汉人居民迁入南京路。这不仅缓解了山东、河北地区土地资源紧张的危机,同时还促进了河南地区的经济复苏。三是安置并赈济灾荒时产生的汉人流民。灾荒发生时,兵马都总管府路对避难至本路的流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安置和救助。熙宗天眷、皇统年间,“陕右大饥,流亡四集”。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庞迪下令开渠溉田,使“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14]2013,解决了大量流民涌入给本路民生治安所带来的冲击。大定三年(1163),中都路“滦州饥民,流散逐食”[14]130,世宗将这些流民安置于山西地区的河东南路或河东北路,“富民赡济,仍于道路计口给食”[14]130。金朝对汉人流民除了使其就食诸路,世宗时还曾下令“阅实其人,使还本贯。或编近县以为客户,或留为佃户者,亦籍其姓名”[14]2037,使流民复原籍或籍入近县。四是安置躲避战乱的汉人流民。如章宗泰和七年(1207),南宋“复陷阶州、西和州”,金朝“诏彻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愿徙内地者厚抚集之”[14]2181。金后期北部疆土不断为蒙元军队吞噬,“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14]2385。为了躲避战乱,流民四散,各路对这些流民进行收置与管理。
金熙宗、海陵时期锐意改革,使得金朝国家体制向中央集权化阶段转化。金朝政府的移民政策总体上以加强皇权向心力和维护统治为主。新进入诸路的猛安谋克户和汉人移民、流民以政府行为的移民为主线,表现为“充实国都”“戍卫地方”“括地耕荒”等。此外,受灾荒、动乱、战乱影响还有部分自发性流民产生。从前文的考察来看,兵马都总管府路对新进入路内的上述人口进行安置并执行国家的惠民政策,体现了其具有掌管本路民政的行政职能,是金朝地方一级行政建置。熙宗以后的兵马都总管府路作为中央在地方的行政机构,其制度的划一对这种集权政体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督导农业、配合通检推排、防治河患
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作为地方的一级行政建置,对辖区内的经济事项具有督导和管理的职能,不仅要鼓励和监督农业生产,还要配合转运司通检推排,同时沿河流域的部分路还要防治河患。
(一)督导农业生产
农业是金朝的经济产业支柱。金朝中央深知粮食和经济作物是解决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问题的最基本的物资储备,因此通过各种方式劝农,扩大农田耕垦面积,增加粮食产量。
金熙宗以后的兵马都总管府路作为地方行政机构,肩负着督导本路农业生产并惩罚违例行为的职责。金代田制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14]1043。大定五年(1165),中都路两猛安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14]1044,世宗命中都路大兴少尹完颜让前往巡察。世宗后期猛安谋克户不自耕种的问题依然严重,大定二十二年(1182)中都路有猛安户不耕种,“悉租与民”,将领受的官田出租给汉人民户,甚至“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严重浪费耕地资源。大兴少尹王脩作为路官,上陈责罚的意见“以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世宗予以采纳[14]1047。又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时京师市井萧条,草莽葱茂”,大兴尹乌陵用章亲课大兴宰及千户屯等耕垦废田[15]310,意图促进农业生产,解决本路粮食短缺的问题。
当饥荒和灾害发生时,路官还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农耕、维护农业生产,进而确保本路的稳定。如熙宗皇统时期,陕西大旱。傅慎微时任同知京兆尹,作为京兆府路的佐贰官,又“权陕西诸路转运使”。他利用兵马都总管府路和转运司路各自的权力,“复修三白、龙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14]2763。大定十八年(1188),世宗诏南京路和大名府路给本路“避水逃移不能复业者”津济钱以赈济,并“量地顷亩给以耕牛”[14]202,使本路灾民重新开展生产和生活。章宗朝,“雨潦害稼”,大名府路长官知大名府事完颜承晖“决引潦水纳之濠隍”[14]2224,将雨水引入护城河,以保护农作物不受水害。
(二)配合通检推排
通检推排是金朝赋役制度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旨在清查户口和物力。《金史·食货志》载“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14]1037。清人赵翼认为金代推排之法与宋代的“手实法”相似[18]627-628。刘浦江先生认为“推排”指“调查核实民户的户口、物力状况,然后据此征派赋役”,“由中央政府进行的全国性的推排”称为“通检推排”[19]27。大定四年(1164),世宗以“贫富变更,赋役不均”[14]1037,推行通检推排之法。杨广文等先生认为太宗天会年间曾行“通检”[20]80。总体看来,金代通检推排应该在世宗、章宗朝才成为定制。日本学者小川裕人先生认为通检推排是在金朝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兵马都总管府路内进行的[21]37,刘浦江先生则认为是通过转运司路来实施的[19]29。刘先生的解释更为合理。
尽管通检推排由转运司路主导,但兵马都总管府路也承担着配合转运司路推排的任务。每次通检推排的官员,人数众多,包括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猛安谋克户和汉人民户都要受到推排。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都路推官、总管府路府判“掌通检推排簿籍”[14]1304,1310。“通检推排簿籍”置于都府、总管府、散府、州(节度、防御、刺史)、赤县(大兴、宛平)[14]1303-1314。这说明在涉及民户问题时,兵马都总管府路还是要参与到通检推排事务之中进行辅助的。世宗以“猛安谋克多新强旧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当自中都路始”,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八月,“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同分路推排”[14]1038。这次推排因受张汝弼、梁肃等反对,疑未完全实施,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兵马都总管府路官员有时也执行推排的任务。
泰和八年(1208)九月,章宗“遣吏部尚书贾守谦等一十三人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14]285,十一月以“转运司权轻,州县不畏,不能规措钱谷,遂诏中都都转运使,依旧专管钱谷事,自余诸路按察使并兼转运使”[14]1308。章宗期望以按察司的监察权加重转运司在州县官眼中的地位,以便于更好地规措地方钱谷。按察司路兼理转运司路后,开始主导地方通检推排。宣宗贞祐三年(1215)废罢按察司路后,转运司路恢复原有职能。兵马都总管府路在此间是配合按察司路进行通检推排的。
(三)防治河患
金朝在中央设置都水监专管河防事务,另在河北西路卫州(今河南省卫辉市附近)置分治监专门规措黄河、沁河,在地方沿河分段设置都巡河官,诸埽所各置散巡河官。但是当重大河患发生或筑堤工事繁重时,中央还需要征役附近兵马都总管府路的民户、军户参与修筑河防。南京路、大名府路和河北西路的防治河患职能体现得较为明显,其路官需要监督役夫修筑河堤、检视河堤并上报险情。其他临近各路,接受中央调遣,协助完成筑防任务,世宗末年开始沿河“四府、十六州之长贰皆提举河防事,四十四县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14]673。
黄河在河南、山东地区水系尤为丰富,河患严重。南京路和大名府路主要防治黄河河患。例如,阳武、原武、东明三县在南京路沿河边界,位于对岸的河东南路孟州、河北西路卫州也在沿河边界。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曾诏遣太府少监张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纥石烈邈督管役夫在这些地区开展筑防工事[14]671。大名府路南境有一小段黄河流经,章宗明昌四年(1193),“都水监官提控修筑黄河堤”,令大名府“差正千户一员,部甲军二百人弹压勾当”[14]675。五年(1194),知大名府事完颜裔参与监护山东地区沿河州县筑堤事宜,并“讲究河防之计”[14]676。河北西路主要参与治理滹沱河河患。如世宗大定八年(1168)六月,“滹沱河犯真定,命发河北西路及河间、太原、冀州民夫二万八千,缮完其堤岸”[14]688。真定府是河北西路治所,河间府是河北东路治所,冀州隶河北东路,太原府为河东北路治所。三路相邻,河北西路路治府遭受严重水灾时,中央征调三路民力共同修筑河防。
金朝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主导下的农业振兴、人口普查、赋税征收和河防建设等民政、民生事项,在地方由兵马都总管府路执行或部分地参与,主旨在于维护和巩固金朝国家的社会稳定发展。金熙宗以后兵马都总管府路对本路农业、赋税、防灾等民政、民生事务的管理,体现了其地方一级行政建置的特性。
三、平决府州县纠纷
金熙宗以后的兵马都总管府路下辖府、州、路下路、县。这些下级地方建置毗邻而设,经常在边界归属,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分配等问题上发生矛盾。立于熙宗天眷二年(1139)六月的《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详细记述了河东南路路官对赵城(今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洪洞(今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境内)两县霍河水权纠纷的仲裁过程,从中可以窥见兵马都总管府路对辖境内府州县的行政统辖及平决路内府州县间纠纷的职能。
事实上在赵城、洪洞两县还隶属于宋境时,这种水权之争就已经存在了。金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两县水权矛盾再次激化。“赵城县申据使水人户虞潮等状告,有洪洞县人户盗使水”,两县纠纷先讼之于府,“府衙数差官,规划不定”,两县向上申诉。十五年(1137)十月,“牒委府判高金部规划,定于母渠上置木隔子,更隔上岸”,均流水势[22]20。“牒委”平阳府判高金部的上级官署疑为燕京枢密院。程妮娜先生认为金初为了控制和戒备汉地,太宗设置在原宋地区的兵马都总管府路不由中央直接统辖,而受都元帅府及其下属的汉地枢密院统辖[23]182。最早兵马都总管府路的路官由都元帅府任命,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并从朝廷选注”[14]65,改由中央直接任命。这也意味着都元帅府和枢密院对兵马都总管府路由直接统辖开始转向部分节制。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即位,废止国论勃极烈制度,改行封建三省制。改革后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受中央直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都元帅府和枢密院的节制。熙宗天眷元年(1138)八月颁布“天眷官制”,完成了女真政权的封建官制改革。新官制的施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建制初期诸路部分官职的任命还存在空缺的情况。总管府府判掌纪纲众务,分判户、礼案,既是路官又是府官。两县纠纷发生近两年后燕京枢密院才牒委平阳府府判高金部处理,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先前府衙不断在差人处理,持续了较长时间。二是此前平阳府府判一职无人出任,天会十五年(1137)十月稍前才由高金部担任。同时,当时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兼平阳府尹一职疑还没有到任官员,这从后面碑文所记的“本府阙员申覆枢密院”也可以得到印证[22]21。
天眷元年(1138)四月,“准奉枢密院上畔,元帅府札子咨送封题到平阳府”[22]20。赵城县张三等上告至枢密院,状告高金部分水不均,请求拆除石堰。公文下达平阳府后,府衙县依旧前后向上申告,请求差官定夺。由于平阳府阙员,十月“准奉上畔,已下钱帛都勾判官朱申计会两县知县及勾取一十一村人户”[22]21,依旧例定水权,使两县民户再无诉讼。此时,燕京枢密院已于九月改为燕京行台尚书省[14]73。行台尚书省是中央尚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兵马都总管府路已经由中央直接统辖。二年(1139)二月,应时任中京(大定府)留守判官朱申之请,行台尚书省责令河东南路绛阳军节度副使杨祯与朱申共同规划水事。四月,洪洞县人张方至元帅监军行府状告高金部、朱申皆分水不均,“乞差新到任近上官员与杨祯奉直同共定夺”。行台尚书省委派“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镇国上将军完颜谋离也将带两县官吏并合千人户亲诣□定水头,仔细检验,及参照积古体例定夺,务要两便”[22]21。这里“近上官员”应指女真宗室或贵族。从上面材料可知天眷二年(1139)四月河东南路才真正有了一路总长到任,由女真宗室或贵族完颜谋离也出任兵马都总管。完颜谋离也检视分水处,认定高府判确实分配不均,于是拆撤水柜,重新量定赵城县占水七分,洪洞县占水三分,并“置碑二亭”为证,“免使更有交争者”[22]22。完颜谋离也将两县官员及水户签署的无异议文书上交都元帅府和行台尚书省验讫,以复命。
“作为记叙刊布的方式,碑刻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公开性与凝固性”[24]77。完颜谋离也以石碑为界,可以确保两县水权的划分以及本路官方裁决的广泛传达。碑文题名“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文末著“镇国上将军、平阳府尹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完颜谋离也立石”。洪洞、赵城两县隶属平阳府,碑文题名书“都总管”,而不用“平阳府尹”,这强调了完颜谋离也路官的身份,也进一步说明了兵马都总管府路具有平决下辖府州县纠纷的行政职能。熙宗天眷官制初行之际,兵马都总管府路处理本路政务时还部分地受都元帅府和行台尚书省的节制。天眷三年(1140),金朝收复河南、陕西地,燕京行台尚书省移置开封,并入汴京行台尚书省[25]59。海陵于天德二年(1150)十二月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14]96,将地方政令全部收归中央。至此,兵马都总管府路作为金朝一级地方行政建置完全并直接地上承中央、下接地方。
四、关于金朝路制性质不同观点的商榷
依据前文的考察,金熙宗以后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具有明确的管理民政、民生事务的行政职能,其性质是金朝一级地方行政建置。学界以往对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性质的分歧,主要基于四个根源。首先是源于《金史》对“路”的概念记载不清晰。“路”一词常见于金史相关文献中,其具体的指代包括多种含义。以往的研究成果有将“路下路”“招讨司路”“统军司路”算作金朝路级建置的情况,进而导致了我们对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性质的误解。其次是基于学界对金朝路制的探讨尚属金朝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金初与金熙宗以后实行的地方路制在形式上存在差异。日本学者三上次男[26]89-142、程妮娜[23]179-183两位先生对金初三种地方路制的拓荒研究为金朝路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积淀与思路蓝本。而学界关于金熙宗以后划一的兵马都总管府路虽已有研究,但在其制度模式和职能结构的全面性细化性研究方面还存在缺失。同时,学界缺乏对金朝多重路制中兵马都总管府路、转运司路、盐使司路、提刑司路(按察司路)的整合性交叉性研究,这对我们理解金朝兵马都总管府路的性质造成了阻碍。再次是鉴于金史研究面临传世文献资料较少的“瓶颈”。由于资料匮乏,金朝路制研究过程中,在论述某些细节问题时,难免存在由于史料短缺而以一个或几个事例为基础进行推论的情况,这也是引起学界争论的原因之一。最后是由于学界对宋朝路制的性质问题存在“地方监察区划说”*参考聂崇岐:《中国历代官制简述》,聂崇岐著《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5-226页;张德昌:《北宋路制简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张帆:《金朝路制再探讨——兼论其在元朝的演变》,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陈长征:《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地方最高行政区划说”*参考王文楚:《北宋诸路转运司的治所》,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28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5页;王瑞明:《宋代政治史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1页;郑世刚:《略论宋代“路州县”三级行政体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李其旻:《宋朝“路”制浅析》,《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4页;王晓龙:《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辑。“地方复式高层政区说”*参考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三种论点。这也继而引发了学界对金朝路制是否具有确切的行政区划性质的争论。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侧重从“汉化”或汉族本位等角度去思考金朝路制对辽宋“道”“路”制度的承袭问题,以及其对宋元之际“路”和“行省”制度的对接关系问题。我们研究金朝路制时需要从“中华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理论出发,以国家为一体,民族为多元,一方面分语境、多视角地探讨金朝路制对辽宋制度的吸收、改革,另一方面站在女真政权“本体”发展的主观愿望和统治观念角度来审视。
学界常以“金朝路制”“兵马都总管府路”“总管府路”指代金朝一级地方行政建置,这是不全面的。笔者依据金朝多重路制的职能特性而提出了“行政路”和“职能路”的概念,借以更明确地界定金朝路制中的多重内容,以便于明晰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对象。“行政路”是指金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建置,既是一种地理区划定义,也是一种行政体制概念。金太祖、太宗时期实行万户路、都统或军帅司路、兵马都总管府路三种不同的行政路制。金熙宗以后实行统一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制,表现为京路、都路、总管府路三种形式。“职能路”则是指金朝专门行使某种职能的路制,是在行政路行政区划基础上划分的职能型路制,主要包括转运司路、盐使司路、提刑司路(按察司路)。其中在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至金宣宗贞佑三年(1215)期间,因政策调整,曾一度出现以按察司路兼转运司路的特殊情况。
学界前辈持有的“军事机构说”“军事治安机构说”需要被进一步商榷。女真族作为我国的北方少数民族,在其民族和军事部落大联盟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孕育并发展出了女真固有的“本体”制度。这种女真“内文化”的源生性,直接影响了后来女真统治者对国家制度的拟定。金朝行政路制在吸收辽宋制度的基础上,还融入了女真特色,具有军政合一的性质,它是适应金朝多元一体国家发展需要的地方行政建置。金朝行政路的职能涵盖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多个层面,受篇幅所限,不再深入论述。笔者认为赵云田、王曾瑜等先生所持的兵马都总管府路是军事机构兼理民政的观点值得商榷。女真以军事立国,金初开疆拓土时期行政路制的军事气息较为浓烈,熙宗以后兵马都总管府路的行政职能更为明显和确定,但依然是军政合一的性质。此外,“路下路”主要领猛安谋克户,是金熙宗以后兵马都总管府路下辖的基层地方建置,与府州地位相同。“招讨司路”“统军司路”是地方军事组织。三者都不是路级建置。
学界前辈所持的“高层政区说”也需要被进一步讨论。金朝行政路对其下辖区域内的府、州、路下路、县具有直接的行政领属关系。正如李治安先生对比宋金路制后认为宋路为监司之路,“未形成正规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而路在金朝才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6]369。金朝行政路制无论从建置、官署、职能、对府州县的统领等各方面而言,都已经是完全意义的一级地方行政建置,具有军政合一性质。它紧密地连接着中央与地方,是金朝政治结构体系的中间环节。有金一代,行政路一直存在。金末战乱迭起,辖境流失,一些行政路的基本建置被破坏,从而导致了金朝政治结构体系的不稳定。这也引起权力结构中新的支点的生成,因此行省制度在金后期开始发挥作用。而到了元代,承金制,“行省”制度完善起来,成为元朝最高地方行政建置,“路”逐渐发展成为“行省”下辖的二级地方行政建置。随着金朝国家制度封建化进程的开展,职能路开始被设置,并对行政路的经济、司法、政治职权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剥离。金朝职能路是以职能特征见长,其各路辖区对应1个或多个行政路。其中转运司路主导经济,盐使司路主管盐务,提刑司路(按察司路)掌控司法监察。但由于职能路制确立于金朝的不同时期,其变革、完善的进度也有差异,因此各职能路制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兼有其他职能。金朝职能路也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但行政路对其下辖区域直接的行政统辖权力以及在金朝政治结构体系中的层级作用,这些都是职能路所没有的同时也是不可能企及的。在政治职能方面,职能路仅是行政路的辅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