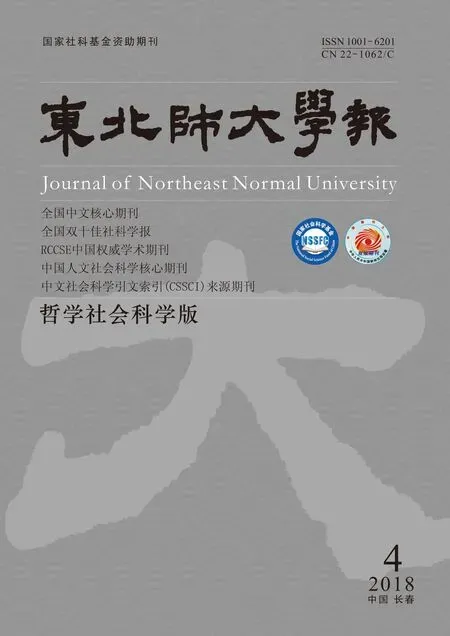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文学理论与实绩——以家庭题材小说为中心
王 天 慧
(大连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大正十三年(1924)10月,以横光利一为核心的作家团体创建了同人杂志《文艺时代》,这标志着日本新感觉派的正式诞生。此后,在为期3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流派成为对当时文坛影响最大的存在。在创建新感觉派后近30年的文学生涯中,横光利一创作出了诸多令日本文学界为之震撼的小说。无论文体还是视角的崭新性,都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可以说,新感觉派文学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现代文学的序幕拉开了。然而,当时的新感觉派除了与既有文坛对抗的既定方针,无论理论建树,还是创作实践,都与成熟的文学流派相去甚远。因此,千叶龟雄在为这一新兴的文学流派命名时,不但将其内在的文学追求呈现了出来,并且预见了这个流派的未来。
一、理论背景
在《文艺时代》创刊的前一年9月,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那次地震对日本文坛造成的震荡,不仅表现在出版业的重组,而且也促使作家们的写作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文学中,私小说和心境小说的特点是指示作家的人格和心境,在这一点上,横光利一创作出的新感觉派小说则完全迥异。1926年,文章《裏と表について》中,横光利一在回忆起4年前的小说《被嘲笑的孩子》时,曾这样写道:“这篇十几页的作品前后共经历了3年的创作时间,作品本身虽然不那么光焰四射,但是语言实感非常强。我一向只欣赏那些具有语言魅力的作品,这篇作品至少是接近这样的境界的。”[1]23不难看出,那时的横光已经具有挑战既有文坛、决心开始新时代文学的明确意识了。
由于创新意识过于强烈,总体来看横光利一的作品,初期前半部分的作品《苍蝇》《太阳》《头与腹》《拿破仑与疥癣》等,在文体上都给读者以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小说《苍蝇》用简练的句子构成和营造了相对冷漠无情的故事情节与气氛,这种冷漠之感总有些和志贺直哉的短篇《在城崎》中所带有的虚无主义氛围相近。这与横光当时崇尚志贺的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得不说及的是,横光早期作品的创作受到志贺文学极大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企及超越志贺的境界。横光早期作品中最大的特征就是明喻、暗喻、拟人和象征等具体概念和抽象语言等写作手法的结合,并由此产生客观性和无情感。
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如火如荼般进行的时期,横光利一创作的作品中,文体尤其独树一帜的应属小说《头与腹》。文字表现的最大特征是生命体和物体的同时性,或者说存在于同一空间。明喻、精短的句子、幽默的飞跃性的比喻等构成了新感觉派文学的基本特征。按照既有文学理念,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情生命体和其他无机物质之间通常要进行严格的区分,使作者与读者对描写对象的区分形成了一种默契。但是横光的文学却是从首先打破那种沉默开始的。他对生命和物体一视同仁地加以描写和表现。因此他将人类描写成无机物,剥去其原有个性、人类性和意志,反之也把人类特性输入无机物之中,将无机物质描写成具有思想的有情生命。
他的作品(特别是《机械》发表之前)充分地体现了新感觉派文学的鲜明特点。主要包括《太阳》《头与腹》《春天乘着马车来》《花园的思想》《上海》,等等。从小说《机械》开始,作品在坚持“新感觉”理念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描写逐渐增加,而且多伴有人物的心理描写,《寝园》与《家徽》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到了1936年,《横光利一全集》十卷本刊行,这样的风格已然开始形成。横光的文体简洁明快,遣词独到的特点尤为突出。因此,横光利一可以称得上是新感觉派真正的斗士。1948年川端康成曾评价横光自创作短篇小说《太阳》起,始终置身于毁誉褒贬的浪潮之中,成为了首先将西方文学与日本传统文学相融合的先驱者。这对横光而言无疑是相对客观的评价。
当横光驰骋于新感觉派文坛时,唯物史观开始广泛传播并风靡日本。因此,那一时期横光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唯物主义文学的作品,以完善自己的新感觉文学理念,主要有《新感觉派与马克思主义》和连载评论《十月文坛文艺时评》等。横光利一的作品中往往具有不指示任何事物,全凭作家的感觉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作品世界的特点。在横光的早期习作《修学旅行记》中也可以看到[2]97,习惯了都市里产业机械噪音和过度听觉刺激的现代情感表现。横光的文体并非仅仅通过汉语的用法而产生视觉的效果,而是在文字的音韵范畴中同时利用对工场噪音也能感受到美的听觉特性。《机械》之后,横光又以《家徽》等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主义文学的探索。之后,发表了针对私小说的《纯粹小说论》,主张“用作者的眼睛”来表现自我意识的深层形象,完成了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小说《家族会议》。同年二月,横光赴巴黎回国之后,开始着手撰写长篇小说《旅愁》。
横光曾批评田山花袋和正宗白鸟等作家的文体是令人们感到绝望的,并主张所谓象征是将人形式化、构图化,在表现作者的世界观时应该基于时代感觉、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而时代感觉也绝不是时代的退步。横光所强调的这些理论,与他反对从人生观角度进行创作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另外,同是新感觉派核心人物的川端康成曾指出在横光文学中随处可见拟人手法的描写,“作者的主观分散成无数的片段,跃入所有的对象之中”,也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赋予万物以生命体征。
可以说,新感觉派时代是日本近代文学对历史上形成的被制度化的知觉与表象体系提出异议的年代。1925年3月,横光在《文艺时代》刊登了《感觉活动——给予对感觉活动和感觉作品非难的驳斥》一文,提出了以自我认知为基础的认识论,为新感觉文学后来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尽管这样的文学志向,与川端在两个月前发表的《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中所提倡的主观基础上的“主客观一致主义”存在着明显差异,日本学术界仍然普遍认为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形为横光,影为川端”,横光利一的文学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川端康成本人也说道:“新感觉的时代,是横光利一的时代。假如没有横光及其作品的存在,也许就没有新感觉派的名称,也就没有新感觉派运动。”[3]17
二、“新感觉”论争
新感觉派以与以往的近代文学的不同,在关东大地震后作为新军和先锋部队,揭开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帷幕。它的源头是将分裂的思想形式化、热衷于将其行为和心理的图式化进一步深入。作为新感觉的骁将,横光反对自然主义的写实,以坚定的意志试图超越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无疑是勇敢地将这一切构想付诸实践的作家。继1925年10月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妻》之后,接下来的3年里,横光始终将家庭题材作为新感觉文学实践的重要内容,创作出了短篇小说《春天乘着马车来》《飞蛾无所不在》《花园的思想》《火点燃的烟》,以及戏剧《测量幸福的机器》等,构成了脍炙人口的“病妻系列”文学。对此,横光本人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仍是新感觉(文学)”“写完这封信之前,我的泪水已决堤。请不要对此鄙视。即使是新感觉,它的泪水也来源自于双眼。”[4]73
从基于事实的创作角度来看,以《春天乘着马车来》与《花园的思想》为主的“病妻系列”与横光以往的文学相比的确是个特例。“《春天乘着马车来》《花园的思想》等,以及以妻子去世和新婚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等,都是横光细腻的爱情受到新感觉派风格的装饰与想象的干扰后,创作出的生动作品。”[5]44也就是说,在横光的这类病妻题材的小说中,至少包含了两个要素:“新感觉”与“基于事实之上的质朴情感”。在《春天乘着马车来》这篇作品发表的41年后,保昌正夫曾这样相对客观地给予了评价:“《春天乘着马车来》是横光的‘新感觉时代’中应当被纪念的一部作品。它内里所包含着的作家温和的秉性和质朴的品格,与‘新感觉’的表现技巧浑然天成,成为了那个时期的最成功之作。”[6]51而同样作为新感觉派文学末期的家庭题材小说,《花园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春天乘着马车来》的续篇。二者既有相似的关联之处,又具备各自的特色。较之《春天乘着马车来》,《花园的思想》众说纷纭的感觉更突出一些。不仅涉及写作手法,而且对新感觉的小说特点也提出了诸多评说,在上世纪30年代又一次引发了日本学术界关于“新感觉”的激烈论争。
首先,反对把这篇小说列入新感觉派文学的言说不绝于耳,“《春天乘着马车来》与《花园的思想》两篇中的美感,既不属于新感觉派,也不属于反自然主义,而偏向于描述人性中美妙的部分。”“令人感兴趣的是,那样以传统风格为主题的作品,作为大震灾的新时代文学应运而生。”[7]2而在另一些肯定这部作品仍属于新感觉文学的评说中,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以由良君美为代表的学者给予了较高赞誉:“这是一部使横光后期创作中必然出现的回归传统与‘新感觉派’的写作特点在紧密的结构中得到高度融合的罕见的作品。”[8]25肯定了作品中真实与幻想的有机结合与灵活转换,文体上把写实与虚构部分完全区分。同时,“妻子深沉的爱和面对死亡的抵抗等人间情感,还是穿透了这种外壳放出光芒。”[9]27
而另一部分从写实主义的文学观出发的评论者,则对《花园的思想》表现出了较低的接受度。认为尽管结尾处充满了新感觉赋予的美感,但若能在内容上再加以深化、增加写实描写的话会令小说内容更加充实;尽管通篇始终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技巧,但略有堆砌之嫌,缺乏真情实感。不难看出,将这场论争的焦点集中在作品内容的学者,并非否定其新感觉的写作手法,而是在普遍认同新感觉所产生的美感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小说中如何将新感觉派主张与传统的家庭题材有效地融合。
无论《春天乘着马车来》还是《花园的思想》,都是大地震后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目全新的家庭题材的产物,也是日本现代文学起点上应该肯定的充满创新精神的代表作。横光运用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在传统的病妻题材基础上,用花朵的美丽色彩点缀出人与人之间的片片真情,创作成系列的极具美感的篇章。对于生存在这个悲惨世界中人的形象,横光并没有采用单一的感觉模式去表现,而选择了质朴的写实与抒情风格。在情感叙述中赋予了“悲伤”复杂的样态。这两篇小说始终在写实中贯穿了横光式的感觉表现,较之传统的自然主义写实小说别出一格。
三、崭新元素
横光病妻物语系列在艺术上被普遍认可,不仅因为采用了悼念妻子的家庭题材,容易触及读者内心,同时也是典型的横光式的新感觉派文学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时期作品擅长从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角度去感受现实世界,并试图从中突出物质存在的不稳定性。《春天乘着马车来》的夫妻对话中,穿插了男主人公的视线。他把复杂情感压抑在内心之中,表现出对病重妻子深沉的爱。《花园的思想》中,男主人公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了。他眼中的妻子仿佛成为“辗转于生死之间的怪物”,自己则成了“情感完全被磨碎的机器”。
《春天乘着马车来》由五部分构成。全篇贯穿了病重的妻子和丈夫之间频繁的对话,这也是作品有别于《花园的思想》的明显特征。这对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情绪包括心理的变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话写得恰如其人、十分独到。第一部分的开头这样写道:“‘啊,你看,那棵松叶最近总是闪着漂亮的光泽’。妻子说。‘你在看松树啊’,‘我在看乌龟呢。’”这段对话尽管是在同一自然场景中发生的,但是关注自然的视点不同,分明是人的心境不同所致。在人际关系图式里极为特殊的夫妻关系中,这样的艺术捕捉无疑是敏锐的、深刻的。夫妻之间的空洞感和距离感也因此油然而生。
作品中妻子躺在家中的病榻上,透过栅栏般的床栏窥视身旁的丈夫。对丈夫的爱越深,便愈加妒忌和猜忌,并由于失去自由产生了“栅栏理论”,怪罪丈夫“你是个除了二十四小时工作以外什么都不考虑的人,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身为作家的丈夫为了生计埋头在书房里,为的是暂时忘掉妻子以便专心致志地完成约稿。丈夫的所为,使夫妻关系在空间上产生了距离。这对“在那里躺着”、身体被“栅栏”所束缚的妻子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结果导致了两个人对话的非协调性的出现。这是病态的人必然出现的病态的心理,同时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限定为自我为中心,永远无法真正地沟通,完全丧失了相互间的信任。
在小说的结构设计上,也突破了既往的新感觉小说中较为单一的模式,将感性与理性有机地结合,完成了“新感觉”中的主客统一。
值得提及的是这篇小说对疾病规律的细节描写在作品结构中起到了尤为特殊的作用。正常人与患者的日常生活规律是明显不同的,这种不同是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介质。横光利一在生活写实的无意识状态下,通过不同细节营造了特殊环境与人物性格、心理包括命运的整体关联,显示了“新感觉”技巧在真实表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样态。小说的前半部分频繁出现的夫妻争吵的场面,以重复性表现了人的承受能力的局限性。
四、修辞与场景
“所谓词语是外在的。闪光的词语可以为内容带来更多的共鸣。因此我喜爱词语,喜爱闪光的外表。我们称光鲜的词语为象征,因此我热爱象征。象征就是使内在发光的外表。用来称量闪光的象征的存在,我把它叫做新感觉派”[10]28。可以看出,横光对新感觉派的界定是源自于对词语的称量的,对于横光来说,“新感觉派”时代就是“全力关注如何用文字表现象征的时代”。横光的理念与保尔·瓦雷里提出的“象征是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方式”是一致的*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法国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诗人、文艺理论家。他的诗耽于哲理,倾向于内心真实,追求形式的完美。作品有《旧诗稿》(1890—1900)、《年轻的命运女神》(1917)、《幻美集》(1922)等,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认为寓意之美是基本的美学形式,因此应当把目光放在词汇或其他象征物所代表的意义上面,以象征来激起某种特殊的情感[11]1-10。
事实上,新感觉派文学的确对象征极为重视。自1925年2月,横光利一在《文艺时代》上刊登了《新感觉论》(原名《感觉活动》)一文,接下来的约10年间,这种以象征为主的“认识论”一直是新感觉文学理论的基磐。在家庭题材的小说中,横光也不例外地如同以往一样,使用了大量的象征表现。比如《花园的思想》中对大海的不同的描写,也是夫妻二人面对命运起伏的象征。“他从没有想过要躲避不断袭向自己的痛苦浪潮。袭来的这些不同波浪,好像在自己的肉体存在的时候就已经活跃了。”无论现实中的、抑或用作比喻的“海”和“波浪”,给予他和妻子的,无不是粗暴与痛苦的感受。
在这篇小说中所展现的新感觉派的自然描写技巧,与写实手法紧密结合,表明了横光所展现的新感觉文学并非把修辞作为吸引读者的唯一手段,而是依据作品的具体需求,使用不同的叙事语言,以完成艺术所需的语言再建的实践活动。
相对于《春天乘着马车来》中较为单薄的人物和单调的场景设置,《花园的思想》的场景则从家宅转换到郊外山顶上一所花园般的结核病院,人物也添加了医生、护士、患者以及山下的农民。因此,《花园的思想》对人物的语言与心理描写更具备外部的条件。
小说以山顶上花园般的肺结核医院为舞台,同时又设置了山下的渔村以及建在山脚边支撑着全村人生活的渔场。“花园”和“渔村”的对立存在,是疾病和健康的对立存在的隐喻与暗示,注定了作品的悲剧色彩和现实生活中的空虚感。病重的妻子一直得到花园里所有人的呵护,病房中放满了采集来的各种鲜花。鲜花与妻子的并存,与世纪末欧洲的艺术家们象征主义美学思想异曲同工,也是“新感觉”之下的一种反差。妻子的端庄与病态,同样是一种日本式的“物哀”。类似的艺术手法,还出现在同期创作的《飞蛾无处不在》《算计的女子》等作品中。
横光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与力学相关的动态描写,可以理解为这是基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文学想象。从《头与腹》的快速列车,到《上海》中对街市、巷口的描写,都展现出场景与人物之间的动态关系,即“将文学科学化的可能性”。
因此,崭新的场景设置不仅提供了丰富的隐喻与象征,同时也使人物的语言与心理动态达到了有效的融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学者三井小夜认为,在照顾患者的场景中往往更容易产生能够将孤立的个体紧密结合的力量,使“围绕着个体的外部环境以及个体之间的关联”[12]75成为突出的焦点。可以说,正是因为《花园的思想》中设置了更丰富的场景,使得诸多人物形象得以丰盈和具化,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也更加细腻地体现出其心理状态与微妙的变化。以家庭为题材的“病妻系列”文学作品,无一不体现了作家横光对妻子深切的哀思与悼念。坂口幸弘曾提出对于失去至亲的人们需要通过“悲伤治疗”去减少其心理伤痛,以进行有效的心理重建[13]183。从这个角度来说,横光的家庭题材小说不仅是他对新感觉文学的实践,也是关于他内心世界的一张真实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