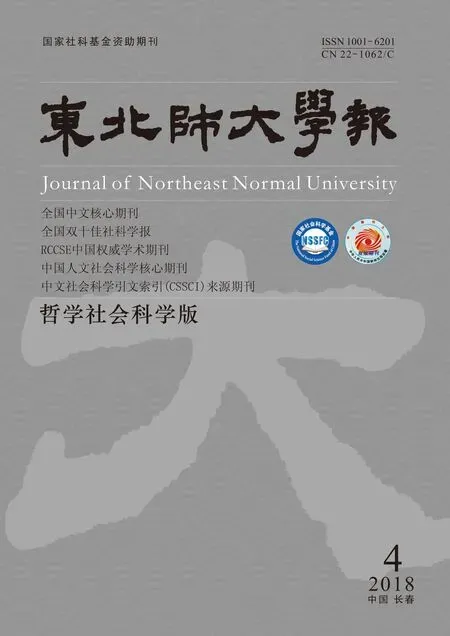改革开放40年舞蹈创作作品类型分析
刘 炼
(东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一、改革开放40年舞蹈创作审美尺度的变化
所谓“审美尺度”,在A.A.别利亚耶夫等人所编撰的《美学辞典》中具有双重涵义:一是艺术品在形象制作方面的规范或传统;二是作为人内在的评价标准[1]116。从定义中可知,审美尺度既是人内在的评价标准,又可衡量评价一件艺术品的创作。探讨舞蹈创作的变化,溯其根源,应该从人的审美变化开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格局,社会历史发生深刻转型,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由此肇始,中国舞蹈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呈现出丰富的样貌与全新的律动。其一,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愈发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生产与贸易过程,并长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率,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日益扩大与深入,其中一个突出表征即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互派留学生与专家学者。一方面,我国留学西方的人数逐渐增多;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外籍学生与专家学者来华交流,甚至还有一些外籍教师在国内担任舞蹈教学工作。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赵汝衡、金星等舞蹈家接连出访,为国内带回新的舞蹈思想、理论及实践经验,并融入他们的舞蹈创作当中,在国内引发一系列回应、延伸与深化拓展。这样的交流活动为中外舞者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契机,使中国舞者对当代西方舞蹈文化的发展现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其二,在全面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精神生活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匮乏走向丰裕。正是在文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现当代舞蹈中“不泯灭个性,讲求动作气场一致,动作状态明确的表演形式”反倒比“动作的整齐化一”更受追捧。其三,人民的思想从相对封闭与禁锢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国外新事物接踵而至、异彩纷呈,国人思想受到了各式各样观念的冲击,民众视野得到拓展,观念得以革新,更加追求个性的展现。故此,人民巨大的创造力得到了解放。在1980年全国首届舞蹈比赛中,作品《希望》就率先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作品中运用现代舞的创作手法,以抽象的、概括力极强的肢体动作语汇,将人类痛苦、失落、挣扎、迷茫、奋斗、期望等复杂情绪表现得十分到位,使观者产生广泛的联想。整部作品以看似不可思议的表现手法,实现了对人类顽强拼搏、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这种新样式的呈现,为改革开放以后作品的创作开拓了新思路。
上述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推动着人们审美的变化,而作为衡量舞蹈作品好坏的审美尺度也自然受到影响,随之变动不定。在这样一个全面开放的时期,丰富、芜杂乃至混乱成为社会文化结构上的特征。从舞蹈作品的创作来看,可谓新潮翻涌、乱云飞渡,有脍炙人口的,有标新立异的,有盲从跟风的,有注重形式而脱离内容的,有注重数量而轻视品质的。这一系列变化虽然打开了舞蹈创作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局面,带来形式与经验的丰富性,但也不免出现泥沙俱下、芜杂不齐的面貌。在此之中虽有一些高标准的优秀舞蹈作品,但也存在盲目跟风下作品质量下降的问题。我们不能被乱花迷眼,迷失于种种艺术风格、形式与经验的玩赏之中,而是应当形成更高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决断力。目前,有关舞蹈需要重质而不是量的探讨已经逐渐增多,这也充分反映出舞蹈工作者们已经意识到在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吁求建立起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审美尺度。舞蹈创作中的审美尺度与舞蹈的创作结果有着直接的联系,审美尺度能够规范与指导作品的创作;同样,舞蹈作品也反映出某种审美尺度的存在。舞蹈创作的审美尺度在变,才形成了舞蹈创作过程中一些典型现象的出现。
二、改革开放40年舞蹈创作发展阶段及其派生的作品类型
(一)改革开放40年舞蹈创作发展的阶段
1.着眼清流求复兴
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处于70—80年代转型期的人们普遍体验到一种历史创伤与文化断裂感,迅速形成了告别“灰色而沉闷的70年代”的社会愿望,在改革开放的前景下,期盼着新时代清新气息的吹入。在精神解放的总体氛围中,文艺工作者普遍认为创作的“春天”已经到来,踊跃参与到文艺复兴的想象与进程当中。真正的复兴,迫切需要重建历史主体,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舞蹈作为精神文化范畴下的一个艺术门类,显然是可以让人民从中汲取精神养分的。它长期以来都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肩负着社会的精神想象,为民族国家的开创与建设提供表意手段和动员手段。因此,这一时期内的舞蹈创作重心比较倾向于树立典型英雄人物形象,弘扬、讴歌进取精神,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与历史规划提供表达方式与形象资源。通过这样一股“清流”的注入,成功慰藉了人民的心灵,重燃人民在复兴路上的希望,激发人民心中热切的追求,鼓舞人民为繁荣的景象贡献力量。以舞蹈作品作为复兴萌芽时期激励人民思想的重要手段,在达到借助舞蹈作品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实现了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并且教育人民的目的。
2.着眼中西合流求创新
1980年代,中国舞蹈同其他领域一样,自感长期“脱钩”,开始寻求“与世界接轨”,别求新声于异邦,转化为自身的创新资源。当此之时,西方现代舞再度传入中国,其新颖的艺术观念、创作理论、表演形式及训练方法,给中国舞蹈界带来较大的影响与冲击。西方现代舞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线性的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但在传播之初,由于相对封闭的国门并不能瞬间全然开放,加之中西方社会背景与思想观念的差异,我们对西方现代舞的接受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适应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舞蹈创作的两种面向:其一是尝试运用西方现代舞编舞技法,以其崭新的视角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其二就是基于我国优秀传统舞蹈形式,寻找其增长点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两者对立与碰击的张力场中,中国舞者对于西方创作理念的介入已经不能置之不理,同时也愈加深刻地认识到本土化经验的重要。中国民族民间舞、古典舞作为传统的舞蹈形式,其风格与独特的舞蹈语汇是我国民族舞蹈的灵魂,又是舞蹈创作中的根基,更需要被保留、传承下去。所以,对于西方舞者所传播的在舞蹈创编及舞蹈表演方面的观念,我们应当有选择性、判断性地拿来,并予以创造性转化。中国舞蹈对于外来舞蹈影响如何吸纳、汰选、转化与自我创造的问题,逐渐为中国舞蹈界所重视。自此,中国舞者们肩负起双重责任来完成舞蹈作品的创作,逐渐进入中西合流下的一种平衡状态。
3.着眼现实求发展
以“及物”的目光观照“现实”,向真切的时代生活掘进,是舞蹈创作的又一个新出发点。此一“现实”,与其说是经典现实主义美学规范中的现实,毋宁说是面向现实生活的现实,是“生活”视野下的现实,是更贴近民众的“现时”/“现世”/“现事”。这类现实题材的创作从普通民众的生活出发,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出真实、朴素的情感,反映和表现或琐碎或突出的问题与事件。它并非空洞的符号搬演,并非“不及物”的高蹈抒情与浪漫想象,并非抽象化、非历史性的主题表达。相反,它是“及物”与“落地”的,是介入现实境况并深入当代生活的,在丰盈的日常经验与细节中寄寓情理、刻画形象。这类创作真诚地向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敞开,向真实的本土生存与时代境遇敞开,能够容纳丰富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经验,拓展了作品的表达空间,增添了现实性、生活性与人民性的活力。这类创作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愈加被重视和需要。
(二)改革开放40年舞蹈创作发展中的作品类型及特点
1.以表现传统故事为主
在着眼清流求复兴的面向/阶段中,舞蹈创作派生出表现传统故事的作品类型。例如,首演于1979年的舞剧作品《丝路花雨》,它取材于敦煌壁画上的内容,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将壁画中反弹琵琶等优美的舞姿形象活现于舞台之上。它作为中国舞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中国敦煌舞流派的产生及确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舞剧相继在朝鲜、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上演,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舞蹈作品对外交流创造了良好开端,推助了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选材于《宋史·韩世忠传》的作品《金山战鼓》,讲述了南宋名将梁红玉带领两个儿子擂鼓助战、抗击金军的光辉事迹,表现出梁红玉的赤胆忠心、不畏艰险,颂扬其将国家命运当作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的高尚品质。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应被人们忘怀的精神,其激励了人民要以国家的富强为己任,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贡献力量。同年创作出来的双人舞作品《再见吧!妈妈》,讲述了一段青年战士离开家乡、告别母亲而奔赴战场的故事。表演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战士参军时与母亲的惜别、儿子对母亲的思念、母亲对儿子的挂念等。青年战士既有作为儿子依偎在母亲怀中的一面,同时,作为战士,他又必须肩负起保卫国家、捍卫祖国荣誉的使命。两种情感的碰撞触动着人们的心灵。这样一位不知名的青年战士,是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士们真实的写照,是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使处于改革开放和平时期的人民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在1986年创作的《盛京建鼓》中,由于建鼓是满族人民祭祖时的一种表演形式,因此整个表演营造出一种严肃、端庄的祭祀场景。此外,为了将满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反映于舞台之上,作品以古典乐舞的表演风格为主来进行表现。作品中无论男女舞者均富有鲜明的民族精神气质,这更让观者看到满族后代对先辈们的无限敬重之情。最后,在同年创作出来的作品《奔腾》中,表现了烈日之下,一群蒙古青年在辽阔的草原上策马奔腾。他们欢腾着,情绪高亢,运用典型的蒙古族舞蹈动作语汇将作品表现得洒脱豪放。伴着轻快明朗的节奏,他们时而在蓝天白云下起舞,时而结伴成群赛跑,呈现出一个民族美好的精神面貌,也寓意着整个中华民族将以激昂奋进的精神状态进行万里奔腾。作品以小见大,以草原青年牧民的真实情感折射出在祖国焕然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全国人民奋发进取、昂扬奔腾的精神风貌。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这一类舞蹈作品的特点:偏向于传统中国舞的表现形式,具有鼓舞人心的重要意义。
2.以表现军旅故事为主
在着眼中西合流求创新的面向/阶段中,舞蹈创作派生出表现军旅故事的作品类型。例如,作品《走·跑·跳》提炼并运用了军队生活中走、跑、跳三种典型状态,表演过程中走、跑、跳层次分明,其动作语汇已经不受传统舞蹈语汇所限制;分别在走、跑、跳上开发出动作的新样式,其中包括对正步练习、跑步前进、跳跃障碍等内容的表现,以流畅有序的连接、丰富的动作语汇完成对军队中训练生活的表现,这是极具创新意义的。它让观者看到了战士的成长历程:战士们以顽强的意志应对重重困难,并最终成为合格的战士。2001年,与《走·跑·跳》表演内容及形式上都有些相似的作品《穿越》首演,它将军旅生活中的种种状态一一呈现。在训练过程中战士们突破自身极限,为穿越火线做好了准备。其表演中以跳跃的动作为主,旨在表现出日常训练中的形态。此外,它在多维空间上的动作表现,彰显出个体与群体之间肢体语言的特殊魅力。双人舞作品《士兵兄弟》,完成了一次突破性的创作,它不是依靠人数众多来烘托壮阔场面,从而吸引观者,而是凭借作品中前所未有的表现方式达到振奋人心的效果。其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源于西方国家的“街头真人行为造型艺术”,以铜人雕塑的装扮、破旧的军装、士兵身上背挎的枪支弹药来增加人物形象的年代感,令形象变得更加逼真,成为其成功表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次,在道具的使用上,由于道具的限制反而使两名舞者的动作更加丰富,创编出很多呈倾斜状的造型,赋予舞姿造型极强的表现力。以上两方面的创新运用,促使作品中所表现的士兵兄弟共同奔赴战场、在战场上互帮互助、遭遇伏击时不离不弃的一系列过程更加真实可信、生动形象。同年,作品《士兵与枪》中,建立起士兵与常伴左右的枪之间的联系:枪虽是武器,但更是与士兵朝夕相处的好友。作品中枪已经不只是士兵形象的符号,它已融于士兵的身体中。其中取枪、擦枪、拆卸零件、托枪行进等动作,已经不只是士兵们与冷酷的军械一同进行的日常军事技能训练,更是他们与枪之间的心灵交流与对话。多样的持枪动作、整齐划一的队形变化,士兵在枪的陪伴下,白天训练、深夜同眠、保卫家园等场景呈现于观者面前;更在枪的映衬下尽显士兵的飒爽英姿。最后,作品《红蓝军》作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舞蹈作品,虽然同样是从军事训练中提取素材,但在选材上已突破传统模式,在内容的表现方式上更是焕然一新。舞台的空间被红蓝两军分割出多种空间,有红军的侦查、蓝军的穿梭等。其表现的故事情节又是起伏跌宕的,过程中有红军的失利,但并不是永久的失败,他们重新休整、再鼓士气与蓝军再次交锋。出乎意料的是结尾处握手言和的处理,通过这样的情节处理来说明红蓝军同是祖国的军队,他们共同保卫祖国,充分展现中国军人风采。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这一类舞蹈作品的特点:军旅题材的舞蹈成为中国舞蹈界内的一枝独秀,具有代表性。它有思想、敢突破、敢创新,对于精神层面上的表达是始终不变的中心。其中既有激扬向上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运用了突破传统的创新表现手法;着力表现中国军人的信念力、意志力、智慧力。
3.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
在着眼现实求发展的面向/阶段中,舞蹈创作派生出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类型。例如,创作于2009年的作品《过早》讲述的是一对卖早点的夫妇的日常琐事,运用诙谐的音乐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生活在市井中普通市民相互理解、互敬互爱、乐观向上的和谐画面。作品将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形象,时而会有买早点、吃早点等动作造型上的停顿。作品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以动静结合的方式表现要突出的内容。当人们集体散去时垃圾散落一地,这一场景让人不禁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陋习;同时,也引发出一段夫妻之间相互关爱之情与邻里之间的友情,这两种感情相互交织,令观者时而被夫妻间的感情打动,时而又回到市井间的和谐情境。作品《大山支教》则表现了赴大山支教的男教师与学生们的生活情景。在教师耐心教书、与学生一起干农活、给学生缝补衣服等生活细节的表现中,教师逐渐与学生们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一边是母亲的期盼,一边是学生们的挽留,令教师陷入是否离开的两难选择。最终,教师选择留在山中,由此塑造出一名典型的大爱无私的教师形象,其奉献精神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同时,作品也反映出大山深处、贫苦地区的孩子们对教育、知识的极度渴望。作品《进城2——返乡》以农民工返乡作为题材,三个急于返乡的人,面对一张车票,回家的强烈愿望让她们争抢最后一张返乡的车票。作品应用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动作,将人物内心焦急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在三人你争我抢中进入高潮部分,两名男民工决定将唯一一个返乡的机会让给女民工,那一瞬间农民工质朴与纯真的性格特征真实流露出来,感染着所有人,引起人们对打工群体的关注与关爱。2017年首演的作品《爷爷们》,展现出一种对老年人生活的新表现方式。它与以往不同,虽选取的是老年人们晚年生活情境,但作品中的老人形象是乐观向上、精力充沛的。蒙古族舞蹈中的硬肩、抖肩、提压腕都成为了爷爷们精神十足的表征。此外,一段作为插曲的广播,传播着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消息,这令老人们的精、气、神更足了,他们以坚定的舞步大步前进,表达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未来的殷切期望。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这一类舞蹈作品的特点:关注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暗喻编者欲抒之意,形成编导与观者之间的沟通;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叙事性强,围绕主旋律,烘托主题思想。
三、新时代舞蹈创作的新导向
当前,中国文化已步入“新时代文化”的历史阶段。对于舞蹈艺术而言,新时代文化的改革发展呼唤其更强的形式创新创造能力。这种创新创造既不能凭空而来,也并非任意而去。同时,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舞蹈创作如何面向未来,如何寻找到与新时代相应的形式与内容,成为广大舞蹈工作者关切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应立足当代中国现实,扎根人民生活世界,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此即新时代舞蹈创作的新导向。
(一)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创作起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不仅为当前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确立了根本立足点。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而创新创造不是游离于时代之外的生造,不能建筑在某种超历史的抽象观念之上,不能脱离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实践脉络,不能罔顾新历史情势下的新现实、新情况与新问题。无源无本的盲目“创新”与袭故蹈常、同质化现象明显等舞蹈创作上的问题,实乃一枚硬币的两面,皆反映出创作者对当前时代深刻变革的盲目聋聩,缺乏对新时代的洞察力、沟通力与表达力。归根到底,这是舞蹈创作思想的落脚点出现了偏差。从“逻辑先在性”的角度看,舞蹈创新思路的落脚点应是新时代的社会现实、新时代的生活本身以及新时代中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而非某种舞蹈艺术的意识、思想和观念。前者乃是舞蹈艺术创新之原初性、根本性的依据,后者只是派生性的。对此问题,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152
舞蹈艺术的创新创造,不能靠玩概念、秀观念以及炮制五花八门的口号,抑或随手拾取所谓“国际”时髦理念,其不应成为缺乏历史基础的艺术观念游戏,不应变为脱离“现实的人”的身体语言游戏。借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这是“头足倒置”的“创新”。有鉴于此,舞蹈创作者应“从人间升到天国”,而非“从天国降到人间”。即是说,我们要立足于新时代,把握新方位,担负新使命,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创作的现实依据与逻辑起点,创作出与新时代相应的高质量、多样化的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的作品着眼新变,聆听新声,能够正确认识并深刻揭示当下中国的主要矛盾,充分表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理想,积极参与到“美好生活”的界定、探索与追求中,同时也充分揭露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产生的种种问题。
(二)确立舞蹈创作的人民性品格
今日舞蹈创作者所面对的是“多元中国”,是多样而复杂的“中国经验”。诚然,“多元中国”是众声喧哗、多重关系交缠的空间,也是不断变化、多向运动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文化与政治的根基与源流。这一根基与源流即是中国人民。“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重申了“人民”范畴,并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中心论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据此,我们要确立舞蹈创作的人民性品格,即以“人民性”作为舞蹈创作的情感倾向与价值立场,面向人民的文化需求与审美要求,注重自下而上的历史,深入人民的现实生活,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展示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
“多元中国”作为开放的空间,“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能动的力量,不断以其变化来改变经验,创造故事。”[3]56我们的舞蹈创作怎样把握其中变动不居、错综复杂的经验,如何讲出其中生动鲜活、引人入胜的故事?换言之,舞蹈怎样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表达“中国经验”?我们如何在舞蹈与新时代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形式与内容?答案即是扎根于今日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与生存现实。这里的“中国人民”并非抽象的概念或现成性的存在,“不可能被任何机械、僵化的本质论表述所把握”,其是“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实体和主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创造自己的“新人”,超越了固有的、体制化的历史、文化与地域范畴,“带有一种突破既有社会文化和政治框架的形式”[4]15。这呼唤着能够为新人经验赋形的舞蹈形式的创新创造。可以说,坚持舞蹈创作的人民性品格,内在地要求着形式创新,也引导着创新的方向。同时,“中国故事”是否讲得好,其中承载的“中国经验”是否被认同,评价与检验的标准也在于人民。只有坚持舞蹈创作的人民性品格,确立人民本位,坚持人民中心,才能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中、语言杂多的局面下找到主导方向,才能实现“有根”的舞蹈艺术创新。
(三)建立中国舞蹈的文化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舞蹈发展史,是在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特殊与普遍多重辩证关系中不断重建“文化自信”的历史,是一个在古今中西复杂交缠中不断重构主体性的历程。在此之中,既有过去/未来的时间张力,也有本土/异邦的空间矛盾,更充满了自我与他人之间对话的喧嚣,而中国舞蹈始终展现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对自我同一性、文化自主性的关切与追求一以贯之。这与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进程相应合,乃是“以基体自身的内因为契机的辩证法式的展开”。我们的文化自信即建筑在这开放、博大、延续的中国“基体”之上,而我们在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创新创造能力也依托于此一基体。同样,新时代的舞蹈创作亦不例外,“要从中国的艺术文化根基出发,发现自身独异的根本气质,又使之生成出普遍性启示的意义。”[5]2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并深刻阐明文化自信这一新时代课题。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正是当下新时代对舞蹈创作提出的需求和愿景。
邯郸学步固不可取,但故步自封也绝非文化自信的表现,反倒反映出失掉自信力之后的焦虑。建立中国舞蹈的文化自信,要求舞蹈创作者既有对民族传统形式的信心,又不乏开放的世界眼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6]57这呼唤“面向未来”的底气与智慧,要求敢于“拿来”:一方面拿来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来”,“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令新质发于旧胎;另一方面拿来国外进步的文化资源,通过翻译,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合理地吸收“进来”[7]52,把中外的差异性包含在中国基体自身同一性的内在辩证法之中。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伊始,中国舞蹈与时代一起走过了自身高速发展、全面开放并不断重构主体性的历程。从总体上看,舞蹈的形式与内容的转变与社会历史的转型一样剧烈而复杂,其间新机迭现、异彩纷呈。改革开放40年,中国舞蹈的创作实践收获颇丰、实绩斐然,在时间上辩证发展,在空间上参差多态,为其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与颇高的创作起点。40年来,中国舞蹈创作在多重面向/阶段中所包含的多种矛盾与张力关系,其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必将在新时代的历史性展开中走向更高的综合、寻找到更新的统一。但这一切不会随着时间的机械推进而自动到场、自然开显,它需要我们自觉地在新时代新导向之下投入到时间中去,通过集体的艺术实践把它创造出来。这要求舞蹈创作立足当代中国现实,扎根人民生活世界,依托中华优秀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实现足以表现中国文明复兴的形式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