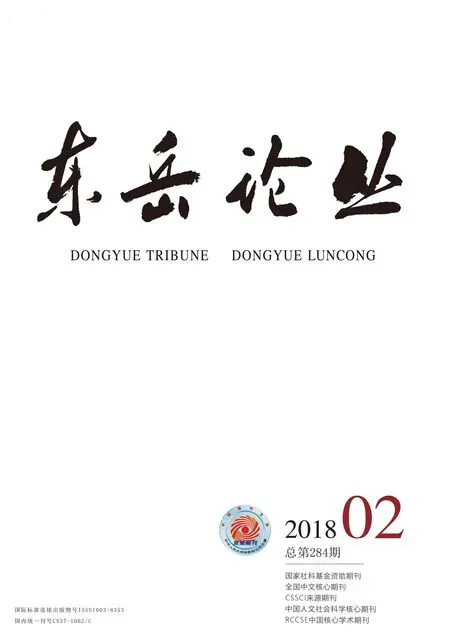鲁迅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探析
颜景高
(山东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02)
一、“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塑造
鲁迅不是积极“投身政治”的职业革命家,也不是追求“独善其身”的书斋学者,但去世后“鲁迅形象”被塑造成迥然相异的两幅面孔。一种观点认为,鲁迅从属于政治人物,他的革命思想熠熠发光;相反的观点认为,鲁迅属于文人类型,根本不关涉政治。伊藤虎丸因而认为:“在中国一个时期里的鲁迅研究,就政治学与文学这个问题上,无疑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是专取战斗的革命家的鲁迅一面,以他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是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模式,力图按照他既成的‘主义’的距离大小和对共产党的忠诚程度,来确定他的位置,从而缩小乃至歪曲鲁迅,同样,就他的文学而言,或把中国革命束之高阁,来论他的文学,或以讨厌政治的姿态把政治和文学割裂开来,这两者都是人们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2页。
从政治化诠释的维度而言,“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塑造源于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革命形势,正如竹内好所指认:“所谓‘革命’,如果广义上说,就是政治。”*[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4页,第134-135页。鲁迅所面临的正是旧中国军阀割据和国民党专制的恐怖时代,他坚定拥护推动中国变革的革命运动,因而他的杂文犹如匕首一般投向实施黑暗统治的独裁者,希冀警醒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中国人。鲁迅去世后依然严峻的中国革命形势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决定了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塑造愈发彰显,20世纪40年代,鲁迅已经被塑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象征,或者说文化圣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鲁迅形象”遭到政治绑架,被扭曲为打倒“牛鬼蛇神”的精神棍子。
吊诡的是,“鲁迅形象”的“去政治化”塑造,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达,这集中体现为以郑学稼为代表的右翼学者们发起的鲁迅研究思潮,他说:“所谓鲁迅的真正价值,就是他以文学家身份,指摘中国旧社会的残渣。他是这工作的优秀者,他又是这工作在文艺上的唯一完成者。我有这种感觉:如果没有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混乱情况误了他,他会在写实文学中,占了一个重要地位。也许他会成为我们的福楼拜。至于今日人们用‘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或‘青年导师’等尊称他,这是一点不相干的。”*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这一派学者因循中国文人依附于当权者的旧传统,将出现的新文化现象统统贬斥为病态文化,进而认定左翼文学和反抗文学是造成社会混乱的祸根,他们虽然认可鲁迅前期作品的文学价值,但彻底否认鲁迅后期作品的社会意义。
鲁迅形象的变迁当然与鲁迅研究者自身的理论认知和价值取向相关,从本质而言,这源于学者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根本误读,正如竹内好所指认:“迎合政治或白眼看待政治,都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除自己的影子……真正的文学不反对政治,只是唾弃由政治支配的文学。”④[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4页,第134-135页。“鲁迅形象”的塑造历程清晰表明,文学的“政治化”“非政治化”以及“泛政治化”都无法从实质上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因为“图解政治”真正束缚的是文学,“脱离政治”真正受限的还是文学,“泛政治化”真正削弱的也是文学,进而言之,极端的政治化立场或者极端的去政治化立场塑造的“鲁迅形象”都是虚幻的,因为这种立场本身就没能脱离“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传统窠臼。
二、鲁迅的“文学与政治”观
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文学作品的政治化传统由来已久。从西方政治文学的源头来看,柏拉图开创了文学政治化的先河,他认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政治标准”,即能够推进社会各阶层的等级教育,促进社会风气的净化,鉴于当时“哲学与诗”的斗争特别激烈,柏拉图极力主张驱逐“诗人”的存在,因而朱光潜先生认为“这场斗争骨子里还是政治斗争”*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从中国政治文学的源头来看,孔子非常重视文学作品弘扬德政的作用,他主张“为政以德”,并强调这种美德的养成可以通过文艺作品熏陶。时至今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文学远离政治的呼吁不断高涨,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永远是一个真问题和新问题,它总是以新的内容和价值取向继续“在场”,正是在此意义上,竹内好认为对政治无所关心的鲁迅在“本质上”却是政治的。
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思想启蒙的使命和民族救亡的任务,使得文学和政治相互纠葛,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作出人生选择,不得不卷入纷繁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争论之中,正如弗·詹姆逊所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从精神特质的维度上说,鲁迅不是传统式的文人学者,他勇于批驳充斥着“瞒和骗”的士大夫传统,敢于戳穿为统治者效命的“聪明人”的真正面孔,致力于解剖中国文化熏陶的“帮闲”“帮忙”以及“帮凶”的本质,进而揭示中国“统治阶级争夺一把旧椅子”的历史真相。从思想启蒙的维度上说,鲁迅不是“西崽式”的启蒙主义者,他没有悲观的抛弃传统文化,而是延续着道家的疏狂精神和怀疑主义,坚守着“越文化”传统中的叛逆性和坚韧性,致力于破除封建专制传统中的“奴性”教化,争取实现“致人性于全”的“立人”目标。
鲁迅认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联,承认文学作品彰显的政治目的。在那个社会动荡的时代,鲁迅没有钻进象牙塔去研究艺术审美趣味,或者走向边城山林抒发怀古幽思,而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去承担当下的社会责任。
对于中国的“革命文学”,鲁迅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他并不认可“文学是革命先驱”或者“文学直接服膺于革命(政治)需要”的所谓“革命文学”,而是深入察觉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内在歧途”。正如马尔库塞所揭示:“革命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的统一,一种敌对的统一,艺术遵从必然性,然而又有其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并非革命的自由。艺术与革命在‘改造世界’即解放中,携起手来,但是,艺术在其实践中,并不放弃它自身的紧迫性,并不离开它自身的维度:艺术总是非操作性的东西。在艺术中,政治目标仅仅表现在审美形式的变形中。即便艺术家本人是‘介入的’,是一个革命家,但革命在作品中会付诸阙如。”*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
鲁迅反思了三个息息相关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文学?文学宣传的限度在哪里?文学与革命(政治)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其一,真正的革命者绝不是通过站队选择革命立场、表现革命姿态的人,因为空喊“革命文学”口号者的革命动机是可疑的,实际上,鲁迅十分反感玩弄革命口号的革命文学,他说:“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85页。进而言之,鲁迅认为革命文学绝不是革命的先驱,而只能是革命时代的产物,他认为恰恰是革命时代塑造了革命文学,而不是相反,因为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革命文学是由革命时代所开启的。
其二,鲁迅认同革命文学引领社会思潮的社会功能,但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文学自身的限度。一方面,革命文学家根本发挥不了、更别说超越或者替代职业革命家的社会功能,鲁迅指出:“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到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绝不是革命文艺家讲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6页,第115页,第115页。另一方面,文艺宣传往往陷入革命(政治)目的论所因袭的传统窠臼,被“国家观念”“民族英雄”以及“政治大局”等政治口号所支配,导致掌权者随意制定文艺宣传的“统一口径”,肆意更改“革命文学”发展的方向。
其三,鲁迅深入解析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悖论,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唯政治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于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⑤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6页,第115页,第115页。从本质上讲,政治要求的是异口同声的统一,而文学艺术体现的是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学是时代敏感的神经,文学家们往往成为不能被接受的“另类”,即使他们的言论表达了社会的一种趋势,“有时他们说的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⑥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6页,第115页,第115页。文艺家被误认为社会动乱的祸根,往往成为政局动荡的牺牲品,因为掌权者往往都在寻求垄断政治话语。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就体现的内容来讲,显然是很政治的,他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有代表性的文学者,也是就政治意义而言的,然而,其政治性却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7页。进而言之,鲁迅的文学体现的是“拒绝专制”的政治,彰显的是顺应“底层声音”的政治。
三、鲁迅开启的“底层政治”立场
中华帝国“超稳定”循环的历史结构表明,“统治权”的攫取俨然是中国传统统治阶级的终极目标,鲁迅指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8页。从权利归属的维度说,底层群众从来没有争取到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封建社会制度的“吃人”本质精巧地融入到等级统治的设计之中,并通过伦理道德的宣扬以及思想控制的遮蔽而代代传承。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破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体制的国家,构建人民参与的政治机制。吊诡的是,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没能够挽救旧中国的命运,反而催生了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人们生活更加困苦的恶果,鲁迅因此指出:“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第3卷),第34页。国民政府“形式化”的选举机制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利益,反而沦为政治专政的工具。
从意识形态的维度上说,政治专制主义的思想渗透已经侵入了“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因而鲁迅往往“更愿意做的乃是去揭示在这一传统的历史规定下中国人的实际人性状况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政治生态;而这才是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张松:《国民性批判与儒家传统之复兴——鲁迅思想在传统文化复兴时代的积极意义》,《东岳论丛》,2016年第11期。近代中国社会革命也没能消除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革命者、甚至革命的领导者也常常不自觉的陷入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宿命循环之中,诡异的是,革命者还往往心仪“新罗马城”“建立特勋”以及“最后的胜利”,进而天然带着“在上面看的姿态”,认为革命(政治)就是最伟大的、最终的事业,根本没有顾及、进而考量革命(政治)的初心,因而“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58页。唯有破除个人自由和解放的政治幻觉,彰显底层群众的政治意识,推进社会结构的转变,才能摧毁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
实际上,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底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因为唯有“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第120-122页。,用鲁迅的话说,“惟有民魂……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鲁迅:《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第3卷),第222页。唯有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对象,才能唤起我们不计身份阶层、不求升迁荣耀的政治参与意识,进而拒绝成为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看客”,这是一种属于民众的政治学,纵然很少能为社会大众所真正理解,正如竹内好所称谓的鲁迅政治学,“其政治性……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9页。这种政治拒绝的是政治专制的肆虐,宣扬的是底层政治的立场,正是在这种政治意蕴中,鲁迅笔下的“‘狂人’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原罪’(‘吃人’),才从审判者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获得治愈。”*[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第120-122页。这种“底层立场”以及从“下面看”的政治新视阈,才能决定性地开启现代政治秩序重建的新方向,这种社会变革纵然阻力重重,但既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研究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拓展,也应该是我们反思与再出发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