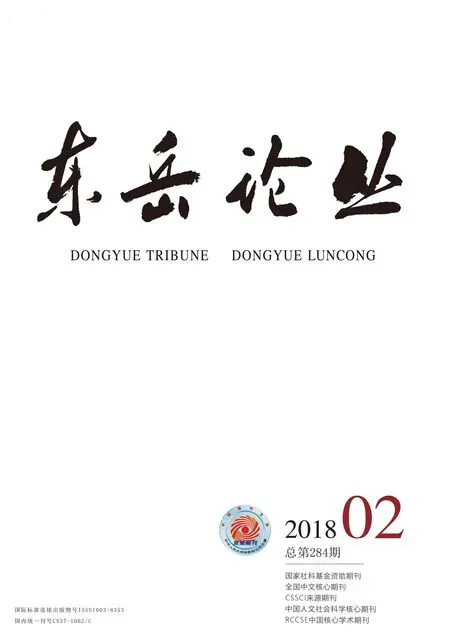幻想的工具化和乌托邦精神
——经典童话与好莱坞电影改编
李莹莹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近几年来,好莱坞电影市场出现了改编童话电影的热潮,一批改编自经典童话①由于论文篇幅所限,本文所指的经典童话(Classic Fairy Tale)指的是以《格林童话》为代表的与民间口传故事密切相关,具有传统的叙事特征和价值观念,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被人们所认可,普遍经历了“一个神话化的过程” (杰克·齐普斯《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的童话故事,并未将类似于《哈利·波特》这样的童话小说涵盖在内。的电影如《血红帽》(RedRidingHood2011)、《白雪公主与猎人》(SnowWhiteandtheHuntsman2012)、《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MirrorMirror2012)、《巨人捕手杰克》(JacktheGiantSlayer2013)、《冰雪奇缘》(Frozen2013)《沉睡魔咒》(Maleficent2014)、《灰姑娘》(Cinderella2015)、《猎神:冬日之战》(TheHuntsman:Winter’sWar2016)《美女与野兽》(BeautyandtheBeast2017)等电影,充分体现出好莱坞电影对于改编经典童话的重视。从电影史的发展来看,好莱坞从诞生之初就开始改编经典童话,其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好莱坞基本没有间断过对经典童话的改编。这种持续的、大量的对经典童话的改编无疑成为了一种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而有意思的是人们看待这一文化现象时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深受大众欢迎,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另一方面则是大部分评论家们对以迪斯尼电影为代表的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的严厉抨击。
评论家们对好莱坞改编电影的抨击与对作为文化工业的好莱坞电影的批判一脉相承,这种批判一方面批评好莱坞商业-工业化的电影忽视了电影的艺术性,使得电影成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批评好莱坞电影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紧密相连,传播了乐观主义、象征秩序回归的大团圆结局、个人主义、简单化的善恶二元论、否定他者的中心论等意识形态②[法]雷吉斯·迪布瓦:《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李丹丹、李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2-36页。。评论家们对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的批评多数集中于对迪斯尼童话改编电影的批判,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他认为沃尔特·迪斯尼(Walt Elias Disney)用现代技术给童话施下了一个咒语:“迪斯尼魔咒的主要魔力在于,他把童话制作成动画,就是为了通过投向银幕的形象所代表的虚假承诺来吸引观众,并转译他们潜藏着的乌托邦梦想和希冀。”*[美]杰克·齐普斯:《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种一边倒的批评,他们认为尽管好莱坞的童话改编电影不可避免地与商业和主流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并不代表这些电影一无是处。苏·肖特(Sue Short)扩大了经典童话改编电影的概念范围,运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ATU(Aarne-Thompson-Uther)分类工具挖掘好莱坞电影中的童话主题,并且试图找出这些主题在性别、道德观等方面的积极性*Short,Sue:Fairy Tale and Film:Old Tales with a New Spi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重审迪斯尼童话改编电影在特定时期对历史的积极影响。如道格拉斯·布罗德(Douglas Brode)就致力于为迪斯尼电影翻案,他的作品论证了迪斯尼电影在美国反主流文化和美国社会文化多元性等方面的正面影响*Brode,Douglas: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ouse:Race and Sex in Disney Entertainment.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9;Brode,Douglas:From Walt to Woodstock:How Disney Created the Countercultur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4.。这些研究的启发在于,在研究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的时候,应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分析具体文本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位置。但这些研究在为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辩护的时候,又有为论证观点而拔高文本的嫌疑,对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的看法仍有失偏颇。
本文力图站在更加公允的立场上看待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既要对好莱坞的文化工业特性保持警惕,看到其如何将幻想工具化,使之物化为一种商品的一面,也不排斥对蕴藏在好莱坞电影中乌托邦精神的发掘。
一、压抑乌托邦冲动
“乌托邦冲动” (Utopian impulse )这一术语是由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提出的,他认为“乌托邦冲动”不同于宏大的乌托邦计划,“这种冲动不是象征的而是寓言的……它表达乌托邦的欲望,并采取各种预想不到的、掩饰的、遮盖的、扭曲的方式。”*[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科幻的乌托邦理论》,选自《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苏湛,李广益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这一提法是对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乌托邦精神(Utopian spirit)的概括。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精神无处不在,它既存在于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这样的具体历史时刻之中,也存在于童话、寓言、建筑、白日梦等具体的形式之中。布洛赫十分看重童话这一形式,他认为童话故事中蕴含的乌托邦精神有助于去想象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使得人类摆脱当下走向“尚未”(not yet)的实现。对于童话而言,其乌托邦冲动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反抗现实和对“尚未”的期许。
童话中总是充斥着不满于现状(或与现状格格不入)的主人公,他们往往不满于既有的地位,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实现地位的提升。这种不满以及对现实的反抗正是乌托邦冲动的重要来源。童话故事中的乌托邦因素突出了人类对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体现在故事主人公们对现实压迫的反抗之上。布洛赫十分赞赏童话故事中弱者的聪明才智,他认为这种聪明不仅能让童话中的主人公道出现实的真相,而且使得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被看上去美好的现实所迷惑,并且最终获得幸福*Bloch E,Zipes J,Mecklenburg F: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Selected Essay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9.P169.。
而童话故事不仅让人意识到了反抗现实的重要性,童话中蕴含的乌托邦冲动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超越了现在,指向未来。这种未来就相当于布洛赫所说的“尚未”。表面看上去童话讲述的都是过去的事情,但实际上它关涉的却是人们梦想中更美好的未来。正如齐普斯所言:“童话故事的神奇意象和魔法能够使读者疏离日常生活和日常期待——如果它们与梦想和愿望结合起来的话,这些梦想和愿望就赋予了它们一种由童话故事的‘前假象’确定的新的特征,正是这个特征唤醒了那可能被压制的、需要表达的乌托邦意识。”*[美]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舒伟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文中谈到的“前假象”(Vor-Schein),是布洛赫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不同于“假象”,“前假象”指的是艺术作品对尚未形成的东西的预先描画,是“尚未”的本质。童话故事中蕴含的乌托邦冲动才是真正吸引人们不断重读童话的重要原因,意识到这种乌托邦冲动能够让人摆脱当下的束缚,对未来心存希望。
因此童话常常被认为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性表现为借助对更好世界的幻想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然而,当被改编到好莱坞电影中之后,童话的这种颠覆性遭到了压抑,童话中对未来的憧憬变成了对当下的确证,其中蕴藏的乌托邦冲动也在反复的模式化改编中被架空。
从表面上看,好莱坞改编的童话电影继承了童话故事中那些不满现状的主人公,如被后母迫害的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但好莱坞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却往往收编了他们身上的反抗性,使之为现实服务。在迪斯尼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SnowWhiteandtheSevenDwarfs1937)中,白雪公主身着破衣烂衫做家务的形象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倾向于将她视为与小矮人一样的平民,阶级差别被电影悄然抹去。影片的结局则颂扬了美国式民主的胜利:白雪公主与小矮人的联盟消灭了邪恶皇后的专制统治。然而这种胜利也只是一种假象,因为紧接着白雪公主就告别了小矮人,跟着王子回到了城堡,即便是在电影中,社会制度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革。迪斯尼的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布洛赫所批判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依然促进某一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对上升时代有所裨益,但它已不再是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一旦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只在照耀既定现实状况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欺骗性的工作,不仅蛊惑人心,甚至还会诱使人们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迪斯尼的这种处理方式更多地是服务于大萧条时代美国社会稳定的需要*关于迪斯尼《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与美国大萧条时代社会文化的关系,参见Mollet,Tracey:“‘With a smile and a song…’:Walt Disney and the Birth of the American Fairy Tale.”Marvels & Tales,Volume 27,Number 1,2013,pp.109-124.,而不是为了让观众疏离日常生活,唤醒观众的乌托邦冲动。
童话拒绝呈现一种已经完成的、确定的世界,其故事往往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在童话故事中,时空背景常常模糊不清,人物行动的原因也往往语焉不详,这种开放性增加了故事解读的多种可能性,也为“尚未”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然而,当童话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之后,童话中开放性的世界却在好莱坞电影中被固定下来,在大量标准化和模式化的故事改编中,童话解读的可能性逐渐地被单一的思想所取代,乌托邦冲动的生发地渐渐地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地,“尚未”变成了当下。
在好莱坞电影发展的各个时期,好莱坞对经典童话的改编都具有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特征。当某一个童话故事的改编被证明能获得很好的票房时,它就会成为一个标准和模式,不断地被类似的电影模仿,直到这个故事无利可图为止。当华纳兄弟公司将童话《灰姑娘》拍摄成青春片《灰姑娘的故事》(ACinderellaStory2004)获得了很好的票房之后,其旗下的华纳首映公司(WarnerPremiere)旋即推出了《灰姑娘之舞动奇迹》(AnotherCinderellaStory2008)和《灰姑娘的故事3》(ACinderellaStory:OnceUponaSong2011)把类似的人物、情节讲述了3遍。甚至当梦工厂推出以颠覆迪斯尼童话为目的的后现代童话改编电影《怪物史莱克》(Shrek2001)之后,也因其大受欢迎而成为了模仿的对象,不仅史莱克系列连续拍摄了4部,而且还带动了一批以恶搞动画人物为目的的电影,如《小红帽后现代版》(Hoodwinked! 2005)、《邪恶新世界》(HappilyNeverAfter2007)等等。这些相似度极高的电影的推出,不断地消耗着童话中乌托邦冲动的吸引力,使之沦为了商业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
目前好莱坞改编的童话电影基本形成了3种模式:迪斯尼式的爱情片、恐怖暗黑式、后现代恶搞式。其中最主流的就是以迪斯尼电影为代表的爱情片,齐普斯归纳了迪斯尼童话改编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 1.女孩爱上了男人(这个男人常常是一个王子),或者想要追逐自己的梦想;2.邪恶的女巫、后母,或者某种邪恶力量想要贬低女孩的身份,或者杀死她;3.这个被迫害的女孩被诱拐,或者被撵出去;4.这个被迫害的女孩奇迹般地被某个王子或者男性气质的帮助者拯救;5.圆满的结局,表现为婚礼、财富、社会地位上升或者对皇室身份的确认。”*Greenhill,Pauline and Matrix,Sidney Eve:Fairy Tale Films.Logan: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XI.这套模式确保了迪斯尼电影的票房,因此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在迪斯尼拍摄的《公主与青蛙》(ThePrincessandtheFrog2009)、《灰姑娘》(2015)、《美女与野兽》(2017)等电影中仍能看到它的痕迹。
在这些大量的模式化改编中,经典童话本身的乌托邦冲动反而遭到了压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好莱坞电影的商业-工业化有密切关系。雷吉斯·迪布瓦(Regis Dubois)认为好莱坞电影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美国商业—工业化电影,它们绝大多数是在全世界发行的高成本制作的大片(blockbusters),是纯粹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首要使命的视听产品。”*[法]雷吉斯·迪布瓦:《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李丹丹、李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页。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支持下实施全面社会管理的明证,它使文化成为了商品,并且自觉地维护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鼓励“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作为文化工业的代表,好莱坞以商业利益为先导,清除了经典童话中的颠覆色彩,逐渐压抑了童话本身所具有的“乌托邦冲动”,将童话变成了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商品。不仅如此,好莱坞的经典童话还将幻想工具化,使之成为了维持现状而非展望未来的工具。
二、幻想的工具化
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不仅架空了童话中的乌托邦冲动,而且还抑制了童话这种创造性艺术的潜能,使幻想工具化并且物质化为一种商品,通过对这种商品的反复营销,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试图剥夺观众的自主意识,让观众认同好莱坞制造的幻觉并为其买单。
工具化是法兰克福学派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具理性而使用的术语。理性原本意味着对永恒理念和真理的追求,但在现代社会中理性被物化,成为了工具。这种理性的工具化以技术理性为思维标准,导向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传统思想中的价值理性遗失,使得人的主体性丧失,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工具理性与文化工业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工具理性对人的奴役,并不体现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让人以享受消费的方式来完成的,大众文化为这种奴役提供了让人愉悦的工具,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仰海峰:《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文化工业作为批判工具理性的重要途径。齐普斯在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幻想的工具化这一论题。他认为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不仅涉及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还包括了对文化工业中想象力缺失的批判。他指出幻想的工具化就是强制性地去除想象力中的崇高因素“在创造者与观众的想象之间进行的调节,通过对幻想文学的形式和意象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工具性表现在大力寻求控制想象力对于这样的工具化现象所产生的桀骜不驯的反抗。”*[美]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舒伟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童话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其创造性与童话的幻想性特征紧密相连。托尔金(J.R.R.Tolkien)对童话的幻想性十分看重,在他看来童话属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第二世界”,即幻想创造出来的想象世界,“幻想是想象出真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但是赋予它们‘内在的真实性’。” “真正的创造性的幻想成立的前提是确信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应当如此;是对事实的认识,而不是被事实所奴役。”*[英]托尔金:《托尔金论童话故事》,王如菲编译,选自路英勇主编:《新知·寂静之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页。也就是说,童话中的幻想非但不虚幻,反而是对现实本质的清醒认识,因此才不会被现实所困。如果说托尔金通过让幻想与现实关联来为童话幻想性辩解的话,那么布洛赫则更关注幻想给予童话超越现实,指向未来的能力。他认为“童话故事叙述的是一个愿望满足的故事,它不会受到故事本身的时间及故事内容的表现形态的束缚。……而童话故事中必不可少的‘很久很久以前’,给人带来的幸福感仍然影响着我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德]恩斯特·布洛赫:《童话故事在时间中的逍遥之游》,选自[美]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舒伟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正因为童话拥有了幻想性,才能给那些不满于现状的人们带来一种愿望得以实现的满足感,从而期许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表面上看,好莱坞以视觉的方式把童话中的奇异事物和神奇的魔法都搬上了银幕,使得幻想变成了银幕上的现实,让人们的梦想成真。但不同于童话那种让人在清醒认识现实基础上憧憬未来的幻想,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中的幻想是工具化了的幻想,非但无助于人们认识现实,反而让人更容易沉溺于具象的虚幻世界中,成为巩固现有社会秩序的工具。这种幻想的工具化主要表现在对幻想的标准化处理,以及幻想的欲望化、商品化之上。
好莱坞的童话改编电影蓄意地通过各种手段对幻想进行标准化处理,控制童话中的想象力,去除童话中存在的颠覆性因素。相较于童话故事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好莱坞更倾向于打造一种封闭的童话改编电影,通过封闭性的电影叙事和奇观化的电影影像,让观众无暇思考童话中蕴含的含义,更难以去想象更加美好的未来。如前所述,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为的是巩固现有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达成则有赖于这类电影封闭性的叙事结构。在好莱坞改编电影中,经典童话那些松散的情节结构被有着严密逻辑联系的情节所取代。因此在这些电影中,公主不可能忽然与一个陌生的王子结婚,他们一定会在结婚前认识并且相爱;邪恶力量陷害主人公的原因也一定会被揭晓出来。这样的封闭式叙事给人十分轻松愉快的观看体验,因为所有的事件都得到了交代,观众不必费心去揣测故事的意思,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中封闭性的叙事基本屏蔽了想象的空间,使得童话中的幻想变成了实现主流价值观念的工具。
好莱坞的童话改编电影还擅长将幻想欲望化、商品化。好莱坞拍摄的童话改编电影隶属于幻想片的一类,这类电影将幻想视为其首要特征,但其中的幻想是压抑了乌托邦冲动的幻想,是与欲望尤其是消费欲望勾连的幻想。
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致力于打造影像化的虚构世界,将童话中的幻想具象化为视觉奇观,以吸引观众进入影院消费,除此而外,它们还试图通过各种周边产品(如各种玩具、礼品和主题公园)的贩卖让观众愿意继续为电影买单。近几年,由于技术的发展,好莱坞电影逐渐从动画走向真人,从2d迈向3d,好莱坞电影花费重金打造了一个个绚丽多彩的“童话世界”。不论是爱丽丝所漫游的奇境,还是灰姑娘那条高科技打造的裙子,其目的都是通过视觉奇观吸引观众消费。观众被鼓励去欣赏再现在银幕上的声像奇观,去购买各种周边产品,而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反思电影的内容。这一系列视觉奇观的营造让观众满足于表面娱乐,来不及去进行更深的思考和批判,童话的幻想沦为了消费娱乐的商品,能够用金钱购买的方式被轻松地占有。好莱坞将经典童话改编成电影,也就是在“对欲望进行有意识的阐释,也即对欲望进行场面调度(mise-en-scène)。”*[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邹赞,孙柏,李玥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这些电影和包装精良的周边商品勾起的不是观众对美好未来的想象,而是观众的欲望,是消费就能使梦想成真的消费主义观念。经过了好莱坞的阐释,观众们的欲望和想象力被局限在王子公主的爱情、个人通过努力奋斗成功等故事中,而影片大团圆的结局也保证了观众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通过幻想的工具化,好莱坞将童话幻想物化为一种可以贩卖的商品,仿佛人们只要买了电影票,就可以进入影院消费被物化的幻想,实现自己的欲望。但实际上,当电影结束,人们必须回归到现实之中,占有幻想的落空促使欲望被再度激发,人们又会再度踏入影院。通过这样的循环,好莱坞悄然形塑了观众的想象力。
布洛赫发掘了童话中的乌托邦精神,使得童话的幻想成为了对“尚未”到来的新事物的预言,但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却致力于控制童话中的幻想,对其进行标准化的处理,使之成为了宣扬意识形态和娱乐的工具。因此好莱坞的改编电影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它们驯化了观众的想象力,用消费主义的观念压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维护了现有的社会秩序。
三、好莱坞电影中的乌托邦精神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工业,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将基于现实认知的童话幻想替换为建立在消费主义观念基础上的消费欲望,试图操纵大众,这样的现象是需要我们警醒和批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就一无是处,这类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抵消童话中的乌托邦因素,或者用詹姆逊话来说,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杂糅在一起的,“最有害的现象可以用做各种意料之外的愿望实现和乌托邦满足的储藏室和隐蔽地。”*[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科幻的乌托邦理论》,选自《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苏湛,李广益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当我们以一种抗拒型的姿态去读解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我们也能从中发掘出乌托邦精神。
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乌托邦精神的发掘建立在对电影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考察观众接受电影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寻找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裂缝;重审视觉奇观中感官体验的价值;考量新媒体语境下观众的能动接受。
尽管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致力于进行封闭性的叙事,让电影文本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生产出了标准化、模式化的电影。但来自童话的乌托邦精神不可能被完全被压抑,齐普斯认为:“人们不会纯粹为了娱乐、开心或浪费钱而去电影院的。他们也受到乌托邦愿望的驱使,会对包含在这些影片的童话故事结构中的积极的乌托邦因素产生反响,因为这些因素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对生活质量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少许希望。”*[美]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舒伟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在电影文本和意识形态之间总会出现一些裂缝,透过这些裂缝,我们能发现电影中的乌托邦精神。在詹姆逊看来,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的首要功能就是维护现有制度的合法性,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合法性的建立并非稳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生产了维护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也潜藏了对现有制度的不满。因此他主张对文本进行症状性阅读,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分析文本中隐藏的裂缝,发掘其中蕴藏的乌托邦精神。
以迪斯尼真人版电影《灰姑娘》(2015)为例。这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好莱坞童话改编电影,在它的改编中,童话《灰姑娘》中那种改变现状、提升地位的愿望被具象化为身为平民的灰姑娘(从电影中的设定看,应该是拥有一定资产的中产阶级)凭借自己的“坚强勇气,仁慈善良”(have courage and be kind)而跻身社会上层的故事。从表面上看,这部电影沿袭了迪斯尼1950年版本中女性通过婚姻提升地位的保守观念,但这部电影同时又是一个具有裂缝的文本,这一裂缝体现在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饰演的矛盾重重的后母身上。凯特因曾经饰演过《霍比特人》(TheHobbit2012-2014)中的精灵女王凯兰崔尔而被观众们称为女王,在《灰姑娘》中,凯特有意无意地将这种女王气场带入后母这一角色中,其老道的演出使得这一人物的光彩压过了莉莉·詹姆斯(Lily James)饰演的灰姑娘。凯特饰演的后母身上混杂了慈爱的母亲、邪恶的后母,以及为形势所困的女性、铤而走险的野心家等矛盾的性格,这些性格突显了这一人物极强的不满情绪,这正是在灰姑娘身上被压抑的情绪。通过后母用水晶鞋胁迫灰姑娘的那段对手戏,电影暗示后母也曾像灰姑娘一样为爱情结婚,但却被残酷的现实(两任丈夫都去世,丧失经济来源)所逼,被迫采用极端手段以谋求独立稳定的生活。尽管电影最终通过后母的失败压抑了这种不满情绪,但通过这一形象,我们看到了凭借个人努力却无法改变阶级地位的可能性,也看到了大团圆结局之外的另一种并不美好的结局。这一裂缝的存在让观众有可能联想到现实中的阶级差异和不满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电影本身的大团圆结局带来的满足感。
布洛赫相信人们有意识的行动将会形成具体可行的乌托邦,对好莱坞电影进行症状阅读正是这样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它要求我们跳脱出文本本身的意识形态,采取一种抗拒型的姿态去读解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从外部入手进行批判。这种症状阅读为揭露好莱坞童话改编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发现其中出现的叙事裂缝,寻找其中蕴藏的乌托邦因素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除了文本叙事中的裂缝之外,症状阅读的方式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影片的主要表现形式:视觉奇观。詹姆逊认为电影的视觉奇观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甚至大过电视,因为电视还会插播广告拉开文本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而电影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性使得“我们在幻觉当中心安理得地认为,镜头所目睹到的所有一切,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毫不走样;因而,我们通过它看到的,也就是存在的全部真相。”*[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可见的签名》,王逢振,余莉,陈静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因此,詹姆逊十分警惕视觉幻象对观众的迷惑。但另一些学者,如研究好莱坞主流电影的米莲姆·布拉图·汉森(Miriam Bratu Hansen)则试图从好莱坞电影的视觉奇观中寻找更加积极的意义,以解释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的风靡。在汉森看来,好莱坞电影不仅需要在叙事性上的研究,更应该从感官层面考察其内涵。她认为好莱坞电影开拓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在感官上的经验,“它不仅仅只是这些电影所展示出来的或者带进视觉无意识的内容,还包括电影开辟和拓展各种未知的感知模式及视觉经验的方式,以及重新组织日常生活的能力。”*[美] 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刘宇清,杨静琳译,《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而且这种经验的形成有助于“观众协调物化(概念的具体化、人的物体化)与美学(感官和经验视界的潜力、焦虑与代价)之间的张力”③[美] 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刘宇清,杨静琳译,《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从而使得人们更加适应现代社会。
汉森的研究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经典童话改编电影所构造的视觉幻境的价值所在。不可否认,好莱坞打造的视觉奇观的目的在于物化幻想,使之勾起人们的欲望,从而成为好莱坞赚钱的工具。然而,这种与物质欲望相勾连的视觉奇观同时也打开了一个空间,使得人们的欲望得以展示和交流,而且不仅主流文化在其中得到了呈现,被压抑的非主流的文化也同样以形象的方式得到了展示。当好莱坞在改编经典童话的时候,需要让这些文字书写(或口头流传)的故事形象化,构建出栩栩如生的童话世界。在这一形象化的过程中,从人物形象到舞台布景、道具、灯光、色彩等等都以具体可感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越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就越能产生视觉的吸引力,但也越具有复杂的意义指向。虽然在好莱坞精巧的叙事框架中,观众们被引导去观看主要的人物和叙事主线,但在实际的观看过程中,丰富的视觉文本反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对《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1937)中邪恶皇后的认同,他曾借自己影片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了一部分观众的真实欲望:“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白雪公主,人人都爱上了白雪公主,而我却偏偏爱上了那个巫婆。”*参见伍迪·艾伦导演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1977)中主人公艾维·辛格的台词。
如果只是阅读童话文本,很少有人会与童话故事中的反派产生共鸣,但观看童话电影却激发了人们对反派角色的欣赏,甚至喜爱之情,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电影在将反派角色形象化的过程中,不仅赋予了这一形象鲜活的生命,而且使得它具有了在压抑的叙事框架中展现自己的机会。在1959年迪斯尼出品的《睡美人》(SleepingBeauty)中,由于故事套路和人物形象与之前迪斯尼推出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以及《灰姑娘》重复,这部电影在票房上遭遇了滑铁卢。然而,这部电影中邪恶女巫以及她所化身的那条恶龙的形象却受到了观众的追捧,以至于这一形象成为了迪斯尼影史上最著名的反派形象之一。当迪斯尼在2014年翻拍《睡美人》时,即重点突出了这一反派角色,甚至连电影的名称都变成了她的名字:《玛琳菲森》(Maleficent,又译为《沉睡魔咒》),造型则基本还原了1959年版本中邪恶女巫的形象,影片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票房认可。这一案例说明电影在创造了视觉形象之后,这一形象的意义不一定会按照创造者的想法被解读出来,正由于视觉形象的丰富性,以及观众的多样性,使得视觉形象有可能会溢出电影创造时的意图,生产出新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电影发挥了汉森所认为的“公共空间”的作用,“电影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不仅因为它吸引了主流文化,而且因为它把自己以及先前被主流文化忽视甚至鄙弃的社会展现出来,放到公众的视野之中。”*[美] 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刘宇清,杨静琳译,《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沿着汉森的这一思路往前更进一步,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电影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围绕着电影形成的接受语境也具备了成为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当前好莱坞的童话改编电影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走入影院观看电影。然而,坐在黑暗的影院中,沉浸于电影打造的视觉幻境已不是观众的唯一选择。越来越多的观众选择网络观影,观影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弹幕实时发送自己对某些片段的观感,与别的观影者交流。甚至还可以将这些行为延伸到观影后,在类似于烂番茄、IMDB、时光网、豆瓣网等电影网站上发表影评、为影片打分,表达个人观点。这种新的传播和接受语境的变化使得观众有了更多的机会表明自己的思想,积极参与到对童话故事的重新讲述之中。以在美国视频网站YouTube上热播的一档节目“诚实预告片”(Honest Trailers)为例,这一节目是网友自发制作的视频,其初衷是在轻松搞笑的氛围中,以模仿电影预告片的形式讽刺电影。节目以网友点播的形式,制作出最多网友希望评价的电影视频。2014年9月该节目发布了“诚实预告片:冰雪奇缘”,这一视频以吐槽的形式,将迪斯尼2013年的热门影片《冰雪奇缘》形容为主题曲《随它吧》(LetItGo)的大型音乐视频,讽刺了电影把女权主义作为噱头,以否定男性角色的方式博取女性观众(尤其是少女们)好感的企图,更一语中的地戳穿了迪斯尼电影启用两个公主为主角,以及其中负责卖萌的角色雪宝(电影中的Olaf,被这部预告片命名为Merchandising,意为圈钱的玩偶)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这种与电影预设的叙事话语不同的讲述方式深受网友欢迎,这一预告片推出之后即大获好评,视频点击率超过了17万*参见百度百科的“诚实预告片”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诚实预告片/19309655.。
可以说诸如视频分享网站、电影评论网站等新型传播媒介的崛起给予那些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的、异质的声音以表达的空间,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当然,这种新兴的传播媒介距离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领域的理想状态还有很大的距离。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中立的公共空间,其中公民能够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对公共领域本身和国家事务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和讨论。由此看来,这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具有一定程度上平等交流的可能性。但哈贝马斯也指出公共领域具有的这种民主功能会在国家权力和商业利益的介入下逐渐失效,因此,不能过于乐观地估计新兴传媒的革命性力量。弹幕或者电影论坛都呈现了一种自发的、无序的状态,情绪的宣泄大过理性的思考。但其中确实展现出来一些不同的声音,电影中维持统一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声音中被打碎,乌托邦冲动在碎片中逐渐显露出来。
同时,观影环境的改变也提醒我们注意到观众们并非铁板一块,观众对电影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本身也具有一种颠覆既定现实的乌托邦精神。当然,不论是通过症状阅读重新读解电影文本,还是新型公共领域开辟出来的讨论空间,都取决于观众的主体性,观众能否挣脱好莱坞刻意营造的梦境,以一种抗拒的姿态来解读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是重寻童话故事乌托邦精神的关键所在。
结 语
通过对经典童话的改编,好莱坞电影营造了一个庞大的“童话电影王国”,这个王国的统治者不再是传统童话中封建社会的国王,而是依靠技术来进行统治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依靠发达的科学技术,好莱坞看似推陈出新地制造了一个个幻想世界,实际上却是用模式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方式重复讲述相似的故事。这些重复的故事压抑了童话中的乌托邦冲动,限制了观众的想象力,试图让观众满足于用金钱就能实现欲望的消费观念,沉浸在好莱坞提供的幻想世界中。好莱坞经典童话改编电影塑造的幻想世界具有极强的欺骗力,因此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警惕清醒地认识它,并对它进行批判。
然而,另一个无法被忽略的事实是,好莱坞的经典童话改编电影确实深受大众欢迎。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用大众都被意识形态成功洗脑这样简化的说法进行解释,因为大众本身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回到文本本身的探寻就显得十分必要。从这些改编电影文本中我们看到,尽管这些文本将幻想工具化,使得电影成为了意识形态管控社会的工具,但如同布洛赫对迪斯尼童话电影世界的评价:“虽然这种世界带有欺骗性,但这种联系仍部分地来自于童话故事。”*[德]恩斯特·布洛赫:《童话故事在时间中的逍遥之游》,选自[美]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舒伟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来自童话的乌托邦冲动并未消失殆尽,好莱坞的童话改编电影仍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人们对“尚未”的期许,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对这些电影文本进行抗拒式的解读,就能看到在这些文本裂缝中存在的乌托邦冲动。正是这些乌托邦精神的存在,使得人们愿意在经典童话改编电影中投射自己的梦想与愿望,从而开启了寻求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