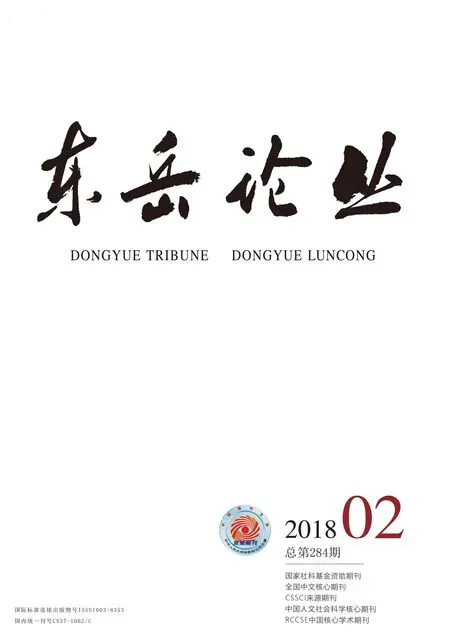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法理基础与进路选择
李秀凤,张 静
(1.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1;2.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100)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费率确立于20世纪90年代。历经20余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就业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的社会保险认知不断提升,适时发展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适当调整社会保险费率的时机基本成熟。2014年12月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询问会”上,国务院领导首次承认社会保险费率过高。2015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降低失业保险费率;6月,进而决定降低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并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记者会上的表态①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表态:“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阶段性地、适当地下调‘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是可以做的。总的是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更是让众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对社保费率下调充满了期待。2016年4月1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36号,以下简称人社部[2016]36号文),初步确定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的下调幅度和执行期限。与此同时,上海率先、其他十多个省市紧随其后纷纷下调部分社会保险费率。社保费率的政策性变动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险费率调整机制的改革开始破冰,社会保险系统的自我平衡机制开始启动。在经济发展逐渐放缓的形势下,社保费率的下调有利于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负担、恢复经营活力、带动社会就业、利好实体经济②莫开伟:《社保费率下降,利好实体经济》,《中华工商时报》,2016年3月31日,第003版。。
社保费率的政策性调整具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够及时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却给社会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定运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险制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财务自主是其区别于其他以税收为财源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标志*钟秉正:《社会保险法论》,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39页。。社保费率下调必然降低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进而影响亿万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险权益。当调整社保费率已为众望所归之时,为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持续运作,这些基本问题需要明确:谁有权调整社保费率?社保费率调整怎样兼顾代际公平?社保费率的调整应当依循哪些正当的程序?因费率下调而降低的基金收入缺口如何弥补?这些问题关涉社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保险的法制化进程。本文将结合社会保险的运行机理,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对社保费率调整的权利主体、依据、程序、基金缺口的弥补等问题展开分析与阐述,以此助推我国社保费率调整的法治化进程。
一、财务自主:社会保险制度的运作特征
社会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它通过参与人的供款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社会风险集中转移给某一组织*Bulletin of the Commission on Insurance Terminology of the Americ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Vol.1,No.2 (May 1965),and Vol.2,No.2 (July 1966).,其本旨在于通过社会互助的方式分摊风险,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于依据保险原则利用参与人的供款收入因应保险给付,因此,参与人的供款是社会保险财务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还包括一般税收、利息等其他不同来源。不同的国家,社会保险的制度模式不同,其财源筹措方式及各类财源比重也不相同。根据政策起因和制度特点上的差异,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福利型”社会保险和“保险型”社会保险两种基本型态*也有观点把“福利型”社会保险和“保险型”社会保险分别称为贝弗里奇模式和俾斯麦模式。参见Ming-Cheng Kuo,Hans F.Zacher,Hou-Sheng Chan,Reform and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nsurance:Lessons from the East and Wes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37.。“福利型”社会保险发端于补救模式下的社会福利政策机制,“保险型”社会保险立基于机制模式下的社会保险政策机制*补救模式和机制模式的分类最初由社会政策学家Titmuss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周弘所长进行了比较论述。参见周弘:《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福利型”社会保险以英国为代表,通常由“公民资格”决定被保险人的主体资格,财源收入主要来自于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供款,实行均一费率,强调普及式的维生水准的均等给付,所得再分配功能显著。“保险型”社会保险以德国为代表,以保障职业劳动者为主,财源收入基本也是以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供款为主,待遇给付与供款工资关联,注重制度的激励效用,强调责任主体的自我负责精神和危险分摊的保险原则,所得再分配的功能较弱。由于“福利型”社会保险往往承载着较重的社会救助的政策目标,一般税收的比重较大。在“保险型”社会保险中,由于自我负责精神和保险原则的强调,一般税收的比重相对较小。为了维持保险财务和给付水准的稳定,社会保险的财源筹措很难依赖单一来源,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保险费、租税以至强制储蓄等筹措方式混合使用的情况,差别仅在于比重不同。不过,随着国家理念的变迁、责任分配的重构以及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一般税收在这两种类型中的比重差别在逐渐减少。
一般税收注资社会保险财务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支付社会保险运作管理费用;二是保费补助及其他负担*张荣芳:《社会保险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实施集中管理体制的国家,前者所需经费主要通过财政专项预算解决,一般不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30条的规定正体现了这一点;后者所需费用构成了政府对社会保险财务的挹资责任,即社会保险财务中的政府责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府责任的大小不同。如日本的《国民年金法》规定“政府需出资全费用的1/3”,我国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法”第3条明确规定:“‘政府’每年度负担本保险之总经费,不得少于每年度保险经费扣除法定收入后金额之36%。”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对政府的财政责任也有明确规定*《社会保险法》第5、13、25、65条。。
与被保险人和雇主的社会保险供款义务不同,政府的注资义务不是其应承担风险移转的对价,政府与被保险人和雇主之间不是社会保险法上的风险共同体,不能形成社会保险法上的社会连带关系*政府不能与被保险人形成社会连带关系的理由主要有四个:一是,政府属于公法人,而非自然人,本身并不会因疾病、老年等而遭遇经济能力减少或丧失的风险,无风险分担需求;二是从历史渊源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本是因缓和阶级斗争、笼络劳工阶级而产生,与社会连带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三是,如果把政府作为社会连带的一方,容易诱发国民对政府注资产生无限诉求,进而破坏社会保险自身的保险机制;四是,在有些体制下,政府已经立于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的保险人地位,如果同时立于被保险人地位而履行供款义务,与法理矛盾。参见孙乃翊:《论社会保险制度之财务运作原则——兼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于健保保费补助之争议问题》,《政大法学评论》,2008年第101期。。政府对社会保险的注资不是基于社会保险上的社会连带关系,而是政府就特定社会政策目的所为的社会给付*张桐锐:《重分配与社会互助》,《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5年第76期。。一般来讲,保费的用途受到保险目的的限定,仅用于该项社会保险制度承保的社会风险所为的支出*张荣芳,熊伟:《全口径预算管理之惑:论社会保险基金的异质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每项社会保险制度都承保着特定的社会风险,如养老保险主要管理着因年老而致的劳动能力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不稳定的风险,工伤保险主要管理着因职业劳动而致的伤害等。然而,社会保险制度在设立之初或在后续发展中往往承接一些特定的政策目标,如因制度改革而致的视同缴费安排、特定群体的优惠缴费制度等。这些特定政策目标的介入使得社会保险制度在承保特定风险的同时,还承载着部分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功能,这种支出与其承保的社会风险无关,对社会保险而言即属于“外部负担”*所谓外来负担基本上系指免付保费、提早或以优惠所得的保险给付。参见邵惠玲:《社会福利国之昨日与今日——以德国社会保险的法制发展为例》,《财产法暨经济法》,2008年第16期。,此项负担如以保费因应,将违反平等原则,故应由国家以租税予以支应⑥张荣芳,熊伟:《全口径预算管理之惑:论社会保险基金的异质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这种由租税因应的保险给付是政府基于特定事由针对不同类别的被保险人所负保险费用的分担,并不是对保险财务的补贴,而是对被保险人个体的给付*蔡维音:《全民健保财政基础之法理研究》,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65页。,本质上仍属于被保险人所负保险费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政府的注资并不是国家财政的兜底责任,也不是国家的制度担保责任,而是对社会保险人赋予特定的社会政策目标所应支出的对价,是政府履行对国民的生活照顾责任所应承担的给付。
在此,政府的注资并非模糊社会保险财务自主的界限,相反,正是社会保险财务自主的体现,也是社会保险财务自主的要求。政府通过一般税收消解社会保险的“外部负担”同时也说明社会保险财务不能与政府的一般财政互联互通,社会保险财务具有封闭性,需要自给自足、自求收支平衡。
无论“福利型”社会保险还是“保险型”社会保险都需恪守社会保险财务自主原则。“福利型”社会保险通常会以租税形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其社会保险税收收入会与政府的一般财政分别建账、分开管理。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法》将用于社会保险的财政资金与政府的一般财政收入分离,社会保障税由财政部国内税务局征收后存入国库,再根据社会保险预算按比例转入社会保险信托基金专户,在扣除行政费用及支出当期给付后,余额再通过法律规定的投资工具保值增值*参见Section 201(a)(b) TitleⅡSSA.。美国的《社会保障法》开创了社会保险由政府直接经办的制度模式。在这种制度模式下,社会保险财务直接来源于由雇主和雇员缴纳的工薪税,社会保险财务区别于一般财政税收,实行自给自足。之所以作出这种制度安排,时任总统罗斯福的说法是“可以防止立法者滥开空头支票导致将来的财政赤字,将使社会保险的花费永远不超过其预定的收入”*Larry DeWitt,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in America,Social Security Bulletin,Vol.70,No.3,2010,pp.1-25.。这种制度模式通过财政区隔与控制的方式将社会保险基金作为“第二财政”,以区别于一般的政府财政——“第一财政”*关于“第一财政”与“第二财政”的具体论述,参见郑秉文:《社保基金的法律组织形式:欧盟的经验教训》,《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而保障政府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职能独立于政府的其他公共管理职能。“保险型”社会保险通常会以保险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由社会保险人的内部组织机构(一般为理事会)负责管理和运营。由于此种类型的财务处理方式通常为现收现付制,保险费率会根据经济发展的态势、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基金支出的状况定期调整,因此,社会保险基金一般不会节余太多,管理相对简单。但财务自主仍是此种类型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
二、社会保险人:社会保险的风险管理主体
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保险同时也是“建立在协调社会成员自助、互助,国家与社会公助关系基础上,依托国家信用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组社会契约”*胡晓义:《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基础性的法律关系主体是社会保险人*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中没有社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这对术语,而是沿用社会保险管理的术语体系,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劳动者(或参保人员)。《社会保险法》第1条明确提出社会保险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保险关系。基于社会保险的保险性,可以参鉴保险法的原理研究社会保险关系。保险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保险关系,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保险人一方和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构成的另一方。作为社会保险法律关系而言,虽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保险人始终作为最为重要的一方主体存在。为区别于商业保险,有必要将社会保险中的保险人称为社会保险人。参见贾林青:《保险法》(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张荣芳:《社会保险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和被保险人。被保险人通过缴纳社会保险供款将自身面临的经济安全风险(或称社会风险)转移至社会保险人,社会保险供款聚合后形成社会保险基金,作为社会保险人承担风险的责任财产,当预定的风险发生时,由社会保险人依法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提供金钱或服务给付。因此,从本质上讲,社会保险人是社会保险的经营主体,是某一社会风险的风险管理者。
虽然社会保险的理念可以追溯至古代欧洲共济之保险组织,但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险却因工业化时代的劳工问题而生,最初存在的目的则是为了安定工人阶级的斗争,消除社会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并借机瓦解产业工人的自治组织对国家统治的潜在威胁*关于社会保险产生的政治动机,参见李志明:《社会保险权的历史发展:从工业公民资格到社会公民资格》,《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丹麦]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滕正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3-126页。。因此,当时的社会保险主要是以劳工阶级的职业类别为基础划分风险共同体,国家强制风险共同体内的成员以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供款并据此建立起供款与给付之间的正比联动,这样,国家强制、保险供款、供款与给付之间的内在关联便成为社会保险的制度性特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险逐渐突破原有的界限,呈现许多新的面相:从对被保险人之选择趋向保障之普遍性,从保费形式的财务结构趋向税收形式的财务结构,从对抗“社会风险”之保障趋向“社会地位”之保障,从保险给付与保费对价趋向给付与社会处境相当,从确保个人生活水准之保障趋向适当分享社会富裕之保障*Ming-Cheng Kuo,Hans F.Zacher,Hou-Sheng Chan,Reform and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nsurance:Lessons from the East and Wes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5.。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保险改革中,智利等拉美国家出现了社会保险私有化的改革浪潮。历经时代变迁,社会保险的经营主体不断演变,有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如美国的社会保障署*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有强制性社会保险与自愿性社会保险、政府直接经营和商业化、联邦政府经营和州政府经营之分,此文仅以联邦政府实施垂直经营管理的强制性保险——老年、遗嘱和失能保险为研究对象。;有的是拥有自治权的社会自治组织,如德国的各类社会保险基金会;有的是按照私法运营的公司法人,如智利的养老金管理公司。不管社会保险的经营主体如何演变,政府主导、国家强制、参保人供款、供款与给付关联以及财务自主始终是社会保险的五大核心特征,是社会保险的本质所在,是社会保险区别于商业保险、国家保险、社会救助的根本标志。其中,政府主导并非政府举办。在由社会自治组织或私营公司法人经办社会保险的体制下,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已经交由合法的社会组织或私人主体提供,这些社会组织或私人主体是相应社会风险的风险管理者,国家的责任在于制定规则和框架立法,“国家责任意在让国家确保私人执行任务的合法性与合乎公益”,国家责任在于特定任务的执行责任和私人执行公共任务有重大缺失或营运不善而有损公益的结果发生时的接收责任;在此,行政机关转化为“计划者、发动者、协调者、控制者、财务提供者、品质保证者、基础建设的准备者”*参见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当社会保险由政府职能部门负责经办时,国家会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将政府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职能区隔于政府的其他职能。美国的老年、遗嘱和失能保险制度属于典型的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体制,专用于社会保险预算的社会保障税进入国库后会形成社会保险信托基金专户,作为政府的“第二财政”,以区别于政府的一般财政,从而保障政府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职能独立于政府的其他公共管理职能,进而将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和社会风险的风险管理者角色融为一体。由此可见,不管哪种制度模式,社会保险人作为社会保险的经营主体都是既定社会风险的风险管理者。
社会保险人同时也是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是指社会保险关系的主体,在社会保险活动中,依据社会保险法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包括社会保险资金筹集关系、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关系、社会保险监督关系以及社会保险争议解决关系等。狭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仅指社会保险基础法律关系,即社会保险的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依法形成的收取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支付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参见林嘉:《社会保障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9页。。无论广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还是狭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作为风险管理主体的社会保险人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主体,处于核心地位,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都因它而生。在基础性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社会保险人依法筹集社会保险供款,形成承担社会风险责任的基金财产,通过保值增值,最终用于支付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法定的社会保险待遇。无论社会保险资金筹集关系、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关系、社会保险基金经营管理关系、社会保险监督关系,还是社会保险争议处理关系,社会保险人始终作为最为关键的一方主体主导、续接着各种权利义务关系。
社会保险费率的调整是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额度,进而影响着社会保险人责任财产的规模与安全。既然社会保险人作为风险管理主体,既是社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又是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是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主体,那么,社会保险人应是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权利主体。
但是,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险自产生之初就具有很强的政治价值和政策功能,甚至被视为“一种为‘消除革命’而进行的投资”*李志明:《社会保险权的历史发展:从工业公民资格到社会公民资格》,《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当社会保险由国家之手承接并受国家权力保障时,社会保险的经营主体随之发生了变化,社会保险人的主体职能也发生了改变,它不仅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法上的管理主体,它承载着双重职能:一是作为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秉承着国家的意志,分担着国家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职能;二是作为自主运营的独立法人,具有独立的经营目的,拥有独立的财产,具备独立的法定权能,独立地承担着相应的经营责任。作为自主运营的独立法人,社会保险人应该拥有独立的财产,但是作为代行国家事务管理职能的重要义务主体,承载着重要的公共政策职能,贯彻着国家的社会政策意志,因此,它不能自主收入和支出,对保险对象的选择、保险费率和给付待遇标准的确定等影响社会保险财务安全关键事项并不拥有独立的权能,保险对象的选择、保险费率和保险待遇标准的确定牵涉“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对应于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的宪法义务,因此必须树立社会保险法定的原则”*张荣芳,熊伟:《全口径预算管理之惑:论社会保险基金的异质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由立法机关决定。既使由政府职能部门担任社会保险人的美国,其社会保险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不能由行政裁量而限制或降低,如果基于公共政策需要或其他任何合理的理由,国会可以改变、修订或废除《社会保障法案》的任何条款,而不被视为违宪*George E.Rejda,Social Insurance and Economic Security,Second Edition,Prentice-Hall,Inc.,1984,pp.25-26.。
在此,社保费率调整的法律保留事项处置与社会保险人作为风险管理主体的社保费率调整的权利主体身份存有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能够在社会保险的双重属性中得到阐释和消融。“社会保险是一种包含‘社会’与‘保险’两种要素的社会机制”*郭明政:《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争议问题之探讨》,载葛克昌,林明锵主编:《行政法实务与理论》,北京: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74页。,“社会”的要义在于强制纳保、法定给付、国家责任与社会衡平;“保险”的要义在于由社会保险共同团体将参保人的供款集合成保险团体的责任财产,用以分散团体成员的风险。社会保险的“社会性”要求其制度设置首先应当考虑大多数国民的保障利益和最急需保障的国民利益,并且还要切断参保人供款与保险给付的直接关联性,禁止保险人参保人员进行经济状况及体能状态的核查与择优选择,从而充分利用“大数法则”吸纳更多的国民参与,藉此达到风险分散与所得重分配的目的,因此,社保费率的拟定首先应当考量大多数国民的经济负担能力,而非社会保险人的效益选择。为了保障社会保险费率的合理性、公正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由立法规定往往成为最佳的选择,并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如现代意义社会保险的鼻祖——德国,自治管理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典型特征,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社会保险费率并非其自治事项。在养老保险、护理保险和失业保险中,立法者在社会法典中细化了保险费计量的基础和保险费的规章*参见[德]乌里奇·贝克尔:《德国社会保险的自治权——理念、组织安排和改革》,《社会保障研究》,2005年第1期,第56-66页。;而在法定医疗保险中,制度实施伊始,国家没有任何权力确定医疗保险的缴费率,医疗保险费率的确定权是医疗保险基金会自主管理的关键事项,于医疗保险基金会间的相互竞争中最终形成*参见[德]赫尔穆特·普拉策:《德国社会保险自主管理的构想与功能》,《社会保障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4-119页。;后来,医疗保险管理委员会的费率确定权受到限制,部分由立法规定。
实际上,社会保险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社会保障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权是我国宪法确认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因此,社会保险权源于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权,是被宪法确认一项基本权利*参见林嘉:《社会保险权利救济研究》,《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4年11月,第12卷第3辑,第53-73页。。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Eide,A.,The Human Right to Adequate Food and Freedom from Hunger,1998.In: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the Right of Food:In Theory and Practice.Rome,Italy 1998.United Nations:New York.。尊重义务要求政府不得随意干涉;保护义务要求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杜第三方的侵害;实现义务包括促进义务和提供义务,要求政府积极作为以确保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参见[挪]A.艾德:《国际人权法中的充足生活水准权》,载刘海年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国家的实现义务虽然并不要求国家亲历亲为,但国家要承担制度担保责任,当社会保险出现系统性支付不能时,保证会通过包括财政补助在内的措施,帮助社会保险基金渡过难关*制度担保责任不同于最后付款人责任。制度担保责任往往表现为紧急援助,财政贷款是第一位的,财政补助是第二位的,当社会保险恢复正常运行后,政府投入资金一般可以收回,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转为补助,而最后付款人责任则并未作此区分,因此,最后付款人责任无限扩张了政府对社会保险的财政责任。参见熊伟,张荣芳:《财政补助社会保险的法学透析:以二元分立为视角》,《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正是这种“制度担保责任”限定了社会保险人的部分权限,将社会保险费率的调整权交由代表全体国民意志的权力机关确定。长期以来,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法律保留事项属性受到普遍的信赖和遵从。但是,当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国家职能等因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国会立法调整费率显然难以及时因应各项因素的快速变化,因此,部分国家对费率调整的法律保留原则进行了修正,将其改革为“依法定要件而自动调整,并授权联邦政府依命令为之”*郑文辉:《健全社会保险财务之研究》,《行政院财政改革委员会研究报告》,2002年8月,第5-29页。。
然而,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解析,社会保险人才是真正的社会风险管理主体,即使因为社会保险的社会性致其最为关键的权利受到限制,其作为风险管理主体的角色权利应当通过其他途径得以体现和彰显。社会保险的财务自主性说明社会保险人虽然不能自主收入和支出,但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预算主体,应当坚守收支平衡原则。社会保险人的财务收支状况并非社保费率调整的唯一诱因,甚至也不是影响费率调整的关键因素,供款者的经济负担能力直接决定着社保费率水平,直接钳制着社会保险供款的征缴。当供款者的经济负担能力出现变化影响到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时,社会保险人会根据支出情况作出预算报告提交权力机关审议*预算报告只是一种信息申报,权力机关的审议也不同于审批。参见张荣芳,熊伟:《全口径预算管理之惑:论社会保险基金的异质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权力机关再根据社会保险人的信息申报,依法调整社会保险费率。也就是说,虽然社会保险人不是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权利主体,但作为财务自主的风险管理主体,能够为社保费率调整提供基金收支情况的数据支撑,从而对社保费率的调整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三、代际公平: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考量因素
社会保险供款费率的确定必须虑及两种因素:一是社会保险财务自主性的要求,二是社会保险供款费率的高低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社会保险财务具有自主性,保持社会保险财务基本自给自足是社会保险制度独立运作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保险制度持续运作的根本保障,社会保险人作为社会保险责任的直接责任主体应当具有根据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状况确定保险供款费率的参与权和建议权。但是,这种权利会因第二因素而受到限制。社会保险是通过国民当前消费的部分牺牲来换取将来保险事故发生时的经济生活安全保障,保险供款支出必然会部分抑制供款人的当前消费需求,当前消费需求的减弱必然会对经济增长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并不突出,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却非常明显。因此,多数国家在经济下行时期都会通过降低社会保险供款费率,将国家社会保险的经济安全保障职能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活力空间,从而保证国家更广范围的社会安全保障。但是,社保供款费率的下调并不能必然导致社保待遇的降低,而且社会保障的福利刚性*福利刚性是指从人的心理角度讲,已经拥有了对未来享受较高退休待遇预期的员工是难以接受退休金大幅缩水的改革取向的。因此,社保待遇的降低总会招来民众的激烈反对。参见张荣芳:《社会保险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也会阻碍社保待遇降低。也就是说,社保费率降低会导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减少,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则不会减少,甚至还会出现随着老龄化的加重而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进而危及社会保险财务自主与安全。
理论上讲,社保费率的调整与社会保险财务自主、社会经济之间的制衡与磨擦可以于社会保险精算中获得部分平衡和缓释。社会保险精算通常以人寿和健康保险精算为基础,尤其在寿险精算中,通过利息理论、生命表、多减因表等多种因子的评估和预设,基本确定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之间的联动效应。但是,相对于私人(商业)保险而言,社会保险精算则更困难,并具有更大的不明确性,因为社会保险精算与出生、死亡、结婚、再婚、就业、失业、失能、退休、平均工资水平、待遇水平、利息率和其他数量繁多的附加因素等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变量密切相关,这加重了通过社会保险精算进行预测的难度*George E.Rejda,Social Insurance and Economic Security,Second Edition,Prentice-Hall,Inc.,1984,p.41.。另外,社会保险精算属于数理分析与推导,基本不涉及社会政策的影响因子。因此,如果纯粹基于精算而确立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则可能引发严重的代际不公问题。如在待遇确定型*养老保险计划可以分为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efit,简称DB)和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简称DC)两种基本模式。在DB模式下,养老金计划发起人或管理者向计划参与者作出承诺,保证养老金收益按预先的约定发放,即养老金待遇水平会根据缴费年限和工资收入水平预先确定,会随物价水平调整,缴费水平会经预算估计定期调整。在DC模式下,预先确定缴费水平,退休时以不断累积的缴费额为基础发放养老金,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缴费总额和投资收益收入,投资风险由参加者个人承担。参见邓大松:《社会保险》(第二版),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郑秉文:《何谓DB与DC》,《中国证券报》,2005年10月21日,第B04版。养老保险制度中,待遇水平由养老金计划发起人或管理者预先承诺,缴费水平根据预算估计定期调整,待遇水平与缴费年限和退休前的工资水平直接相关,与缴费水平没有直接关联。在积累制待遇确定型(即financial defined benefit,简称FDB)养老保险制度中,因缴费水平而引起的代际不公问题不会十分明显;但就现收现付制待遇确定型(defined-benefit pay-as-you-go,简称DB-PAYG)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会根据预先的承诺兑现当期(或近期)的待遇支出,再根据当期(或近期)的待遇支出经过预算估计当期(或近期)的缴费水平。如果人口结构发展平稳,缴费水平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代际公平问题不突出;但在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当期(或近期)劳动力人口的缴费负担会愈益增大,代际不公问题凸显*由于缴费确定型社会保险制度预先确定缴费水平,待遇水平取决于个人账户中累积的缴费额和投资收益额,主要体现为参保者人生不同阶段的经济互济,基本不涉及不同参保者之间的经济互济,因此基本不存在代际公平问题。。此种问题同样存在于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短期性社会保险中,如医疗保险。老龄化的加重必然增大退休者的医疗保险需求和待遇支出,进而增加当期(或近期)就业年龄人口的缴费负担。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风险承担主体并不相同。在纯粹缴费确定型体制下,费率调整的不利结果会由当代缴费者退休时承受,如果有纳税人补贴的话,则由纳税人承受;在完全积累的待遇确定型体制下,则由当代工人承担费率调整带来的不利结果;而在部分积累的待遇确定型体制下,因费率调整所致的风险可能在当代工人和未来的工人间分散*Nicholas Barr and Peter Diamond,Pension Reform:A Short Gui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37.。正是因为费率调整蕴含这些问题,各国对社会保险费率的调整幅度都持谨慎态度,幅度变化不宜过大,从而使得费率调整既能满足社会保险财务自主性需求,又能兼顾当期缴费者的缴费负担、以及缴费者与待遇享受者之间的代际公平;正是因为潜在的代际不公问题,将社会保险费率调整列为法律保留事项才能确保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衡平兼顾。
四、从政策到法律:我国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进路选择
社会保险作为经济安全的保障措施,财务自主的制度运作特征内在地要求社会保险费率的适时调整。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形势、人口结构、经济安全保障的理念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社会保险费率却一直沿用至今,实属罕见。这次的社保费率调整顺时应势,开启了社会保险财务的自平衡机制,同时也提出了社会保险财务如何自求平衡的新课题。
国家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属于给付行政,是一种授益行政,但其实仍是国家行政对人民自由生活的一种干预,是现代社会国家职能不断扩张的体现。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立在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因国家行政广泛地介入人民生活而产生对个体自由和财产权的限制而必须接受制度实施的正当性拷问。奠基于“生存照顾”理念之上的“服务行政”理论为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提供了正当性证成。福斯多夫认为每个人自求多福应是过去社会的信条,今日的社会,“个人生活之危机,已移转由社会承担。个人危机已与社会整体之生存休戚与共,此亦构成了国家公权力应予介入之理由。”*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进而丰富和改变着公民财产权的状态。国家承担着对国民的积极的生存照顾义务,公民拥有要求国家提供适当的生存照顾的权利。在给付国家*二战之后,国家形态由秩序国家转化为给付国家。在给付国家理念下,国家作为行政作为给付的承担者,负担愈来愈重,为此国家进入“保障国家”阶段。参见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第73-98页。之下,这种要求国家提供适当的生存照顾的权利已经成为公民的一项“新财产权”*“新财产权”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瑞克(Charles A.Reich)在论文《新财产权》(New Property)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广泛介入,公民的福利权利也是一种财产权,是一种新财产权,这种新财产权同样需要程序性保障。See 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Yale Law Journal,Vol.73,Issue 5,April 1964,pp.733-787.而受到重视和保护。虽然这种权利的内容会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往往与社会政策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将其转变为法律问题,用法律的原理和技术予以支持和保障。相反,随着社会保险权利是“权利”而非“特权”观念的普及和深入,将关涉公民社会保险权利的具体内容拟定完全交由政策裁量,显然也不符合法治社会的建设要求。当然,为了保存自由,有限度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但“新财产权”的建立为公民带来保障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和独立。“法律虽然不能创造更好的民族或更好的团体,但是它能为我们预留坚守崇高理念的自由呼吸的空间”*See 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 After 25 Years,24,U.S.F.L.Rev.223-271,1989-1990.。人社部[2016]36号文初步确定了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依据和幅度,但与科学、合理、规范的费率调整机制的形成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将社会保险费率的政策性调整逐渐回归于“法律之治”,才有利于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一,从调整的权利主体看,社会保险费率的调整权性质上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原则上由立法机关行使;待条件成熟后,调适为依法定要件而自动调整,并授权中央政府发布。我国属于政府直接管理型的社会保险组织管理体制,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专职责任部门依政府的行政体制设置,隶属于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管理和执行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事务*参见郭静:《社保经办机构的发展特点及趋势——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国际比较之二》,《中国社会保障》,2011年第2期,第27-29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是我国中央级别的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社会保险的政策拟定和实施的监督管理,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各地的具体实践和发展动态,能够为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供最有力的论据。目前,关于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规范性文件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拟定和发布,未尝不可;但是,从长远看,社会保险费率的变动牵涉的利害主体广泛,社会影响深远,授权中央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的组成机构依法定要件自动调整更为合适。
第二,从公平性保障的角度看,应建立利益关系人参与机制和指数化的动态调整机制,依此确定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幅度和频率。虽然我国建国初的社会保险制度沿袭前苏联的做法,实行国家保险制度*所谓国家保险是指仅由企业单方缴费,劳动者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即可享受国家给付的保险待遇的做法。这种做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具体解析见本文第一章第一节第二部分。,但是,从制度渊源上分析,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应属俾斯麦模式的脉系。俾斯麦模式的特点在于雇主与雇员共同缴费、保障的程度依据被保险人原先的收入(即劳动提供的等级与价值)确定、基金由工会组织代表与资方代表依法共同管理*参见郭明政:《社会保险之改革与展望》,台北: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页。。这种模式基于工会与雇主代表乃是广义上经济活动的代表的假设,把社会对话作为制度的内建要素*参见郭明政:《社会保险之改革与展望》,台北: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页。,强调雇主与雇员的共同参与、协商与博弈,将关涉社会保险权益的重要事项交由利益关系人自主管理与协商,国家主要肩负政策引导和法律监督之责。俾斯麦模式奠基于工业社会以传统雇佣为主的组织环境,以强有力的集权国家为后盾,对雇主和雇员的组织性具有较高的要求。雇主和雇员的团体组织性源于其深厚的社会自治的制度传统。工业社会的挑战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改变着国家的角色功能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进而助推着责任分配的重构。在法治国家理念下,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和行政权力的依法行使角度规范国家治理和保障人民权利;在社会国家理念下,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国家需要承担积极的给付义务,此时,国家责任并不只是“‘政府或公务员’的责任,而是‘整体社会’与‘全国人民’的责任”*钟秉正:《社会法与基本权保障》,北京: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52页。。因为权利的社会性,国民在享受给付权利的同时往往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与义务对应的还有国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利。国家理念的发展与转变意味着国家并非万能,无力事事亲为,社会主体的自我规制反而能够减轻国家治理的负担。
就社会保险费率调整来讲,利益关系人主要包括社会保险人和社会保险的供款义务人。社会保险人是风险管理主体,是保险责任的承担者,理应拥有社会保险费率的决定权。虽然由于社会保险的特殊性,出于权利保障的考虑而将社会保险费率调整权作为法律保留事项,由立法机关行使,但是,社会保险人毕竟是风险管理的义务主体,与其承担的义务相对应,应当通过参与权的设置在费率调整的决策过程中体现社会保险人的意志。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险供款义务人的义务内容。社会保险供款义务人包括用人单位和被保险人。用人单位是社会保险供款的主要义务主体,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履行协力义务,所享有的多是程序性权利,参与权的设置可以通畅其意志的理性表达渠道,形成良性的缴费激励机制。
利益关系人参与机制侧重于程序公平,费率调整的实质公平更需依赖于科学、合理的指数化调整机制。指数化调整机制的设立应当充分考虑经济场域、人口/家庭场域、行政管理场域(财政补贴)中各种与经济和人口指标相关的因素的动态均衡。目前的费率调整措施仅从社会保险基金的结余状况和用人单位的承受能力衡定调整的必要性和调整的幅度、频率,而未能充分考虑改制成本、就业形式、实际缴费率、人口流动、人口净增长率和净赡养比等影响因子,虽然短期内能起到明显的效果,但长期而言,不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持续运作和法制化发展。指数化调整机制虽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却是社会保险制度持续运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它的设立会使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置更加公平正义。
第三,从社会保险基金平衡的角度看,类型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应建立适宜的补缺机制。简单地说,社会保险基金缺口的产生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转轨的成本,二是制度自身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总会伴随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出现的“视同缴费”和“优惠缴费”处理规定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对社会保险制度本身来说即为沉重的“外来负担”,应由政府的一般财政买单。制度自身的原因包括社会保险实际供款水平、基金的增值能力等方面。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同样影响着基金的实际支付能力,牵涉金融市场的环境和投资渠道的选择等问题,此处不赘。社会保险的实际供款水平受实际供款基数、供款群体和实际供款费率等多种因素影响,实际供款费率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险基金的平衡。一般来讲,社会保险费率的降低调整除了受制于经济发展态势因素外,还应当立基于合理的基金支出盈余期间的限定。根据社会保险财务自主的要求,因社会保险费率的降低调整而致的基金缺口应属社会保险财务自求平衡事项范围,不应由一般财政填补。因此,社会保险费率的降低调整应该限定在基金的承受能力限度内,应在保险精算的基础上保持限定期限内基金的适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