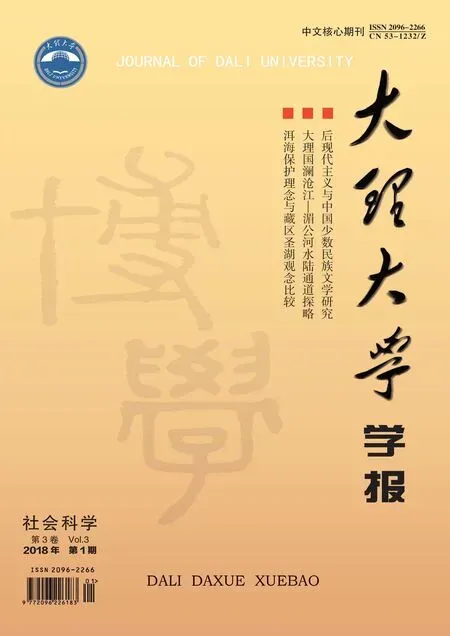乡村都市化背景下以“水”为中心的村落社会
——以南北两村为例
李陶红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一、水资源与乡村都市化研究结合的可能性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乡土中国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是以“土”为中心的社会,以“土”为中心形成的农业社会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本色。“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1〕10费孝通在分析中国农民为何聚村而居的原因时,也指出水的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1〕11费孝通先生虽然提及水这一要素,但对其并未如“乡土社会”的理论建构那般付诸心力。王铭铭提出从以“土”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乡土中国与水利中国之间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纽带〔2〕。麻国庆提到“水”的视角是了解中国基层社会民间组织的重要出发点〔3〕。
深入分析可发现,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土地的优良程度与其所依赖的水资源密切相关,水资源的可利用程度直接体现土地的实际利用价值。从一定程度而言,以“水”为中心的社会研究是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以“土”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一种补充,也是深入社会结构研究的有效途径。于区域研究而言,现有水研究的相关理论也渐与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林美容的祭祀圈理论等居于同等位置。于单个村落而言,水的研究可以解释村落生态、生计、信仰等文化要素,进而建立起社会结构的立体构图。
乡村都市化由我国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提出,主要用以区别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城市化”“都市化”等的理解和研究①关于周大鸣教授对乡村都市化的具体论述,可参见周大鸣著《现代都市人类学》第21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第100-108页。。乡村都市化的提出及研究,将关注点从城市本身拉回到乡村,关注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强调乡村与城市的互动,由物化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的过程。意在爬梳在都市化浪潮下,乡村如何在都市化气息的“裹挟”之下,原有均衡、同质的稳定农业社会体系被打破,地方社会如何适应及改变都市化气息,如何在好恶交织的都市化进程中适应、改变、挑战、发展的复杂策略过程。
以上可见,水资源是研究村落社会结构的切入口,乡村都市化正是当下村落社会结构变化的提炼,因此二者的结合具有可行性。在乡村都市化的“裹挟”之下,均衡、同质的稳定农业社会体系被打破,而这样的一种变化在水资源方面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本研究将乡村都市化作为背景,以水资源为切入点,来观察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由水这一特殊资源带来的村落社会的变化过程。同时也将乡村都市化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导,结合村落社会的发展实践,指出乡村都市化背景下村落社会的困境及其实践重构。在此,笔者的研究路径与研究结论仅是一种可能的尝试,还望与学界讨论。
本研究的田野点,选取南北两个村落。北方村落选取山西介休洪山村,是缺水地带的代表。南方村落选取湖南通道上岩坪寨村,是水资源丰富地带的代表。两个田野点的选择是基于区域的关照和类型的考量。
二、洪山村水资源与村落社会变迁
(一)洪山村水环境
洪山村因洪山泉得名,出自洪山村的洪山泉,属汾河水系,为山西省19个重点岩溶大泉之一。洪山泉素有“胜水流膏”的美称,为“介休十景”之一。整个洪山泉域汇水系统的范围总计632平方千米。据20世纪90年代的资料统计,面积占介休市1∕3的洪山灌溉区域,其粮食产量却占到全市1∕2以上①相关数据由洪山水利管理处提供。。洪山泉域是介休市粮食作物主要产区,有“介休粮仓”之称。
位于洪山泉源头的洪山村,因近水之便,伴随水资源开发的村落历史较为悠久。有史可查的洪山村历史约有3 000年,关于洪山村的历史文献记载早已有之,其记载与狐岐山、狐岐胜水的记载紧密相关。《山海经》中有记载:“狐岐之山无草木,多青碧,胜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汾,其中多苍玉,即此俗名洪山。”〔4〕洪山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是在当地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基础上积淀的文化,是一部由水写就的历史。
依赖水这一自然资源,洪山的农业发展居于介休区域前列,也促发了水利经济,如水磨、制香、陶瓷、琉璃等,成为此地有别地无的优势经济。同时形成锁链效应,制香、陶瓷、琉璃又带动造纸、编草绳等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构成了洪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由水资源促发了经济交往,进而促进地域间人群的互动,激发社会活力,形成一定范围内的手工业制造中心与商业活动中心,这与同时代的农耕社会相比,显示出其优越性与独特性。具有得天独厚水资源的洪山村成为繁荣富庶之地,有“晋中小江南”“小北京”“小香港”等称号②关于洪山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水”“经济资源的水”“文化资源的水”与当地社会的关联,可参见周大鸣、郭永平等著《延续的文明:山西介休的历史透视》第192-229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二)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的洪山泉断流
2014年2月,洪山泉彻底断流,对洪山村社会变迁而言具有标志性和颠覆性。直至现在,洪山泉仍未复流。洪山泉断流与洪山灌区大面积的农业用地增加有关,在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洪山泉所要供给的灌溉面积为1 627 hm2,至1958年,洪山泉所要供给的灌溉面积增加至8 667 hm2③此数据参考原洪山水利管理处续忠元先生所编写的《介休县水利志》第46页(内部资料,1986年)。。过快的农业增速,造成洪山泉供给严重不足。这一事实也带来资源的反弹,农业用地的过度消耗,带来农业生产成本投入过大,而农业收入抛去成本所获无几。面对虚弱的土地,很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催生打工经济。据洪山村村委会提供的资料,在20世纪70年代,洪山村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067 hm2。而到现在,建筑用地、退耕还林、抛荒弃荒等因素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33 hm2。面对水资源的枯竭,村民在土地上的耕耘已经难以为继,很多人家会将土地免费送给别人耕种,以便有更多的精力来从事打工行业,甚至有土地送不出去的情况。从表面来看,凡是农业人口均拥有土地,但实际而言,当地半数以上的村民有土地但已不再耕种,形成不愿意从事农业的“农业人”〔5〕。
洪山泉断流的直接原因在于洪山村周边区域煤矿开采及打井造成洪山泉域的破坏,洪山做出了都市化进程中对资源强力需求的牺牲。20世纪70年代,在洪山村与运吉村之间有县营的洪山煤矿(现已停办);在洪山村与杨家庄之间有镇办的洪山镇煤矿(现已停办);在洪山镇与连福镇接壤处有20多个小煤矿,现在仍有5家在运营;在洪山镇与龙凤镇之间有开山取石、开挖小煤窑的情况;在洪山镇与平遥县接壤处,也有一定数量的煤矿。这些区域均涉及到对洪山泉域保护区的破坏,而洪山泉域范围内除洪山村外,均有打井的现象。90年代,曾在洪山镇与平遥接壤处打井,致使出自洪山村的泉水流量减少,洪山当地还与平遥有一场因为水的官司。
洪山泉断流导致当地人口流失。洪山村的居住人口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约有6 000多人。从80年代初开始,洪山村的人口渐有下降,随着水资源的减少,当地的陶瓷厂、水磨等高耗水的厂子关停,当地人也被迫到外地谋生。2000年,具有洪山村户口的人数为5 112人,其中户口在洪山村却并未住在洪山村的人口数为252人①人口统计数据资料由洪山村村委会统计员张育政提供:2000年洪山村户主姓名底册。。至2010年,洪山村户口人数为4 434人,其中户口在洪山村却并未住在洪山村的人口数为1 313人,他们中的1 124人居住在其他乡镇,尤其多居住在介休市区②人口统计数据资料由洪山村村委会统计员张育政提供: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快速汇总表。,洪山村人口流失现象明显。致使人口流失的因素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洪山村因水断流带来的生存危机,致使一部分人外迁,尤其是水资源缺乏,当地可容纳上千工人的陶瓷厂关停,造成当地工人的流失,原洪山水利管理处也因当地无水而搬迁到别地;二是因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集中办学的需要,原处于洪山村的洪山镇中学合并至介休市区,部分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随孩子迁到介休市区居住。水资源缺乏与教育资源缺乏的双重因素,将洪山当地人抛向别处。水资源的丧失让当地农民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同时因教育资源被强力剥夺,农民丧失在当地通过好的教育走向继续发展的通途,只得举家离开,为了接受好的教育从而获得理想的发展,去介休市区打拼。
三、上岩坪寨水资源与村落社会变迁
(一)侗寨水生态
上岩坪寨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居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处。上岩坪寨是一个自然村,因行政管理的需要划分为上岩和坪寨两个行政村,上岩有348户计1 445人,坪寨有327户计1 376人③数据来源于2013年独坡乡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最新数据统计资料。。侗乡有“无溪不花桥”〔6〕的说法,水与侗族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笔者将上岩坪寨定位为“水乡”侗寨的缩影,这里村民与水和谐共居:以线状流动存在的河流、消防渠,以面状静止存在的稻田、鱼塘,以点状分布于村寨间的水井,共同构成当地的活性水资源系统。上岩坪寨耕作的土地面积中近90%是稻田④90%的稻田比例数据由当地村支书杨献光先生评估提供。,因此水稻种植成为上岩坪寨最重要的农业形态及生计模式。村民在丰富水资源的基础之上,发展了稻田养鱼模式⑤对稻田养鱼模式的生态学意义,学界的论述成果非常多,亦非常成熟,笔者在此不赘述。。侗寨村民与水这一自然资源和谐共居,体现的是侗族特有的生态审美及与生态和谐共存的诗意栖居。以“水”为中心的村落生态共同形成了水资源的活性系统,在实现和谐人居环境方面发挥效用,成为侗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生态诠释〔7〕。
(二)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的侗寨水资源
侗寨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在延续中出现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乡村都市化进程的推拉力作用下,打工经济的出现造成大批量的劳动力外流,依赖水资源而进行的水稻种植渐有荒废之势。很多村民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依靠仅有的稻田维持生计。波普金在《理性的小农》一书中指出,农民是经济理性的主体,主要受个人利益的驱使〔8〕。在继续稻谷种植与打工之间,村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纷纷加入打工的队伍,使侗寨呈现出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家中的人口格局。打工经济的收益超过水稻种植的收益,成为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人口外流引起其农业地位下降,从笔者于2013年8月亲历的当地求雨仪式过程的简略及态度认知的转变中,就很显而易见〔9〕。乡村都市化的直接后果,即造成当地主流生计方式从农业经济到打工经济的转变。在生计方式的转变之下,稻田逐渐荒芜,水利设施逐渐失去功能,建筑用地挤占鱼塘、消防渠等传统的消防系统。村落的水污染问题也逐渐暴露。一方面,当地的水资源利用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也能看到侗寨村民在生计变迁面前的应对。例如侗寨兴起的以“田糖农业合作社”为标志的农村农业合作社,提高了农业效率,也成为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路径。
结合乡村都市化背景来分析侗寨水资源利用方式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最为显著的是人口因素。从上岩坪寨的现实情况来看,人口持续增多,但稻田资源和已有的水资源总量没变,如果所有的人口都将劳动力附着在稻田的耕作上,必然造成“农业的内卷化”趋势,形成一种实质上没有发展的发展。而自90年代起出现的打工经济,就是有效缓解当地人地矛盾、疏散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有效应对,整体改变当地的“农业内卷化”境况。劳动力从种植水稻的生计模式中抽离出来,也是当地村民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表现。因此造成现有稻田疏于管理的现状,也正是村民为寻求最佳生存状态的适时选择。因人口增长及外出打工带来人口流失,打工的经济效益明显高过种植水稻带来的经济效益,导致传统农业不受重视,水稻种植在当地生计模式中的地位下降,水资源利用效率变低〔10〕。
四、从“水”看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的村落社会
(一)以“水”为中心的村落社会
以南北两村为例,不论是缺水村落,还是水资源丰富的村落,水都内嵌到村落社会生产生活、村落组织、村落地方文化中,内化为信仰,通过水的视角,可以全盘关涉村落社会的形态和结构①水与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村落组织、信仰、生态文化等的论述,可具体参见笔者的研究:周大鸣、李陶红《侗寨水资源与当地文化——以湖南通道独坡乡上岩坪寨为例》,载《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第51-58页。。不管是缺水村落,还是水资源丰富的村落,自然形态的水的供给总是不稳定的,相比较而言,缺水村落的水利管理比水资源丰富村落的水利管理更为缜密。由于作为自然资源的水的不稳定,需要一套缜密的制度实现水资源利用的优化,从水即可看到中国社会是一个缜密而稳定的农耕文明体:稳定的慢结构。当下,不管是水资源缺乏村落,还是水资源丰富村落,都面临着一样的水资源问题。水之变背后的村落之变又与乡村都市化紧密联系,稳定慢结构的农业基色下的村落社会在乡村都市化的“裹挟”下被打破或是重构。
(二)村落“弹持”与内生发展
洪山村当下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匮乏问题,资源匮乏带来了当地社会的剧变。以洪山村为代表的水资源与民众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是周边诸多区域的发展困境。洪山村仅仅是诸多村落中自然资源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紧张的缩影。水资源丰富的上岩坪寨,一样暴露出社会发展的问题。水资源的传统利用方式与现实利用方式存在差异,影响侗寨水资源利用的因素中,既有桎梏,又有动力。
以洪山村为代表的泉域社会,在历史的开发及利用过程中是以跨越村庄的方式发展的,其良好运行建立在村落间协调与沟通的基础之上。过去的泉域社会有超出村落的合作机制,现在的泉域社会的危机治理仍需要这样的合作机制。洪山泉域的保护,仅以洪山村为保护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跨越以行政区划为限制的有形边界,建立更大区域范围内的联动机制。这不仅是泉域跨区域存在的现实,也是泉域保护的需要。同样的,如洪山村、上岩坪寨这样的单体村落,面临无可阻挡的被乡村都市化“裹挟”这一事实,就明确了单个村落的存续与发展需要上升到“跨越有形边界”的范畴来把握。
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洪山村和上岩坪寨因为既有的土地难以为继,打工成为地方新的甚至是主要的生计来源。打工经济是典型的外附型经济,需要反思的是,洪山村、上岩坪寨出现的打工经济是否是转移当地劳动力,实现地方最优发展的最佳途径。不可否认,打工成就了作为个体的“我”的发展,一些发展较好的个体成为立足于城市的新移民。但从普遍的意义而言,打工这一形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地方社会的发展还是得回到内生型发展上来。
现有洪山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种外附型的发展模式,较为典型的是打工经济的出现。而就现实的洪山村的发展而言,外附型的打工经济仅停留在满足村民基本的生活需要上,难以满足村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洪山村发展的考量还是需要回到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上来。其内生型的发展模式在洪山有可行性,并且也已经在实践的路上,当地源神庙到水利文化博物馆的价值转变就是一例,是在不放弃地方文化价值,又为适应乡村都市化背景需求所做出的发展策略调整。在内生发展模式的探索中,当地将文化产业开发作为发展的转变点,以文化产业开发为动力,实现当地文化的再生产,用文化的再生产带动洪山的整体活力。回到侗寨,地方社会围绕水形成的一套水文化体系亦给我们启示,侗寨自古保留下来的人与水和谐共居的图景,及更深层次人与水的文化关联,这些都应化作当下侗寨发展过程中处理人与环境关系需要回归的观念本位。
乡村都市化中,我们应该关注乡村衰落的表象背后所蕴藏的乡村社会强大的维系机制。从这个面向来看,村落共同体并未瓦解,村落依然有着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乡村都市化进程中,村落具有“弹持”能力,即自我修复的功能,而这样的修复功能主要依托文化来实现。以两个村落为例,乡村都市化背景下,传统的文化资源又重新自我修复。通过南北两村的研究,“生存性智慧”和“社会底蕴”或许能成为解释村落“弹持”能力的路径。“生存性智慧”指的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应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11〕,“社会底蕴”则意图强调“生存性智慧”产生以及赖以生存的原因〔12〕。这两个概念的价值在于都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性本能,而人如何生存以及以何种方式生存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面临的问题。
在乡村都市化大背景下,如何关注地方社会的发展,洪山村、上岩坪寨可作为鲜活的案例来讨论。在此背景下,地方社会文化是延续与断裂并存,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文化的断裂性应该建立在对文化延续性的充分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在历史长河中,文化的生产无处不在,而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产,一定是建立在对既有文化事项的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乡村都市化的乡村衰落表象下,是复杂的文化转型过程,是乡村内部经外力刺激迸发出来的修复与适应。在乡村都市化的主动接纳或被动承受的过程中,乡村自我的文化自觉和自觉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民众智慧。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王铭铭.心与物游〔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9-162.
〔3〕麻国庆.“公”的水与“私”的水:游牧和传统农耕蒙古族“水”的利用与地域社会〔J〕.开放时代,2005(1):83-94.
〔4〕黄竹三,冯俊杰.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3:181.
〔5〕李陶红.水资源与地方社会:以山西介休洪山村的兴衰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37(3):9-14.
〔6〕《通道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通道侗族自治县概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0.
〔7〕周大鸣,李陶红.侗寨生态与水资源的传统利用模式:以湖南通道独坡乡上岩坪寨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5(2):50-58.
〔8〕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310-322.
〔9〕周大鸣,李陶红.侗寨水资源与当地文化:以湖南通道独坡乡上岩坪寨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5(4):51-58.
〔10〕周大鸣,李陶红.侗寨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通道独坡乡上岩坪寨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5(3):44-50.
〔11〕邓正来.“生存性智慧模式”: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1(2):5-10.
〔12〕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J〕.社会,2015(1):7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