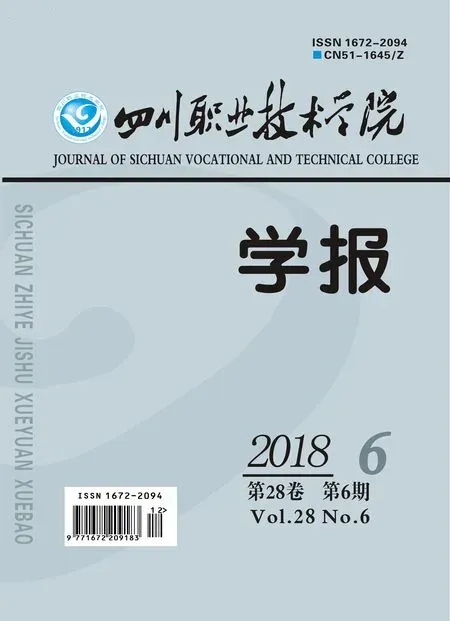论美国引领思想舆论的主要举措
张永红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日趋复杂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思想多元化已经成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面对各种思想舆论相互激荡导致的人们价值观念、社会理想、道德规范等的分化,任何国家(经由执政党或政府)都会进行必要的价值整合,通过对思想舆论的引领减少思想的震荡和冲突,以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优势地位。美国在社会治理实践和应对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注重思想舆论引领,使思想舆论的传播方式、发展方向、社会功能等能够朝着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的方向转化和流变,其中一些举措令人深思。
一、运用法治方式促进社会共识
美国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法治是美国引领思想舆论的重要方式。一方面,美国法治传统为资本主义社会规定了基本的价值遵循。我们知道,法律制度是寻求价值一致性的重要手段,在法律所体现的一整套规则体系背后,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价值选择和对不同价值的顺序排列。在美国,法治的推行使“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被提到主要地位,尽管这些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但它们毕竟是对抗特权、专制、压迫等的手段,因而容易在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体中取得共识。而且,法治所反映的尊重规则的价值追求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价值规定性,体现了一种不同于历史上的神治、人治等的价值取向。人们常常感叹美国人对个人自由和集体纪律的平衡能力,以及对待名人违法犯罪行为等的理性态度,这实际上是与美国法治强调规则、“对事不对人”分不开的。在法治社会里,只要将法治所体现的基本价值主张维护好,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价值共识,就可以起到对多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和缓和社会矛盾,对多样化社会思潮起到了引领作用。社会思潮就是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和冲击的思想潮流,是一定时期里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要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就必须深入了解思潮背后所存在的社会矛盾的性质和表现,采取有效措施缓和和解决这些矛盾,并在此基础上使社会思潮发生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变化。在美国,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思潮无处不在,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少数族裔民权主义等源远流长。当某种社会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造成根本冲击的时候,美国往往会利用法治的方式维护这一社会思潮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诉求,从而缓和和化解社会矛盾,使思想的潮流不至于漫出制度的“堤坝”。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思潮的冲击下,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试图更好地关照和保障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民权法、投票权利法、“肯定性行动计划”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虽然在这之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依然存在,但已不像五、六十年代那么突出,这使得社会反叛思潮由于失去了重要的刺激因素而逐渐沉寂下去,既实现了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也使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得到恢复。美国的法治传统在有效整合和动员社会积极因素、预防执政资源流失、促进利益关系和思想的一致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发挥学校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
学校教育是传播社会主流政治文化即统治阶级政治文化的重要渠道,它在实现思想引领、使人们形成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思想意识、促进多元社会整合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在《知识堡垒》一文中强调美国教育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在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们是主要的保卫者。我们的中小学、学院和大学意识到这种责任对于教育的含义。……这个工作正在成为对我们的未来公民进行美国民主生活的教育的一部分。”[1]美国的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尽管很流行,但资本主义及其优越性的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反共产主义教育等始终居于学校教育的核心位置。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些学者就提出了“课程就是政治文本”的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批判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迈克尔·阿普尔,他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对课程的意识形态性做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课程的价值关涉性。自90年代开始,美国掀起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浪潮,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很多学者转向直接进行价值引领的品格教育,对学生进行直接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引领成为新一轮道德教育的重点。
表面看来,美国非常强调教育和学术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始终是有前提的,就是不能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相冲突。对于各种与主流价值观相冲突的思想意识,美国主流社会总是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抵制。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美国历史教科书问题。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全国中小学教学中心公布了一套全国历史教学标准,要求学生关注奴隶制、移民和都市贫民的经历、尖锐的劳资矛盾、强占印第安人土地、种族歧视、麦卡锡主义,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等,使学生认识“美国梦”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标准”由于揭露了美国的阴暗面而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参议员斯莱德·戈顿抨击“标准”是“披着历史伪装的意识形态”,要求防止这些“极具破坏性的”“标准”进入学校。最终,美国参议院以99:1的绝对多数通过戈顿提案,“标准”的作者被迫修改与美国“主流历史”相分离的“错误概念”[2]。在美国,校园里的争论虽然活跃,但都难免受到“熔炉”思想的限制,教师一般来说只能在意识形态的边缘地带做些细节上的修补,但却不能跨越意识形态的边界。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尽管美国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不少,但由于学校教育所集中反映的核心价值观、政治观长期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即便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学生反叛思潮,最终也沉寂了下去,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这与美国学校教育的社会教化是分不开的。虽然当时的青年学生看上去比他们的父辈要激进得多,但事实上很少有人真正跨入与父母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而是基本上“位于光谱的同一边”[3]。美国通过发挥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教化和灌输功能,以及在多元社会文化背景下整合和统一社会成员思想的功能,实现了对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引领。
三、借助宗教的价值引领和政治导向作用
美国是个宗教情绪极为强烈的国家,宗教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美国的政党政治越来越成为分裂美国社会的重要因素,但在宗教问题上,美国人对各种宗教团体的态度总体上却比几年前更加积极了。在从0到100的“感情温度计”上,美国成年人对几乎所有宗教团体都做出了比2014年6月的调查更高的评分,而且一般来说,拥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做的评价更高[4]。
在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中,美国统治阶级习惯于借助宗教力量将社会大众的宗教信仰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力量。美国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主要内容大多可以在宗教教义中找到根源。美国历史学家德格勒就曾经说过,清教主义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5]。在日常生活中,美国宗教界人士常常深入到军队、大学、医院、监狱等组织中,专门为军官和士兵、学生和教师、医生和病人、警察和犯人等人群提供宗教服务,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引导人们自觉依据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引领、改造、修正或批判其他社会观念和思想潮流。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宗教在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暴政”、引领民众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期间,基督教是“美国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重要立足点”及“在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性质和美国国民性的宗教基础之间”划界之工具[6]。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占领所谓的“道德高地”,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把宗教自由、人权等问题融为一体,继续利用基督教传播推行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消解非美价值观,极力按照美国价值观塑造国民思想和世界面貌。甚至在战争问题上,宗教也发挥了思想引领的作用。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曾经把争取独立自由的政治任务与宗教旗帜巧妙结合起来,将争取民族独立说成是上帝的意旨和安排,以此来引导和动员广大民众。在现代社会,美国宣扬基督教主张的仁慈、博爱等价值观,并认为美国人充当“世界警察”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职责,以此消除社会上的“异见”、“杂音”,为霸权主义和干涉行径清除思想障碍。
由于宗教在思想引领方面的巨大作用,许多美国的政界领袖都很重视与宗教的关系。自20世纪中叶起,美国每年都举行由总统、参众两院议员参加的全国早餐祈祷会。美国总统不仅信仰宗教,而且与宗教界知名人士关系密切。美国福音派牧师格雷厄姆就曾先后连任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总统竞选及执政期间的非官方顾问和白宫布道家[7]。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在白宫成立了一个学习领悟上帝“精神”和“旨意”的“中央圣经研习小组”。这个宗教小组的主讲人是领导着美国43个分部和20多个海外机构的宗教组织负责人拉尔夫·德罗林格,具有广泛的宗教影响力,而该小组也因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被外界认为暗含着政治主题。政界领袖的宗教信仰及政府与教会和宗教人员的密切关系,使政府可以利用宗教特有的力量宣传政府合法性,从而提高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达到争取民心、引领民意的目的。
四、利用民意调查了解和引领民意
民意调查(也称民意测验)是把握民众社会心理和思想动态,进而在思想引领中取得主动的重要手段。美国是民意调查的发源地,它的民意调查可以追溯到1824年《宾夕法尼亚人报》举办的模拟投票。在长期的实践中,美国形成了面访调查、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等民意调查方式,以及适合对某一事件或现象进行深度探索的焦点团体调查方式。民意调查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美国舆论研究和选民行为研究的发展,对美国塑造舆论、引领思想、制造同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意调查是美国实现民意管理的有效机制。面对当代社会民意如流水般的复杂特质,民意调查为民众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担当了美国民主守门人的角色,同时也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政策的合理变迁、减少社会多元价值观冲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对此,美国学者戴维森深刻地指出,尽管社会上仍然有各种游行、骚乱和罢工,但如果没有民意调查,骚乱和暴乱将会更多。他强调,“当公众舆论中出现暴力性表达时,我们应该仔细地审视我们自己的表现,问问我们是否在某些工作中有所失误。”[8]美国名目繁多的民意调查所产生的各种数据,不断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着作为判断依据的第一手材料。
美国不仅利用民意调查了解民意,而且还影响和控制民意。如果说前者发挥的是“化验师”的作用,那么后者发挥的就是“化妆师”的作用。尽管民意调查离不开对科学方法的运用,但它不是绝对中立或中性的,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政策行动,要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杜鲁门时期的总统顾问乔治·埃尔西说得明白:“总统的工作是去引导民意,而不是去做(民意的)盲目追随者。”[9]在这个过程中,民意调查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利用民意调查左右民意的例子并不少见。美国学者劳伦斯·雅各布斯和罗伯特·夏皮罗经过访谈发现,在尼克松时期,政府曾经迫使民意调查机构与其合作,这其中包括:“在民意测验结果公布之前就可以获得信息,使白宫能够采取措施扬长避短;促使民意测验机构选择有利于政府的问题和措辞方式;修改测验结果。”[10]在政客们眼里,民意调查远不是反映民意的一面镜子那么简单,它还可以作为操控社会舆论的工具。一般而言,基于调查产生的民意一经发布,本身又会成为一种舆论,形成“乐队花车效应”或“羊群效应”。就是说,民意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往往会成为社会大众关注、议论和思考的话题,反过来又会对民众的态度产生影响,实现民意调查的示范沟通功能,产生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潮流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有选择的民意调查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活动,民调机构也总是试图巧妙地传递与政党、政府的立场、利益、价值观相吻合的信息。
为了更加有效地引领民意,美国一些专门研究民意问题的机构,如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皮尤研究中心等,还对民意的制造、使用和表达等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等多种民调方法,为引发公众价值观和情感的共振,或制造一定的环境影响和改变公众态度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五、多举措强化媒体的思想舆论引领力
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沟通方式和渠道,媒体通过对新闻报道内容、报道量和报道时间的安排,以及对事件发生原因及同其他事件的联系的解释,持续向公众输送经过选择的材料和观点及其对这些材料和观点的分析、评论,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信息接受下来,从而形成某种特定的思想倾向与态度,实现影响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识、引领思想舆论的目的。在美国,媒体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新闻界的力量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原生力量”,“它决定公众讨论的议事日程;而且这一广泛政治力量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它决定人们谈论和思考什么……”[11]为了达到引领舆论的目的,美国媒体惯用的手法,是“把语言夸张、滥用、曲解”,然后用所谓的“真相”,或者用“足以称得上所谓官方的消息”垄断性地占据版面,迫使其他新闻被推迟或干脆取消,从而在不断的重复中将“主义”变成“既成的真理”[12]。美国媒体常常在民众面前将自己塑造成“言论自由”的代言人,但实际上,媒体宣传的目的在于散播一系列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以此维持大众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拥护,同时围绕现存权力分配的合法性主题建立社会共识。更直接地说,美国媒体的宣传体制不过是统治阶级引领和控制民众思想舆论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公关,善于通过媒体向民众宣传其意图、计划、政策,了解舆论并采取多种措施引导舆论。为了有效控制和引导媒体,美国总统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新闻秘书,而且还通过直接召开记者招待会阐明政策立场。为了制造媒体事件,美国总统频繁发表经过精心设计的演讲、声明、谈话。用美国学者玛莎·库玛的话说,“虽然新闻界不是政府的直属部门,但是总统和白宫通讯宣传人员经过通盘考虑确定了一些途径,以便利用新闻媒体向广大民众和他们心目中特定的若干团体传递总统信息。”[13]美国的政客们、尤其是总统总是会奖赏那些友好的记者,惩罚那些不友好的记者。总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批准哪些记者参加,拒绝哪些记者,都表明了一种奖惩的态度,政府在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或试探外界反应时,也总是会向一部分与其关系密切的记者“走漏消息”。而媒体记者们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消息,特别是在撰写调查性报道或要了解所谓“内情”或“内幕新闻”时,就必须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否则就会处处碰壁。为了协调政府与媒体之间的联系,美国政府有时会直接聘用专业媒体人担任要职,如在阿富汗战争前任命广告巨头夏洛蒂·比尔斯女士为专门负责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为了体现“新闻自由”和媒体的“价值中立”,获取公众信任,更好地引领舆论,美国政府还善于利用为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宣传美国价值观和政府政策。这些带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或自己制作各种广告、传单开展宣传,或在资金、信息等方面为媒体提供帮助,在内宣和外宣上都担负起越来越多的“美国责任”。
美国的媒体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表面上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与政党的自由权力,但它在根本上是受政府和政党控制的。美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利用媒介公关技术控制媒体,实现新闻流的定点投放,给媒体“喂食”,更好地塑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单面人”,使社会思想舆论向着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方向发展。
结语
美国的思想舆论引领从根本上说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表现出很大的阶级局限性、误导性和欺骗性,但其对思想舆论引领的高度重视和对多种引领方式的运用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思想舆论引领是不断壮大主流思想、巩固政权、稳定社会、防止因忽视或错误引领而导致混乱无序的需要。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曾说:“任何社会,为了能存在下去……必须紧密围绕保持其制度完整这个中心,成功地把思想方式灌输进每个人的脑子里。”[14]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层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不同思想舆论将带来各种社会情绪的交织碰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此,我们必须重视和持续加强思想舆论引领工作,避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被动的局面,不断夯实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思想舆论引领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发挥各种宣传阵地、传播手段的作用,以及法治方式、社会力量等的引领功能,要避免将思想舆论引领工作仅仅局限于学校和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简单化做法,通过多方参与、同向发力强化引领合力,使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公民的日常生活理念。从根本上说,我国思想舆论引领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内在的吸引力,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借鉴并恰当运用合乎我国国情的引领方法,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价值共识,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集聚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