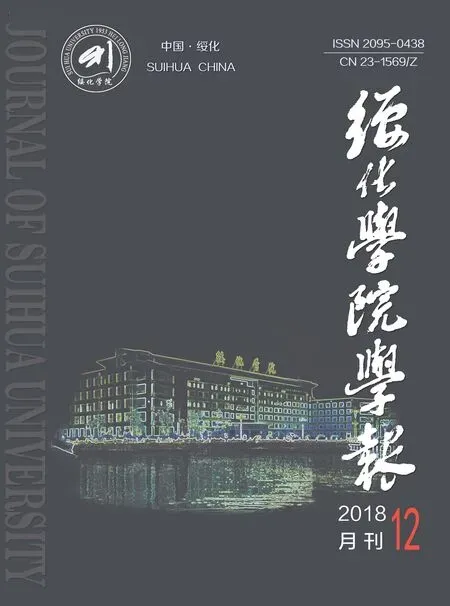叶广芩小说论
于 静 范庆超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32)
叶广芩,1948年10月生于北京,满族,叶赫那拉氏。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木川》《状元媒》《采桑子》《全家福》等;中短篇小说集《黄连厚朴》《山鬼木客》《梦也何曾到谢桥》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女性文学奖等奖项。
一
《青木川》主要讲述了陕南山区的一个名叫“青木川”的小镇的前世今生。小说采用回忆笔法,通过曾在青木川领导剿匪工作的解放军三营教导员冯明的“访旧”展开叙述,连同青木川老人们(诸如魏元林、魏漱孝、郑培然、许仲德等)的追忆,复现上个世纪50年代青木川的民间历史。小说叙述的动力和契机便是对青木川的“访旧”。除了离休老干部冯明之外,小说另有两个寻访者,分别是冯明的女儿作家冯小羽,以及冯小羽的同学钟一山博士。这三个寻访者的寻访,构成小说的三条叙述线索。冯明寻访的是自己的“革命记忆”,冯小羽寻访的是青木川的土匪魏富唐的传奇人生,而钟一山寻访的是杨贵妃与青木川的历史勾连。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其中冯小羽寻访的部分,即有关土匪魏富唐的传奇人生,是小说的叙述重心。关于这部分,叶广芩付诸了很多的笔墨,讲述了魏富唐如何创建地方武装、归顺共产党的始末、被剿灭的境遇,以及兴办教育、发展经济、开启民智的义举。还叙写了他与朱美人、大小赵、谢苗子、谢静仪的爱情传奇,塑造了一个民间史语境下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土匪形象。而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要目的。对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土匪,人们总容易将其脸谱化,想当然地视之为“无恶不作”“十恶不赦”,实则有违于历史的实际。叶广芩想改变人们对土匪的常规化理解,也想藉此纠正人们固化、平面化的历史观。
《状元媒》是一部具有“家史”性质的小说。小说以“回忆录”式的口吻,讲述了我的父母在晚清状元刘春霖的撮合下结为连理的“状元媒”故事。并以此为背景,勾连起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叶广芩凭借自己的京剧喜好、戏剧文化积淀以及人生体验,别出心裁地使用戏名来象征性隐喻、对应诸般人生形态,营造一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叙述氛围。正如叶广芩自己概括的那样:“小说以父母的结合为契机,以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的故事为背景,以我的视觉为轴线,冠以京剧的戏名而写成。”小说的篇章由十一个戏名组成,分别为“状元媒”“大登殿 ”“三 岔口”“逍 遥津”“三击掌”“拾玉镯”“豆汁记”“小放 牛”“盗御马”“玉堂春”“凤还巢”。主要讲述了我的父母、我的舅舅陈锡元、我的表兄大连和小连、我的七舅爷、我父亲的同学王国甫、我的五哥、我家的老厨子莫姜及其丈夫张安达、我的五姐和五姐夫、我自己的人生际遇。这部小说最活跃的因素就是人物。这些人物的身份各异,活动的社会空间广阔,具有一定的社会标本性和历史概括力。由他们组成的人物形象系列,有效地串联起一部老北京的“人生史”。这种人生史虽然具有一定的民间色彩,带有几分“野史”意味,但得到了叶广芩“家族史”的辅证,又表现出一定的合历史规律性,因此具有了一定的“信史”色彩。这种蒙着“野史”面纱的“信史”,无疑有助于了解北京百年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
《采桑子》也是一部带有“家史”性质和自叙色彩的小说。依然是以我为视角,叙述了北京金家十四个子女的故事。因为同写家族故事,所以《采桑子》与《状元媒》难免存在一定的情节交叉,某些家族成员的人生经历在两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互现。但两部小说又有明显的不同。首先,《采桑子》的生活容量要小于《状元媒》。所涉人物相对较少一些,多局限在家族内部。而《状元媒》包罗的人生更广阔。其次,《采桑子》将纳兰词的词牌作为篇章名,而《状元媒》则以京剧的戏名作为章节名。二者的象征思维机制虽然相似,但寄寓的旨意和情感却不尽一致。“今日将其《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一词的词牌、词句作为本书书名及章节名,一方面是借其凄婉深沉的寓意,弥补本书之浮浅;一方面也有纪念先人的意思在其中。”(《宋桑子·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而《状元媒》采用戏名冠谓章节则更多倾向于戏剧情节与人生内容的对应性勾连,多属“知识性隐喻”,而《采桑子》的“词牌象征”则偏向“情感性隐喻”,所以《采桑子》的抒情性更强,“凄婉深沉”的情感氛围也有效烘托了小说的悲剧性叙事。
《采桑子》中的人物命运大都带有悲剧色彩。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爱新觉罗子弟的命运悲剧?在叶广芩看来,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八旗子弟劣根性”。对于“八旗子弟劣根性”的揭示,体现了叶广芩作为一位满族作家、一名“八旗子弟”后裔的民族自省意识,或者说是对满民族性格的负面因素的失望。“八旗性格”固然有“劣根性”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在《采桑子》叙写的某些八旗子弟的命运悲剧中,我们也分明看到了某些正面的“八旗性格”(或者说“八旗精神”)。比如老五金舜锫的儿子金瑞对婚姻的选择,我们看到了“八旗性格”的积极方面,比如超功利、超庸俗的取向,重义轻利的品格。这些性格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导致了八旗子弟的物质贫困,但也成就了他们一股子“劲儿”、一种精神气格。这种“劲儿”,可能在凡夫俗子看来是一种“愚劲儿、傻劲儿”,但身临其境的八旗子弟们确视之为当然,践行之、坚守之,且不为世俗所动。这种“劲儿”无疑带有贵族气,富于超现实、超功利色彩,体现了满民族精神的超拔性。
再如老七金舜铨,他是名满京师的画家,他一生醉心于“文人画”。无论生活境况如何,绘画界发生了什么新动向,他都不改初衷,始终追逐一丝不苟的工笔画风,并沉浸其中、自得其乐。尽管他会遭遇尴尬,但金舜铨依然还是那么飘逸儒雅,坚守着自己的艺术标准。这种喧嚣中的坚守,在很多情况下,正是产生一流艺术的必要前提。在中国文化史中,之所以能够涌现出众多一流旗人艺术家,不能不说与这种倾心“体物”的“八旗性格”紧密相关。如果说对于“八旗子弟劣根性”的批判符合人们习惯性的历史心理预期,那么对于正面的“八旗性格”的发现确有些“出乎意料”。但正是这种正面发现,显现出叶广芩作为满族作家的一种民族文化自信。《采桑子》的满族文学品格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如果说《采桑子》《状元媒》的家史叙述带有自叙色彩的话,那么《全家福》则可以说是一部他者的家史。在这部小说中,叶广芩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了京城著名建筑世家赵家第十九代传人王满堂家族几代人,以及灯盏胡同儿街坊邻里们从解放前至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王满堂及其街坊邻里的家庭生活史在小说中占据了很大篇幅,这使得小说显得有些散碎,但也展示了寻常生活的百态。很多人生的酸甜苦辣、离合悲欢、生死爱恨在这里得以展现,引发人们对人伦道义的理性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生活史的叙述中,我们总是能够捕捉到类似于“公私合营”“发公债”“修建人民大会堂”“大炼钢铁”“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中美建交”等时代历史讯息。这些讯息或者出自于家庭成员们之间的谈话,或者来自某些家庭成员的亲身经历,总是有一些可靠的见证。如果仔细捋顺一下,会发现这些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严谨次序,显然是经过了叶广芩的用心编排。她试图通过家庭生活来演绎时代的变动,并且倾向于通过家庭生活的乱离来折射时代历史的荒谬。这就使得《全家福》的家庭生活史叙述超越了日常性,具备了承载政治历史的功能性价值。
除了家史之外,王满堂及其后代的“建筑工作史”也是《全家福》的重要内容。小说要突出的正是王满堂热爱建筑业、热爱古建筑文化这种执着的职业精神和传统文化捍卫意识。为了将这个问题引向深入,叶广芩还有意设置了对比性存在,这便是王满堂的后代们对王满堂心之所系的建筑业的态度。这当中,叶广芩不断地让王满堂发声,规训那些偏离了行业正道的“不肖子孙们。这些规训,不仅是职业规训,更是道德规训,在世风日下的当今,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二
除上述几部长篇小说,叶广芩还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主要收录于中短篇小说集《黄连厚朴》《山鬼木客》《梦也何曾到谢桥》等。根据这些小说的题材内容,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复现抗战记忆、反思战争后遗症的作品,诸如《风》《霜》《雾》《雨》《霞》等;第二类是表现陕西民间生活的作品,以《天上船》《对你大爷有意见》《岸边》《上镜》为代表;第三类是呼吁野生动物保护的作品,包括《狗熊淑娟》《熊猫‘碎货’》《老虎大福》《山鬼木客》等;第四类是题材视点比较散碎的、较难统一归类的作品,主要有《夹金山穿越》《孪生》《学车轶事》《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寂寞尼玛路》《套儿》等。
在第一类题材的小说中,《风》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我”(研究日本战后法律经济的学者)寻访战争遗迹,以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六支队少佐西垣秀次和汉奸(华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突破口,复现了1943年5月华北日军制造的“临州大屠杀”的历史细节。小说一方面是为了凸显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另一方面也是想呈现历史的复杂性,试图改变对“汉奸”和“侵略者”习以为常的“脸谱化理解”。《霜》主要讲述了日军战争遗孤李养顺在中国成家立业后重返日本,所遭遇的种种文化隔阂和生存困境。从侵略施动者的角度反思战争代价。《雾》通过展示慰安妇张高氏的苦难,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但小说的主旨并不止于此。而是通过日本的“女权主义者”修子对待张高氏的功利主义态度(将张高氏视为其“捍卫女权”的符号),以及战后日本民间团体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敷衍,折射日本社会对待侵华历史的不诚实、不悔改的顽梗态度和反历史倾向。《雨》原名《广岛故事》,以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历史背景,通过两个怕雨(受核爆炸所导致的黑雨之害)的老人山本柯子和柴田榕子的受害经历,谴责核战争对人类的无穷伤害。《霞》的题材性质与《霜》类似,依然关注的是日本战争遗孤重返日本的膈膜问题。只不过主人公变成了金静梓。小说主要展现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金静梓,与吉冈家族的成员们在历史观、战争观、家族观、两性观、生活观等方面的分歧与差异,折射出海外战争遗孤重返日本社会的艰难。
在第二类题材的小说中,《天上船》以“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回忆了“我”赴陕西农场插队的生活。“插队记忆”显得琐碎:“我”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改造的经历、被拖拉机手歧视、与农村夫妇之间的患难情谊、充满诗意但却无望的爱情……小说的主要目的是记录“被荒废的青春”,进而引向历史反省。《对你大爷有意见》依然是第一人称视角,记述了“我”在野竹坪乡政府挂职副书记期间的一段见闻。鲜香椿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她是一个性情刚烈的离婚女人,她为了“竞选”乡政府的妇联副主任,送“我”五瓶香椿,希望“我”能投票给她。她的理由是“我是真想为女人们说说话做点事”。尽管“我”对她表示同情和理解,但还是无法改变已经“内定”的习惯性套路。鲜香椿虽然向乡政府抗议,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小说通过一个离婚的乡间女子向流言蜚语、向男权政治的抗争,张扬了女性意识。同时也显示出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在乡村基层政治秩序中“天真的尴尬”。《岸边》和《天上船》题材类似,都属于“知青小说”。仍取材于作者曾经的农场插队生活。讲述了“我”与农场其他几位成员:开拖拉机的老万、做饭的李瘪、厂长兼指导员雷春茂之间的日常生活交往。从这些交往中,我们可以窥见许多历史的痕迹,诸如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成分论、大跃进、五·七道路。这些历史的负效应均不同程度地作用于“我”这一代人的生活,造成了“我们”的迷惘、痛苦、尴尬和无奈。这是叶广芩此类“知青小说”的共同旨向。
在第三类题材的小说中,《狗熊淑娟》讲述了一只名叫“淑娟”的狗熊的遭遇。因它是一只老狗熊,盈利价值不大,所以遭到了动物园的遗弃,被卖给了民间马戏团。饲养员林尧积极奔走求助,为“淑娟”寻找归宿,希求获得企业的领养。但最终“领养它的人也是要吃它的人”。“淑娟”的熊掌成了餐桌上的美味。小说谴责了人类伤害野生动物的残忍。同时,通过林尧和“淑娟”之间的真情和默契,说明人类和动物的爱也可以到达人际之爱的层次,进而从爱的表达能力上肯定了动物与人类的平等。《熊猫“碎货”》记述的是四女一家人对熊猫“碎货”(山里人对所喜爱的孩子的昵称)的怜悯与拯救,凸显人类对于动物的温情,呼吁人和动物的和谐。但小说的生态思想并不止于此,有两处情节值得注意:第一处情节是四女对“碎货”天性的尊重(“又脏又咬人的熊猫才是真熊猫”[11]],第二处情节就是“碎货”最后咬碎了窗框,冲出小屋,返归自然。这就强调了“自然才是野生动物的归宿”的成熟生态观。《老虎大福》讲述的是山里人二福对大福(老虎)的深情,表现一种人和动物的缘分和默契。这种“物我合一”的状态与二福爹对大福的猎杀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显现出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残忍迫害和疯狂索取(将虎油、虎肉、虎骨、虎皮悉数瓜分)。猎杀大福的原因在于它吃掉了农户的家猪,当人的利益被野生动物伤害时就一定要以牙还牙吗?没有其他的生态策略吗?如何科学理性的解决人和动物的矛盾,进而实现人和动物的和谐共居?这是该小说关注的深层生态问题。
在第四类题材的小说中,《夹金山穿越》是一部具有“穿越”色彩的小说。我们在一次考察藏区的归途中,在海拔3000多米的夹金山产生了一次神奇的幻觉:我们与当年翻越夹金山的红军一老一少两名战士相遇。对于这次奇遇,作者援引的观点是:“有人提出了时空的缠联和存在转移的观点,过去、现在、未来,此地和彼地,时空宇宙的每个部分都交互折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尽缠联的全像。”(《夹金山穿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这似乎可以解释“穿越”现象。小说的新颖题材和奇幻色彩使其具有某种探索性质。《孪生》的主题有关孝亲人伦。即使“我”知道“我”与肖小梦是真正的孪生姐妹、与毓松并非真正的孪生兄妹,“我”依然没有选择依附富贵之家,而是同毓松一起承担家庭的重担,奉养病中的母亲。“直系血缘”在“非亲道义”面前,并非具有绝对优势,这是小说的重要旨向。《寂寞尼玛路》带有散文色彩,讲述了“我”去西藏尼玛的旅行见闻。对少数民族地区贫穷的优思、对少数民族人民真挚性情的感动,体现了作为满族作家叶广芩的少数民族情怀。《套儿》以儿童视角叙写了“我”与儿时的玩伴“套儿”之间的往事。小说以童年游乐记忆开始,以“套儿”患痨病搬家离开从此下落不明结束,表现了一种人生无常感。小说既是缅怀故人,也是缅怀时光、缅怀老北京的胡同生涯,儿童记忆中散发出浓浓的“京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