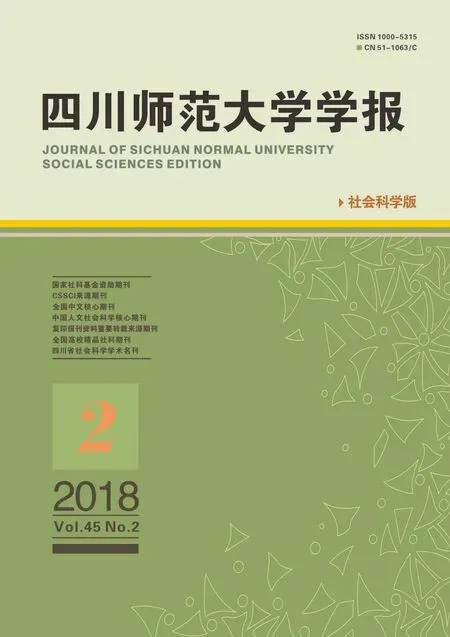“法律信仰”危机与选择:伯尔曼的问题与方案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法律信仰”或许是20世纪最响亮的法律语汇之一,伯尔曼在讲演中无数次提及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同样振聋发聩[1]28。由此,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进入中国法律人的视野,甚至每个法学院的必修课程都会提到它。然而,这句话本身的光鲜亮丽却让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某些问题:伯尔曼为何会提到“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个命题旨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解决的问题确定的话,那么有无与之相竞争的理论?对于中国当下而言,是应该把这个论题作为某种“训诫”,抑或是作为某个解决问题的理论?如此种种问题,尽管长期包含在关乎法律信仰的话题中被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但似乎依旧缺乏有说服力的论断以及与之相应的深度阐释。
从一个更宽泛的论域来看,近年来,围绕法律信仰所进行的论述大多是在认肯其对法治事业起积极推进作用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对法律信仰本身的可能性抱有批评和否定态度的论者则相对较少。但是,对法律信仰论进行批判的观点,其论证力量却不容忽视。比如,有论者直言法律信仰本身作为命题的错误性,究其原因则在于法律并非信仰的合宜对象,并且也难适中国国情[2]。也有论者从功能视角出发,认为在社会控制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的法律与宗教实难合一,并且从有效性的角度而言法律更要求正当合理与现实可行的特性[3]。一些学者在理论移植的角度上指出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实践之间的内在悖论,并历数法律信仰与传统间的鸿沟、在法律信仰的理解上倾向于法律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等弊病[4]。还有一些批评聚焦于作为自为领域的信仰与具有可错性和工具性特征的法律之间的张力,认为信仰法律缺乏法理上的依据[5]。
上述批评多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信仰论上展开的,其中伯尔曼的观念大多时候只是作为论述的引子或线索,并非论述所关照的中心。而专门以伯尔曼的论述为基础并在回溯和反思其观念基础上进行批评阐述的,当首推范进学先生《“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一文,伯尔曼的经典论题在文中得到了重新审视[6]。范先生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伯尔曼所提到的“整体性危机”及其应对之道,继而对伯尔曼的贡献进行了概括,认为其旨在寻找“法律与宗教的内在联系,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忠诚”;认为伯尔曼所言并非“信仰”,而是“信奉”或“信任”,我国法学界可能都误读了伯尔曼;最后对法律信仰的国内研究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信任”模式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范先生的文章或许是在要求我们不要对某些未经仔细辨别的论点采取盲目引用的态度,由此,仔细的寻找文本的原有之意以及澄清可能出现的错误成为范文的重点所在。就范文提出的论点而言,笔者同意其对整体性危机的历史梳理,但不赞成将“信仰”改变成“信奉”或“信任”,对中国语境下的守法模式从“信仰”变化为“信任”也另有异议。下文仅就范先生的论点以及前文之问题展开论述,并就此问题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提出某些可能性的思路。
一 整体性危机及其各方应对
西方法律在20世纪遭遇的整体性危机在《法律与宗教》中得到详述,这场危机是“自我对觅得秩序和意义”[1]8的信心的缺失。而《法律与革命》也在导论中回溯了这一危机,并将其表述为“对作为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共同体的西方本身的信念和对9个世纪以来维系西方文明的那种法律传统普遍丧失了信心”[7]46。按照伯尔曼的理解,法律丧失整体性后,西方文明恐怕也难免受到威胁,固然,这可能是将论题予以放大以引起各方关注的做法,但伯尔曼以此也是为了突显他所重视的问题:如何重构这种整体性?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的肇始或许可以追溯到休谟,其“是”与“应当”分离的著名论证实则给出了整体的幻灭,此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逐渐式微加速了危机的形成[8]509。在法学领域,实证法学运动也摆脱了法律源于某种神秘莫测的教条这一陈旧观点,而是被当作一种“事实”。边沁认为法律是符号的集合(an assemblage of signs),因此不涉及价值而仅仅只是事实[9]1。由此,“事实命题”成为了广义法律实证主义的标志,用事实陈述替代规范性陈述,用“习惯命题”替代合法性命题,成为了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法学的主流。奥斯丁认为,如果不诉诸于制度事实,就无法说明构成法律的规范是什么,也无法说明作为行为理由的规范是什么[10]1。就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而言,对其正当性的判断,不能诉诸那些有效性不依赖于人类意志和制度的先验标准;恰恰相反,制度正当性所依赖的不是社会理想,而是社会成规——习惯和惯例[11]723。然而,由实证主义带动的这场运动却为自己留下了难解之谜:基于科学的法律体系无法保证其完整性,法律存在漏洞无法避免,逻辑本身不能替代现实的生活。由此,之后的法学思潮便专注于反实证主义(反逻辑)和反形而上学(反自然法),规范性问题被消解,逻辑性问题被放逐,法律在一朝之间几乎被彻底的现实化。在那个时代,霍姆斯曾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揶揄自然法,认为自然法只是“醉汉”眼中的“绝代佳人”[12],而法学家追寻普遍有效准则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的观点几乎将实证主义逼得理屈词穷[13]3。由此,由形而上学来保证的法的整体性成了玩笑,由逻辑来保证的整体性已经让位于“经验”,法律不再是整体的,多元论者大行其道,现实主义法学提出的“法律既没有那么确定又没有那么明晰”口号几乎使得法律成为一地碎片[14]187。法律这种分崩离析的图景引起“规则的怀疑”,面对法律规则的解构,对法律本身“丧失”信心几乎成为必然[1]19,78。有鉴于此,如何把握和重拾整体之法?
诚如我们所知,20世纪法律的整体性问题也正是规范性的重建,法哲学领域内更是如此。在实证主义内部存在哈特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在政治哲学层面罗尔斯通过“实践性反思”来建立当代的规范性,在现象学领域通过“意向的就是规范的”这一论题而展开讨论,德沃金通过“帝国”式的神话所包涵的“正确答案”命题来维系法律的规范性和整体性。当然,在《法律与宗教》中,伯尔曼也试图面对这个问题,他正是通过法律与宗教的联系来揭示法律的整体性问题,这也是对“工具论”的挑战[1]17。
哈特在其根本观念上捍卫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认为关于法律的“事实命题”、“因袭命题”和“分离命题”是实证主义的关键[15]593;但哈特反对奥斯丁“主权者命令”的事实性描述,而且他用“规则事实”替代了“主权者命令”的事实,并企图用“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赋予“习惯命题”以规范性[16]193。这些工作旨在通过“法律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这一论题,来重塑关于实证主义的“整体的法”的形象[16]79。但哈特认为法律可能出现漏洞,提出需要法官进行“缝中立法”的观点,实际上使法律的不确定性得以借此展开,如同一扇“凯卡波尔塔之门”,法律的整体性又将面对法官恣意的危险[16]7。在整体中留下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无异于使整体不复存在,似乎也与法律实证主义“基于个人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不受他人任意的威胁”的宏愿背道而驰。如若从哈特的语言哲学背景来探究,哈特实则是在反对“私人语言”的同时又赞同了“私人语言”,这是哈特理论中的悖论。尽管后继者力图挽回哈特学说的败局,但哈特关于法律整体性的努力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实证主义自身难以完成这一任务①。
在解构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下半叶,罗尔斯以忧思而决绝的情怀与态度扛起了重构规范性的重担。这决不意味着罗尔斯是无知的——没有意识到在功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内外夹击下重新选择思考规范的整体性建构问题会面临多大的质疑与困难;恰恰相反,他正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失败与规范性问题被瓦解的现状。于是,谨慎的罗尔斯敏锐地选择了一条回到反思的理性主义道路,康德对于规范性的建构方案成了他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首先,罗尔斯同意将康德的“道德人”作为其论证的起点,理性的预设将使得个体具备自我选择与道德行为的能力;其次,罗尔斯原创性地为这种道德主体加上了“无知之幕”的限制,屏蔽掉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对于各方主体之偏好的影响,用预设各方在群体生活中的理性选择代替了古典自然法理论中由对上帝的信念所保证的规范义务,同时拒绝了功利主义以目的来评价行为之正当性的信条。这样,罗尔斯最终完成了“原初状态”下的个体进行自我立法的反思性实践,并保证他们在一般考虑的基础上得出普遍性的正义原则,以实现对于整体性规范的建构。这种基于反思性的规范建构与思想实验,从“弱前提”出发,却可以得出“强结论”,为可接受的正义原则提供可信赖的证明。在此,正义原则之正当,源于“原初状态”下的个体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种普遍共识与彼此同意,而法律的整体性在此作为规范性问题的一部分,也经由正义原则而得以保全[17]91-124。于是,整体性问题在此实现了复活。
如果说罗尔斯是从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视角进行整体性论证,那么德沃金则致力于构建一个纯粹的“法律帝国”以统合法律的整体性。德沃金最早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体现在其成名作《认真对待权利》中,“正确答案命题”就是其“整体性”法律观念的基本观点,他指出,“正确答案命题”本身是一种“前后一致方式的陈述”,并认为“正确答案命题的神话,不仅顽强,而且成功,这种顽强和成功可以证明这并不神秘”[18]290。在随后的《法律帝国》里,德沃金用“章回小说”和“法官赫拉克勒斯”重新回应了这一问题。德沃金一直致力于提供一种融贯的理解,将“正确答案命题”与规范性问题相联系,并建构一套对于法律诠释的整体性论证[19]63。尽管德沃金对于法律帝国的构想同样是基于反思性实践,但与罗尔斯的“思想试验”不同,德沃金的方案是“现象学”的,他采取了“朝向事情本身”的策略,直面法律实践。在实践中,规范性“被给予”我们,因为“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提供了共同体法律实践最佳的建构性解释”[20]255。
伯尔曼同样在直面整体性这个令人纠结与不安的话题。他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将法律与宗教做类比,初看起来,或许这种分析方法有些牵强,但其论证过程却是令人震撼的。伯尔曼坚信,法律的纯粹国家化很可能将导致其规范性的丧失,西方历史上每一次革命的过程都是法律的宗教性逐渐被消解的过程,与世俗化相伴随的是法律神圣性的消褪,权威逐渐被瓦解。事实证明,在法律实证主义甚嚣尘上的20世纪,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法律几乎被彻底世俗化,“没有信仰的法律褪化为僵死的教条”[1]12。于是,伯尔曼面临着同样的时代性难题:我们如何走向未来?他从宗教和法律的相似性中得出,法律自身需要保持一种适度的神秘,以维系社会对其规范性权威的一种虔诚。法律是整体的,其规范性的来源使其获得整体性的保证。与此同时,伯尔曼也试图通过这种观念激发公众对于法律的忠诚,因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远较强制力更为重要”[1]17。在此,伯尔曼的观念是整体的,不论对“法律”一词作何理解,这都是一个不能进行拆分的概念,因为其目标就在于重塑法律的整体性,并将规范性作为法律整体的基石。由此,在“法律必须被信仰”当中所谈及的“法律”是作为整体的法律,并且伯尔曼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整体性危机”。宗教的关键在于信仰,而将法律与宗教做类比后,伯尔曼的方案在于使法律获得宗教性的高贵,由此对于整体的法而言,论及的也只能是“信仰”。现今由“be believed in”展开的论争,就伯尔曼的本意而言只能是信仰。
在论及此一话题之时,范进学教授认为伯尔曼视野中的法律“有五种观念”,因而将伯尔曼总结为“综合法学”,并指出“法律信仰”是需要区分“法律为何”才能论述的,最终得出“法律信仰”的提法其实不是伯尔曼的观念[6]。依笔者之见,伯尔曼实际并未区分各种关于“法律”的概念,因为整体性要求我们不能再去进行这样的区分,即使进行区分也不能将这些不同的概念完全分离开来,因为这一切都在整体之中,而“完整性所需要的视野,这一视野必定超越了现在威胁着要毁灭我们的种种分裂”[1]7,这是伯尔曼论及法律信仰的关键所在。由此,伯尔曼指出法律信仰并不值得怀疑,他正是想通过这一论题来直面法律的整体性。其实,纠缠于伯尔曼是否提出“法律信仰”并不是最主要的,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试图通过“信仰”来挽救法律的整体性是否值得?这一问题无疑更具有学术上的价值,用法律的宗教性来维系整体性的观念的做法是否可能比规范性论证更有意义呢?换言之,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伯尔曼理论的优缺点,而非他是否谈及了法律“信仰”抑或“信任”。
二 有“法律信仰”意味着什么
如前所述,通过历史性的分析,伯尔曼试图为20世纪的法律整体性危机提供“信仰”这一药方,但其效果究竟如何?对此可以循着他的思路来发现问题的根本。在将法律与宗教进行类比后,伯尔曼给出一个新的洞见:“只有在法律通过其仪式与传统、权威与普遍性触发并唤起他们对整个生活的意识、对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的时候,人们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1]35换言之,整体性的法的重生意味着其需要具有宗教的形式甚至实质。可以看出,伯尔曼所论及的“法律信仰”,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与“宗教信仰”相似,然而这种相似性的观念意味着什么?对此可能需要将论述稍微拉远一些。
在今天,“法”被写进了法典,“美”被用以各式各样的表演,宗教经验往往被认为是一系列的意识,人们很容易“技术性”地或“科学化”地认为自己正在经历人生的神秘,而事实上所完成的是通过技术使自己与真实相分离。在技术世界不断强化的知识获得过程中,苏格拉底式的无知与自省被探知和征服自然世界的雄心所取代,当人们觉得自身对世界的把握是不言而喻的时候,实则只是一种傲慢。伯尔曼多次批评这种傲慢,比如“从事法律的人……不关心终极目的,一味任用理智的怪物”[1]18-24。在法学领域,早期的实证主义者比如边沁,后来的现实主义者比如霍姆斯,也是这种傲慢的典型。边沁对法律的“计算”显得过于乐观,他试图通过功利的计算来得到“法律”,乃至于完成一部“完整法典”[21]304-308。与此相对,宗教本身需要完成的第一步则是人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从而超越此前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对超验的实在保持谦卑。
宗教信仰的产生,在于对自身置于超自然的在场中的感觉,亦即感觉到自身对超自然事物的依赖[22]10。神秘之物向我们呈现自身,随之附带起神秘感的涌现。无论具有何种对神秘事物的信仰,这种超自然的在场,都将呈现为某种可诉诸“神圣”来描述的事物[22]135。而“神圣”事物所引起的“赞美与敬畏”,将可能统合实际经验中无尽的多样性。事实上,这就是为何逻辑的源头不是逻辑的,规范的源头也不是理性的产物,法律的源头(有效性)本身也不是基于理性或是事实。在康德凝望沉思于“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之时,其中的体验或许也不乏某种神秘,其原因正在于,如果尝试用理性去应对自然或自由,那人们将一无所获[23]220。同样,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神秘之物自身自我显现”,这种神秘本身是“不可言说”的[24]219。这位20世纪的哲学家因此要求“要登上高处之后,把梯子丢掉”,“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会正确地看待世界”,这里的超越意味着对事实的超越[24]105。宗教信仰本身被这种神秘感所统领,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蒂里希曾经这样做出总结:“信仰不是对某种不确定事物在理论上的肯定,而是对超越日常经验事物的生存性接受。”“这种不确定事物的存在超越了任何‘存在’的事物,而且任何‘在者’都参与到它。”[25]154由此看来,有宗教信仰意味着我们对超验事物的敬畏,由此秉持某种终极性的观念。
这里马上会产生的疑问是,如果信仰的对象是神秘的,那么信仰如何存在?20世纪的思想家们通过“象征”理论来对此予以说明。象征是指某种可以将我们引向神秘之物的客体,其不同于“标志”:标志仅仅指向客体,象征则超越客体。蒂里希曾经这样做出论述:“象征式的语言可以独自表达最终事物,信仰的语言是象征式的语言。”[26]45为着友谊而在朋友之间互相馈赠的纪念品,尽管价值可能微不足道,如若遗失,可能也不会影响与朋友的关系,但作为象征,其重要性往往也是不言而喻的。象征密切关系着我们对超自然实在的经验能力,宗教本身也就是某种象征,关联到我们对超越之物的体验。
上述离题之语旨在说明,基于对个体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对神秘事物理应怀有敬畏。信仰完全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超越了理论推理与科学知识的“外向性”态度。有了这样的认识后,便可着眼于“法律信仰”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如果沿用前述关于象征与标志的区分,我们就可以追问,究竟应该把法律作为纯粹的客体还是作为象征?如若当作客体,那便是实然论题;如果是象征,那么意味着法律除了对外在行为进行规制外,还在于对某种价值性的主张和要求,这恰恰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力图展现的主旨[1]20-22。
相应地,对于法律的概念而言,伯尔曼持有这样的看法:“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在进行立法、判决、执法和立约的活生生的人,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宗教也不只是一套信条和仪式,它是对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目标表现出共同关切的活生生的人。”[1]11法律自身既然具有超越性,而我们也可以从传统中去理解这种超越。法律不是“实然”的规定,不是“客体”本身,而是具有某种终极意义的“象征”,通过这种象征的意义,客观性、正义、公正等价值才有容身之地。由此可见,伯尔曼旨在通过“法律信仰”来解决整体性危机,法律本身则作为“象征”,有信仰意味着我们把法律视为“内在的”或“自身的”规则,法律既是客观性的存在,同时又是超越性的存在。此前危机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人们“错误假定,法律是外在于人的,并非他全部存在的一部分,它与爱,与信仰和恩典无关”[1]92。换言之,有法律信仰意味着我们要向经验性的法律开放,而且需在直面自身的局限性的同时看到超越的法。
由此可见,伯尔曼以“法律信仰”来克服整体性问题,用超越来统摄法律的事实与实践,这是将规范性诉诸于信仰的方案。从中我们也需要明确,这一目标显然是不能通过“法律信任”来完成的。因为信任本身是某种经验性的而非超越的判断,信任至多解决守法问题,却与整体性问题的路径大相径庭。伯尔曼的工作实则是在追根溯源的意义上对问题进行的思考,要求从超越中看到法律的整体性。如其所言:“人类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此,他需要对超越其自身的真理的信仰,否则,社会将式微,将衰朽,将永劫不返。”[1]38这里所说的“超越”是对经验的超越,最终将指向某种永恒的力量。在多样性中迷失的我们,将可能借助这种力量获得整体。
实际上,尽管其本人未必同意,但伯尔曼的理论不完全是论证,某种程度上说倒更像是在运用某种修辞术。他以“法律信仰”致力于法律整体性的努力,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规范性的诉求,这种努力毫不犹豫地触及法律最终极也最无道理可讲的源头,而在他看来也就是回归西方法律的宗教性传统。伯尔曼在著作中这样看待规范性和整体性之间的关联:“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与原则具有普遍性。”[1]30在此,有法律信仰更意味着法律在获得某种宗教化的神圣力量之后,以整体的方式展现自身。同样,在个别实在法可能出现与整体性不兼容的时候,我们可以基于整体去对它进行否定,也就是“规则须维护法律最一般的原则”[1]75。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要从非整体的观念去理解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的观念,恐怕会出现误读。实在法和高级法的分野不适合伯尔曼论及的“法律信仰”,“整体的”才是他问题的关键。伯尔曼的进路不同于罗尔斯诉诸理性反思来把握整体性的方式,也不同于德沃金通过反思性实践去寻求整体性的方式,而是将未知和无知、个体的有限和要面对的无限以及历史和当下直接呈现出来,从而让人们获得对整体的法的虔诚。从这个角度看,伯尔曼具有强烈的存在哲学气质,他的确也数次以这样的方式阐释问题,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这句:“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情感,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1]105虽然伯尔曼对罗尔斯的论述颇有微词[1]195,但笔者并不打算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比较,而只想再一次指出:伯尔曼的确在谈“信仰”,不能用“信奉”或“信任”取代它,他用规范性的观念在看待法律,我们不能认为他还在分析逻辑的框架中。
三 “法律信仰”作为中国问题
如范文所述,国内在论及法律信仰时,确有将其中之“法律”一词作实证化理解的倾向。当法律完全被实证化之后,法律信仰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这是因为完全的实证化不能给任何超越留下空间。现阶段我们根本无法完成“法律信仰”的构建问题,没有敬畏和彻底的无神化使得信仰本身只能增加“滑稽感”和“幽默感”[2]。
国内学界对“法律信仰”这个命题的批评,似乎不约而同地集中于其本身作为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概念”这一焦点上[27]206。这固有其根据,但是漏掉了同样具有根本意味的问题:伯尔曼力图回答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伯尔曼提出的问题有意义,甚至对于我们自身的法治实践有意义,那么尽管其方案相较中国国情而言缺乏针对性,但并不意味着问题本身不值得更深层次的探究。实际上,对于我们自身法律的规范性和整体性而言,伯尔曼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尽管在他看来,整体性危机的确是西方的危机,但整体性问题与规范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难道在我们自身的法律实践事业中就没有规范性问题和整体性问题吗?只要法律或者规则存在,这个问题恐怕便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就法律及其约束力的来源这些关键的法理学问题而言,如果继续沿用强制论的观点,那么同样明确的一点就是,一种强制力的有效性在缺乏规范性证成的情况下只会是暂时或短暂的,并且强制的后果只能是反强制,由此伯尔曼才说:“法律只在受到信仰,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1]17-18如果仅仅把法律视为一系列的规则,那么同样可能的一点就是,我们迟早会迷失在无数碎片化规则的海洋中,因此伯尔曼才批评说:“法律主要不是法规或者适用这些法规于案件的法律观点的汇编,不是对如何把法规应用于案件的各种方法加以分析的博学论著和文章的汇集。这些都是专家们头脑中法律的残迹……”[1]66
毫不夸张地说,除非拒绝法理学,否则这些问题将会被一直追问和思考。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法律的规范性问题需要直面和回应法之为法的原因,规范性不仅作为法律有效性的保证,也与整体性问题的意义相关。当今学界对“法律信仰”和“法律信任”的争论,几乎都忽视了伯尔曼的问题,而将其答案与中国现实状况进行比较,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其实,“信任”或“相信”固然有其优点,但本身并不解决规范性和整体性问题,信任是一种互信机制,是“人对他人或者制度普遍存在的一种相信而敢于托付,并通过行动体现出来的具有确定性的意识活动”,而非某种“象征”式的超越[28]。由此,尽管范文在最后部分力图说服我们用“信任”替代“信仰”,但这两个命题本身是在解决不同维度的问题,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无法通过互信机制带来规范性,也无法通过信任而获得自我认同,信任也不产生超越性的“终极关怀”。伯尔曼诉诸信仰的解决方案,算是西方法学史上解决整体性危机的可能出路。如果我们抛弃其问题本身,仅就伯尔曼给出的答案予以论争,实则是一种类似于一叶障目的以偏概全。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伯尔曼提出的这个宜于深思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移植和检验其教条式的答案。伯尔曼的方案可能存在问题,但这不能算是问题的关键。
今天,重新审视法律的规范性问题至关重要。然而,当下的中国面对着更复杂的状态,试图将我们自身的规范性问题嵌套进西方理论中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与此相对,国内学界也一直在进行着探索规范性来源的尝试。比如,有学者追溯我们可能展开的规范性探讨的起点,也有学者直接将这一问题诉诸“本土资源”,还有学者要求我们“对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秩序展开思考和反思”②。在阅读伯尔曼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通过“法律信仰”来完成统合性的努力,我们自身又何尝不是在进行这样的努力?从这一点而言,伯尔曼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具有某种统一性,但我们的历史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这注定统合性的努力可能需要选择其他道路。
其实,只要我们注意到整体性危机与20世纪出现的法律的规范性问题相联系,我们就不会对伯尔曼的论题产生误解。在我们的时代,缺乏敬畏与信仰几乎意味着我们在寻求自身的意义上产生困惑,这不是西方才有的困惑,我们也面临这样的困惑。在建立规则的同时,如何注意到规则本身可能具有的超越,不在规则的世界里迷失我们自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我们在参详西方论著的同时,不能只看到论据是否契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更应该回到问题本身,这难道不正是法理学应有的态度吗?
注释:
①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私人语言不能在语言游戏中表达,排除私人语言是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本身的封闭性造成的。从哲学史来看,这一排除则继续着从“我”到“我们”的转向。从语用学的角度看,由于“使用”决定“意义”,那么就不可能私人地“使用”语言。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参见: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 tr.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9. p.61, 71, 76, 79, 91. 法律实证主义后有科尔曼所持的“包容性”实证主义理论(inclusive positivism),力图从中走出一条道路,但这条道路实则已经走到了实证主义的对立面。科尔曼的观点,见:Jules Coleman.ThePracticeofPrinci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德沃金对科尔曼的批评,见:Ronald Dworkin.JusticeinRob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9.
②起点型的研究往往将论题铺陈于“我们可能展开现代性的起点”这一问题之上,国内此方面论述颇多,从中国某种特定思潮的转变入手,探寻我们规范性可能发轫的起点。其中,汪太贤先生的著作是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参见: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苏力先生是“本土资源论”的代表,其实很多人都误以为苏力是“后现代”或者“地方性知识”论题的代表,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苏力的目标旨在“揭穿靠不住的保证,打消虚假的预期”,实际上,他认为“创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把苏力作这样的解读,显然积极得多。“对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秩序展开思考和反思”是邓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当中的话语。在多年前,许多人都评价过这本书,非常可惜的是“反思性实践”的观念依然没有深入人心,这本是20世纪之后的基本学术规范;更为可惜的是邓先生的“反思性实践”的论点当年鲜有评论。(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2006,(3).
[3]范愉.法律信仰批判[J].现代法学,2008,(1).
[4]刘小平,杨金丹.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J].法商研究,2014,(2).
[5]刘焯.“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J].法学,2006,(6).
[6]范进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J].政法论坛,2012,(2).
[7]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8]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BENTHAM J.OfLawsinGeneral[M].London: Athlone Press,1970.
[10]AUSTIN J.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1]COLEMAN J. Rules and Social Facts[J].HarvardJournalofLawandPublicPolicy,1991,14,(3):703-726.
[12]HOLMES O W. Natural Law[J].HarvardLawReview,1918,32,(1):40-44.
[13]HOLMES O W.TheCommonLaw[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4]HORWITZ M J.TheTransformationofAmericanLaw, 1870-1960——The Crisis of Legal Orthodox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5]HART H L A.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J].HarvardLawReview,1958,71(4):593-629.
[16]HART H L A.TheConceptofLaw[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4.
[17]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8]DWORKIN R.TakingRightsSeriously[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9]ENDICOTT T.VaguenessinLa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0]DWORKIN R.Law’sEmpi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1]SCHOFIELD P.UtilityandDemocracy:ThePoliticalThoughtofJeremyBentha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2]鲁道夫奥托.论神圣[M].成穷,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邵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5]蒂里希.存在的勇气[M].成穷,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6]TILLICH P.DynamicsofFaith[M].New York: Harper & Row,1957.
[27]张永和.信仰与权威:诅咒(赌咒)、发誓与法律之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8]彭泗清.关系与信任研究[M]//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